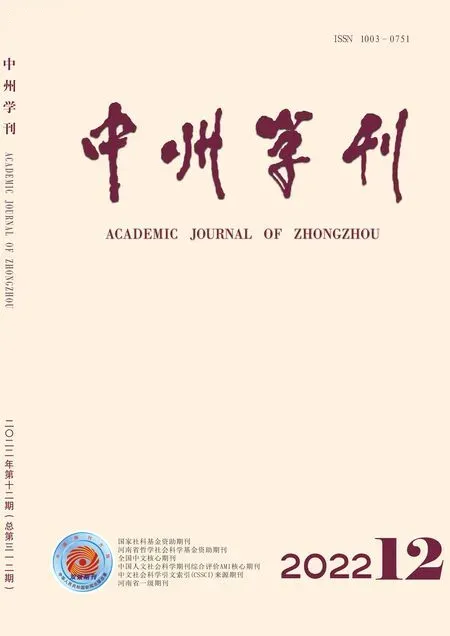機制與策略:網絡情緒動員何以發生?*
丁 漢 青
情緒動員的概念較多引自情感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提出的“情感整飭理論”。霍赫希爾德認為,情緒是形象塑造、社會交往以及達成特定目的的手段[1]。此后,與之相關的新概念大多以其為主體框架,再與具體情境相匹配。千禧年之后,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利用情緒發起社會集體行動的現象高發于網絡。人們不斷通過情緒渲染,營造聲勢,博取關注,贏得認同。“誰能在網絡上制造出情感爆點來,誰就基本掌握了某一時段的話語主導權。”[2]于是,后來的學者就將情緒動員概念與其多發地“網絡環境”緊緊地嵌套在一起,衍生出網絡情緒動員一詞。網絡情緒動員就是在網絡中利用網絡化的情緒表達方式,借助網民的同理心與正義感,達到改變事情發展進程目的的一種社會動員方式。
一、網絡情緒動員的主體
情緒動員主體指的是情緒動員的發起者。在網絡環境中,隨著話語權的下放,情緒動員主體顯示出多樣性,既包括社會地位高者,又涉及普通民眾。但并非所有主體發起的情緒動員都能獲得社會矚目,掀起輿論波瀾。從當下來看,草根中的弱者與機構媒體所發起的情緒動員更易激起共鳴,導向網絡集體行動。
弱者之所以能成為情緒動員的主體,與中華民族“扶危濟困”的道德傳統有關。弱者作為弱勢的一方,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更容易收獲大眾的同情與憐憫。同時他們身上夾帶的“創傷”與“悲痛”自帶爆點,更能戳中大眾的“情緒神經”,喚起大眾的同理心與為之鳴不平的行動動力。再加之弱者悲憤、痛苦的媒介表現對觀者形成不斷的刺激,能夠令社會不同群體在正義感的驅使下為他們發聲。因此,社會學家斯科特也將情緒動員稱之為“弱者的武器”[3]。
媒體一方面是弱者情緒動員的助推者,為弱者提供發聲渠道,通過不斷渲染弱者罹患的不幸與創傷來加深大眾對弱者的關切與憐憫;另一方面,媒體也是情緒動員的主導者,常調用情緒來凝聚人心,達成共識,促進社會團結。媒體的這種情緒動員優勢與其掌握的資源和具備的能力密不可分。首先,媒體長期踞于話語高地,因豐富的媒介資源和緊密的媒體關系網絡而更易令聲音曉喻大眾。其次,媒體具有熟稔的情感表達技巧和深厚的用戶心理洞察能力,更懂得利用大眾的“痛點”“怒點”來喚起公眾情緒,攻占用戶心智,達到“一擊即中”的情緒動員效果。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人民日報》為首的主流媒體賬號曾發起多次“為疫區加油”“共克時艱”的情緒動員,在抗擊疫情、穩定局勢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傳統媒體,社交媒體圈層化傳播的特點還賦予許多自媒體賬號以情緒動員的機會。這些自媒體同樣可以通過調動其所處的垂直領域用戶的情緒來達成行動目標。如在“鐵鏈女”事件中,以鄧飛、羅翔、胡錫進為代表的社會知名人士就多次為“鐵鏈女”發聲,通過闡述“鐵鏈女”背后的悲慘故事,促成了一場以解救“鐵鏈女”為目標的集體行動,吸引了大量網友參與,最終幫助“鐵鏈女”成功獲救。
二、情緒動員頻現于網絡的深層原因
當下,網絡情緒動員已變得愈發常見,甚至表現出無情緒則無法推動網絡動員的發展趨勢。情緒動員頻現于網絡的深層原因,一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化,二是由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所引發的消極社會心態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俠義情結。前者為外因,后者為內因,內外因碰撞促成了網絡情緒動員在現實社會環境中的發展與壯大。
(一)外因:技術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
學者趙鼎新認為社會變化是運動發生的重要因素,它使人們對事物的接受度在短時間內發生急劇變化[4]。誠如斯言,當今中國高速發展、日新月異。在眾多變化中,互聯網技術無疑是近些年影響社會運動最顯著的外在變量。互聯網技術所創就的傳播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政治格局[5]。具體體現在當下公共發言的低門檻性,有學者通俗地將之闡述為“隨便什么人對隨便什么問題都可以隨便地說些隨便的話”,公共領域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方主體、眾說紛紜的局面[6]。在社會變化帶來的新一輪話語權博弈中,情緒動員因在網絡當中的優勢成了各方斗爭中的重要工具。
而網絡情緒動員之所以能在網絡情境中被凸顯出來,主要源于其低成本、見效快。網絡作為一個開放的公共平臺,接入者可以低成本發聲,在其上發布內容,公布信息。隨著民眾話語權增多,人們對民主社會便有了更多的想象、更高的要求,表現之一就是面對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現象容忍度降低了。在對抗“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問題時,情緒動員成為人們有效的處理手段之一。理性的信息容易被淹沒在海量的內容里,而悲傷、憤怒的情緒卻具有強感染力,能快速“吸睛”,在短時間內形成強大的傳播力,達到動員者預期的轟動效果。
由此來看,網絡技術的發展激發了大眾的話語權意識,催生了社會追求民主的思潮。由于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網絡情緒動員在這場全新的話語權爭奪中被凸顯出來,成為全新的斗爭工具。
(二)內因:消極社會心態與俠義情結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雖為動員者提供了行動機會,但大眾的廣泛參與才是促使情緒動員能夠發揮社會影響的底部結構力量。而大眾之所以對情緒動員如此敏感,原因有二:一是由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所引發的消極社會心態;二是潛藏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俠義情結。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網民中占主流的“三低”(低年齡、低文化、低收入)、“三多”(在校學生多、企業人員多、無業人員多)人群,恰恰又是此社會主要矛盾所引致的負面效應的承受者,由此促生的網民不滿情緒很容易在網絡上積壓[7]。待到網絡事件被貼上對應的身份標簽(如官與民、貧與富等)時,身份認同意識會促使網民迅速站隊,共情心理誘出他們心底的消極情緒,消極情緒在相互感染中轉化為“情緒急流”,致使輿論在短時間內到達高潮。
此外,正直勇敢、鋤強扶弱、扶危濟困的俠義情結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不涉及階層間沖突的熱點事件中,網民參與動員行動更多是出于一種俠義情結。正如美國哲學家埃里克·霍弗所說:“熱烈的相信我們對別人負有義務,往往是我們遇溺的‘自我’攀往一艘流經木筏的方法,我們看似是在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實則是拯救自己。”[8]因而,每當有弱者在網絡中求助,人們會為之仗義執言。再加之網絡的匿名性對他們現實身份的保護,使他們更勇于在網絡上抒情達意,表達自己的見解,來獲得道德上的“滿足感”。
三、網絡情緒動員的一般策略
網絡情緒動員的一般策略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利用情緒引發共鳴,為情緒動員“造勢”;另一類是利用傳播手段營造別樣輿論環境,為情緒動員“供能”。情緒作為動員的基礎,能錨定大眾對事件持有的基本態度;傳播手段則可將這種情緒態度由“淺”引入“深”,轉化為民眾具體的行動力量,來達成動員的效果。
(一)通過情緒的調動引發共鳴,為動員“造勢”
在微粒化社會中,情緒成為連接個體的獨特渠道,情緒共振為人們帶來了新鮮的體驗,也成了網絡情緒動員的基礎。總的來看,網絡中的情緒動員多以悲情、懷疑、憤怒、恐懼等負面情感為主,而戲謔則以某種詼諧、自嘲等喜劇性元素為人們的情緒調動做出了貢獻。
1.悲情策略:通過情境渲染和形象塑造突出悲劇色彩
從悲劇事件的性質來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發生,即不存在人為主觀參與的事件,如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另一類是人為導致的悲劇事件,如暴力襲擊等。當悲劇事件為自然災害等自然發生的事件時,情緒的動員通常是通過對災害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等進行情境渲染,激發人們的悲情情感;而當悲劇事件是人為導致時,對事件主體悲劇身份的塑造則成為情緒動員的重點。悲情策略下的情境渲染和形象建構是一面“放大鏡”,不僅突出了事件造成的悲劇后果、事件主體面臨的悲慘境遇等,還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博取網民的關注,使其產生同情心理。而在互聯網環境中,信息的快速傳播也伴隨著情感的流動,網民的同情心理能夠超越時空限制,實現同頻共振,從而達成情緒的動員。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主體為何,當悲劇事件是人為導致時,相對弱勢的一方很容易引發大眾對相對強勢一方的譴責,并帶來網絡民粹主義的隱患。在當今的網絡場域中,悲情策略下的情緒動員并不少見,需要注意規避網絡民粹主義的潛在影響。
2.懷疑策略:思維定式引導下的群體共識
在網絡輿情中,懷疑情緒主要指網民在對待輿情事件時,通常會質疑某些特定群體的傾向。例如,在一些涉及政府官員的新聞中,網民根據自身經驗或社會認知等,常常將事件與政府不作為、官員貪污腐敗聯系起來;而面對與師生關系相關的輿情事件時,則習慣于將教師歸為錯誤的一方……懷疑情緒的產生往往并非經過有意調動,而是大眾自發形成的思維定式。近年來,官員貪污落馬的事件被頻繁報道,老師不體恤學生事件在網絡上頻頻發酵,特定群體的形象逐漸與一些負面標簽“綁定”。對特定群體的標簽化認知進一步導致了網民面對輿情事件時,習慣性地質疑特定群體。
當社會與媒介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人們負面的“固定成見”后,“遇事兒必先疑”成為公眾普遍采用的認知策略。因此,在網絡輿情事件中,通過懷疑策略進行情緒造勢,其著力點正在于引導公眾在思維定式的作用下產生相似的觀點,從而在意見一致的基礎上形成情緒共鳴。
3.憤怒策略:強調社會秩序與塑造對立形象
憤怒是人的一種基本情緒。在網絡輿情事件中,運用憤怒策略進行情緒動員通常伴隨著社會秩序的強調和對立形象的塑造,以此呼喚公民正義感的產生。強調社會秩序是指突出說明輿情事件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以及事件主體對社會法律規范、道德準則的漠視與踐踏。強調社會秩序能激起憤怒情緒的原因是,現代社會的目標是追求發展,而現代公民的行為亦被期待應符合道德與法律的雙重規范。某些損害社會利益、違背道德和法律的事件被媒體曝光后,網民會認為這些事件阻礙了自身和社會的發展,并因此產生憤怒情緒。這種憤怒情緒驅使著人們呼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并進一步形成群體共鳴,引發情緒動員。塑造對立形象則指當輿情事件存在兩方主體時,著重強調兩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并突出一方的強勢和另一方的弱勢,或突出一方的施暴者形象與另一方的受害者形象,以此來撩撥網民的神經。當前,中國社會的官民關系、警民關系、醫患關系、貧富關系、城鄉關系和勞資關系等成為最主要的矛盾關系[9]。因此,當網絡事件涉及上述這些對立群體的矛盾時,往往能夠激發人們的憤怒情緒并實現情緒動員。
4.恐懼策略:事實與想象性威脅激發恐懼情緒
恐懼情緒的動員主要依賴于“威脅—受眾—恐懼—轉發”的鏈式機制[10]。因此,作為源頭的威脅內容是否使網民產生危機感或不安全感,是利用恐懼策略實現情緒動員的關鍵。威脅內容分為兩類:一類是事實性威脅內容,即在事實上存在對人們產生威脅的可能性,如傳染疾病、自然災害;另一類是想象性威脅內容,即某些威脅可能并不存在、發生概率較低或無法對人們產生實質傷害,但人們想象威脅確實存在并產生情緒波動,甚至付諸行動的可能性。想象性威脅主要通過新聞媒體或公眾輿論等發揮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在極端恐慌的情況下,其狂熱與非理性態度也為謠言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因此,明確信源與信息的真實性,是利用恐懼情緒進行網絡情緒動員的關鍵。
5.戲謔策略:以喜劇化的表達形式實現全民狂歡
利用戲謔策略進行網絡情緒動員,關鍵在于以喜劇色彩實現全民狂歡,即通過喜劇方式作用下的“全民性”和“狂歡性”完成情緒調動。一方面,自嘲、反諷等詼諧幽默的表達是一種較淺層的敘述,能夠以“全民性”特征動員戲謔情緒。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4.4%[11]。龐大的網民規模意味著其受教育程度、知識水平等的參差不齊。因此,相較于官方話語,更加通俗易懂的喜劇化表達使得大范圍的情緒動員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喜劇化的表達形式切中了網民使用互聯網放松休閑的目的,因而其“狂歡性”也具有較強的情緒特征。伴隨著現代人生活壓力的與日俱增,互聯網成為人們在閑暇時刻放松娛樂的主要空間。戲謔的表達方式無疑具有娛樂性質,如利用貼標簽、制造表情包、網絡流行語等形式進行情緒調動,其解構了嚴肅、復雜的社會現象,以一種輕松詼諧的方式實現傳播,因而能夠迅速引起人們的討論和共鳴。總之,喜劇化的表達形式不僅提高了網民對輿情事件的參與度,而且還借助輕松和幽默的色彩舒緩了人們生活中的壓力,是利用戲謔策略進行情緒動員的關鍵。
(二)通過傳播手段的運用營造輿論環境,為情緒動員“供能”
在調動了人們情緒的基礎上,傳播手段的運用能夠為網絡事件提供輿論環境,加深人們對事件的情緒與情感,將之逐漸轉化為網絡行動力,最終實現網絡情緒動員。
1.利用多種媒介形態全面展現輿論事件,調動網民情緒
從早期人類文明誕生時的口語、文字,到近現代以來的圖像、視頻,隨著媒介形態的變遷,傳播的手段和效果也在發生著變化。放眼當下,互聯網所具有的“融媒體”甚至“全媒體”特征,能夠帶來文字、圖片、音視頻等各媒介形態的“全景式”展現,因而也成為網絡情緒動員的關鍵策略之一。
大體來看,音視頻在網絡情緒動員中的使用頻率較為廣泛。這不僅是由于其相比于文字等接受門檻更低,而且還因為其多樣化的形式和突出的風格特征能夠為網民帶來新奇的體驗。其中,短視頻的運用在網絡情緒動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短視頻是產生于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媒介新形態,具有移動、輕量、碎片等特點[12]。基于此,短視頻彌補了文字、圖片等媒介形態“在場感”不足等問題,并較好地契合了網民移動端的碎片化使用趨勢,為人們提供了“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臨場感,因而能夠較好地調動人們的情緒。除此之外,短視頻對人們視覺、聽覺等感官的直觀刺激也為情緒動員提供了條件。
圖片也是網絡情緒動員所依賴的主要媒介形態之一。以表情包為例,它再現了人的表情、動作及姿態,能夠喚起人的情緒[13]。一方面,其雖體量較小,往往僅為有限的圖像,卻蘊含著豐富或深層的含義,因而傳播效果較好,能夠引起人們的廣泛共鳴。另一方面,表情包的制作門檻較低,網民在表情包創作與傳播過程中參與度高,較易形成群體狂歡的景象。由此看來,無論是廣泛共鳴,還是群體狂歡,表情包都構成了網絡情緒動員的關鍵要素。
與音視頻和圖片相比,文字在網絡情緒動員中發揮的作用雖不甚廣,但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手段。在利用文字的情緒動員中,運用最廣泛的是網絡流行語或網絡熱詞。“內卷”“后浪”“逆行者”等網絡流行語不僅朗朗上口,還反映了某些熱門社會現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調動網民的情緒,實現情緒動員。
當然,網絡情緒動員對文字、圖片、音視頻等的運用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將上述媒介形態有機結合,進行全方位、立體化的呈現。多種媒介形態的結合豐富了網絡輿情事件的傳播內容,提高了傳播效率:在網民規模方面,其影響范圍更廣;在網民情緒體驗方面,其作用程度更深。總的來說,媒介形態的結合運用對情緒調動有著較好的效果,是一種重要的情緒動員策略。
2.通過敘事策略引發歸因效果,喚醒網民情感
歸因是源于格式塔心理學的一種認知加工過程,它不僅是人們自然的心理機制,也是一種關鍵的情感喚醒機制[14]。因此,當網民面對未知的輿論事件時,往往通過歸因機制推斷事件發生的因果關系,并進一步喚起情緒與情感。敘事策略通常指圍繞輿論事件產生的新聞報道等所采用的語法措辭、敘述方式等微觀話語結構以及敘事主體、文章主題等宏觀報道結構。新聞報道的敘事策略類似于“框架效果”,與后者相比,前者更關注新聞生產的結果,即生產出的信息本身。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均強調不同的敘事策略或框架對受眾認知差異的影響。例如,艾英戈的研究指出,新聞報道采用故事框架(episodic)容易導致受眾將問題歸因于具體的個人,采用主題框架(thematic)則導致受眾將問題歸因于國家或社會,也就是說,媒體對事件的敘述框架影響了受眾對事件責任的認知[15]。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人們為了追求判斷過程的簡單化,一般依賴更容易想到的事情來歸因,卻很少考量全部因素[16]。因此,在網絡輿論事件中,信息表述的敘事策略所引發的歸因效果,將引導公眾產生某種特定的認知傾向,而人們的認知與情緒感往往相伴而生,在此基礎上得以實現網民情緒的動員。
不同敘事策略影響下的歸因效果具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感官化敘事引導的表層歸因。感官化的敘事方式所導致的表層歸因在網絡輿情事件中有著較為普遍的體現。感官化報道指能夠較大程度地帶給人們感官刺激和情緒反應的敘述方式,包括通過感性的文字、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圖片或影像等進行渲染,采用故事化的方式突出“臨場感”“沖突感”等[17]。由于這種敘事策略聚焦于人們的感官,對輿論事件進行淺層、片面的呈現,因此易導致網民產生表層歸因傾向。表層歸因是一種對事件的簡單化推斷,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網民之間的意見分歧,形成態度的統一,而態度的統一則為網民的情緒動員奠定了基礎。
另一類是符號化敘事引導的外向型宏觀歸因。符號化敘事也是一種常見的敘事策略,指的是對具體事件進行符號化和抽象化表述。在涉及輿情事件的新聞報道中,符號化敘事通常表現為弱化個體因素和放大社會因素,并將偶然事實抽象化為必然性社會事實。舉例來說,隨著近年來民告官事件的頻發,媒體對民眾和官員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符號化的特征。在新聞報道中,民眾被抽象化為“弱勢群體”中的一員,而官員則成為“強勢群體”“權力”的代言人,即個體和具體因素被抽離,宏觀、抽象的因素則被強調。因此,在符號化的敘事下,民與官的對立就不僅僅是個體之間的對立,而上升至群體之間的對立。
3.利用群體認同凝聚共識,促進情緒動員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會自動地將人進行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并明確自己所屬的群體,以所屬群體身份定義自我[18]。在互聯網中,這種認同不僅同樣存在,而且更容易實現。群體認同的形成給網絡情緒動員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相關研究指出,群體認同對群體情緒有著重要的影響[19]。而群體認同之所以能夠強化群體情緒,是因為它提供了針對某一事件而產生的群體分享基礎,從而提高群體成員情緒體驗的趨同性[20]。此外,群際情緒理論指出,當社會分類與群體認同出現時,將產生指向內群體和外群體的群體情緒。也就是說,群體成員通過對內群體和外群體的感知,將對內群體產生更多的積極情緒,而對外群體產生群際敵對、群際厭惡等消極情緒[21]。由此可見,在群體認同的基礎上,人們不僅容易根據自身的群體成員身份產生特定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反應還能夠通過群體內的趨同性達成同頻共振,強化集體團結,促進情緒動員。
那么,基于互聯網的群體認同如何得以實現?群體認同依賴于群體的產生,故網絡群體認同得以實現的第一步是網絡群體的形成。在互聯網上,人們基于相同或相近的關注焦點以及對局外人的排斥,劃定群體內部成員與群體外成員間明確的身份邊界,形成“想象的共同體”——網絡群體。接下來,在網絡群體產生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群體規范和群體壓力為群體認同提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群體規范和群體壓力可以有很多表現形式,但其最終的作用方式則更多地表現在意見層面,即群體內部的意見環境影響了人們的態度和觀點,從而進一步形成群體共識。最終,儀式性活動不斷增強群體的凝聚力。在網絡空間中,儀式性活動包括網絡投票、彈幕刷屏等,通過儀式性活動,群體成員之間形成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建立起穩定的群體認同。總之,在網絡情緒動員中,利用身份邊界形成“想象的共同體”,并在群體認同的基礎上凝聚共識,也是較為常見的情緒動員策略之一。
四、結論與討論
在“情緒動員”概念被確立之前,人們就已經注意到情緒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不過,有的研究者認為,社會運動中的個體由情緒支配,是非理性的;而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社會運動中的個體是清醒理智的,其行動不受或很少受情緒的支配。客觀地講,人始終是理性與非理性、理智與情感的統一體,特定時代框架下的社會運動則會側重于顯影人理性或非理性、理智與情感中的一面。與此相應,圍繞情緒在社會動員中作用的爭論經歷了“突顯情緒”(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50年代)—“否定情緒”(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重拾情緒”(20世紀90年代至今)三個階段,情緒動員這一概念也在跌宕起伏中由社會動員的邊緣逐漸走向中心位置。“突顯情緒”階段的代表人物為法國思想家勒龐。勒龐生活在法國的動蕩年代,目睹了法國大革命后的暴動與騷亂,見證了一般民眾是如何在聚眾中失去理智的。這些所見所聞促使他產生非理性群體易受情緒驅使的認知。此外,布魯默、特勒、斯梅爾塞等亦傾向于強調情緒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在“否定情緒”階段,勒龐等學者有關個體為易受情緒驅使的非理性主體的假定并未得到在“理性至上”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后繼研究學者們的認同。這些后繼研究者們認為,前人的非理性觀點帶有對當時社會運動的道德審視,不具有客觀性,并提出資源動員與政治過程兩大經典理論。在“重拾情緒”階段,受文化分析和情感社會學的影響,賈斯珀、古德溫、馬庫斯、卡斯特爾等人重新認識到情緒在社會抗爭中的作用,主張情緒即使面對最理性的決策也很有力量。研究者們對社會運動中情緒作用的認知變化顯示,社會運動中始終交織著理性與情緒的力量,不存在單邊主導。討論社會運動究竟是由理性或情緒主導并無太大意義,更有價值的研究關注點是發現社會運動在何種情境下易受理性支配,又在何種情境下會被情緒調動。情緒動員作為情緒主導情境下的社會動員形式也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青睞。
當今社會,互聯網已經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查看消息、點贊、評論、轉發已是人們常見的生活方式。在技術賦能下,網絡集體行動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全新力量。而情緒動員作為網絡集體行動的“推手”,其重要性也日漸凸顯。從主體來看,網絡情緒動員的兩大主力分別為弱者與媒體。弱者悲慘的經歷、痛苦的媒介表現更容易引發大眾同情與憐憫,獲得大眾的支持。而媒體則因其所占據的“話語高地”、龐大的關系網絡、熟練的話語技巧和深厚的受眾心理洞察等,亦更容易在網絡上收到“一呼百應”的效果。
情緒動員頻現于網絡的外因在于網絡技術的可見性與匿名性為民眾宣泄情緒、表達觀點及尋求認同提供了便利。情緒動員因其低成本、高效價的優勢而演化為權力博弈的重要工具。內因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所引發的消極社會心態在以“三低”“三多”人群為主的網絡空間中尤顯突出,致使被貼上敏感標簽的網絡事件很容易成為網民宣泄消極情緒的“出口”;另一方面則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扶危濟困的俠義情結促使網民愿意以低成本在網絡上扶危濟困,尋求道德的“滿足感”。
情緒動員的策略主要包含兩類:一類是調動情緒,為情緒動員“造勢”,常用的情緒調動策略包括悲情、懷疑、憤怒、恐懼、戲謔等。另一類是通過傳播手段的運用營造輿論環境,為情緒動員“供能”。傳播手段策略則包含利用多種媒介形態全面展現輿論事件,調動網民情緒;通過敘事策略引發歸因效果,喚醒網民情感;利用群體認同凝聚共識,促進情緒動員等。第一類情緒動員策略側重于奠定情緒基調,第二類情緒動員策略則側重于強化情緒內核,使人們能夠一步步地在情緒的調動下逐步走向集體行動,達到情緒動員的目的。
與網絡事件相伴隨的情緒動員無疑對社會及社會運動有著積極的影響。例如,一些涉及社會弱勢群體或社會不公事件中的情緒動員,能夠激發人們的同情、關愛等情緒,體現出公眾對公平、正義等進步價值觀念的追求,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社會安全閥”的作用。不過,網絡情緒動員過程有時會伴生謠言傳播、輿論審判等“次生災害”,不僅不利于網絡空間的良性發展,而且還可能導致消極的社會抗爭事件,破壞現實空間的規則和秩序。因此,在網絡事件的傳播過程中,需要把握好情緒動員的程度和邊界,以情緒共鳴疏通社會矛盾,為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與和諧的社會環境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