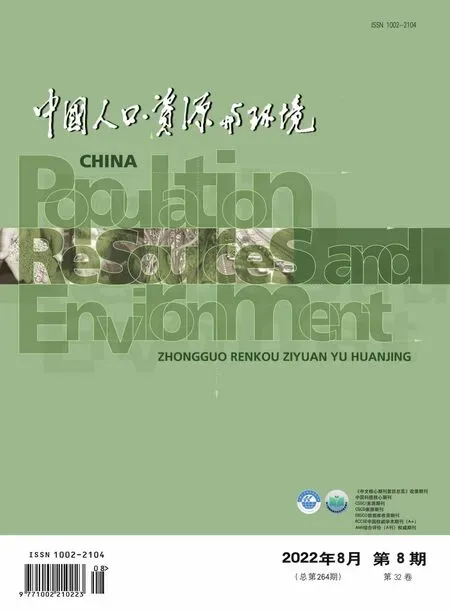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百年黃河流域保護和發展的歷程、經驗與啟示
黃承梁,馬軍遠,魏 東,張連輝,張彥麗,杜焱強
(1.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732;2.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3;3. 濟南社會科學院,山東 濟南 250099;4.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5.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和永續存在的偉大搖籃。千百年來,黃河既以其奔騰向前、百折不撓的千古不廢之氣勢孕育了華夏文明,又以其善淤、善決、善徙的特性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憂患之河”。從古老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鯀禹治水)開始,中國人民以自強不息、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始終同黃河母親河同呼吸、齊命運、共患難,始終同黃河水患進行幾千年不屈不撓的斗爭。在長達3 000 多年的時間里,黃河流域始終是中華民族大一統歷史進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心地帶。“奔騰不息的黃河同長江一起,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1]4。”黃河,凝聚和賦予了中國人民太多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情感與智慧;治理黃河,也歷來是中華民族安民興邦的大事。
中華民族進入20 世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黃河的治理也由此進入了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黨和國家始終將治理黃河、推動黃河流域發展作為歷史性、戰略性任務持續推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始終對黃河懷有深厚的情懷,始終高度重視黃河的治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們,將黃河作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源泉,制定并實施治黃方略,為治黃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持續實施治黃方略,開辟了黃河治理的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生態文明建設在“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性、基礎性地位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重要內容的戰略認知,立足新發展新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掀開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宏大的歷史篇章。特別是2019 年9 月18日、2021年10月22日,習近平先后在河南鄭州、山東濟南主持(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可以說,在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歷史性的時空跨越,是中華民族在千百年愛黃、治黃關系史上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共產黨100年來關于黃河情懷、黃河保護、黃河治理、黃河高質量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生動的人與自然關系史,是一部生動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奮斗史、復興史,是一部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史。
站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治理黃河的百年歷程、借鑒其中的寶貴經驗,對于開創治黃事業新局面,加快構筑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推進共同富裕,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1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們的黃河情懷和黃河治理
1.1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保障革命”為主要目標的黃河精神的彰顯與區域性治黃初探
黃河不僅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苦難記憶,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歷程的苦難輝煌。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不屈不撓、生生不息的“黃河精神”,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成功實現從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的戰略大轉移,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和總后方,成為中國的革命圣地。對黃河的感恩和敬畏之情,及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也由此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黃河的豐富情感中最為深沉而濃重的情懷。
在抗日戰爭時期,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毛澤東聽后給予了“百聽不厭”的高度評價[2]。該曲“表達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共御外侮的英雄氣概,體現了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蓬勃向上的偉大精神”[3]。解放戰爭時期,黃河見證了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的歷史性轉折。如威震華夏的劉鄧大軍就是在黃河流域發展、壯大起來的。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從山東東阿至山東東明150 km 的黃河沿線上,擊潰國民黨軍隊的黃河防線,強渡黃河,揭開了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是年9 月,毛澤東在陜北神泉堡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和重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期間,曾指出:“沒有黃河,就沒有我們這個民族啊!”[4]621948 年3 月,在陜北吳堡縣川口渡過黃河奔赴西柏坡時,毛澤東又說:“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4]66。因此,在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的締造者們那里,黃河就是令人敬畏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我們民族的驕傲”[5],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源泉。
這一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深刻認識到黃河的重要性,但對黃河本體的把握、系統化保護的探索、流域環境與發展的認知相對較少,黨領導的治黃事業具有鮮明的“保障革命”特征。該時期的治黃事業中,黨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廣泛發動群眾,堅持“人民治黃”,集中于黃泛區救助,依靠人民力量推動革命順利向前。如1938 年的花園口決堤事件使得農業減產,外部糧食輸入受阻,河南黃泛區出現饑荒危機。危急關頭,在黃泛區的中共水東獨立團“以通許-杞縣-太康三縣交界地帶的黃河東北岸為根據地”[6],積極領導群眾調整生產策略,對環境進行改造和利用,開展護糧行動,保障群眾生活生產和革命建設活動。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黨領導人民積極開展水利建設和農田灌溉運動,當地群眾“積極響應‘自己動手,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的號召,成立水利合作社”[7]。又如上文所述,1947 年6 月,劉鄧大軍渡過黃河后,鄧小平立即接見了冀魯豫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要求動員武裝力量保衛黃河,部署開展治黃工作。冀魯豫黃河水利委員會及所屬南岸修防處段隨即動員10萬民工迅速開展復堤整險工作,并于7 月23 日提前完成西起長垣大車集、東至齊禹縣水牛趙莊300余公里的復堤工程[8]。這也就是說,強渡黃河是為了人民解放,修護黃河是為了護佑人民。
1.2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改造自然”為鮮明特征的治黃探索
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共產黨全面探索治理黃河提供了重要客觀前提。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了以“改造自然”為特征的大量實踐。隨著經驗的不斷總結、科學技術的進步、對黃河客觀規律認識的深入,黃河治理問題開始由表及里、由區域擴展到整體,治黃事業取得重大進展,黃河流域治理開發進入“全面治理,綜合開發”的新階段。
將黃河由“害河”變為“益河”,一直是毛澤東的心愿。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說:“自古道,黃河百害而無一利。這種說法是因為不能站在高處看黃河。站低了,便只看見洪水,不見河流!”“將來全國解放了,我們還要利用黃河水澆地、發電,為人民造福!那時,對黃河的評價更要改變了!”[4]63新中國成立后,從1952 年到1955 年,毛澤東先后四次考察黃河,多次聽取相關匯報和召開治黃會議。也正是在此期間,毛澤東發出了廣為流傳、動員和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治理黃河的偉大號召:“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9]。”在1952 年10 月底第一次考察黃河時,毛澤東就提出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強調“一定要治服它,決不能再讓它出亂子”[10]622;還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10]621。在這里,所謂“借一點來”,有兩個重要內涵。一是毛澤東認為黃河“是一條天生的引水渠[11],”是開發北方和西部的重要戰略支點。二是這“借一點來”,是南水北調戰略構想的雛形。1953 年2 月,毛澤東在“長江”號上向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詳細詢問南水北調事宜時說:“三峽問題暫時還不考慮開工,我只是先摸個底。但南水北調工作要抓緊[12]。”1958 年3 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描述了利用黃河進行南水北調的宏偉景象:“打開通天河、白龍江,借長江水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連起來了[13]。”可見,在這幅藍圖中,黃河自身的治理利用與南水北調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成都會議正式通過的《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決定興建丹江口工程。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于1958 年9 月正式開工興建,1974 年全部完成初期工程,為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打下了堅實基礎。
開展水土保持與修建水庫,是治理與利用黃河的兩大基本途徑,一直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后,在考察黃河或聽取治黃工作匯報時,毛澤東多次強調要重視黃河流域尤其是黃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1953 年2 月,毛澤東南下考察途徑鄭州時,向王化云了解三門峽水庫建成后的使用年限等問題,強調修水庫的同時應注意黃河流域水土保持的問題,“要修水庫,不要修泥庫”,展現出非凡的遠見卓識[14]。在毛澤東的重視與推動下,1955 年7 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正式啟動全面治理黃河的工作。此規劃中的一些治黃原則和措施方案,對治黃工作起到了長期指導作用[15]。1964 年12 月,周恩來在國務院治理黃河會議上指出:“舊中國不能治理好黃河,我們總要逐步摸索規律,認識規律,掌握規律,不斷地解決矛盾,總有一天可以把黃河治理好。”“總的戰略是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于生產的河[16]。”
總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們,為新中國治黃事業與南水北調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礎,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特別是毛澤東對黃河深摯而豐富的情感,彰顯了一代偉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值得后人繼承和發揚的寶貴精神遺產。
2 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黃河情懷和黃河治理
2.1 黃河治理開發實事求是,奠定中國黃河治理開發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始終以務實的精神關心著黃河治理與開發。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推動法治化建設和組織機構建設相結合,將大江大河等環境保護上升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從而奠定了中國黃河治理開發的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基礎。
“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構筑黃河岸邊“綠色城墻”[17]。1978 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在西北、華北、東北地區建設三北防護林體系的重大戰略決策。后來,鄧小平親筆為工程題詞——“綠色長城”。該綠色長城利于降低黃河岸邊的風沙危害和控制水土流失,實踐也證明,“治水之本在于治山,治山之要在于興林”是符合客觀規律的。
黃河治理開發的法治化建設取得重大進步,環境保護首次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79 年9 月《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1983 年正式把環境保護確定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8],1987 年發布中國首個五年環境規劃——《“七五”時期國家環境保護計劃》,其中提出“要努力控制長江、黃河、珠江等七大江河的水質污染”。
重視機構建設,推動大江大河等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化。1978年,中國建立“黃河水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黃河水質監測中心站”;1982 年,中國組建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內設環境保護局;1988 年,國務院獨立設置國家環境保護局。這些機構的建立與完善,有利于黃河流域治理開發的深化發展。
2.2 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規模治理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堅持興利除害和確保黃河安瀾
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度關切黃河治理開發這一重大問題,深切地意識到治理黃河歷來是安民興邦的大事,必須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江澤民反復強調:“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定要研究開發黃河,興利除害,把黃河治理好”[20]。
“為人民治黃事業樹起了一座新的歷史豐碑”的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是我國水電生產力的歷史飛躍[21]。1991 年2 月,江澤民對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壩址以及黃河大堤險段等進行了全面視察,對于小浪底工程這一“造福人民的好事”寄予厚望。1997 年10 月,黃河小浪底工程截流成功,對黃河調水調沙、黃河下游防洪防凌、水資源優化配置與調度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讓黃河變害為利,為中華民族造福[20]。”江澤民指出,黃河流域對實現中國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具有戰略意義。1999 年6 月,江澤民從黃河中游的壺口開始,經過三門峽、洛陽、鄭州、開封、濟南,最后抵達東營黃河入海口。在鄭州,江澤民主持召開黃河治理開發工作座談會指出:“21 世紀即將到來,我們必須從戰略的高度著眼,繼續艱苦奮斗,不懈努力,進一步把黃河的事情辦好[22]。”要求黃河的治理開發要堅持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兼顧防洪、水資源合理利用和生態環境建設諸方面,把實現好資源持續利用與環境保護、治理開發相結合。
大規模治理黃土高原水土流失,退耕還林,再造秀美山川。黨中央著眼加強生態建設、維護生態安全,提出“退耕還林、封山綠化”戰略,江澤民向全黨全國發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號召[23]。江澤民指出:“通過植樹造林解決兩大心腹之患。一是解決長江、黃河上游植被稀少、泥沙俱下給我們國家帶來的巨大水患。二是加大沙漠化的治理力度,實現人進沙退而不是沙進人退[24]。”在已有的三北防護林工程的基礎上,中國進而開展了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長江中下游地區等重點防護林建設工程。其工程范圍之廣、規模之大,堪稱世界生態工程建設之最[25]。
2.3 探索水利建設之路:黃河治理開發的智慧延續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黃河的治理要更加尊重自然,更加側重人水依存,更加注重保護,其理念轉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黃河流域的小浪底、萬家寨、龍羊峽等水利樞紐工程也于這一時期建成。
要進一步把黃河的事情辦好,讓黃河更好地造福中華民族。2006年,胡錦濤指出,黃河治理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依托;同年,溫家寶也指出,要遵循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以水資源可持續利用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6]。2009 年10 月,胡錦濤先后在濟南、濱州、淄博、東營等地考察,十分關注黃河工作,在視察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時,要求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明顯改善黃河入海口的生態環境。
通過工程措施和科學調度,黃河作為“國之大者”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2009年初,黃河流域包括甘肅、陜西、山西、河南、山東等多個省份同時遭遇特大干旱,多省人畜飲水困難,特別是作為國家糧食主產區的豫魯兩省旱情尤為嚴重。在此背景下,國家共調度黃河干流23.8億m3水量,注入五省旱區,實現灌溉面積247.2 萬hm2。正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盡管局部旱情百年一遇,但河南、山東兩省在大旱之年的夏糧產量增產豐收,實現歷史新高,山東刷新了2000 年以來夏糧產量的紀錄。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一系列涉黃治黃水利工程的實施和科學合理的調度,使黃河水成為造福水,澤被四方;水電資源也得到有序開發,水電裝機從300 多千瓦增長到2 000多萬千瓦[27]。
加強頂層設計,持續深化黃河治理體制機制建設。2006年,國家層面第一次為黃河專門制定的行政法規——《黃河水量調度條例》頒布實施。2011 年7 月,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央水利工作會議,再次提出要把水利作為國家基建優先領域,明確了水利改革發展的若干重點任務,其中著重提出“在繼續加強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的同時,加快推進防洪重點薄弱環節建設”,爭取通過五到十年的努力,扭轉中國水利建設明顯滯后的局面。目標是促進水利可持續發展,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水利現代化道路。雖然該會議未直接提及黃河,但卻對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和防洪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水利體制機制,著力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加快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制度,把節約用水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活生產全過程[28]。
總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和引領下,黨和國家的治黃思路更加貼合自然規律與經濟社會發展特征,治黃的科學化和系統化水平明顯提升。治黃理念開始關注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黃河流域治理與保護的普遍價值追求。
3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3.1 習近平高度重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刻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黃河流域突出問題的基礎上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習近平心系黃河,非常關心黃河的保護和治理,牽掛著黃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十余次奔赴沿黃九省區考察調研[29]。2014年3月,習近平到河南蘭考了解黃河防汛和灘區群眾生產生活情況;2019 年7 月,習近平在內蒙古鼓勵當地干部群眾保護好生態環境,筑牢中國北方重要生態安全屏障;同年8 月,習近平在甘肅調研時發出了“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偉大號召[30];2020 年5 月,習近平在山西考察時指出:“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推進能源革命、推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增強太原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1];正如前文所述,2019 年9 月18 日和2021年10 月22 日,習近平先后兩次專門就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主持座談會。習近平從宏大的歷史視角和戰略高度提出“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強調保護黃河的根本宗旨是“讓黃河造福人民”,指出了黃河流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地位和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河治理的巨大成就,分析了“表象在黃河、根子在流域”的重大問題,明確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目標任務以及加強領導的措施,科學完整擘畫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藍圖,掀開了黃河治理、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篇章,奏響了新時代的黃河大合唱。
3.2 保護黃河是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戰略考量和出發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2019 年沿黃九省區地區生產總值、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2012 年增長了50%和54%。2015 年打響脫貧攻堅戰以來,沿黃地區貧困人口如期實現脫貧。2017 年以來,中央財政投入專項資金支持河南、山東兩省實施黃河灘區居民遷建工程。到2019 年年底,河南灘區地勢低洼、險情突出的30萬人的安置區建設任務基本完成、復墾土地253.33 hm2;山東省60.6 萬灘區居民的防洪安全和安居樂業問題基本解決。沿黃地區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顯著提升[32]。在增進民生福祉這一宗旨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根本立場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其核心就是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福祉。讓高質量發展回歸到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期待的初心上,尤其是滿足人民對清新空氣、清潔水源、舒適環境、宜人氣候等生態產品的需求,是新發展階段下讓黃河成為“幸福河”的具體內容。從以消除水患為主要目標的黃河治理到以造福人民為宗旨的高質量發展,立足新發展階段,實施黃河國家戰略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具有全新的歷史使命和重大意義。
3.3 新時代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重點和基本遵循
一是必須統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生活著4.2 億的人口,不發展就不能提高沿黃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分布眾多的能源、尤其是煤炭資源,為全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黃河流域是重要的糧食產區,是國家糧食安全的保證。同時,黃河流域是中國生態脆弱區面積最大、類型最多、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水資源嚴重短缺、生態質量惡化等因素制約。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是解決水資源供需矛盾、保障黃河安瀾的迫切需要,是防范生態安全風險、筑牢北方地區生態屏障的現實需要,是促進全流域戰略協作、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需要,是彰顯中華文明、凸顯文化自信的時代需要。
二是必須以系統工程思路推動黃河流域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黃河流經九個省區,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系統工程,不僅涉及水沙關系、水資源保護利用、生態保護,還涉及產業協作、文化傳承等多個領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各省區利益訴求不完全一致,單純靠省區層面協調解決跨區域重大問題,難度很大。目前除流域水資源保護和利用開發外,其他方面還存在九龍治水,分頭管理等問題,亟待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管理,打破“一畝三分地”“各掃門前雪”的思維定式,加強省區間協調配合,跳出一省一域看黃河,站位全國大局謀發展。堅持系統觀念、進行協同治理,堅持生態優先、推動綠色發展,堅持底線思維、高效利用水資源,是新時代實施黃河國家戰略的思想指引、行動指南和實踐路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謀劃協同治理。加強黃河流域各省區和政府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從解決九龍治水、分頭管理等問題入手,統籌推進各項工作,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
三是必須堅持底線思維,把水資源作為剛性約束,全面推動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習近平多次強調指出,要堅持“有多少湯泡多少饃”,牢牢把握“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的原則要求。依水而定,就是要把節約和保護水資源放在優先位置,作為衡量戰略實施成效的重要標尺。量水而行,就是要把維護河流健康、改善水生態環境、平衡水沙關系等作為重中之重。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牢牢把握水資源先導性、控制性和約束性的作用,統籌全流域生產、生活、生態用水,推進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實行全民節水行動,抑制不合理的用水需求,促進人口經濟與水資源承載力相協調。“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問題,歸根結底在于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自覺走出生態優先新路子。當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對新形勢,黃河流域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堅持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以嚴格的生態保護倒逼高質量發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生態保護。通過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相結合,形成相得益彰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激發沿黃地區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
總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視為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進一步闡明了保護黃河對中華文明的歷史意義;將生態優先、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作為治理黃河的基本原則,推動治黃理念實現歷史性升華;將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和魂,進一步明確了保護黃河的精神內涵與時代價值。習近平關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作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流域治理、綜合治理、協同治理方面實現了重大創新和突破。以重要國家戰略全面部署、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黃河的系統認知與高度重視,把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的黃河治理歷程推進到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度。
4 中國共產黨百年治理黃河歷程的基本經驗和主要啟示
4.1 中國共產黨是百年治理黃河歷程的核心領導力量
黃河的治理、開發和保護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從毛澤東“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到習近平“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心系黃河治理,為黃河治理傾注畢生心血。在百年治黃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發生著深刻變化。由區域性表象治理到全面系統的“治本”,由試圖征服自然到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由局部治理到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綜合治理,由單一行政管理到行政、市場和法治多手段并用的過程,最終改寫了治黃歷史,創造了黃河“歲歲安瀾”的歷史奇跡,可謂艱難曲折,卻又波瀾壯闊。黨關于黃河流域治理、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歷程說明,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黃河事業才能不斷繼承和向前推進。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總能夠基于生態現狀、發展階段、歷史條件和核心目標,不斷完善治理黃河理論主張,推進流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保障和全面引領,才能推動治黃事業不斷取得新進展與新突破。
特別需要指出,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人民觀,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走群眾路線。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血脈相連,黨的主張得到人民群眾普遍擁護,黨的治黃方略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的花園口決堤事件引發的饑荒危機的解決、解放戰爭中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新時代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無一不是在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下順利向前推進的。這種人民立場、人民本位、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立場和百年不懈奮斗的根本價值遵循。
4.2 黃河流域發展和保護事關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
黃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升華,是中華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的重要承載區,是凝聚中華民族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石。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回望百年治黃歷程,中國共產黨人對黃河傾注了深厚的情感,從“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9]到“要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1]11,將治理黃河和文明建構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基于此,必須守護好中華文明的根和魂。習近平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33]。”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哺育了中華民族,開啟了中華文明,見證了中華崛起,鑄就了中華精神,是中華文明的深邃象征和永恒圖騰[34]。完成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黃河及凝聚其中的民族情結、黃河文化、黃河文明,是中華民族凝聚民族共識、強化國家認同的重要根基。
從生態文化的角度看,黃河文化也承載著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生態智慧、融合現代文明成果與時代精神、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使命與重任。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 000 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35]。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取向廣泛見于中國古代典籍,《黃帝內經》“善言天者,必應與人……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人合一”、《管子》四篇的“圣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等都是生動體現。因此,黃河治理問題在更深層意義上關乎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發展的文明形態。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一方面繼承傳統文化優秀生態智慧,發揚時代精神,改造和提升傳統文化,使傳統生態文化符合時代價值;另一方面把培育生態文化作為重要支撐,通過發揮生態文化的價值引領作用,使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入人心,從而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轉化為全體中國人民的自覺行動。
4.3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系統性、歷史性、長期性國家戰略工程
第一,從系統思維和辯證思維看。治理黃河,表象在黃河,根子在流域。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并非一地一段的事情,而是一項全流域治理工程。一是要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和大局觀。“黃河沿岸的發展一定要有大局意識,站在國家的、全局的角度考慮,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36],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關系,增強“一盤棋”意識,在重大問題上以全局利益為重。二是提高系統思維能力,堅持整體論。要立足于全流域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把黃河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謀劃,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三是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強調“兩點論”。要把握好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既放眼長遠,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干在當下;要堅持正確政績觀,準確把握保護和發展關系,既要把大保護作為關鍵任務,打好環境問題整治、深度節水控水、生態保護修復攻堅戰,又要加強頂層設計,以完善的制度和體制機制為根本上實現綠色發展、構建現代化的生態經濟體系奠定體制機制保障。
第二,從統籌發展和保護、協同推進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看。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于干旱半干旱、半濕潤地區,生態系統原本脆弱,長期的人類活動對生態造成了巨大壓力。當前,經濟社會已嚴重超出生態系統承載力。因此,黃河流域治理首先應在“生態優先”理念的引領下既加強生態環境治理,又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是要明確治理的重點,即著眼構建國家“兩屏三帶”生態安全戰略格局,從黃河流域當前的突出環境問題入手,以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等重要生態功能區為抓手,全面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水沙關系調節、水資源利用與管理、防洪防汛等治理重點,改變流域生態環境脆弱現狀。二是要統籌治理,即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在突出區域差異性的基礎上實行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統籌謀劃,形成系統性的流域治理格局,以夯實生態建設根基,拓展生態環境承載力空間,推動人與自然更加和諧。三是要加強生態保護源頭管控,嚴格落實主體功能區規劃,嚴守生態保護、永久基本農田和城鎮開發邊界“三條紅線”,優化流域生產、生活、生態“三生空間”,加強產業準負面清單約束,著力發展循環經濟,培育綠色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持續優化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格局。
第三,從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看。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發揮中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是走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協同的綠色發展之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綠色生態產業培育,將循環經濟體系與綠色發展模式融入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進程之中;將生態資源與產業融合發展,推動生態產品價值提升和生態產品市場化,提升生態產品經濟價值,使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相得益彰。二是推動流域生態城市群建設。依托流域中蘭州-西寧城市群、寧夏沿黃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晉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等多個國家級城市群,探索以生態、低碳和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為目標核心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深度融入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加強流域城市群協調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廊道。三是加強流域省區一體化發展,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開發。構建跨省區溝通協調長效機制,最大可能消除地方保護,將行政區資源、區位特點等的差異性和流域協調發展相結合,形成互利共贏的格局。特別是以“一帶一路”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為紐帶,暢通陸海雙向開放大通道,構建“一帶一路”與黃河流域的“雙循環”發展格局[37]。
第四,從組織制度和體制機制保障看。一是機構支撐。從中國共產黨在1946年就有冀魯豫解放區治河委員會始,黨不斷完善黃河治理與保護機構,相繼成立了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上游水資源保護局等多層次流域治理機構,它們在安瀾黃河建設、提高流域治理能力、推動流域治理體系現代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體制機制和政策支撐。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構建了一系列系統化的生態保護制度和高效運行機制,如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河湖長”制等,為流域治理開發提供了重要體制機制保障;建立健全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治理相關政策體系,如“退耕還林”、取水許可、產業發展負面清單等,通過精準施策提高流域治理能力。三是法治支撐。新中國成立后,黨始終堅持依法治國,將中國國情和發展現實相結合,加快生態環境領域立法,大力推動法治社會建設,先后探索建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體系,使得黃河治理實踐活動“有法可依”。現在,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印發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綱領、發展路徑、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全國人大正在為保護黃河、促進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制定法律。四是科技支撐。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注重發揮科技創新的帶動引領作用。通過黃河水情的研究、水利工程的優化、環保技術的進步、生態保護理念的更新等,黃河治理最終由局部治理轉入全面治理、由“治標”轉向“治本”。
4.4 新時代黃河國家戰略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既事關中國東西部區域、南北區域的協調發展,也事關整體促進共同富裕,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內在要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復興。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黃河流域治理保護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提升。但受歷史現狀、黃河流域治理的復雜性等因素影響,當前流域治理仍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一是水安全問題。習近平指出,水安全是黃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目前,黃河仍然是世界范圍內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難度最大、水害嚴重的河流之一。特別是近年受全球氣候變化的復雜深刻影響,極端天氣頻發,防大汛、抗大災,加快構建抵御自然災害防線的任務還十分繁重。二是流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突出。黃河流域是中國名副其實的“能源流域”,過去的粗放發展導致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嚴重,自然生態承載力接近極限。由工業污染蔓延的農業面源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形勢仍然嚴峻,流域治理面臨著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雙重考驗。三是流域內存在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平衡、違規取水和粗放用水現象突出、經濟用水擠占生態用水、沙塵災害預期增加、土地沙化現象嚴重、部分地區面臨二次沙化威脅等問題。
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系統解決黃河流域治理面臨的難題,開創治黃事業新局面,真正做到“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真正實現“黃河寧,天下平”的美好愿望,就要堅持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推動黃河母親河永續發展的先鋒隊、中流砥柱和核心領導力量,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根本遵循。特別是著眼中國2030 年、2060年碳達峰碳中和“雙碳”目標的實現,充分發揮黃河流域上、中游地區風、光資源優勢,結合上游水電資源和中游地區煤炭、天然氣的雄厚基礎,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及相關上下游產業,將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與此同時,著力發展其他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區域發展,多措并舉推動黃河流域產業高質量發展,著力提升黃河流域對外開放水平。只有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新發展理念,解決黃河流域發展活力不強、高質量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才能更好地保護和治理黃河,建設人水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