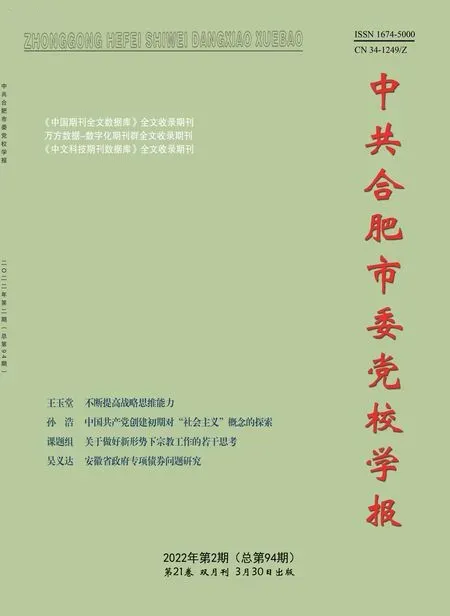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對“社會主義”概念的探索
孫浩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社會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近代中國吸引了諸多愛國志士的關注與討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孕育著中國革命方向的論爭也就此展開,“社會主義”概念之辯開始流轉于各個派別。中國共產黨創建后,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共黨員給予“社會主義”概念以新的意義與詮釋,在同其他主義的論爭中塑造了“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形象。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概念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概念的研判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鑒與指導,也為“工農武裝割據”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要明晰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對“社會主義”概念的認知理路,就必須從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即緣何選擇社會主義、選擇何種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何以實現三個維度進行分析。
一、緣何選擇社會主義:人類社會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
對“社會主義”概念進行考察,就必須厘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中國共產黨在闡述“社會主義”概念時,以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視角,對資本主義發展特征與趨勢進行了初步梳理與解讀,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昭示社會主義的科學性。
(一)弊端與困境:資本主義孕育了自我崩潰之因素
“不懂得資本主義,就不會懂得社會主義。”[1]404欲揭示社會主義的優勢,就必然要對資本主義的本質進行分析與研判。雖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特征與中國國情認知不夠全面、深刻,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態勢尚未系統掌握,但仍對資本主義本質進行了初步的解讀,指明了資本主義自我崩潰的根本原因。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上,中國共產黨人首先認可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步性,指出,“資本制度能把全社會分散的資本集中起來,使家庭的農業手工業進而為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并使社會物質的文明增加可驚的地步”[1]403。在此基礎上,他們歸納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兩大優勢,即資本集中與財產私有。資本集中使資產階級推翻了家庭手工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形成了資產階級的社會;財產私有則使社會財富集中于少數資本家之手,推動了資本產業的擴大再生產,使資產階級的勢力遍及西歐與北美各國。同時,中國共產黨人指出,正是這兩大優勢即財產私有制下的資本集中孕育了資本主義自我崩潰的因素,使得資本主義在生產與分配等問題上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危機。
生產組織擴大化與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崩潰,針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從兩個方面展開批判。首先,生產組織的擴大化使生產活動日趨社會化,無數勞動群眾為少數資本家所束縛、掌握。這種變化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出來并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其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缺乏社會的調節與統計,陷入無政府狀態。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不受政府監管,亦不受社會需要的支配,而是為了競爭私利盲目增加商品,使社會生產超過社會需求,即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陳獨秀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因為社會需要而生產,乃是因為增加他們出賣的‘商品’而生產;只為出賣而生產,非為使用而生產,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1]403這種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擴大化與社會需求不能滿足生產之間的矛盾一旦爆發,便會引發資本主義的恐慌。如李大釗所說:“資本主義制度能使社會破產,使經濟恐慌和貧乏,能使大多數的人民變為勞動無產階級,而供奉那少數的資本家。”[2]331
財產私有使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從而深陷殖民戰爭的泥潭。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財產的私有。財產私有使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其他人則逐漸喪失購買力,因而造成生產力與消費力失衡,引發剩余生產的恐慌。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謂失衡,是指生產力超過消費力,而非超過社會需要,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弊端所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為緩解本國的剩余生產壓力,將商品傾銷至其他國家,以商品換取貨幣,由此產生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為了保有與增加殖民地,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要抵抗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另一方面要組織強大軍力搶奪新的殖民地。這便是“資本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尋垂盡,帝國主義者間相互爭奪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這三者合起來乃是帝國主義之致命傷。”[1]405就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而言,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條件,是財富的積累與資本的增值,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工人逐漸走向聯合,“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3]412-413。
(二)升華與超脫:社會主義是“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主義
通過對資本主義固有弊端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人類社會歷史演化的進程,進一步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超脫性,將社會主義塑造為“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主義,既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與初心,也推動了“社會主義”概念為勞動群眾所熟知。
在塑造社會主義的形象之前,中國共產黨人首先對“社會主義”概念即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行了詮釋。對于“社會主義”的定義,中國共產黨人有一個逐漸深化的認知過程。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諸多主義各行其道,社會主義者與反社會主義者時常開展論戰,社會主義的真諦也在這一階段逐漸闡發出來,“知識階級中表同情于資本家的與表同情于勞動者的兩派,旗幟越發鮮明”[4]490,中國共產黨人也借此對社會主義的宗旨、立場、內涵加以詮釋與宣揚。就其宗旨而言,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人就認識到,社會主義是立足于世界、為全人類而奮斗的事業。正如惲代英所說:“社會主義學理上的根據,以為人類是共存的,社會是連帶的。我們要求個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類的幸福。”[2]478就其立場而言,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階級斗爭的作用,認為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財富公有。李達在同梁啟超辯論時便指出:“要謀社會全體的福利只有把這種自由競爭和私產制度永遠除去,而建設永久的共產社會。階級由對峙而斗爭,而社會主義運動的大勢以成。”[4]494-495就其內涵而言,李大釗從三個層面概括了“社會主義”概念的內涵:一是政治層面,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之目的;二是法律層面,必須廢除舊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實現公有制合法化;三是經濟層面,應當給予勞動者分配自身收益的權利,即“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5]245。
在明晰社會主義的定義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繼而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比優勢塑造“社會主義”概念的先進性。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資本集中,(二)財產公有”[1]406。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者并非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集中,他們所反對的主要是財產私有。因為實現財產公有之后,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分配方式便全然改變了。在財產公有制即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由于生產資料的公有,社會生產將不復以前的無政府狀態,而是依據社會需要進行生產,以滿足需要為指向,而非以追求利潤為目標。在分配層面,剩余勞動隨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而消逝,也就不再有保持生產力與消費力均衡的必要,因為社會生產是依據社會需要進行的,不會有剩余生產的風險。“爭奪殖民地、半殖民地銷納剩余生產的帝國主義即侵略主義”[1]407也便失去了意義,如此方可實現世界的和平。
此外,中國共產黨人還基于經濟組織的變化趨勢佐證選擇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孕育了自我崩潰的因素,“舊經濟組織的自然變化,已指教我們:帝國主義的那條舊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1]405。而擺在中國人面前的,除了帝國主義之外,便只有社會主義道路可走,這也是人類社會之歷史演進的趨勢,因為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是最具革命性的階級。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指出,中國要救亡圖存,并沒有現成的道路可以走,只有靠中國人自己探索,披荊斬棘,掃除障礙。
可以說,通過對緣何選擇社會主義的解釋,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塑造了“社會主義”概念的先進性與科學性,也指明了通往社會主義的曲折性與長期性。在同其他主義論戰的過程中,既加深了自身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也將“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推及廣大勞動群眾。
(三)世界與中國:半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的必然選擇
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詮釋與形塑“社會主義”概念時面臨的核心命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決定了能否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為闡釋社會主義對中國的適用性,中國共產黨人從經濟、政治與階級力量對比等角度論述了當時之中國已經具備了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
李大釗指出:“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于世界經濟勢力之外。”[6]359可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國的經濟與政治聯系日益緊密,中國已經不能離世界而獨立,因此,要論證社會主義是否適用于中國,須先了解世界政治經濟情形之變化。
政治方面,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打破了舊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隨即迎來一波高潮。但俄國革命引起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他們聯合起來通過改善工人地位、鎮壓勞工運動等方式壓制各國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正如瞿秋白所說:“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俄國急取攻勢,俄國無產階級獨力奮斗,而西歐工人方暢心滿意于社會改良政策。”[7]463
經濟方面,受“一戰”影響,歐洲諸國不僅政治動蕩不安,經濟亦遭受極大損失,甚至已到接近破產的境地。“如英國素來是一個有錢的國家,戰前是世界的債權國。戰后變為美國的債務者。”[1]405
為了維護國內政局的穩定,恢復國家經濟,資本主義國家將目光投向廣袤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一方面設法緩和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加緊掠奪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源。這就導致中國雖然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實業的階段,“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6]359由此,中國共產黨人指出,中國已經具備了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并且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因為“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6]359。
對社會性質的認識決定了道路與方向的選擇,在研判中國政治經濟情形之前,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揭示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表面上雖說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個半殖民地”[1]414。中國的政治經濟實權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因北洋政府名義尚存,不算是完全的殖民地,但現今之中國,“不論國會省會的議員,無不是大軍閥小軍閥的機械”[8]48,更遑論北洋政府。中國政治實質上受制于帝國主義,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皆處于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之下。陳獨秀也總結道:“總統、內閣、國會都建筑在軍閥勢力上面,而軍閥又壓倒在外國帝國主義國家之下,這是中國現在政治實在情形。”[1]416
就中國的經濟現狀而言,“國內新式生產機關絕少,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4]490因為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由自由競爭發展到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共營的階段,中國繼續追逐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腳步,“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萬里,我們尚在初步”[6]359。加之中國的經濟狀況,如關稅、工商業、金融、交通、礦業等完完全全由資本主義國家所支配。基于此,李達作出了判斷:“當著產業萬分幼稚的時代又伏在各國政治的、經濟的重重勢力之下的中國,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和各資本國為經濟戰爭,恐怕要糟到極點了。”[4]499因此,若要改變中國實業之薄弱,抵抗資本主義的剝削,社會主義是最合適的革命道路。
通過對世界與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剖析,中國共產黨人闡述了社會主義何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何以能拯救廣大勞工群眾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使得“社會主義”概念同中國革命現實狀況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中國革命指引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二、選擇何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通過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論證了選擇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但是,當時的中國存在著許多社會主義派別,究竟應選擇何種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又是哪一種社會主義?這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詮釋“社會主義”概念時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一)中國共產黨人對幾種主要社會主義流派的分析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社會主義各流派之間因政見不同而爭執不休,除共產主義之外,當時流傳較廣且有組織力量的社會主義流派主要分為四種,即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為詮釋真正的“社會主義”概念,中國共產黨人對以上幾種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進行了分析與批駁。
1.基爾特社會主義:鼓吹經濟與政治相分離
基爾特社會主義亦稱“行會社會主義”,是20世紀初英國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潘蒂、霍布遜、柯爾等。五四時期,經梁啟超、張東蓀等人的引介與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流派之一傳入中國,曾在中國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基爾特社會主義否認階級斗爭,希望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生產聯合會,繼而掌握生產管理權,他們主張改善工人的條件,但不推翻現存社會制度,意圖通過改良的方式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基于經濟與政治二元論與職能劃分,主張國家與基爾特(工會)各負其責,即由勞動階級(工會)掌握生產管理機關,由資本家掌握國家政權機關。他們主張“用蠶食手段,漸漸獲得生產管理權,以達到工業自治的目的”[1]407。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基爾特社會主義在同中國共產黨人的論戰中逐漸敗下陣來,陳獨秀指出,他們有兩個不可掩蔽的缺點,“(一)把壓制生產勞動者底國家政權法庭海陸軍警察完全交給資本階級了;(二)政治事業和經濟事業有許多不能分離的事件,例如國際貿易之類事也”[1]128。
2.無政府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空想主義
20世紀初,歐洲工人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被部分留日、留法的中國學生所接受,進而傳入中國。他們將中國傳統的“大同”“均平”等思想糅雜在其中,形成了中國無政府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劉師復、黃凌霜、區聲白等人。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流行較為廣泛,在全國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團體。他們主張絕對的自由,反對一切強權,主張消滅國家、政府、警察、監獄等。在財產所有制問題上,他們主張廢除私有制,消滅家庭。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之前,無政府主義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因為他們主要反映的是貧苦農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等對專制剝削的反抗。但由于無政府主義否認階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其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主義。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面對無政府主義展開批判。在經濟方面,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絕對自由“因為沒有強制力去干涉調節,自然會發生生產過剩或不足的弊端”[1]129;在政治方面,若廢除法律與國家機關,社會必然運轉困難,“凡有社會組織,必有一種社會制度,隨之亦必有一種法律保護這種制度”[1]129。因此,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層面,無政府主義都是走不通的。
3.工團主義:站在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對立面
工團主義又稱“無政府工團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法國的索烈爾和拉加德爾等。工團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中間分離出來的學說,在中國雖存在一些擁躉,但并沒有形成廣泛影響。工團主義的主張主要有兩點,一是階級斗爭,源于馬克思主義;二是不要國家及政權,出自無政府主義。由于工團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被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對立方,隨著國際工人運動的失利而消亡。
4.國家社會主義:逐漸走向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這里所講的國家社會主義主要是指在馬克思主義中分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流派,常被拿來同共產主義作比較,兩派的具體主張存在著明顯區別。就主張而言,中國共產黨人在四個層面揭示了國家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一面。其一,國家社會主義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勞資攜手的理論,但“已令勞動者從事選舉活動,已利用資本階級底政府國會采用社會政策改善勞動底地位”[1]131,這實際上已經放棄了階級戰爭的革命手段,走向了改良主義。其二,國家社會主義主張通過議會實現社會主義,但議會制度本是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統治而設立的,通過議會政策廢除資本私有制,其成功率尚不可知。單議會政策本身便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一貫的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主張。其三,國家社會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9]27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明明是馬克思的主張,國家社會主義卻棄之如敝屣。其四,生產機關集中到國家手中對于共產黨來說是最初的手段,對于國家社會主義卻是最終的目的。國家社會主義具有很強的國家主義色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共產黨在國內尚未統一時便致力于開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見,“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格斯底學說,并且明明白白反對馬格斯”[1]133。
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上述幾種社會主義流派的分析與批駁,進一步深化了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與認知,也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指導。
(二)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底科學的社會主義”
從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詮釋來看,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指“馬克思底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交鋒中,中國共產黨人著重闡釋了共產主義的主張與原則。
共產主義主張實行堅決的階級斗爭,這點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不同。在階級斗爭的立場之上,集合無產階級中最有覺悟、最具革命性的先進分子組織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即共產黨。階級斗爭取得勝利后,應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與工團主義不同),并且通過無產階級的國家壓制資產階級的反抗,加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之中。“然后漸漸滅絕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及私有習慣與心理,建設無產階級的工業與文化,最后達到廢除一切階級無國家的共產社會”[1]411。
關于共產主義的原則,中國共產黨人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闡述。第一,堅持科學的根據。所謂科學的根據,即根據社會歷史演進規律與現社會的經濟文化狀況做出判斷。對于改造社會,不能只看到主觀的改造意愿,而必須在客觀上觀察社會的物質條件是否有改造的可能性。第二,社會改造應按步驟進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取得政權的步驟與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10]49。因此,關于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清晰的認知,陳獨秀指出:“因為各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進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驟不能一致。”[1]412第三,每一個步驟都要采用革命的方法。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一蹴而就的,“從組織共產黨一直到實現社會主義,其間須經過幾多步驟,每個步驟之中,或者又須經過幾多曲折的步驟,但每個步驟都必須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這是革命的馬克思派之特色”[1]412。
在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為了維護正統的“社會主義”概念,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展開過多次論戰,深刻剖析了諸如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幾種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社會主義流派的理論缺陷與反馬克思主義本質,同時也向中國人民尤其是勞動群眾展現了共產主義的科學性。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認知更為全面,開始初步擘畫中國的革命道路。
三、社會主義何以實現: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而言,走向社會主義是救亡圖存的必然選擇,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革命方式、革命階段等問題加以解答,同時也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
(一)革命方式: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
“社會主義”概念總是同無產階級聯系在一起。“社會主義如何在中國開始進行,就是勞動階級應該如何開始奮斗”。[1]418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兩點原則。
一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無產階級的特性決定了他們比任何一個階級都更為集中,更具有組織紀律性。同時,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低下,他們不占有生產資料,所擁有的只有勞動力。這就決定了“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11]8。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無產階級應當積極參與革命運動,將農民、小資產階級等其他階級團結在自己周圍,通過暴力手段打倒軍閥等反革命勢力,引導著其他階級革命到底。如瞿秋白所說:“無產階級應當引導大多數半無產階級的份子,成就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而以嚴厲手段鎮服資產階級的反動,并且遏制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畏怯不前。”[8]204
二是必須采取堅決的革命行動。關于中國革命的方式與途徑,中國共產黨人指出,奪取政權大多分為兩種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大多從議會、憲法著手,但這種運動多歸于失敗。因此,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一如李達所說:“將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或者有采用勞動主義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而所謂直接行動,“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種非妥協的階級爭斗手段”[4]506-507。陳獨秀也認為,雖然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較為薄弱,但帝國主義的壓迫迫使中國人不能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了,因為“有產階級的政治家政客底腐敗而且無能和代議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在歐美更格外破產了”[1]133。
(二)革命階段:關于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分歧
關于社會主義的革命階段,李大釗認為,中國若要達到社會主義,應當采取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方法,就是無產階級獨攬政權”[2]205。意即革命成功之后,應當直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陳獨秀等則認為無產階級應該先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等待資本主義獲得發展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指出,社會主義唯有通過純粹的國民運動方可實現。即“團結民眾的勢力,滿具革命的精神,絕不與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這就叫純粹的國民運動”[1]419。在陳獨秀的設想中,只有推翻了帝國主義與軍閥,取得國民革命的成功,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瞿秋白則指出:“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能生出社會主義來,只有他能造成社會主義公有生產資料之技術上的基礎。只有他能造出數量多而覺悟深的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民權主義)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種子才能開始萌動——那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才顯然暴露。”[8]191-192在瞿秋白看來,無產階級應當首先投身于資產階級革命,將帝國主義與軍閥推翻之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而實現建設社會主義之目的。瞿秋白在此特別強調“勞工階級”應在國民革命中取得領導權,最終實現社會主義。
由此可見,在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階段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初期并未達成一致的意見。直至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協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的政策,這一分歧才得到暫時解決。即“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2]289。在國民會議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統一全國的人民政府。這實際上承認了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這也為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了伏筆,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逐漸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黨的力量遭受了極大損失。
四、奠基與鏡鑒: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社會主義”概念探索的理論意義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12]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雖然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探索尚存有分歧與誤區,但中國共產黨人圍繞緣何選擇社會主義、選擇何種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何以實現三個維度的闡釋,明晰了社會主義的適用性與科學性,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推動了“社會主義”概念的中國化,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借鑒與指導。
(一)理論武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在一百年的奮斗中,我們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歷史大勢,正確處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12],逐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武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在對“社會主義”概念進行闡釋與探索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發生了論戰與沖突。在論戰中,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深化了對“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認知,從而初步總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幾個特征。第一,對于共產黨來說,將生產機關集中到國家手中是必要的手段;第二,真正的共產主義是致力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三,共產黨所依據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最終要造成的是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
真理愈辯愈明,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論戰,深化了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廓清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關于為何選擇社會主義、選擇何種社會主義的疑問,有力地回擊了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對馬克思主義的污蔑,同其他的社會主義流派劃清了界限,將俄國共產黨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榜樣,明確指出,“只有俄國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1]133。通過論戰,“科學底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成為指導中華民族實現獨立與解放的思想武器。
(二)理論具象:推動了“社會主義”概念的中國化
“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12]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自創建初期便面臨的重大命題。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13]651。可見,只有通過民族形式實現馬克思主義,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初期便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
在對“社會主義”概念的詮釋與探索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也推動了這一概念的中國化,將晦澀的理論概念同中國的革命現實結合起來,以說明社會主義與中國的適配性。中國共產黨人在緣何選擇社會主義、選擇何種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何以實現三個維度闡釋“社會主義”概念的同時,立足中國國情,論證了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中國,在經濟文化發展較為落后的情況下,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務。這實際上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民族形式展現出來,推動了“社會主義”概念的中國化,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論具象,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理解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基礎。
(三)理論借鑒: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經驗與指導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12]中國共產黨人在詮釋“社會主義”概念的同時,也對中國革命道路與革命方式進行了討論,雖然在社會主義的實現路徑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何以實現所進行的設想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論借鑒,提高了中國共產黨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水平,為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寶貴經驗。如在革命領導權方面,李大釗認為必須由無產階級掌握革命的領導權。瞿秋白也指出無產階級是覺悟最深的階級,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必然在于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何以實現的命題中,陳獨秀等人提出了國民會議運動的主張,即全國各革命階級團結起來,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召開國民會議,以此作為革命勝利后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主張不僅初步提出了統一戰線思想,也為國共合作提供了理論依據,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基礎。
此外,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對“社會主義”概念的認知也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比如雖然堅持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但并未深入研究無產階級應當如何取得并維護自身的領導權;對于中國革命的連續性的認知不夠清晰,并未完全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對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搖擺性缺乏分析與了解等。但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詮釋與探索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使“社會主義”一詞廣為人知,也對后來“工農武裝割據”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論指導與經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