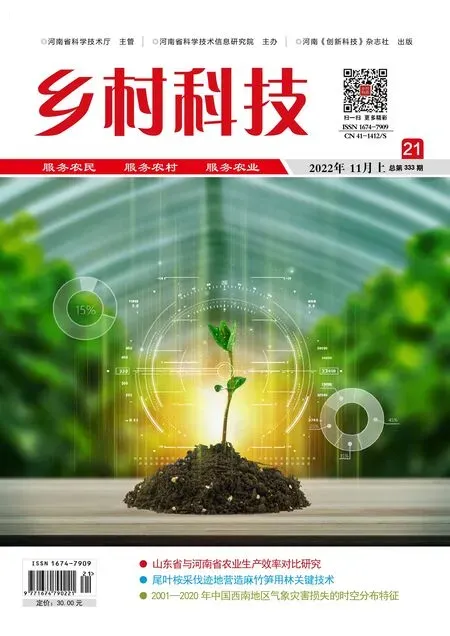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角下民族地區礦區生態修復的思考
——以霍林河礦區為例
裴占杰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00)
0 引言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必須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這為民族地區開展生態治理工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動指南。我國民族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在早期發展中以礦產資源開采等產業為主,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隨著國家對礦區地質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重視度的提高,加之民族地區居民環保意識逐漸增強,民族地區礦區生態治理和修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于此,筆者以霍林河煤礦為例,探究如何進一步以礦區生態修復工作帶動當地農民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實現全面鄉村振興。
內蒙古自治區霍林郭勒市位于科爾沁草原腹地,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是一座因煤而興的城市。我國工業化建設初期,對煤炭的需求量倍增,煤炭供應出現緊張局面,我國五大露天煤礦之一的霍林河煤礦應運而生。隨著煤炭工業的快速發展,當地的生態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截至2013年,霍林河露天煤礦占用、損毀土地面積達933.8 hm2,6 a內投入的復墾資金僅有419萬元,復墾面積僅98.916 1 hm2,已開展治理區域的治理效果較差[1]。2018年以來,霍林郭勒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露天礦區的具體條件,先后制訂實施多項礦山生態環境治理措施。截至2021年,霍林郭勒市完成礦山生態修復治理面積0.41萬hm2,實現區域內全部礦山的生態治理,共建成4個綠色礦山[2]。在礦區生態治理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礎上,當地積極探尋治理后的草原和土地再利用方式,著力發揮礦山生態治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時,該市鼓勵與草原和土地密切相關的農牧民積極參與復墾礦山再利用。
1 鄉村振興與礦區生態修復的理論邏輯
1993年,美國經濟學家Auty提出“資源詛咒”假說,他發現一些擁有豐富礦產資源且以這些資源為主導產業的地區,雖然存在短期內經濟迅速增長的情況,但是資源并不能給這些地區帶來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甚至還會抑制該區域的經濟增長。自然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成為我國學者研究“資源詛咒”問題時的重點對象,礦產資源開發已經成為資源儲備豐富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柱,但礦產資源開發并未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發展,甚至還壓縮了當地諸如農業等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這樣脆弱的經濟體系終將對其經濟發展產生阻礙。而伴隨長期的礦產資源開采,這些地區的資源逐漸耗盡,生態環境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甚至許多地區修復受損生態環境所需要的成本遠遠高于開采礦產資源創造的經濟價值。
從“資源詛咒”假說的角度分析,霍林河礦區周邊鄉村日漸衰退,主要是由于當地的農牧業經濟發展水平遠低于煤炭產業發展水平,導致許多農牧民逐漸退出農牧業。但這些農牧民受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的限制,無法進入煤炭行業,造成農村勞動力和資金外流,最終霍林郭勒市礦區周邊鄉村逐漸衰退。究其本質,主要是在煤炭開采和后期礦山生態治理的利益分配過程中,當地的農牧民未能從中獲得充足的保障民生資金,這使得霍林郭勒市礦區周邊的鄉村發展不夠樂觀。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3],其內在邏輯在于依托產業興旺實現生活富裕,在生活富裕的同時實現生態宜居[4]。就霍林郭勒市礦區的發展而言,傳統農業和煤炭產業都不足以滿足以上目標,而依托現有礦山治理成效發展生態產業是最好的選擇。同時,在未來的礦山生態修復工作中,霍林郭勒市要堅持經濟效益和人文關懷并重,這樣才能實現有效治理和鄉風文明。因此,在未來的礦山生態修復工作中,霍林郭勒市要致力于實現將礦區鄉村振興與礦區生態修復規劃有機融合,鼓勵農牧民積極參與礦山修復工作,依托礦山生態修復發展生態產業,實現鄉村經濟轉型升級和礦山生態修復可持續,享受到礦山生態修復帶來的紅利,建設新時代美麗鄉村。
2 民族地區礦區生態修復的成果反思
礦區生態修復是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一環,也是建設“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的美麗鄉村的重要途徑。2016年,原國土資源部等5部委發布的《關于加強礦山地質環境恢復和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大力探索構建“政府主導、政策扶持、社會參與、開發式治理、市場化運作”的礦山地質環境恢復和綜合治理新模式。近年來,一些民族地區的礦區生態修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也逐漸顯露出來。筆者以霍林河礦區為例,通過開展相關調研活動,從鄉村振興的視角出發,總結當地生態修復工作的不足之處。
2.1 參與主體較為單一
霍林河礦區生態修復和治理工作的責任主體僅有政府和礦產企業。在礦區生態修復過程中,政府主要根據國家相關政策要求,依據當地礦區生態受損具體情況和礦產企業實際情況,制訂相關礦區生態環境修復治理規劃與具體工作方案,在礦區生態修復和治理過程中進行監督,對礦區生態環境修復與治理成果展開評估。在整個治理過程中,政府還會在資金上對礦區生態修復工作給予一定的支持和幫扶。由此可見,霍林郭勒市人民政府在礦區生態修復過程中承擔了執行國家政策、決策修復規劃和監督的責任。遵循“誰破壞、誰修復”的原則,礦山企業作為霍林郭勒市礦產資源的開發主體理應成為其礦區生態修復工作的具體執行者。
農牧民是礦區生態修復的主要利益相關者,但他們對礦區生態修復的相關知識儲備和認識不到位,通常只關注礦區生態修復能否為其帶來經濟效益,忽視礦山修復所帶來的其他效益,因此不會積極主動參與礦區生態治理工作。而諸如社會投資者、金融機構和科研院所等社會組織的相應訴求,在礦區生態修復過程中也沒有得到滿足,因此,這些主體參與生態修復的意愿較低。由此可見,除政府和礦產企業兩個主體外,基本上再無其他群體參與霍林郭勒市礦區生態修復工作,礦區生態修復的參與主體較為單一。
2.2 經濟考量缺乏
長久以來,政府在礦區生態修復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這導致在生態修復規劃中常以政府績效和經濟效益作為利益訴求。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各地政府陸續改變以往唯GDP論的政績考核模式,將綠色發展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5]。因此,對于轄區內存在礦區的地方政府來說,用生態效益各項指標衡量礦區生態修復成為當地政府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期望相關生態修復項目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居民收入等,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
但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民族地區的政績考核以當地的經濟發展為主,并未將該地區礦產資源開采后的生態修復情況納入政績考核,導致這些地區在此時期內一味地追求GDP增速,忽視了礦區生態修復。2018年,中央第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進行檢查時發現,霍林郭勒市人民政府對于礦區生態修復監管不到位,礦區內存在大量應治未治區域,且已修復的區域修復效果不理想,因此要求其進行整改。此后,霍林郭勒市人民政府加大對礦區生態修復的投入力度和監管力度,在較短時期內完成了大部分的礦山治理工作。但由于大批礦區生態修復項目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導致這些項目在實施時僅追求了生態效益和環境效益,并未從獲取經濟效益的角度對項目進行謀劃,未能實現與當地產業發展相配合,缺乏一定的經濟考量。
2.3 拆遷農牧民安置方式欠妥
礦區在開采過程中不僅會形成占地面積巨大的礦坑和排土場,而且會對礦區內地表生態環境和地下水資源造成難以逆轉的毀壞,產生的粉塵對附近區域的空氣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我國民族地區礦產資源豐富,在其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過程中大量耕地和草原被占用,嚴重壓縮了民族地區農牧民的生存空間,臨近礦區的村莊會出現水資源短缺、空氣質量惡化等現象,嚴重干擾了當地農牧民的生產生活。
霍林河礦區周邊農牧民的生存空間被擠壓時,當地采取了大多數此類地方所采取的村莊集體搬遷方法,對農牧民原有住房和耕地面積進行評估作價,農牧民按照估價額度,選取城區中劃定的安置區域內的房屋進行置換。雖然農牧民的居住環境在此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大多數農牧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農村,突然的易地搬遷割裂了其主要的社會關系和人際網絡,使其難以適應城市生活。除此之外,失去耕地和草原的農牧民也不具備除從事農牧業以外的專業技能,加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導致其在城市中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謀生,而城市保障體系又因其農牧民的身份將之拒之門外。因此,許多已經搬遷的農牧民又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返回農村生活,阻礙了礦區的生態修復。
2.4 生態文化傳承、延續困難
我國民族地區工業化發展起步晚,許多民族地區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以游牧和農耕的生產方式為主。這樣的生產方式與采集、漁獵的生產方式相比,所受的自然條件限制有所減弱,但生產過程中自然條件對勞動的限制仍然很大,自然因果性的作用還在很大范圍內限制人類勞動。因此,在我國少數民族的民族傳統文化中,包含了許多關于保護環境、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觀念[6]。
霍林郭勒市地處內蒙古自治區科爾沁草原腹地,當地的農牧民世代以這片草原為生,逐漸形成了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尊重生態、愛護草原的生態文化觀念。但隨著當地煤炭產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現代化生活和工業化生產方式與當地農牧民早期形成的生態文化觀念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大量耕地和草原被占用,許多農牧民不得不離開世代生活的農村,到城市中謀求生路,長期的城市生活使其生態文化觀念逐漸淡薄,而其后代更是從一出生就遠離了形成這種生態文化觀念的草原生活環境,導致民族地區生態文化觀念難以得到傳承。
3 民族地區礦區生態修復的路徑
3.1 激發多元主體參與生態修復
要想保證民族地區礦區生態修復成效,僅靠政府和礦山企業作為礦山修復的責任主體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建立起政府、礦山企業、農牧民和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基本格局。
激發多元主體參與生態修復,要從增強各主體意識、協調各方利益訴求以實現生態修復資源合理分配和構建完善的激勵機制等方面入手。
3.1.1 提高各主體參與生態修復的意識。對于農牧民等仍未參與生態修復的相關主體,應使其樹立生態修復的參與意識。政府通過積極舉辦相關講座,靈活運用各類媒介進行宣傳、教育,使該類主體意識到自己是礦區生態修復的受益者和主人翁,改變其認為生態修復工作只能由政府承擔的傳統觀念,在其心中樹立起與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共謀發展的礦區生態修復理念。
3.1.2 協調各方利益訴求,實現生態修復資源合理分配。霍林郭勒市著力打造以政府為主導,由礦山企業、農牧民和相關社會組織為組成的生態修復利益共同體。政府做好生態修復的統籌規劃工作,促使各主體樹立對礦區生態修復的共同價值導向,建立共同目標,協調好各方利益訴求,改變以往既是礦山生態修復“運動員”又是礦山修復“裁判員”的形象,將一部分產生經濟效益的修復項目交給其他修復主體,促進修復資源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合理分配,使其從生態修復中獲取到生態效益的同時取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對于農牧民等個人無力承擔生態修復項目的主體,可由村集體牽頭成立合作社,以合作社為單位謀求參與生態修復資源的分配。
3.1.3 完善激勵機制。政府針對不同主體采取不同的激勵措施,提高其參與生態修復的積極性。例如,政府對參與生態修復的農牧民給予一定的幫扶資金和物質、精神獎勵,或根據礦區生態修復和綠色礦山建設情況,針對礦山企業出臺免稅政策等[7]。
3.2 探索“礦山修復+生態產業”模式
生活富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目標,而產業興旺是帶動鄉村居民生活富裕的關鍵因素。因此,發展產業的選擇是霍林郭勒市實現礦區鄉村振興的關鍵。霍林郭勒市早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發展,造成產業發展出現二元分化,高速發展的工業未能帶動農業發展。當地要想實現農業蓬勃發展,就必須創新優化農業發展路徑,而依托礦山修復成果發展生態產業成為打造生活富裕、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的最優選擇。
3.2.1 發展“礦山修復+生態農業”。政府將礦山修復所復墾或已經復墾種植了經濟作物的土地和修復的草原的使用權,合理流轉到農牧民的手中,使其按照生態修復相關規劃科學種植相應經濟作物,發展畜牧養殖。政府依據礦區各村鎮的具體情況,打造農業采摘園和農牧業“一村一品”的小鎮經濟,并且發展相關農牧產品的銷售和深加工產業,實現產業鏈延長,保障農牧民增收。
3.2.2 發展“礦山修復+生態旅游”。霍林郭勒市地處科爾沁草原腹地,素有“草原煤城”之稱。而霍林河礦區的露天煤礦開采與傳統礦井作業不同,其開采作業流程和開采環境全部暴露在外部,在其排土場可以俯瞰全部作業流程和向下挖掘的層層地質景觀。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其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發展旅游業,打造“草原煤城”旅游小鎮和“草原煤城”品牌文化,發展旅游經濟。在此過程中,長久居于礦區周邊的農牧民可以借助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對礦區及其周邊地理環境的了解,參與發展旅游業。
3.3 妥善安置拆遷農牧民
3.3.1 對拆遷農牧民的安置工作進行合理規劃。政府應統籌考慮拆遷農牧民對安置區域人文環境和物質條件等的適應性,選取適宜區域對拆遷農牧民進行集中安置或分散安置,避免出現“孤島式”農牧民移民社區。
3.3.2 有針對性地對拆遷農牧民進行生態修復相關技能培訓。政府應按照當地企業用工的具體需求,組織企業或聘請專家對拆遷農牧民進行工作技能培訓,使具有一定學習能力的拆遷農牧民在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后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以此在相對應的城市安置點中開啟新的生活。此外,政府可按照礦區生態修復過程中所出現的工作崗位對失地農牧民進行相關技能培訓,為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3.3.3 依托已修復區域建立拆遷安置點。對于礦區周邊完成生態修復的土地或草原,政府通過對其科學合理地整合與規劃后,在其附近建立新的農牧民安置點,安置由于各種條件限制而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實現再就業的拆遷農牧民,將此區域的土地或草原重新承包給安置點的農牧民。
3.4 重塑“草原煤城”生態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強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保持戰略定力。生態文化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要尤其注重生態文明建設,重塑“草原煤城”生態文化。
3.4.1 精神文化層面。政府應深度挖掘當地農牧民原有的民族傳統生態文化觀念,與當地打造綠色礦山的生態文化理念相融合進行優化、保護與傳承,從而喚起礦區周邊農牧民對于礦區生態修復與礦區生態保護的集體認同感。
3.4.2 行為文化層面。政府要充分發揮引領作用,積極引導當地農牧民和企業參與礦區生態文明建設,促進農牧民從認知向行動轉變;打造“文化+”產業模式,實現“草原煤城”文化與礦區周邊鄉村產業融合發展,帶動鄉村生態產業發展。
3.4.3 物質文化層面。物質文化是展示和宣傳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的最佳陣地。政府在礦區周邊的鄉村設計建造中應融入“草原煤城”文化符號,以“草原煤城”生態文化為主題,規劃建設生態修復科技園、草原露天礦山公園、草原露天煤礦博物館等,運用綜合多樣的物質文化形式對“草原煤城”生態文化進行展示與宣傳,為礦區周邊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助力實現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