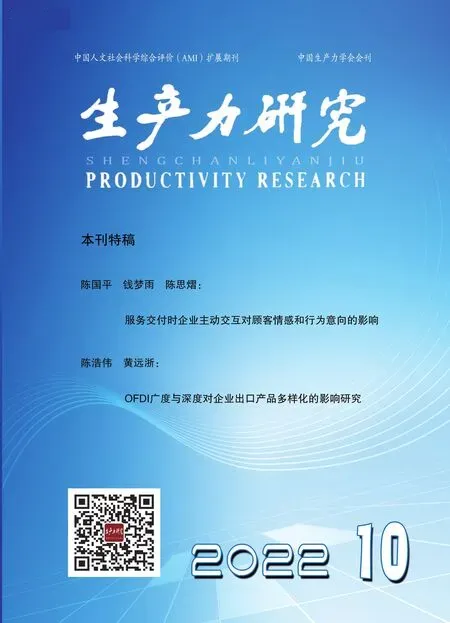黃河流域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
何 靜,李 蕓,金 丹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2.陜西省房地產業綠色發展與機制創新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55)
一、引言
《中華人民中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生產性服務業作為衡量地區現代化水平和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具有強功能支撐、高密度空間集聚和不斷對內對外輻射擴散的特點,能重塑城市產業格局,是城市在國內國際雙循環背景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黃河流域橫跨九省,是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試驗區以及中華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的重要承載區。近年來,黃河流域的發展很受重視,但就目前來看,黃河流域各省區要素資源比較匱乏、產業倚能倚重、低質低效問題嚴重,需要有較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集群。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推進,城市群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近年來,黃河流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加快建設,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涌現。生產性服務業是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兩業融合的重要結合點,為了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引領產業結構升級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對于黃河流域城市群而言,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集聚如何影響城市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如何調整才能更好地適應市場環境變化,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Hansen(1990)[1]分析了美國地區數據,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生產率增長的關鍵。Grubel 和Walker(1989)[2]指出,生產性服務業蘊含著更多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黃繁華和郭衛軍(2020)[3]從本地效應和溢出效應角度出發,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顯著促進長三角城市群本地和鄰近地區的經濟增長。李斌和楊冉(2020)[4]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資源效益三方面構建城市經濟績效評價指標,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對城市經濟增長均有正向溢出效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還能夠通過降低制造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制造業效率(江靜等,2007;宣燁,2012)[5-6]。陳明和魏作磊(2018)[7]認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生產率存在較弱的正向效應,各細分行業對制造業生產率影響具有差異性。王文等(2020)[8]采用PSTR 模型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能促進制造業生產率的提升,且證實了城市規模在其中的調節作用。劉葉和劉伯凡(2016)[9]的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提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途徑。總的來說,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知識技術溢出效應、規模效應、要素配置效應等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增長。
(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
關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大部分結論具有一致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通過知識技術的空間溢出效應、規模效應及環境的正外部性推動制造業升級,促進制造業價值鏈攀升(高康和原毅軍,2020;喻盛華等,2020)[10-11]。溫婷(2020)[12]基于全國239 個地級市的數據,從生產性服務業整體集聚和分行業內部集聚兩維度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整體集聚對產業升級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各行業內部集聚溢出效應各異。張治棟和黃錢利(2021)[13]通過空間面板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進行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有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裴耀琳和郭淑芬(2021)[14]基于2008—2017 年的中國城市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促進資源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主要通過要素流動、結構優化等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促進黃河流域城市群產業結構調整。
(三)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趙越強等(2021)[15]認為現階段主要依靠產業結構升級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關系。曹聰麗和陳憲(2019)[16]運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研究,發現在不同城市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城市規模條件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模式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經濟增長效應不同。張治棟和秦淑悅(2018)[17]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調整能明顯促進本地區綠色效率的提升,但對周邊城市綠色效率提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于斌斌(2015)[18]認為在城市化階段,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能帶給地區經濟增長較為明顯的“結構紅利”,高級化調整是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階段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發現,產業結構調整能通過要素配置效應、知識技術溢出效應、競爭效應等影響經濟發展,此外,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知識、勞動密集型產業,產業結構調整能促進其中的要素流動,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產業結構調整對黃河流域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大部分學者直接研究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經濟增長或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忽略了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在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產生的作用,且多數文獻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群為研究對象,關于地級市的研究中,也較多討論了東部地區城市的情況,不論是在城市群的層面,還是在地級市的層面,鮮見關于西部地區和黃河流域城市群的研究。因此,本文建立空間計量模型研究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以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為樣本,實證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產業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
三、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城市經濟增長:用各城市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代理變量。為了剔除價格因素影響,以2003年為基年,用各地區各年的GDP 指數對GDP 進行調整。人口用全市年末總人口表示。
2.核心解釋變量
(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本文選用區位熵來測算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構建方法如下:

其中,Eis表示城市i 的生產性服務行業s 的就業人數,Ei為城市i 的全部就業人數,Es表示全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人數,E 為全國總就業人數。就業人員均為城鎮單位就業人數。
(2)產業結構調整。合理化和高級化是優化產業結構的兩個基點,本文從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兩個方面來構建產業結構調整指標。
產業結構合理化:借鑒陳紀平(2013)[19]的做法,用泰爾指數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泰爾指數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負相關,為了將其轉換為正項指標,最終選取泰爾指數的倒數來計算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計算公式為:

其中,Yi和Li分別表示產業i 的產值及從業人數,Y 和L 分別表示總產值和總從業人員數。RIS 是正向指標,RIS 值越大,產業結構越合理。從業人員為城鎮單位從業人員。
產業結構高級化:采用付凌暉(2010)[20]的做法,將一、二、三各產業GDP 增加值占GDP 比重的組成三維空間向量X0=(x1,0,x2,0,x3,0),然后分別計算向量X0與按一、二、三產業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與X3=(0,0,1)之間的夾角θ1、θ2、θ3:

產業結構高級化(OIS)的計算公式為:

OIS 是正項指標,OIS 值越大,產業結構水平越高。
3.控制變量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還選取以下控制變量:(1)城市消費水平(Cons):采用市轄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作為代理變量,消費一直以來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之一,需要控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2)房地產投資(Real):用市轄區房地產投資額表征。(3)城市金融存量(Fin):用市轄區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與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之比衡量,良好的金融系統能促進資金向高效率部門轉移,增強系統經濟效率。(4)居民工資水平(W):用市轄區職工平均工資衡量。工資水平可能通過影響企業成本或調整產業結構進而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5)固定資產投資水平(Inv):用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征。(6)政府干預程度(Gov):用市轄區財政支出占GDP 比重衡量。(7)技術投入水平(Tec):用市轄區政府財政支出中科學與教育的支出比重表示。
(二)數據來源
剔除濟源、楊凌示范區、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海東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平羅、青銅峽、靈武、賀蘭、永寧、中寧等13 個數據嚴重缺失的城市,本文最終選取2003—2019 年黃河流域66 個地級市數據進行研究。所有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城市統計年鑒》、EPS 數據庫以及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公報,個別缺失值采用插值法及平均增長率方法進行填充。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本文對變量進行了對數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為研究空間溢出效應,本文建立了空間計量模型。同時,為確保計量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根據空間相關性來源的不同,在空間經濟地理嵌套權重矩陣下分別進行LM、LR、Hausman 檢驗和聯合顯著性檢驗。如表2 所示,LM 檢驗和LR 檢驗結果均顯著拒絕原假設,選擇空間杜賓模型,同時,根據Hausman和聯合顯著性檢驗結果,選擇時間固定效應模型。模型設定形式如下:

表2 模型估計形式的檢驗結果

其中,i 和t 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PGDPit代表城市經濟增長,β 為系數矩陣,Xit為控制變量向量,μt表示時間非觀察效應,φit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空間相關性檢驗
本文采用Moran's 指數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表3 的結果顯示,2003—2019 年黃河流域樣本城市的全局Moran's 指數總體上呈先增后減的趨勢,2011 年達到最大值0.222,此后逐步下降,2019 年達到最小值0.084。檢驗結果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均為正數,說明黃河流域城市經濟增長在空間分布上并不是隨機的,存在較強的空間正相關性,可以對其進行空間計量回歸。

表3 黃河流域城市經濟增長的Moran's I 指數檢驗結果
(二)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的回歸結果與分析
從表4 回歸結果列(2)可以看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系數為4.897,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生產性服務業能通過知識溢出、規模經濟、要素重組等促進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發展,而其空間滯后項系數為-1.414,顯著為負,說明本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阻礙了鄰近城市GDP 的提升。OIS 和RIS每提升1%,經濟發展分別提升1.539%和0.104%左右,說明黃河流域城市群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能明顯促進本地城市經濟增長,且高級化影響程度遠高于合理化,目前我國黃河流域的產業發展以第二產業為主,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比較低,需要相應提高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交互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對其求導ρPGDP/OIS=-2.768SG,說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邊際經濟增長效應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負相關,原因可能是黃河流域仍處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早期階段,產業結構單一,產業基礎薄弱。

表4 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回歸結果分析
從控制變量來看,城市消費水平(Cons)估計系數為0.127,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居民消費釋放可以通過帶動資金流通、刺激市場等推動黃河流域經濟發展。居民工資水平(W)估計系數為0.292,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提高居民工資水平能吸引更多的勞動力進而推動經濟發展。固定資產投資水平(Inv)系數為0.293,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增加固定資產投資能提高黃河流域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Gov)系數為-0.409,在1%水平上抑制城市經濟增長,過度的政府干預會擾亂市場秩序,造成資源浪費,阻礙黃河流域城市經濟增長,不利于城市發展。房地產投資(Real)估計系數為-0.055 3,在5%水平上抑制地區經濟增長,原因可能是黃河流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房地產行業發展狀況欠佳,對地方經濟拉動作用不突出。城市金融存量(Fin)對黃河流域城市經濟增長促進作用較小,原因可能是黃河流域發展基礎較為薄弱,金融結構需要完善。就各變量估計系數的大小來看,固定資產投資(Inv)和居民工資水平(W)估計系數分別為0.293 和0.292,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最大。
(三)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分析
如表5 結果所示,各變量的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的顯著性均有較高一致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直接效應為4.975,顯著為正,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顯著促進本地城市經濟增長,而其間接效應為-2.017,顯著為負,說明本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阻礙了鄰近城市GDP 的提升,可能是由于黃河流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程度較低,且受地理條件等的制約,各區域之間經濟聯系程度不高,難以形成有效的區域分工和協作機制。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直接效應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產業結構調整能明顯促進黃河流域本地區城市經濟增長;間接效應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產業結構調整對周邊城市經濟增長產生一定抑制作用,OIS 每提升1%,PGDP 下降0.248%,RIS 每提升1%,PGDP 下降0.0173%。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提高在促進黃河流域本地區經濟的增長同時吸納了部分其他城市資源,從而抑制其他城市經濟增長。

表5 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分析
(四)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的比較分析
黃河流域城市群是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心,其經濟發展與黃河流域發展前景息息相關,同時,橫跨北方多個省份的黃河流域城市群,在縮小南北差距、促進民生改善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黃河流域區域發展差異較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不同,需進一步研究各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產業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進行研究。
1.三大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特征比較。圖1為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結果,可以看出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在2003—2019 年整體上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同時,各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存在差異。其中,2003—2019 年關中平原城市群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最高,山東半島城市群的集聚水平在2003—2011 年低于中原城市群,2011 年山東半島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集聚指數分別為0.817 2和0.816 8,之后兩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基本持平。

圖1 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比較
2.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三大城市群回歸結果分析。從表6 中SG 的估計結果來看,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平原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估計結果分別為9.521 和16.890,說明兩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顯著促進地區經濟增長,較之于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平原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太顯著(10%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上存在差異,山東半島城市群集聚水平相對較低,規模效應得不到有效發揮,因此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影響。從產業結構的估計結果來看,山東半島、中原和關中平原城市群RIS 系數估計結果分別為0.099 2、0.198、0.107,三大城市群產業結構合理化均能顯著促進地區經濟增長,關中平原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OIS 系數分別為-2.128 和-0.140,說明產業結構高級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兩城市群經濟增長,可能是由于關中平原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過高,政府盲目追求產業升級,“過度去工業化”現象嚴重,導致產業結構與經濟質量水平不匹配。就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產業結構調整的交互項結果來看,三大城市群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邊際經濟增長效應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正相關,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邊際經濟增長效應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負相關。

表6 黃河流域三大城市群回歸結果分析
五、穩健性檢驗
(一)改變權重矩陣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將改變空間權重矩陣來對基礎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本文在空間計量模型中主要采用的是經濟地理嵌套矩陣,在穩健性檢驗中將選取地理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進行SDM 模型回歸。表7 結果表明,改變空間權重矩陣設置帶來的影響并不明顯,仍與上文基礎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的計量結果是穩健的。

表7 地理矩陣回歸結果分析
(二)樣本偏差
考慮到省會城市在城市規模、行政級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等方面和其他地級市存在顯著差異,為了降低這種非隨機性對估計結果的影響,在回歸中選擇剔除省會城市的樣本數據,以此驗證本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結果如表8 所示,由估計結果可得,在剔除濟南、鄭州、太原、西安、呼和浩特、銀川、蘭州、西寧八個省會城市的樣本數據后,僅有房地產投資系數符號發生變化和個別變量顯著性發生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本文的計量結果是穩健的。

表8 剔除省會城市回歸結果分析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黃河流域城市群2003—2019 年的面板數據,分別以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及山東半島、中原和關中平原三大城市群為樣本城市,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黃河流域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產業結構調整與城市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發現,第一,黃河流域城市群經濟增長存在空間相關性,在統計上是顯著的。第二,從黃河流域城市群整體來看,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能明顯促進黃河流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且高級化影響程度遠高于合理化;在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的雙重作用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明顯促進黃河流域城市群本地區經濟發展,但阻礙了鄰近城市GDP 的提升。第三,從三大城市群來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還受各城市群集聚水平影響:在產業結構調整影響下,中原城市群和關中平原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山東半島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太顯著。第四,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邊際經濟增長效應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負相關,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邊際經濟增長效應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正相關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當前黃河流域發展要充分發揮產業結構調整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經濟增長效應的帶動作用。現階段需要合理規劃和引導黃河流域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根據不同城市群的現實情況制定合適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規劃;要注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水平,建立與城市群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產業結構;同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相輔相成,大力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業;要強化固定資產投入和資金投入,優化發展環境,加快人才隊伍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