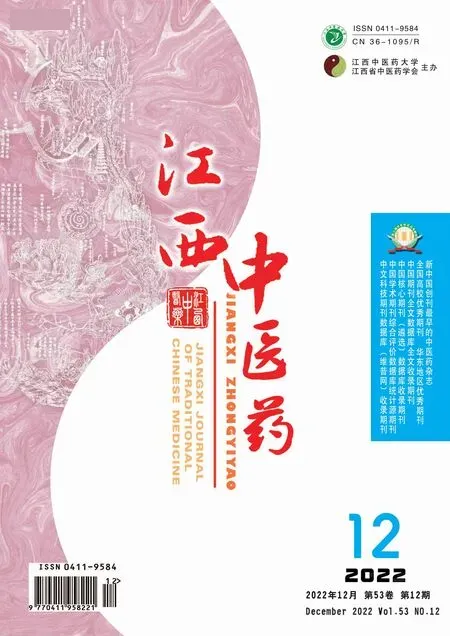傳統藥學中西交流史料研究綜述(下)
——史料整理研究中的史料
★ 邱玏(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北京 100700)
相關研究成果中運用的史料較為零星而分散,尚有一些專門的史料整理研究,相對比較集中,從中均能檢索到與傳統藥學中西交流相關的內容,按照整理研究的對象,可分為以下兩大類。
1 文獻類
是指史料整理研究的對象是以文字為主要技術手段記錄傳統藥學中西交流歷史的載體,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1 綜合類
即包含多種文獻類型的史料整理研究。重要的如張星烺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為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國與歐、亞、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國家和地區往來關系的史料摘錄[1]。包含中國典籍(正史、類書、地理志、筆記等)和外國史籍資料,加以注釋和考證,被榮新江譽為“迄今為止中外交流史領域最好的史料合集”。原出版于1930年,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朱杰勤整理的校訂本,對原書進行了一些增補、刪削與校正,2003年、2018年重印再版,是研究明末以前中西交流史重要的史料基礎。
1.2 史籍類
即歷史典籍。如陳邦賢《二十六史醫學史料匯編》輯錄了二十六史中記載的藥物原文,將藥物按照植物藥、動物藥、礦物藥和合成藥的類別分類,涉及藥物中西交流內容[2]。目前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已組織人員修訂完畢。
1.3 年鑒類
即按年度連續出版,匯集了上年度各行業或某一行業發展成就和事實的資料性工具書。中醫藥行業年鑒如《中國中醫藥年鑒》(1983—至今)、《中國藥學年鑒》(1982—至今),均包含傳統藥學中西交流的內容。
1.4 期刊報紙類
即期刊和報紙。如王吉民等《中國醫史外文文獻索引》收集了從1682—1965年,國內外書刊上用拉丁、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文字發表的與中國醫學史有關的文獻[3]。上海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中文醫史文獻索引(1792—1980)》、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第一輯(1903—1978)》《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第二輯(1979—1986)》收集整理了相應時間段內發表在雜志、報刊上的與醫學史相關的論文資料,均包含豐富的醫藥中西交流的內容[4-6]。段逸山主編《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匯編》,選編清末至1949年出版的重要中醫藥期刊47 種,分五輯影印出版[7-8]。以上均包含中藥中西交流的研究論文。
1.5 著作類
即著述或譯著。如王吉民等《中國醫學外文著述書目(1656—1962)》收集了從1656—1962年間國內外出版的有關中國醫學的外文著作目錄,包含藥學著作70 余部[9]。
1.6 地方志類
即記錄某一地區(行政區域)自然和社會情況的文獻,簡稱方志。1996—2002年,中國文化研究會在大規模文獻普查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中國本草全書》,其中包含843 本中國古代地方志記載的本草文獻[10]。萬芳等《方志與藥學史研究之芻議》即是在該項研究基礎上產生的研究論文,探討了歷代地方志保留的大量藥學史料中有關地方藥物貿易的內容,與外來藥物密切相關[11]。2010年,科技部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中醫藥古籍與方志的文獻整理”項目由7 省市地方高校相關研究機構承擔了方志中醫藥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并形成了相關研究成果。
1.7 筆記小說類
即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包含范圍非常廣泛,凡是不可歸類的各種隨筆記錄的雜識、札記、筆談等,皆可統稱為“筆記小說”。目前國內出版的筆記小說史料專著有《筆記小說大觀》(1912年版、1983年版和1986年版)、《歷代筆記小說集成》(1995—1996年)、《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套裝精裝本:1999—2007年,單行本:2012—2021年)、《全宋筆記》(2003—2020年)、《歷代史料筆記叢刊》(1957—至今)等。挖掘整理筆記小說中醫藥學內容的專著有陶御風等所著的《歷代筆記醫事別錄》《筆記雜著醫事別錄》,輯錄了傳世的歷代筆記中關于藥物的記載,并詳細注明出處,便于后學者進行檢索和考證[12-13]。鄢潔碩士研究論文《宋代筆記小說中的藥物文獻研究》系統總結了歷代筆記小說中的醫藥學資料、宋代75 部筆記小說中的藥物學資料[14]。以上都包含醫藥交流和外來藥物的內容。
1.8 本草類
即古代記載藥物的著作。歷代本草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本草中有關藥物貿易和外來藥物的記載繁多,重要的如《本草圖經》《外臺秘要》《海藥本草》《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拾遺》《本草補》等,相關研究論文如:彭華勝等《〈本草圖經〉中的外來藥物》、黃斌等《〈外臺秘要〉外來藥物的考察》、王家葵《域外方藥:〈海藥本草〉》、譚曉蕾等《〈本草綱目〉收錄外來藥物的整理研究》、肖雄《外來藥物在明清中國的記述與使用——以〈本草綱目拾遺〉為中心》、甄雪燕等《石振鐸〈本草補〉研究》等[15-20]。系統整理本草類文獻外來藥物的專著尚未出現。
1.9 檔案類
即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記錄。就傳統藥學中西交流領域而言,舊海關檔案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一手資料。近年整理出版的相關史料有《中國舊海關史料》(2001年)、《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2003—2007年)、《中國舊海關與近代社會圖史》(2006年)、《中國舊海關稀見文獻全編》(2009年)、《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2014—2016年)、《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2013年)、《海關總署檔案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出版物(1860—1949)》(2017—2018年,即將全部出版)、《浙江省檔案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內部出版物》(2020年)等。系統挖掘海關檔案中藥貿易資料的研究目前尚未出現。
清朝尤其是康乾雍三朝,傳教士來華,中西交流頻繁,有關清宮檔案中記載了中藥西傳的史實,以及西方傳統藥物的傳入和使用情況,比較重要的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1996年)、《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1984—1985年)、《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1993年)、《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1991年)、《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2009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折》(1982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2005年),故宮博物院《藥材、藥具庫藏檔案》等。近期中國中醫科學院與故宮博物院正式簽署合作協議,隨著合作深入,館藏的進一步開放,有望在整理上述資料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新史料。
1.10 網絡資料類
即記載互聯網信息的史料。重要的如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中國中醫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編的《中醫藥國際參考》(1996—至今)等,作為內部刊物的形式發行,2017年以后不再出紙質版,以數據庫的形式供檢索查閱。其資料主要來自中醫藥機構官媒以及新浪、搜狐、人民網和各種民間媒體等,對于當代中醫藥國際交流史料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 文物類
是指在傳統醫藥中西交流歷史過程中產生并遺留下來的,一般具有百年以上的實物性遺存。一般包括:遺跡、遺址、石刻、墓葬等古建筑物及相關物品,器具、藥物、包裝、廣告、工藝品等代表性實物,書簡、金石、古籍、書畫等古舊圖書文獻資料等。
中醫藥文物除保存在考古部門之外,各類型的中醫藥博物館是其主要保存和陳列的場所。傅維康《60年來的中國醫學史博物館》和和中浚《中醫高校博物館及中醫藥博物館建設的喜與憂》兩文指出:截至2010年,各地中醫院校、科研機構相繼設立的醫史博物館、陳列館或中醫藥博物館,加之各地中醫藥企業建立的中藥博物館、古代名醫所在地政府建立的名醫紀念館、各地中醫院建立的中醫博物館、民間中醫藥博物館以及少數民族醫學博物館等,經粗略計算,我國的中醫藥博物館已近50 家[21-22]。此外,經數屆兩會委員提案和眾多專家學者呼吁,國家中醫藥博物館的建設目前已拉開帷幕。
早期建成的一些醫史博物館,依托博物館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文物史料基礎,廖果《中國歷代醫藥衛生文物特點述要——以中國醫史博物館展陳為背景》指出:“中國醫藥文物自然包括了百余年來(以至更早時期)的中外醫學交流方面的文物”,如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博物館主編出版了我國第一本醫史文物圖集《中國古代醫史圖錄》《中國醫史博物館文物選粹》,并與上海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共同主編《中國醫學通史·文物圖譜卷》等[23-26]。近年隨著文物研究的拓展,更多的文物研究成果出現,如曹暉等主編的《“一帶一路”中醫藥文物圖譜集》,其中“中外交流篇”以當時交通與人文為背景,集中介紹了中外醫學交流的出彩文物,“海藥書影篇”將本草典籍中域外傳來藥物的彩繪圖之書影作了專題展示[27];2017年,由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承擔,依托國家出版基金資助,歷時5年調研了故宮博物院等國內外博物館100 余家及眾多私人收藏家的文物,出版了《中華醫藥衛生文物圖典(一)》,共拍攝文物圖片5 200 余幅,并按照名稱、朝代、形質、規格、醫學用途、館藏地等輔以中英文圖注介紹,是近年來文物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28]。以上均包含中藥中西交流的文物圖片。
另一種情況是國內收藏和展陳缺位,文物流失海外,據李經緯《加強醫藥衛生文物收藏保護迫在眉睫》一文指出:“我國散落國外的醫藥衛生文物,據估計數以千件計。”[29]以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物為例,2002年、2003年出版了首套由鄭金生主編的《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2005—2010年又陸續出版了由曹洪欣主編的《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珍版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叢書》(影印本)、《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續)》(點校本),2016年又出版了鄭金生主編的《海外中醫珍善本古籍叢刊》[30-35]。此外,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的30 余年間,曹暉對于《本草品匯精要》的版本及其流傳進行過系統的考察和整理研究,涉及流傳于德國柏林、意大利羅馬、法國巴黎等圖書館的各種版本。
3 思考和總結
3.1 關于史料的搜集
前人的研究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作用。若要完成一部好的歷史作品,無論我們秉持怎樣的史學理念,采取怎樣的史學研究方法,建立扎實的史料基礎是前提。而這“扎實”二字,可以借用黃龍祥《史料的構成分析與整體研究》一文中的一句話來概括:“要想對歷史問題的本來面目做出準確判斷,必須首先保證文獻的全與真;其次是史料的相互關系。沒有這兩個基礎,我們最后得出的結論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錯誤的。”[36]因此,史料種類越豐富,構架的史料鏈越趨精細復雜,我們在解讀還原歷史圖像的過程中,就越有可能從個體的樹木而見整體的森林,得出更為客觀、真實的歷史真相,從而為科學合理歷史觀的提出奠定基礎。以文物史料搜集為例,目前已有的文物史料基礎不僅豐富和促進了中國醫學史的研究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對外交流的窗口作用,實現了跨文化傳播的目的,但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說,遠遠不能滿足目前所需,從傳統藥學領域來說更顯捉襟見肘,多集中于中藥標本、企業歷史文化、傳統制藥方法等的陳列和展示,對外交流領域涉及少或者基本缺位,因此,系統搜集、補充傳統藥學中西交流的文物史料顯得尤為必要。而散落海外的文物回歸,也絕非一人之力短期之內可以完成,需綜合國家、政府、科研團隊的力量共同完成。
在史料搜集方法上,已有前輩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人類學與中醫藥研究相結合已不屬什么前沿問題,但仍是一種值得采用的重要的史料搜集方法。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常常出現官方統計數據、國內外相關報道與深入實地調查訪談所得史料差異甚大的情況,因此,“所得結論與事實不符,策略、建議當然適得其反”[37]。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意義正在于此,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親赴現場進行觀察、參與、訪談并獲取資料,探究傳統藥學在異域文化的他者視角中的真實身份、角色認同及其發展變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方數據的片面和失真,為解析交流過程中的文化融合、沖突等問題,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由此,產生了另一種需要搜集的新史料:口述史料。正如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中所說:“口述史方法最主要的優點:即它的彈性,也就是恰巧在需要證據的地方掌握證據的能力”[38],通過事先制訂詳細的訪談提綱,走訪國內外傳統藥學專家、親歷者、普通從業者,在互動交流的探討中,獲取第一手的訪談文本、音頻、視頻、照片、數據、實物等資料,對于史料的完整與補充,觀點的創新與激發,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口述史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由于年代久遠、訪談者記憶偏差、訪談資料出現錯誤,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訪談者的觀點呈現一定的差異,帶來史料的相對不穩定性等,由此引入以下史料整理的問題。
3.2 關于史料的整理
傳統史料學除了搜集史料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整理史料,整理目的有二:一是將初步搜集來的史料通過核對、鑒別、考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將史料進行初加工,確保史料的相對真實性;二是通過傳統目錄學的方法,將經過初加工的史料分門別類進行整理編次,撰寫提要、索引等,匯編成冊,為史料的檢索、查找和使用提供便利。以下重點對史料的真實性作一說明。
在史料整理過程中,第一手的歷史文本及作者本人的原始記錄等直接史料至關重要,傳抄、轉記的信息尤其要注意鑒別。對于存疑、矛盾的史料,也需要進行多重鑒別、考證,如案頭考察和田野調查、田野調查和官方數據以及案頭考察之間有出入,則應搜集更為豐富的旁證史料進行辨偽,多重證據法才能還原史料的真實面目,口述史料也應進行后期的廣泛核實,以確保史實的真實性。正如黃龍祥非常生動的比喻:“史料庫越大越全,其價值越高,但有效利用的難度也就越大。猶如一串串珍珠斷裂后沉入大海,要將其一顆顆打撈上來,再確定其原來所屬的珠鏈,并確定其在這一珠鏈中的正確位置(序列號),最后恢復其舊貌,其難度可想而知。”[36]史料的整理常常伴隨著非常繁瑣、細致、嚴苛的求證、研究過程,也唯有把這些工作做細做實,才談得上更好地治史。
文末用傅斯年先生的話來做總結:“必于舊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運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糾正舊史料。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39]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歷史思潮如何變幻,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仍是每一個治史工作者首先必立定的根基,以傳統藥學中西交流為專題內容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迄今為止尚屬拓荒階段,需要有志者同心協力,通力合作,共同開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