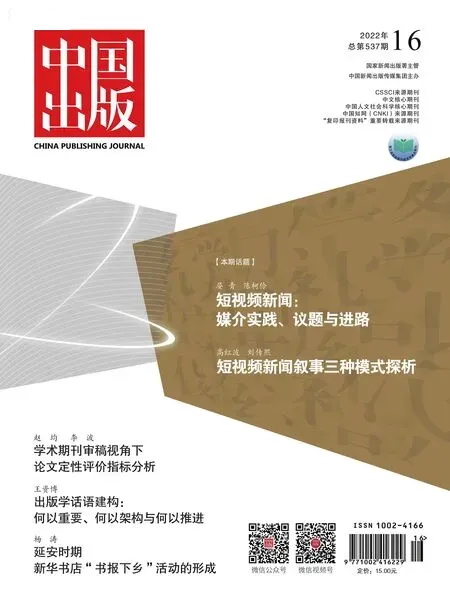共青團成立之初出版活動綜覽
□文│馬天祥
1922年5月,在黨的直接關懷和領導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成立了全國統一的組織。這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成立,[1]更標志著中國青年運動進入到了一個嶄新階段。而這個嶄新階段的發軔,則可以追溯至早期革命思想的傳播和地方性團組織的建立。
一、建團前后進步刊物的出版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廣大覺醒的愛國青年成為這場運動的先鋒,開辟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紀元。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青年中的進步力量率先覺醒,并直接以社會主義為理論導向成立自己的活動團體。
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率先成立。至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一大”時,全國“已有上海、北京、武昌、長沙、廣州、天津、南京、杭州、唐山、保定、塘沽、潮州、梧州、佛山、新會、肇慶、安慶等17個地方團組織,團員總數逾5000人”。[2]團組織的從無到有,團員人數的由少到多,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1949年4月,擔任過團工作主要負責人的任弼時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曾代表黨中央對建團工作給予充分肯定,他說1920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對建黨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作用”。[3]當然,這一切最終要歸功于黨的領導。組織上的準備作用,可以理解為全國各地廣泛建立起來的團組織,逐漸成為黨組織的后備軍和共產主義的預備學校;而思想上的準備,則可以理解為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在建團活動的號召下,依托既有和自創刊物,將馬克思主義等進步思想,廣泛地傳播到全國人民心中。
從五四運動到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再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召開,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中,縱然也夾雜有迷茫和彷徨,[4]但我們仍能從與建團活動息息相關的各類刊物的創辦和出版入手,真切體悟到一百年前那群熱血青年所保有的初心和肩負的使命。梁啟超先生在《傳播文明三利器》中,將學校、報紙、演說三者并列,[5]而在這三者中,學界公認“報章的功業最為顯而易見”。[6]足見當時報紙在引領新思潮、塑造國民意識方面的突出貢獻。
在這一時期,一大批進步青年主編的刊物陸續創刊發行: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1919年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天津創刊、1919年8月《平民周刊》在太原創刊、1919年10月10日《雙十》周刊在杭州創刊、[7]1920年1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在北京創刊、1920年8月15日《勞動界》在上海創刊、[8]1920年9月28日《勞報》在天津創刊、[9]1920年9月《青年之友》在保定創刊、[10]1920年10月20日《廣東群報》在廣州創刊、1920年11月7日《勞動音》在北京創刊、[11]1920年12月15日《勵新》在濟南創刊、1921年春《武漢星期評論》在武漢創刊、1921年5月1日《新江西》在南昌創刊、1922年1月15日《先驅》在北京創刊、[12]1922年2月26日《青年周刊》在廣州創刊、1922年8月1日《少年》在法國巴黎創刊、[13]1922年11月9日《唐山潮聲》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創辦,[14]以及1923年10月23日《中國青年》在上海創刊并發行至今。
這些刊物的創刊發行,對五四運動前《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宣傳新文化、傳播新思想形成了有益補充,還對當時京滬兩地《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晨報副刊》、《京報副刊》這“四大副刊”的內容起到了有效呼應。“四大副刊”在當時雖然也刊載過反對愚昧落后,提倡新思想、新觀念的內容,并及時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但其定位較偏重于“文藝佳作”,且所宣傳的革命理論也存在“駁雜不純”等問題。翻檢原始期刊文獻可以發現,《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為紀念“十月革命”,于1920年11月3日、7日、8日、9日四期連載羅素在湖南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同時在這四期還刊載有關教育、翻譯、時人評論、古代機械、游記感懷等文章;《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作為綜合性學術副刊在翻譯刊載馬克思《勞動與資本》的同時,亦大量刊載無政府主義、杜威實驗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杜里舒和柏格森唯心主義哲學及更為大量東西方經典文學作品;《晨報副刊》確有推出“勞動節紀念”專號、“俄國革命紀念”專號,[15]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這些舉措都使之成為《新青年》之外傳播馬克思主義、介紹“十月革命”的重要陣地,然而在介紹革命理論方面,《晨報副刊》同時宣傳社會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等學說,并且后期出版重心更加偏向于國內詩歌、小說乃至國外佳作的翻譯和出版。《京報副刊》作為綜合性刊物在稿件安排方面,通常會將時事評論與詩歌、小說、游記、感懷、科學簡訊等編輯在一起。綜上所述,這些綜合性的刊物或受制于其服務階級的“局限性”,或受限于其宣傳理論的“不徹底性”,往往將正確的聲音湮沒于吵雜與喧囂之中。要而言之,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有可能主張之極點”。[16]
因此,在黨的領導下,以宣傳革命思想為宗旨的新刊物的問世,在體例上和內容上打破傳統報刊的束縛,更好地服務正確革命理論的傳播和推動地方革命力量的會聚。在以上列舉的刊物中,有許多刊物已然成為當地進步青年追求真理的指路明燈,甚至直接發展成為當地團組織的機關刊物。如:《平民周刊》成為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先驅》成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遷往上海出版后,又成為團中央機關刊物;《青年周刊》成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少年》成為旅歐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成為團中央機關刊物。再一次印證了全新刊物的出版與各地進步青年組織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良性互動,從而為全國各地黨團組織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
二、推動廣大青年實現從進步思想到革命思想的跨越
從宏觀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為“分水嶺”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前,各地進步青年在五四運動偉大精神的感召下,秉承強烈的愛國情感和時代使命,紛紛自發地會聚起來,依托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就某一地區、某一行業、某一現狀、某一社會問題展開揭露和批判、示威和抗爭,“他們組織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以使運動組織化,以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店罷市為手段,展開了持續的長期的斗爭”,[17]如北京學生聯合會、天津學生聯合會、武漢學生聯合會等。然而隨著廣大青年批判和反思的深入,必然在客觀上會產生對前沿思想和先進理論的渴求,而這種渴求伴隨著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探查和對前沿思想與先進理論的逐步了解而變得愈發強烈。恰如周恩來同志提出“覺悟社”的宗旨,就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積極“灌輸世界新思潮”。[18]因此,五四運動以來至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前,各地進步青年形式多樣的“讀書會”“研習社”日趨發展壯大。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天津的“覺悟社”,湖南的“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利群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團體。當然,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青年團體所學習和探討的,尚屬進步思想范疇,其中難免夾雜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振興國家的迫切渴望與西學東漸的雙重影響,往往導致“無政府主義思想,連同清教主義、自我犧牲精神以及用公眾意愿和自愿協會中的烏托邦式信仰摧毀既存制度的主張”,[19]都在各主要城市對不少的青年團體造成了影響。
而作為歷史發展的主流,代表著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俄國,這些真真切切的事實都讓廣大青年不約而同地走上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正途”。恰恰是這種自發的、自覺的變化,實現了青年團體和刊物從宣傳進步思想到宣傳革命思想的深刻轉變。當時各地進步青年陸續建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這些全國各地青年自發組建的進步團體,都為不久以后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輸送了大批優秀骨干。
當然,這一時期由于北洋政府及地方軍閥勢力的封鎖,各地團體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了解渠道非常有限,大多依托地緣便利條件及相關行業優勢進行交流傳播。毛澤東在長沙發起建立“俄羅斯研究會”,研究會《簡章》第一條即“以研究關于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20],宣傳馬列主義及蘇俄建設成就,提倡留俄勤工儉學,并發行《俄羅斯叢刊》。周恩來在天津參與創建的“覺悟社”,“社員經常在一起談論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經過研究和比較,列寧的事業吸引住了他們。他們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21]邀請李大釗詳細介紹馬克思主義,并發行《覺悟》。武漢的“利群書社”,銷售各種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雜志,“出版內部刊物《我們的》和不定期刊物《互助》,是長江中游地區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也是武漢地區進步青年的對外聯絡點。該社不僅與《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有業務往來,還和北京、上海、長沙等進步社團保持密切聯系”。[22]除此之外,張國恩和董必武同志籌辦的武漢中學,還通過“利群書社”為廣大青年引進了大量進步刊物,“其中包括毛澤東同志主編的《湘江評論》,以及《共產黨宣言》《俄國新經濟政策》《共產主義ABC》《社會發展史》《新青年》等。這些進步書刊在武漢中學廣為流傳,從而為建立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23]保定的“文學研究會”,安志成和同學王錫疆等成員自發學習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為進一步傳播先進思想,“文學研究會”成立書報販賣部,“暗中出售《新青年》《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進步書刊和馬列著作。當時,不僅育德中學的學生們在這里買書,男二師、六中、河大、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也經常來這里買書,這個書報販賣部成為當時保定傳播新文化,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重要陣地”。[24]潮安“青年圖書社”,在潮州開元寺內開設新刊販賣部,銷售來自京、滬的《新青年》《新潮》《新生活》《新婦女》《少年中國》《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數十種書刊。此類情況在當時并不罕見,就像陽光總會穿透烏云,只要有進步青年團體活動的地方,就會有大量進步刊物突破重重封鎖傳播真理、播種希望。
三、黨的引領提升團組織宣傳出版水平
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后,更是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革命思想的傳播注入了強大動力。作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的地方青年團組織,其宗旨在于“實行社會改造,宣傳社會主義”,考查其后1922年5月“一大”通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奮斗目標,我們不難發現社會主義青年團所關注的,更側重于直面現實的不公和思考具體的社會改造。這種求實、務實的“側重”使進步青年在學習思想和理論的同時,更加渴望掌握社會改革實踐的成功經驗。而在當時國際、國內反動勢力的雙重封鎖下,關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建設的報道卻十分有限。《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致中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書》直言:“資本主義把俄國的勞農政府四面圍住,并且建立隔開各國無產階級的障壁。”[25]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恰恰就是要在這一點上取得突破。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所在地,即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漁陽里6號,既是“中俄通信社”社址,又是“外國語學社”校址。“外國語學社”實際上是中共發起組和俄共(布)代表團聯合創辦,意在輸送進步青年赴俄留學,為革命培養干部的基地。與此同時,“中俄通信社在此設立后,就組織外國語學社的青年學生,擔任該社的繕寫、油印、收發等工作。早期共產黨員邵力子時任《民國日報》經理及副刊《覺悟》的編輯,這樣中俄(華俄)通信社的大量通訊就能夠在該報的‘世界要聞’欄上發表”。[26]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外國語學社”始終以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公允的態度,及時地報道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范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俄通信社)其稿源大部分直接來自俄國赤塔、海參崴、莫斯科等地,也有少量消息轉譯于英、美、法等國報刊雜志”,[27]極大地開闊了國內進步青年的視野。僅就1920年7月—1921年7月一年間,中俄通信社發表的各類新聞稿件就有212篇。[28]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鑒于這些高質量通訊稿件飽含的思想價值和信息價值,該通信社稿件“不僅在《民國日報》上大量刊登,而且還被中國各地30多家報刊采用”。[29]
作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及后來團中央刊物的《先驅》,也在遷往上海后得到了更為長足的發展:于1922年第5期在刊載《萬國青年共產黨柏林會議之經過》《國際青年共產黨黨綱》關注國際青年共運時事的同時,亦刊載《今后中國的青年應當怎樣的運動?》《在國際青年共產革命運動之下,我們中國青年應有的覺悟》等深入思考的文章;1922年第7期在刊載《法蘭西工人運動的最近趨勢》的同時,亦刊載《中國勞動運動應取的方針》《告做勞動運動的人》等具有指導意義的文章,做到了真正意義上實時報道與輿論引領的合理兼顧。伴隨著基層團組織宣傳出版水平的日臻完善,這種“兼顧”逐漸成為了各團組織機關刊物的特色與專長。
四、結語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召開之后,全國性的社會青年團組織已然形成,先進的思想、正確的輿論、堅強的組織三者緊密結合在一起,團的宣傳出版工作更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始終為黨的偉大事業持續貢獻蓬勃的力量。回顧一百年前共青團成立之初的出版概況,重溫一百年前熱血青年的赤誠與執著、堅毅和守望,更能讓我們打破時空的隔閡,去體會他們保有的初心和肩負的使命,為新時代奮進在“兩個一百年”趕考之路上的共青團人,注入“中國力量”!
注釋:
[1]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名稱便由此而來。
[2]費迅.青春熱血五十年 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69
[3]鄭洸,主編.中國青年運動六十年[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70—71
[4]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文件》指出:“那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只不過帶有社會主義傾向,并沒有確定了哪一派社會主義。所以分子就很復雜: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有,工團主義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沖突。在這種狀態下面,團體規則和團體訓練,就不能實行。團體的精神,當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實在辦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暫時解散!”參見:共青團廣州市委員會、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編.中國共青團創建時期史料選編[M].內部資料,2015:105
[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M].北京:中華書局,1936:41
[6]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晴畫報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2018:1
[7]1919年11月1日,《雙十》周刊改名為《浙江新潮》。
[8]《袁同疇回憶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先后》載:“(上海)青年團成立之后,除《宣言》外,還出版刊物《勞動界》,為機關報,最初由我主編。《勞動界》除了宣傳主義,還調查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我們工讀互助團同學曾親至各工廠實際調查,并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故本文將《勞動界》歸為青年團所編之刊物。參見: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中心編.中共創建史研究(第3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7
[9]《勞報》出版二十天左右,遭到警察廳查禁,但第二天旋即改名《來報》繼續出版。《來報》即取英文“勞動”(labour)之音譯。《來報》發行20余天,又被北洋政府再次查封。其后,曾在馬千里的幫助下改名《津報》,繼續出版。參見:方漢奇、李矗主編.中國新聞學之最[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199
[10]寧樹藩.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461
[11]《勞動音》共計出版5期,隨后改名《仁聲》繼續出版,不久停刊。
[12]《先驅》從第四期起,前往上海出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歸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
[13]《少年》至1923年12月10日,共計出版13期。隨后,根據國內團中央指示,旅歐共青團將《少年》更名為《赤光》,并于1924年2月1日出版發行。
[14]西南交通大學校史編輯室.西南交通大學(唐山交通大學)校史(第一卷)[M].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116
[15]如《晨報副刊》1922年11月7日刊載的《俄國革命紀念:俄羅斯十月革命》《俄國革命紀念:教育比革命還要緊》《俄國革命紀念日雜感》等。
[16]黃仁宇.中國大歷史[M].北京:三聯出版社,1997:276
[17]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175
[18]宋一秀,楊梅葉.周恩來早期哲學思想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38
[19]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M].陳仲丹,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393
[20]康文龍,主編.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1917—1927(上)[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339
[21]魏宏運.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28
[22]谷安林,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組織機構辭典[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5
[23]鄭州鐵路局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共黨史大事記選編[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3:452
[24]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二)[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76
[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188
[26][28]陸米強.試述早期共產黨組織在上海開展的三則史料編輯出版工作[M]//喬萬敏,俞祖華,李永璞,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317,318
[27]陳紹康,朱少偉.我黨最早的通訊社[J].新聞記者,1984,4(20)
[29]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