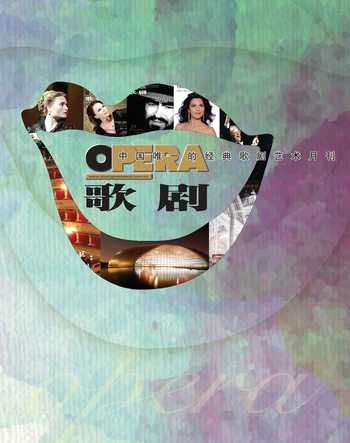莫扎特歌劇《伊多梅紐斯》觀后
邱克



OUTLINE / On October 1, critic Qiu Ke watched Mozarts opera Idomeneo in NewYork. Thi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opera productions presented by the MetropolitanOpera House during this performance season. Today, when the Russo-Ukrainianwar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the shadow of nuclear war has been worrying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evisiting this opera by Mozart is truly significant.
10月1日,我在紐約觀看了莫扎特24歲時創(chuàng)作的歌劇《伊多梅紐斯》(Idomeneo ),這是美國大都會歌劇院2022-2023歌劇季最早演出的劇目之一。本來紐約州在9 月7 日已經頒布了解除口罩令,但不久后紐約州疫情又開始反彈,美國疾病中心再度向紐約州部分地區(qū)提出戴口罩建議,以減緩新冠疫情卷土重來以及確診病例增加的趨勢。大都會歌劇院也積極響應,規(guī)定所有進入歌劇院的觀眾必須佩戴口罩,并向觀眾免費提供口罩。合唱隊的一個演員竟然戴著口罩上臺,之后在另外一個演員的提醒下尷尬地摘下了口罩。
《伊多梅紐斯》是莫扎特創(chuàng)作成熟階段的第一部正歌劇,代表了一種積蓄達五年之久的充沛渴望,是莫扎特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中結出的成果。據說,莫扎特喜歡這部歌劇勝過自己的所有其他作品。此劇的故事背景為希臘神話,在特洛伊戰(zhàn)爭中,伊多梅紐斯因遭遇海上風暴,全船沉沒,曾對海神發(fā)誓,只要海神保佑他能活下來,他愿意把第一個看到的人獻給海神。經漂流脫險后,第一個見到的竟是王子伊達曼特。由于他沒有辦法對自己的親生兒子下手,導致眾神傷害了他成千上萬的子民。而在克里特島上,作為俘虜的特洛伊公主伊麗亞與希臘公主艾萊特拉都在愛戀王子,這也讓伊多梅紐斯非常苦惱。后來伊麗亞愿替伊達曼特成為祭品,海神被感動,兩人幸福地結合。
莫扎特一直渴望創(chuàng)作自己的歌劇,但他的故鄉(xiāng)薩爾茨堡卻是歌劇的沙漠,他對薩爾茨堡大主教的不滿日益加深,跟父親利奧波德的矛盾也越來越厲害。幸虧在1780年,莫扎特遇到富有藝術天賦的巴伐利亞選帝侯卡爾· 西奧多,才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創(chuàng)作《伊多梅紐斯》的大好機會。1781年1月29日,《伊多梅紐斯》在慕尼黑首演,獲得巨大成功。莫扎特的藝術造詣被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從而轉變了人們對嚴肅的意大利音樂戲劇的認識,創(chuàng)作出了一部18 世紀歌劇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品。
《伊多梅紐斯》不僅使莫扎特的音樂才華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其樸素的人文主義思想也得到發(fā)揚,讓我們感受到莫扎特心靈深處善良、純真的一面。本來這個希臘神話屬于悲劇,表現出人類面對大自然和神靈的無奈和絕望,經過莫扎特的巧妙構思,把暴力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和家庭痛苦、人民對戰(zhàn)爭的憤怒以及對和平的渴望,都通過優(yōu)美的音樂進行表達。結尾則變成了以非暴力的形式推翻了武士君主,王子通過共識和包容得以解救,人神之間相互理解,民族之間相互和解,善良戰(zhàn)勝了邪惡,美好戰(zhàn)勝了黑暗,全劇以理性和愛的勝利而告終。在俄烏戰(zhàn)爭進入新階段、核戰(zhàn)爭的陰影一直讓各國人民憂心忡忡的今天,重新觀看莫扎特的這部歌劇,實在是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首次來大都會擔任指揮的弗雷德· 霍內克(Manfred Honeck)是莫扎特的同鄉(xiāng),這位奧地利指揮家是一位深諳維也納傳統(tǒng)的大師,目前是匹茲堡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jiān)。霍內克2018年被國際古典音樂獎評為年度藝術家。他早在2007年擔任德國斯圖加特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jiān)期間就指揮過《伊多梅紐斯》,因此這次指揮起來可謂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其明確和細致的手勢富有詩意,讓管弦樂團和舞臺演員都能在一種相互協調、輕響適當的狀態(tài)之中,并通過音樂的變換,精準表達角色的情感狀態(tài)和緊張的情節(jié)。大都會歌劇院合唱團的表現極佳,幾段主要的合唱曲都能打動觀眾的心, 特別是“ 平靜的海洋”(Placido è il mar)溫柔典雅抒情,各個聲部層次分明又極度融合,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難怪自從維多利亞時代以來這首合唱曲一直是合唱團的摯愛。
首先出場的是扮演伊麗亞公主的中國女高音方穎。她出生于寧波奉化,上海音樂學院畢業(yè)后到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深造,2009年榮獲中國音樂最高獎項金鐘獎,2015年獲得享譽世界的美國林肯中心西格爾音樂獎,是當今歌劇界最有潛力的當紅新銳女高音之一。她的聲音純凈豐富,開放而完美,被英國《金融時報》譽為“可以讓時間停止”,《紐約時報》也稱贊她是“清新、具感染力的女高音,演技嬌媚具有風韻”。在2018-2019樂季,方穎首次在薩爾茨堡演出莫扎特的《伊多梅紐斯》,取得圓滿成功,為大都會的這個樂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幕中“父親,兄弟們,永別了”(Padre,germane, addio)是伊麗亞獨自在房間哀嘆自己的命運的詠嘆調。“可悲的暴風雨幸存者,失去了父親和兄弟。”“為什么上帝會給我們安排如此悲慘的命運?”悲傷的嘆息和憤怒的吶喊滲透始終,這個落魄公主錯綜復雜的心理被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在第三幕著名的詠嘆調“溫柔的微風”(Zeffiretti lusinghieri) 當中, 她溫文爾雅, 敞開心扉與微風、花草和樹木交談,發(fā)現她對王子念念不忘,已經愛到無法自拔的地步。接下來的每一個樂句都散發(fā)著自信和溫暖,刻畫了伊麗亞多愁善感、自相矛盾的內心情感以及善良勇敢的音樂形象。方穎的表演樸實動人,婉轉悠揚的歌聲、無懈可擊的演唱技巧讓人陶醉,不時贏得觀眾的熱烈喝彩。
高貴的王子伊達曼特這一角色原本是為閹人歌手而寫的,但莫扎特在1786 年也改寫過男高音角色。1964年帕瓦羅蒂就在英國的格林德伯恩(Glyndebourne)歌劇節(jié)上扮演過伊達曼特。當時帕瓦羅蒂剛剛在歌劇界嶄露頭角,已經引起同行的關注,他們紛紛說:“一定要過來聽聽這個年輕的意大利人!他太不可思議了!他太不可思議了。”
但大都會歌劇院的演出中都是采用女中音版本的伊達曼特。最早的王子扮演者應該是1970 年起就在大都會演出的著名女中音弗雷德里卡· 馮· 斯塔德(Frederica von Stade),她也是迄今為止該角色最頻繁的表演者。另外瑞典女中音安· 索菲· 范歐塔(Anne-Sofie von Otter)在1991年和1994年以其獨特的神韻和風格演唱了這一角色。
“80后”的美國女中音凱特· 林賽(KateLindsey)畢業(yè)于大都會歌劇院的“ 林德曼青年藝術家發(fā)展計劃”,2007年曾獲林肯中心MartinE.Segal 獎并開始在大都會演出。這是她首次在大都會扮演伊達曼特王子。她嗓音圓潤細膩,色調豐富多彩,表情自然動人,既能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又能保持優(yōu)美的音色,充分體現了莫扎特音樂的優(yōu)雅和大方。她與伊麗亞公主的二重唱:“我將忠誠于你……你是否愿意做我的丈夫?”堪稱完美,兩種音色珠聯璧合,宛如天籟。
嫉妒的希臘公主艾萊特拉(Elettra)是一個悲劇人物,這一角色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令人生畏。大都會最初選了德國瓦格納女高音爾加德· 貝倫斯(Hildegard Behrens),她在1982年的演出引起轟動,并在1986 年重演。之后,美國的卡羅爾· 瓦內斯(Carol Vaness)是一位嗓音豐富的女高音,為這個角色帶來了更真實的莫扎特風格,后來在接下來的三個歌劇季里都是請她來出演這個角色。
這次大都會邀請了舞臺經驗豐富的“80后” 意大利女高音費德里卡· 隆巴迪(FedericaLombardi)扮演艾萊特拉,她的聲音穿透力強,戲劇表現力豐富,在第三幕一場充滿狂怒的瘋狂場景中失去了理智的表演十分成功。她那“哦,瘋狂!哦,暴怒!”(DOreste, dAjace)的詠嘆調充滿了哭泣、喘息和吶喊,將她的嫉妒和憤怒推向了高潮。她看到情敵投入她心上人的懷抱,嫉妒到發(fā)狂。由于絕望,她痛苦迷茫,極度沮喪,甚至產生了幻覺。這個被激情所奴役的被拋棄者,預示著夜女王的花腔狂暴和野性情緒。也有人說,也許艾萊特拉是潛伏的憤怒,等待在世紀末爆發(fā)革命。
國王近臣阿爾巴斯由意大利男高音保羅· 法納萊(Paolo Fanale)扮演,他細膩甜美的音色,賦予了該角色更加內斂和溫和的性格,雖然花腔聽起來有點不舒服,顆粒感不足,流暢性欠缺。
美國黑人男高音伊薩卡· 薩維奇(IssachahSavage)扮演了祭司。他的演出經歷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出演了威爾第最苛刻的兩個角色,分別是奧賽羅和《阿依達》中的拉達梅斯。2019年在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他也扮演過祭司這一角色。當他責備國王放棄他的職責時,嚴厲的斥責聲如洪鐘,增加了張力和懸念,提升了戲劇性。
很奇怪的是,雖然該歌劇的名字是《伊多梅紐斯》,但國王伊多梅紐斯卻是最后上場的。雖然如此,這仍是劇目中最具挑戰(zhàn)性的角色。海神拯救了伊多梅紐斯,他需要把他在岸上遇到的第一個人獻給海神,但這個受害者卻是他自己的親生兒子伊達曼特,所以他自始至終都在為此苦苦掙扎,并最終屈服于眾神的旨意。
扮演伊多梅紐斯的“70后”美國男高音邁克·斯拜厄(Michael Spyres)2020年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次亮相,出演了《浮士德的詛咒》。他自稱是男全音(Baritenor),近年出版的專輯名就是《男全音》。邁克· 斯拜厄可以從Low C 唱到High C,真假聲切換自如,曲目范圍也特別廣泛,從莫扎特、威爾第到多尼采蒂、羅西尼。有人稱他是歌劇界的魔術師,似乎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唱瓦格納《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的角色。對男高音來說,《伊多梅紐斯》雖然沒有太多的炫技部分,但難度之高也是到處可見的。
首先是大都會歌劇院1982 年首演時,第一個伊多梅紐斯的扮演者是帕瓦羅蒂,他為這個角色設置了一個標桿。帕瓦羅蒂選擇歌劇的時候非常小心謹慎,跟多明戈相比,他出演的歌劇數量非常有限,莫扎特的歌劇只有這一部。他回憶說:“我的日程表上有一部歌劇,雖然在我的音域范圍之內,對我卻是一個挑戰(zhàn),它使我感到緊張。因為這不是我熟悉的威爾第的那些熱情洋溢的歌劇,需要的是‘那么嚴肅,那么刻板,那么專注,一點都不有趣。” 所以他特別認真對待這一角色,對飽受折磨的父親的形象刻骨銘心,獲得廣泛的好評。英國著名評論家希拉里· 芬奇(HilaryFinch)說過:“無須多言,帕瓦羅蒂就是伊多梅紐斯。他非常投入的表演,表現出了國王偉大的心胸,他的憤怒在這一超越生命的情境中顯得恰到好處。”
除此之外,多明戈也兩次在大都會扮演過伊多梅紐斯(1994年和2000年),還出版過完整的專輯。所以觀眾先入為主,已經有一個明確的尺度。可惜邁克·斯拜厄還沒有達到兩位大師的境界和火候,跟2017年大都會扮演伊多梅紐斯的另一位“80后”美國男高音馬修· 波倫扎尼(Matthew Polenzani)相比,邁克·斯拜厄氣勢雄偉,勇武有余,細膩不足,輕巧性不夠,尤其缺少那種精致和內在的抒情音色。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他的那首詠嘆調“從海的遠方”(Fuor del mar),崇高而莊嚴,準確表達出主人公在努力調和父愛和宗教義務時所做的掙扎,可惜他的花腔不是很流暢,唯一一個高音也不是很理想。希望假以時日,他對莫扎特正歌劇的演唱可以逐漸成熟,不光具有高超的聲樂技巧,還能成為一個盡善盡美的歌唱家。
但總的來說,邁克· 斯拜厄的表演還是很到位的,能夠恰當地用他的肢體語言和聲音處理激烈的戲劇沖突,如憤怒、悲傷、痛苦和絕望。他與伊麗亞、伊多曼特和艾萊特拉的四重唱“我將迷失于汪洋之中盡嘗孤獨”(Andrò, ramingo e solo)概括了歌劇中四個主要角色被各自相互沖突的困境所撕裂的時刻,使全劇激情奔涌的音樂特征達到了頂點。這首曾經讓莫扎特自己難以自持、淚如泉涌的四重唱也感動到了在場的觀眾。令人聯想到威爾第在寫作《弄臣》第三幕中的四重唱“美麗的愛之女”(Bella figlia dellamore)時一定從莫扎特的這一作品中得到靈感和啟發(fā)。
“歌劇網”(OperaWire)的主編和共同創(chuàng)始人大衛(wèi)·薩拉查(David Salazar)說,盡管有一些不足,歌劇《伊多梅紐斯》瑕不掩瑜,演員陣容和管弦樂隊都是頂級的,應該是大都會本演出季的第二部必看作品。
最后, 我想起帕瓦羅蒂的一段回憶, 他在1961年開始唱歌劇的時候,有人對他說,抓緊時間演吧,歌劇快沒人看了。這次在新冠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2022 至2023年的演出季一共準備上演23部歌劇,其中7 部是全新制作。即使是《伊多梅紐斯》這樣的冷門劇作,也會上演6場(9月28日至10月20日),10月6日至20日還在大都會歌劇院電臺的SiriusXM 頻道355上進行現場直播,演出的音頻也于10月20日在大都會的網站(metopera.org)上進行了現場直播。2023年4月22日,該劇還將通過Toll Brothers-大都會歌劇院國際廣播網絡進行直播。這都說明歌劇迄今為止依然很受歡迎,歌劇《伊多梅紐斯》的未來應該仍然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