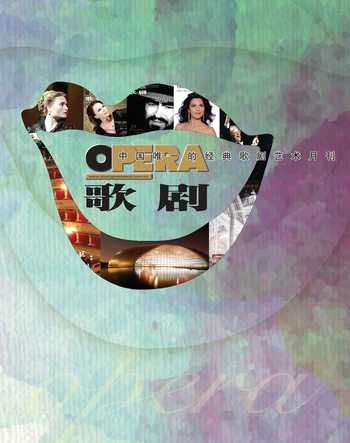自帶流量的“安娜”魅力何在?
游暐之



OUTLINE / Anna Karenina , amusical created by the MoscowOperetta Theatre, has toppedbox office records since it openedin 2016. The Chinese-languagev ersion of Anna Kareninapremiered at the Shanghai GrandTheater from October 15 to 23before launching a national tour.
中文版俄羅斯音樂劇《安娜· 卡列尼娜》,于2022年10月15日至23日,在上海大劇院完成國內首站的演出,隨即開啟其他城市的全國巡演。如果將“中文版”“俄羅斯音樂劇”“安娜·卡列尼娜”設定為三個關鍵詞,排在首位的,一定是“安娜·卡列尼娜”。145年前,列夫· 托爾斯泰發表長篇小說《安娜· 卡列尼娜》,自此,這部鴻篇巨制就成為音樂、戲劇、舞蹈、影視等藝術創作的寵兒。“安娜· 卡列尼娜”不僅是原作小說和相關文藝作品中最富有魅力和傳奇色彩的女性,也成為讀者和觀眾心目中最悅目、唏噓、嘆惋的女性。所以,任何文藝創作一旦選擇“安娜·卡列尼娜”這個題材,就已經自帶流量號召力了。
由莫斯科輕歌劇院創制的音樂劇《安娜· 卡列尼娜》,首演于2016年,一經推出就穩坐俄羅斯舞臺戲劇票房之首。由于創制這部音樂劇的是輕歌劇院,所以作品就不可避免帶有輕歌劇的氣質,載歌載舞,歌舞分家。劇中歌唱的部分,雖然演員也會根據戲劇情境的需要伴以相應的肢體表演,但并非舞蹈化的表現;而舞蹈的場面雖然都與戲劇情境緊密結合,但是舞蹈演員只舞不唱。這與我們今天熟知的絕大多數歐美音樂劇還是有差別的,比如《西區故事》《巴黎圣母院》《獅子王》等,在這些作品中,歌舞是一體的,也就說,參加演出的演員在能力上是需要唱、演、舞兼具,尤其是群演場面,演員們在歌唱的同時都需要完成一定技術難度的舞蹈表演。如此比較的話,《安娜· 卡列尼娜》的演繹形態確實更接近于輕歌劇或歐美早期的音樂劇。
當然,并不是說音樂劇就一定需要演員歌、舞、演兼具,藝術可以有宏觀的規范,但是并沒有統一的標準。無論是歌舞兼具還是歌舞分家,只要能夠很準確地完成創作者想要表達的戲劇主題和內容,那么演繹形式就不應成為束縛藝術表達的桎梏。俄羅斯音樂劇《安娜· 卡列尼娜》是有著突出俄式風貌的一部成功的音樂劇作品。這種俄式風貌除了選材的故事本身,更在于其音樂、舞臺、表演等是一個完全的整體。
所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千個人心中也會有一千個“安娜· 卡列尼娜”。作為莫斯科輕歌劇院,其在音樂劇中塑造什么樣的“安娜·卡列尼娜”,恐怕和當前觀眾期望看到的“安娜”需要保持一致。這也是目前該劇在戲劇素材的選擇和思想表達的方向上,選擇走充分尊重原著但是簡約表達之路的原因。列夫· 托爾斯泰被譽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和“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這樣一位有著深刻思想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是不會將《安娜·卡列尼娜》當作言情小說來創作的。事實上,安娜的愛情只是原著中的一部分,與安娜的人生選擇并列的還有列文的選擇,且作家用于列文的筆墨絲毫不遜于安娜,所以這部小說其實是雙主人公的一部作品。甚至從情感上來說,列文被托翁傾注得更多一些。因為列文這個人物,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作家本人生活理想的投射。所以,小說也是以列文收尾的。安娜的愛情,只不過是當時整個社會所處的選擇迷茫的背景性反映,而列文、渥倫斯基、卡列寧等,代表的恰恰是當時俄國社會充滿矛盾的不同階層。
這部音樂劇則模糊了原著所展示的處于變革前夕俄國的社會背景,聚焦于安娜的愛情和人生選擇。這對于僅有兩個多小時的音樂舞臺藝術而言,不僅是最經濟的選擇,也是最容易與觀眾的欣賞需求達成共識的。因為任何一部舞臺藝術作品,首先需要具備觀賞的功能。對于《安娜· 卡列尼娜》這個題材而言,觀眾買票走進劇場,最期待的就是要看音樂劇如何解讀安娜的愛情悲劇。當然,講述故事的方式很多,這部音樂劇采用的是象征寓意和如實陳述相結合的方式。列車在劇中不僅是現實當中的交通工具,同時也通過“列車長”反復強調的一句唱詞“人生是一趟無法回到起點的列車,不要輕易跳下軌道”,帶給人們富有哲思的警示。“列車長”的人設具有戲劇銜接和戲劇敘述的作用,而他每一次的警示,都是在戲劇情節發展到一個節點之際,讓觀眾對安娜的命運產生一種共情化的不安。雖然這是一個沒有懸念的戲劇故事,但是戲劇的緊張度依然會通過“列車長”反復的“嘮叨”而強化。“列車長”在劇中很容易讓人想到德語音樂劇《伊麗莎白》中的“死神”。不過,我個人以為,本劇中“列車長”就是一個警示人生命運的預言家,他和《伊麗莎白》中的“死神”不同,他并沒有和安娜發生直接戲劇交集,只是作為旁觀者,在一旁默默觀察安娜等人物的所作所為。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列車長”亦可看成是觀眾的舞臺形象代言。
本劇從戲劇結構、戲劇脈絡、戲劇素材等方面是完全尊重原著的,敘述簡潔,情節清晰,原著當中的幾個核心人物,安娜、渥倫斯基、列文、卡列寧、吉蒂等均有戲份。當然戲份最重的還是安娜。從渥倫斯基、列文和吉蒂之間的三角戀情,到安娜、渥倫斯基、卡列寧之間的婚外戀情、婚姻矛盾的糾葛,每一個情節都取自原著。雖然沒有清楚交代事件具體發生的時間,不過依然能從人物情感的種種變化、舞臺美術場景季節的改變,感受到主人公安娜在這段感情磨難中所經歷的時間流逝。
音樂劇《安娜·卡列尼娜》的音樂創作非常精彩,突出的優點在于,它找到了俄式音樂劇的音樂戲劇表達方式,有很強的俄式民族音樂的辨識度。在前期主辦方的宣傳片段中,這種感受還不算明顯,但是當坐在劇場,完整聆聽全劇的時候,那種從始至終的俄式音樂記憶,會一次次強烈沖擊著人們的視聽感官。并且,這種記憶又與傳統古典風格的俄國音樂戲劇有著截然的不同,它是將俄國民間、傳統、古典音樂的素材,賦以充滿節奏感、旋律性、戲劇性、時代性的表達,帶給觀眾極具俄式風貌的當代時尚體驗。現場小型弦樂隊的演奏,也讓舞臺整體呈現更富有靈動感。
舞蹈段落是這部音樂劇充分展現俄式風貌的最重要元素。首先是舞蹈的編排與劇情結合得嚴絲合縫,火車頭舞、車輪舞、代表溜冰場的輪滑舞、收割舞、社交舞會舞等等,這些舞蹈既構成展示戲劇的背景,同時與燈光、音效、多媒體結合之后,也成為獨特的戲劇語言。俄羅斯本就是歌舞大國,舞蹈的歷史積淀深厚無比,本劇中,所有舞蹈段落都是一種綜合編排之后的合理運用,古典芭蕾、現代芭蕾、俄羅斯民間舞、現代街舞等等,一切素材都為了戲劇的終極表現而存在,也因此,會令觀眾產生一種自然而然的國別和民族的代入感。
本劇舞美設計是非常地道的音樂劇舞美,硬件極簡,效果卻極豐富,非常適合巡演需求。朋克風的鋼架,可以通過移動進行多種變化組合,鋼架上裝有可供投影的冰屏,以滿足所有戲劇情境的舞美需要。冰屏的畫面效果細致,無論是體現俄式建筑內外景,還是體現俄羅斯鄉村的自然風光,都相當逼真。舞臺居中的橋式鋼架,兩邊的階梯,中間的橋洞,又將舞臺的立體空間進行了上下左右合理的劃分,便于表現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戲劇情節。橋式平臺下的橋洞是專屬于火車進出的,每當列車進站,在音效和聲效雙重的刺激中,觀眾的戲劇感受會格外震撼。以現代技術營造的舞臺美術,處處體現出一種歷史感的俄羅斯的古典美,絲毫不會讓人產生違和感。
本次演出節目單上,主創團隊分為俄方和中方兩組,俄方除了編劇尤利· 金、作曲羅曼· 伊格納季耶夫,還有導演阿麗娜· 切維克,編舞伊琳娜· 科爾涅耶娃,音樂總監康斯坦丁· 赫瓦特涅茨,舞美、服裝設計維亞切斯拉夫· 奧庫涅夫,燈光設計格列勃· 費里施金斯基,化妝造型設計安德烈· 德雷金等,中方主創團隊有中文劇本譯配劉文飛,導演雷悅,音樂總監趙繼昀,舞蹈編導俞辰曦,聲樂指導李偌祎,執行音樂總監萬相墨等。俄方主創悉數署名,一是版權的要求,二是在中文版的制作過程中,俄方原班主創特別是導演阿麗娜· 切維克,一直通過線上親自指導這次中文版的排演工作。所以,中文版《安娜· 卡列尼娜》,除了演唱、臺詞是中文,演員是中國演員,其他方面的呈現均是俄原版的直接翻版,可謂是最大程度保持著俄版的“原汁原味”。
中文版《安娜· 卡列尼娜》上海站10月16日下午場演出,卡司為徐麗東(安娜)、洪之光(渥倫斯基)、王藝清(卡列寧),李明嶼(列文)、米晨晨(吉蒂)、郭亢(列車長)、熊郁菲(帕蒂)等。中文版演繹,最大的困難在于,演員要做到讓在座的每一位觀眾,看到、聽到的是“俄羅斯”音樂劇。也就是說,要讓觀眾認同這些講著中文的“俄羅斯人”。其實,中文演繹外國作品,無論是當年配音版的電影、電視,還是中文版的莎士比亞戲劇,以及近年來頻頻出現的中文版歌劇、音樂劇等,這種模式并不稀奇。但是在很多演繹中,觀眾還是會出戲,會有這是“演出來的人物”而非“就是這個人物”的感覺。在我看的這一場中,個人覺得演員的選擇和定位都還是準確的。
主角安娜的飾演者徐麗東雖然身材嬌小,但是能力不錯,聲音具有穿透力,表演也很投入富有激情。米晨晨飾演的吉蒂,形象與人物很接近,端莊、高挑,聲音和演唱也很好。卡列寧和列文的飾演者王藝清、李明嶼,二位演員外形和造型都很接近,開始的時候因為不熟悉,甚至有些分不清。隨著劇情的發展,且兩個角色聲部不同,劇中也基本沒有戲劇交集,所以還不至于混淆。雖然兩位演員的歌唱和表演都不錯,但個人覺得在造型上還是要有明顯的區分,并且卡列寧的形象還需要更蒼老一些。盡管本劇中對于人物的復雜性做了最簡化的處理,但是原著當中,安娜與卡列寧正是因為年齡和思想上的不對等,才導致了安娜的愛情悲劇。音樂劇中,即使不體現這個事件背景,也還是需要通過化妝造型來暗示出安娜婚姻的不平等。熊郁菲飾演的帕蒂,雖然只在劇中的戲中戲里出現了一小段,但是她的演唱贏得了場內觀眾非常熱烈的掌聲。除卻上海主場的因素(熊郁菲是上海歌劇院的女高音歌唱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她明亮、靈巧、輕盈的花腔,不僅契合劇情的表現需要,同時也讓觀眾在音樂劇當中欣賞到了純正的美聲演繹,也算是這部劇送給觀眾的額外禮物了。
說到歌劇演員,就不得不提渥倫斯基的飾演者洪之光。他也是在這部劇中,聲音、形象和表演方面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位演員。在第一場戲中,渥倫斯基一出場,直感便讓我認定這個演員選對了。洪之光個頭高挑,容貌清俊,鼻梁挺直,濃濃的劍眉之下略顯凹陷的雙目,深褐色的卷發,略帶憂郁和玩世不恭的氣質,與渥倫斯基的形象很是契合。而當他亮嗓之后,才發現這位演員不僅形象立得住,唱功也了得。他的音色圓潤,音域很寬,低音部穩重厚實,高音部自如嘹亮。渥倫斯基在劇中是第二主角,他的戲基本上要與安娜發生交集,無論是獨唱還是重唱、對唱,洪之光完成得都很有質量。在冰場舞蹈一段,洪之光穿著輪滑和群演一起冰舞的場景,也體現了這位演員唱、演、舞俱備的綜合能力。
之后了解到,洪之光是東方演藝集團首位海外引進人才,美國杰出歌劇人才獲得者,以全額獎學金從耶魯大學歌劇表演專業博士畢業。洪之光曾參演《卡門》《費加羅的婚禮》《法爾斯塔夫》《弄臣》《仲夏夜之夢》《賈尼· 斯基基》《郵差》《堂吉訶德》《萊斯之旅》《波希米亞人》《托斯卡》《馬可· 波羅》《錢學森》等30多部中外歌劇作品,是有著深厚舞臺實踐經驗的青年藝術家。此番從歌劇轉戰音樂劇,洪之光在方方面面都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為了形象上與人物更加吻合,洪之光特意瘦身6公斤。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洪之光以自己的實力和專業素養,成功完成了這次難度很高的跨界挑戰。
截至發稿之時,中文版音樂劇《安娜·卡列尼娜》還在國內其他城市熱演當中。中文版的國外音樂劇制作,對于當前疫情阻礙的國際文化交流來說,不失為一種彌補。當然,即使沒有疫情的影響,中文版的國外音樂劇(或其他藝術形式)的制作,也是值得提倡和推廣支持的,因為這不僅是給中國觀眾有及時了解國外最新舞臺藝術創作的機會,同時對于國內同行業從業者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實踐鍛煉的機會;另外,中文版的演繹,對于中國演員而言,會更直接深刻地理解作品所要表達的內容,從而在舞臺上展現出更真摯的情感,這也是中文版演繹國外作品最突出的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