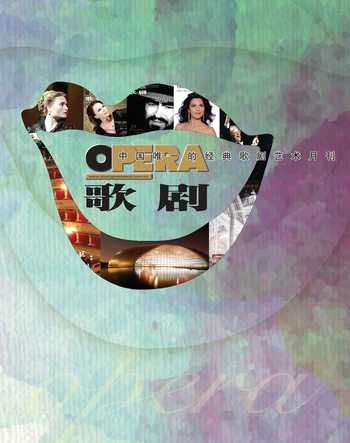普契尼歌劇詠嘆調“星光燦爛”音樂結構巧思
魏揚



三幕歌劇《托斯卡》劇本由意大利兩位劇作家路易基· 伊利卡、裘塞佩· 賈科薩根據法國劇作家維克多里恩· 薩爾杜的同名五幕悲劇改編,戲劇時間為1800 年6 月,地點為羅馬,意大利作曲家賈科莫· 普契尼作曲,1900 年在羅馬首演,是真實主義歌劇的代表作。伊利卡擅長多變的結構和對人物細節的描述,賈科薩擅長劇詩韻OUTLINE / The aria E lucevan le stelle in Puccinis Tosca containsundulating and dramatic melodies reflecting the composers keen,exquisite and delicate approach to opera and drama.文,普契尼赴羅馬對劇本細節實地考察,拜訪原作者薩爾杜,花了約三年的時間創作完成。第三幕中詠嘆調“星光燦爛”旋律跌宕起伏,戲劇性強,其中有兩個人物:具有進步思想的畫家馬里奧· 卡瓦拉多西(男高音)和監獄看守(男低音)。很多人覺得它特別美但卻太短不過癮,這其實是誤解。從音樂結構上看:普契尼將樂隊和男高音作為一個整體,設置了一個三部曲式(見表1),總時長約十分鐘,是一個完整的音樂結構,只不過大部分歌唱旋律由樂隊演奏,只有再現部第二段完全由男高音演唱。從戲劇結構上看:深夜將盡黎明之前,教堂鐘聲響起,弗洛麗亞· 托斯卡乘馬車焦急地趕往圣· 安杰洛城堡營救愛人(前奏);卡瓦拉多西被行刑隊帶上(呈示部);他臨死之前為了留一封信給托斯卡,將戒指送給看守(中部);他望著漫天星光燦爛,寫下訣別信(再現部),唱起詠嘆調:“星光閃耀,大地散發芬芳,園門吱吱響,漫步沙徑上,她來了,遍體生香,擁入我懷中。甜蜜的親吻,多情的纏綿,我顫抖著掀開面紗,露出嬌美的容顏。但愛情夢幻消失,時光已逝,我將在絕望中死去!我從未如此熱愛生命,熱愛生命!”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戲劇結構。“星光燦爛”從音樂和戲劇兩方面體現出普契尼敏銳、精巧和細膩的歌劇思維,是它成為傳世名曲的基礎。歌劇表演者和“粉絲”們要充分領悟,不能斷章取義,要在保證音樂結構和戲劇結構的完整性基礎上,才能真正理解、表現和欣賞之。
一、“星光燦爛”音樂結構中的三部曲式
從歌劇中聲樂與器樂的關系來看,瓦格納將聲樂作為他交響“樂劇”的主要聲部,有聲樂聲部器樂化的傾向,而普契尼則與之相反,是將器樂作為歌唱旋律的重要角色,有器樂聲部聲樂化的傾向,但他們二位無疑是將聲樂與器樂結合得最為緊密的歌劇作曲家,將器樂深刻地、有機地、真正地融入戲劇之中。“星光燦爛”第三幕開場的牧童之歌結束后,教堂鐘聲鱗次響起,是詠嘆調“星光燦爛”的前奏開始,幽靜的田園氛圍和緊張的戲劇矛盾恰成鮮明對比。曲式圖示見表1。
表1 中,三部曲式包含前奏、呈示部、中部、再現部和尾聲共五個部分,呈示部為三句樂段,三句同頭為平行句法,第二句運用模進擴充樂句,第三句向下屬方向轉調推動小高潮。中部為展開性中部,包含兩個樂段,復樂段結構。再現部增強性再現,包含兩個樂段,為重復樂段,男高音的主要唱段在最后一個樂段。
二、主題材料在結構中的彰顯與雪藏
呈示部的主要主題材料有四個:1. 拱形對稱材料;2. 斜折向樂匯;3. 斜向級進材料;4. 分解和弦材料。位于主題頭部最具辨識度的核心材料是拱形對稱材料,其次是第二句模進中使用的分解和弦材料(見譜例1)。而位于主題句中間部分的斜折向樂匯和斜向級進材料則被廣泛使用在前奏、中部第一段和第二段中(見譜例2)。
(一)主題段變化重復中的層層遞進
主題段為三句樂段,平行句法,三句的句頭相同,是變化重復關系。第一句簡潔地呈示主要主題材料,第二句句中旋律移高八度,運用模進手法擴充樂句長度,第三句轉調到達高潮后立刻轉回原調。三句的關系與“鳳頭、豬肚、豹尾”的文章結構相一致。
(二)雪藏的核心主題材料
拱形對稱材料按半音數計算音程向位為“+7+1+2+2-2-2-1-7”,前后精確對稱。分解和弦材料的音程向位是“-3-3”,為減三和弦分解(見譜例1)。
拱形對稱材料只出現在主題段三個樂句的句頭,分解和弦材料則固定使用在主題段第二句中部,全曲一共三個A 段,拱形對稱材料在9 個a 句的句頭使用9 次,分解和弦材料在三個a1 句的句中使用三次,而其他結構位置則完全沒有使用,被雪藏起來,這種有的放矢的益處是加強主題的辨識度,增強呈示、展開與再現的三部性結構感。
(三)主題材料的彰顯
斜折向樂匯是一個完整的樂匯, 音程向位為“+2+1-7”。斜向級進材料的音程向位是“+2+2+2+1+2+2+1+2”,為音階級進式的進行。在全曲各結構位置的使用情況見譜例2。
譜例2 中,呈示部主題段的斜折向樂匯和斜向級進材料被廣泛使用在前奏、中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中,但每一次都有變化,變長、變短、加花、逆行等。加強了全曲的材料一致性,也使全曲籠罩在有如爬升后墜落的斜折向宿命之中。
三、調性布局中的戲劇性力量
“星光燦爛”調性布局為“e-F-B-E-B-e-g-e-D-Aa-A-a- B-D-A-e-D-b-d-b-d-b”,其中前奏為“e-F- B-E- B-e”,呈示部為“e-g-e”,中部為“e-D-A-a-A-a- B-D-A-e-D-b”,再現部為“b-d-b-d-b”,以同主音關系轉調為主。例如呈示部e 小調的關系大調G 大調的同主音小調是g小調,再現部b 小調的關系大調D大調的同主音小調是b小調,而中部“A-a-A-a”轉調是直接的同主音轉調。調性布局見圖1。
圖1中,前奏從教堂的早禱鐘聲開始,遠處、近處、不同音高、不同調性的鐘聲逐漸交織在一起,普契尼為了寫這場戲曾專門赴羅馬圣· 安杰洛城堡聆聽鐘聲效果。“星光燦爛”中突出強調向下屬方向的轉調,呈示部和再現部都是向下屬方向的同主音關系轉調,而非主題段艷麗的轉調托起主題段的小調“平臺”。“普契尼明顯受到‘寫實主義風格的影響,把這陰暗悲沉的劇情,透過清楚逼真卻又無比優美的旋律,淋漓盡致地讓劇中人處于政治與愛情的凄慘命運下,著實賺人熱淚。”①調性布局則預設了陰暗悲沉的基調。
余論
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詠嘆”不須多。從表1 中可見,“星光燦爛”前景音色中的弦樂齊奏(濃)、單簧管獨奏(淡)、小提琴組高音區(明)、男低音獨唱(暗)等如同濃綠萬枝,襯托著男高音獨唱的一點紅,如果將這濃綠萬枝都砍掉,只剩下最后一段的男高音獨唱,顯然不符合普契尼的音樂構思和戲劇構思。
斜折向樂匯是普契尼詠嘆調中使用得最多的主題樂匯之一,例如:歌劇《波希米亞人》中詠嘆調“冰涼的小手”“人們叫我咪咪”“啊!可愛的姑娘”“舊大衣”“大家都走了么?”;歌劇《曼儂· 萊斯科》中詠嘆調“我從來沒見過”“褐發、金發姑娘當中”;歌劇《圖蘭朵》中詠嘆調“柳兒,你別悲傷”;歌劇《賈尼· 斯基基》中詠嘆調“我親愛的爸爸”;歌劇《西部女郎》中詠嘆調“米妮,我從家鄉來”;歌劇《蝴蝶夫人》中詠嘆調“美國人在世界流浪”等。所以,斜折向樂匯被梁升輝稱為“普契尼的旋律密碼之一”②,這項新的研究成果似乎揭開了普契尼動人旋律神秘面紗的一角。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尖銳評判普契尼的評論如今已難得一見,如:“從佛羅倫薩和曼圖阿的文藝復興晚期人文主義到20世紀50年代完全不同的新古典主義。不言而喻,與維持歌劇繁榮興旺的大量‘礦渣相比,真正‘純鋼的數量其實很少……理查德· 施特勞斯和賈科莫· 普契尼,今天,他們的作品被貯藏在保留劇目中,幾乎帶有某種懷舊意味。對于某些歌劇院而言,這些作品幾乎成了暢銷商品的同義語。其實那都是些二流貨色……《托斯卡》這部蹩腳、低劣的作品,在當今一般層次的觀眾中無疑最受推崇。”③這段話顯現了一個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理論家形象,他對于觀眾癡迷的情感體驗,對于歌唱家發自心底的摯愛采取完全無視的態度,從自己主觀設定的“作為戲劇的歌劇”角度妄加評論,這位科爾曼有可能是一位戲劇理論家,而絕非歌劇理論家。
“在威爾第身后,面對著他矗立在歌劇歷史進程上的豐碑——《納布科》《弄臣》《茶花女》《唐卡洛斯》《阿依達》《奧賽羅》……新進的歌劇作家們若不獨辟蹊徑是很難有大作為的。賈科莫· 普契尼居然能在基本無改于威爾第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路子的前提下,以其感人肺腑的戲劇情節和優美清新、結構縝密的音樂,成為威爾第之后意大利最有影響的歌劇作曲家。” 筆者認為,普契尼最突出的貢獻在于直入人心、充滿真摯情感、充滿愛的旋律,并讓這些最美的旋律通過有效的組織手段在最恰當的位置綻放,讓本已入戲太深的觀眾熱淚盈眶,情緒和情感得到充分釋放。至于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歌劇作曲家,歌劇迷、歌唱家、樂隊的樂手和指揮等愛歌劇的人,才是最有發言權的評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