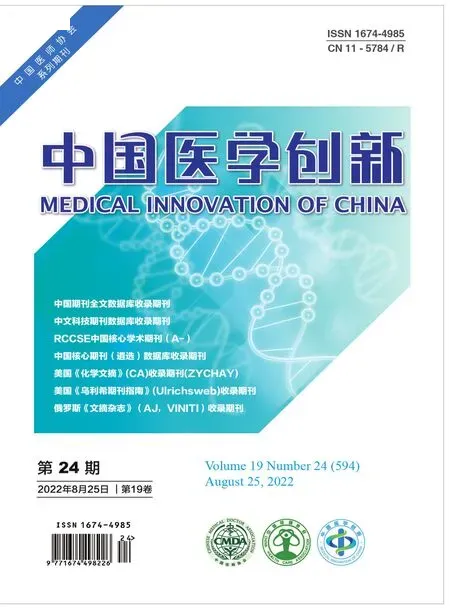臟層胸膜侵犯在非小細胞肺癌中診斷與預后的研究進展*
李炫呈 黃云超 趙光強 孫卓琛 所元東 李首卓 寧雄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2020 年發布的全球癌癥統計報告中指出,2020 年中國肺癌發病人數達82 萬例,死亡人數達71 萬例,均位列我國惡性腫瘤首位[1]。臟層胸膜侵犯(VPI)是影響非小細胞肺癌(NSCLC)預后的重要不良因素之一[2-3]。VPI 的準確診斷與預測,對于治療方式的選擇及預后評估尤為重要。
1 臟層胸膜解剖及對腫瘤分級分期的影響
覆蓋在肺表面的胸膜是臟層胸膜,臟層胸膜與肺實質緊密結合不可分離,并且彎折入肺裂內,形成不可分離的整體。在之前的解剖生理中認為在彈性纖維染色的幫助下,制片質量較高的切片可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到胸膜的5 層結構[4]。有研究表明,這5 層結構中包括顯色明顯的外彈力層及寬度不均的內彈力層,且內外彈力層存在相互融合的情況[5]。因此兩層存在的融合情況使得通常可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到4 層組織學結構,即:(1)位于基底膜上的單層間皮細胞,稱為間皮層;(2)間皮下結締組織層;(3)根據內、外彈力層的融合或分隔,可表現為一層或者兩層結構的彈力纖維層;(4)將肺實質和彈力纖維層分隔,厚度不均的結締組織層[6]。
VPI 定義為腫瘤突破到臟層胸膜彈性纖維層及以外組織,無論其是否暴露于胸膜表面。由于彈力層的結構存在變異,此處的彈力層概指內彈力層、外彈力層及兩者間的組織[7]。2009 年國際肺癌研究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IASLC)第7 版肺癌TNM 分期中提出了改進的Hammar 分級標準,將肺癌胸膜侵犯分為四類:PL0 為腫瘤未突破臟層胸膜或侵入臟層胸膜表面但未超過臟層胸膜的彈力纖維層;PL1 指腫瘤突破臟層胸膜彈力纖維層但未達到胸膜表面;PL2 指腫瘤超過臟層胸膜彈力纖維層且侵犯胸膜表面;PL3 指腫瘤侵犯壁層胸膜及其相鄰結構,PL1 和PL2 被歸為VPI 陽性組,而PL0 被歸為VPI 陰性組[5,8]。2017 年發布的第8 版TNM 分期中指出,VPI 的判定依據腫瘤是否累及彈性纖維層,主要適用于病理分期。因而以此標準診斷VPI 時,應將內彈力層、外彈力層及兩者間的組織視為一體。這一定義及分級基本沿用了第7 版TNM 分期的內容,研究重點轉向到腫瘤大小細分對分期及預后的影響。第8 版肺癌TNM 分期標準明確指出:早期NSCLC 侵犯臟層胸膜時,不論結節是否≤3 cm,T 分期都應從T1提升至T2a。這也使得TNM 分期應從ⅠA 期(T1N0M0)提升至ⅠB 期(T2aN0M0)[9]。因VPI 產生的升期對于臨床治療方案的選擇是存在顯著影響的,最新版的2020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非小細胞肺癌指南中提到,不建議對ⅠA 期非小細胞肺癌進行輔助化療,而ⅠB 期非小細胞肺癌(包括有高危因素的肺癌),臨床上需要根據個體情況選擇術后的后續治療[10]。
2 彈力纖維染色在VPI診斷中的作用
彈力纖維層是臟層胸膜中受到最多關注的解剖結構,1988 年國際上提出肺癌胸膜侵犯分級的同時,也為腫瘤突破臟層胸膜彈力纖維層即是腫瘤侵犯臟層胸膜這一觀點提供了依據。Liang 等[11]一項1 055 例的病例研究也證實了彈力纖維染色在測定VPI 方面效果顯著,因此彈力纖維染色應該被推薦作為評估VPI 的標準方法。目前VPI 的評估以病理學診斷為主,彈力纖維是肺支氣管及肺泡的支撐結構,具有維持正常肺泡解剖學結構和生理學功能的作用。當肺部出現病變,如惡性腫瘤時,彈力纖維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病變,如增生、斷裂等[12]。常規HE 染色下,病理醫師通過判斷彈力纖維組織結構的變化情況及腫瘤細胞與彈力纖維層之間的位置關系,可以明確肺癌是否發生胸膜侵犯。但在實際操作中病灶中細胞成分的差異及彈力纖維不可預測的變化會使得這種判斷存在誤差風險。因此在HE 染色下難以評估的情況下,彈力纖維染色的應用可以較為有效地觀察到腫瘤細胞是否侵犯或者突破彈力纖維層。這種染色方法也受到了IASLC 第8 版肺癌TNM分期的推薦。目前常用的彈力纖維染色法主要包括以下幾種:Weigert 間苯二酚-品紅法、Schmorl 彈力纖維染色法、Gomori 醛復紅染色法、Verhoeff-VanGieson 彈力纖維染色法、維多利亞藍彈力纖維染色法等[13]。彈力纖維染色可以將彈力纖維染成藍綠色,但難以明確腫瘤是否侵犯或突破彈力纖維層。角蛋白免疫組化染色可以顯示可疑的腫瘤細胞,但無法指明其與彈力纖維層之間的位置關系。近年來,角蛋白免疫組化聯合彈力纖維染色的雙重染色方法得到了關注。孔潔等[14]使用免疫組化角蛋白聯合彈力纖維雙重染色的方法,使上皮細胞和彈力纖維同時染色,明確顯示腫瘤與臟層胸膜彈力纖維層之間的位置關系。王敏等[13]的研究表明,使用雙重染色識別陽性率更高,同時可以判斷更早期的胸膜侵犯。Wang 等[15]通過比較細胞角蛋白AE1/AE3 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聯合維多利亞藍,GAF 或Weigert 的間苯二酚-紫紅色(WRF)的雙重染色方法,發現維多利亞藍和全細胞角蛋白免疫染色準確度最高。他們建議在VPI 難以評估時聯合使用維多利亞藍和全細胞角蛋白免疫染色。丁聞潔等[16]提出了彈力纖維染色聯合雙重免疫組化染色方式診斷胸膜侵犯的方法并在臨床獲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臨床上染色方法的選擇并無定論,更多取決于實驗室的標準及操作者的臨床習慣和經驗,期待雙重染色的廣泛應用能夠推進染色方法標準化的進程。
3 VPI對NSCLC預后的影響
隨著彈力纖維染色的應用及TNM 分期的不斷完善,目前已有多項研究證明VPI 是NSCLC 預后的危險因素[17-18]。Jiang 等[2]進行的一項涉及27 000 例淋巴結陰性患者的meta 分析,通過腫瘤大小分組,對伴或不伴VPI 的患者進行了為期5年的生存數據分析,證明了VPI 降低了相關患者的總生存期。Adachi等[18]回顧性分析了2005-2007 年在橫濱胸外科聯盟附屬九家醫院接受完全切除術的639 例NSCLC 患者的臨床病理學特征和結局,證實了VPI 的存在即會導致患者預后惡化這一結論。Manac’h 等[17]對1984-1996 年1 281 例接受根治性肺癌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預后分析,證明了胸膜侵犯是患者預后不良的重要因素,并且側面印證了脫落腫瘤細胞經縱隔淋巴通路進入胸膜淋巴管引流這一假說。除以上研究以外,Shimizu 等[19]、Shin等[20]、Maeda 等[21]也持相同的看法。
目前VPI 的研究多聚焦在VPI 與腫瘤大小的關系、胸膜侵犯分級、淋巴結轉移對預后的影響這幾方面上。第8 版TNM 分期系統將腫瘤按照大小進行T 分期,VPI 對預后的影響也多以此為組別進行分析。腫瘤≤3 cm 的研究中,Kawase 等[22]回顧性分析了日本肺癌聯合委員會登記的4 995 例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和預后,得到結論如下:伴有VPI 的T1a的預后明顯差于無VPI 的T1a,但有VPI 的T1b與無VPI 的T2a、有VPI 的T1b與無VPI 的T2b的生存率無顯著差異。即有VPI 的T1b與無VPI 的T2a/T2b預后相似。有VPI 的T1a的預后明顯差于無VPI的T1a,但有VPI 的T1a與無VPI 的T1b、有VPI 的T1a與無VPI 的T2a的生存率無顯著差異。有VPI 的T1a預后與無VPI 的T1b/T2a相似。這也側面呼應了第7 版TNM 分期中伴有VPI 的T1期腫瘤升期的改動。Luo 等[23]進行的一項基于3 項隨機臨床試驗和9 項回顧性研究的meta 分析指出,腫瘤組織較小的患者,通過病理學檢查辨別是否存在胸膜轉移尤為關鍵。陳天羽等[24]認為在腫瘤最大徑≤3 cm 的肺腺癌中,VPI 與患者預后影響存在顯著的聯系。然而,Tian 等[25]認為腫瘤≤2 cm 的病例預后不受VPI的影響,但在腫瘤為2~3 cm 的淋巴結陰性的完全切除術的患者中,VPI 確為不良預后因素。Nitadori等[26]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觀點。Huang 等[27]的一項關于Ⅰ期非小細胞肺癌內臟胸膜侵襲預后意義的meta 分析提示,VPI 是Ⅰ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一個與大小相互獨立的不良預后因素。Chen 等[28]、Heidinger 等[29]也支持這一觀點。總之,目前多數研究確定VPI 即為影響非小細胞肺癌預后的重要不良因素,但在腫瘤大小對于預后的影響上趨于細化,這仍需相關研究和設計進一步證實。
在3~5 cm 的腫瘤分析中,Kawase 等[22]研究顯示,有VPI 的T2a預后明顯差于無VPI 的T2a。有VPI 的T2a和無VPI 的T2b之間的生存率無顯著差異。T2a合并VPI 的預后明顯優于T3。綜上所述,有VPI的T2a與無VPI 的T2b預后相似,提示有VPI 的T2a應升級為T2b。Qi 等[30]的一項基于SEER 數據庫的4 005 例3.1~5.0 cm 的pT2N0M0期的NSCLC 患者數據的回顧性分析指出,VPI 陽性的pT2aN0M0期NSCLC 患者與VPI 陰性的pT2bN0M0期NSCLC 患者相比,總生存率無顯著差異,且VPI 與年齡、性別、分化等級和腫瘤大小明顯相關。Jiang 等[2]進行的meta 分析顯示,伴有VPI 的腫瘤≤3 cm 的患者5 年生存期明顯優于腫瘤大小為3~5 cm 伴有VPI 的患者,但與腫瘤大小為3~5 cm 不伴有VPI 的患者生存期無明顯差異。然而Yanagawa 等[31]的一項433 例Ⅰ期非小細胞肺癌術后患者預后的回顧性分析表明,在多因素分析中VPI 并不是獨立的預后危險因素。Tian等[25]的研究證實腫瘤大小為3~5 cm 或5~7 cm 的病例的預后不受VPI 的顯著影響。Yang 等[32]一項基于SEER 數據庫9 901 例接受肺部切除術患者數據的傾向評分匹配研究表明,伴有VPI 的腫瘤1~3 cm的患者存活率顯著降低,而在腫瘤≤1 cm、3~5 cm的組別里無明顯差異。Adachi 等[18]的研究也顯示了腫瘤大小超過3 cm 的患者,VPI 存在與否,對生存率沒有顯著影響。
在5~7 cm 的腫瘤分析中,多數研究認為此大小規模的腫瘤伴有VPI 時,應提升其T 分期。Shim等[33]、Yoshida 等[34]認為T2b期的腫瘤若確認VPI存在,則分期應提升至T3。David 等[35]進行了一項基于1 166 例pN0M0期行肺葉切除術的NSCLC 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研究表示VPI 與腫瘤直徑超過5 cm的患者預后呈負相關。同時也有部分研究存在不同的意見。Kawase 等[22]的研究就顯示VPI 陽性的T2a和VPI 陰性的T2b之間,VPI 陽性的T2b和VPI 陰性的T2b之間無顯著的生存差異。Tian 等[25]的研究支持5~7 cm 的病例的預后不受VPI 影響這一觀點。
于此之外,一部分專注于VPI 的程度對于預后影響的研究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論。一方面研究結果認為VPI 與生存率顯著降低相關,但PL1 和PL2 之間無生存差異。Shimizu 等[36]在一項超過1 600 例患者的分析中發現PL1 和PL2 之間生存率無顯著差異。Kawase 等[37]還報道了一項在2 700 多例使用彈性染色評估VPI 的患者隊列研究中,PL1和PL2 之間無生存差異。Adachi 等[18]在一項包含639 例患者的研究中發現VPI 的具體程度對術后生存沒有影響。Wo 等[38]的研究結果也支持這一觀點。換言之,VPI 是否存在對術后生存的影響遠遠大于VPI 侵犯深度對術后生存的影響。相比之下,Hung等[39]認為PL2 是淋巴結陰性NSCLC 中生存率較差和頻繁復發的觀測指標。Wang 等[15]進行的一項meta 分析也證實了PL1 患者的生存率優于PL2 患者。陳天羽等[24]認為在腫瘤最大徑≤3 cm 的肺腺癌中,VPI 與預后不良顯著相關,但只有PL2 是患者PFS 的獨立預測因素。Liang 等[11]近期進行的一項基于1 055 例患者的研究表明,只考慮淋巴結陰性病例時,PL1 組的生存率明顯優于PL2 組。
在以上研究方向之外,VPI 與非小細胞肺癌病理學類型及腫瘤分子特征是否存在聯系也受到了一定的關注。Le 等[40]認為EGFR 信號通路可能通過其下游效應基因miR-135b 促進VPI 的發展。Lin等[41]在172 例腫瘤不超過2 cm 的患者臨床資料中觀察到EGFR 突變與VPI 之間無明顯關聯。Shi等[42]從508 例手術切除的Ⅰ~Ⅲ期NSCLC 患者中采集臨床病理特征和隨訪信息,分析發現EGFR突變與NSCLC 的VPI 發展顯著相關。Heidinger等[29]2019 年進行的一項286 例和切除胸膜表面直接接觸的腺癌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發現,實性結節中VPI 的發生頻率明顯高于亞實性結節,這也側面印證了組織學上關于表現為實性結節的肺腺癌較亞實性結節肺腺癌更具侵襲性這一事實。Zhang 等[43]研究發現伴有VPI 的肺癌較不伴VPI 的分化更差,Lakha 等[44]發現與無VPI 的患者相比,患有VPI的患者更有可能出現腺癌。Deng 等[45]在一項包括403 例腫瘤大小≤3 cm 的NSCLC 手術患者的臨床和病理特征的回顧性分析中證明,VPI 陽性組中腺癌的比例往往高于VPI 陰性組,病理類型與早期NSCLC 中的VPI 顯著相關,伴有VPI 的非小細胞肺癌比不伴有VPI 的NSCLC 更容易發生淋巴結轉移。
目前關于VPI 與組織學類型、腫瘤侵襲性、分子特征、淋巴結轉移等之間的聯系影響的研究并未受到廣泛關注,這些研究方向的深入應該可以成為下一步了解研究VPI 的關鍵點。目前的研究主要建立于病理學上對于VPI 的診斷,雖然目前彈力纖維染色已成為診斷VPI 的主要染色方法,但是并未有權威的執行標準及共識性的染色方法選擇的確定,這可能會引起診斷的誤差及對研究結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