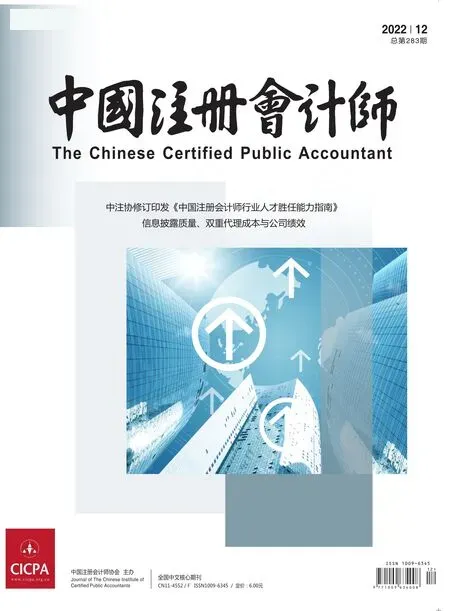對賭協(xié)議形成反向股份回購涉及企業(yè)所得稅問題探討
| 楊煥貴 杜虹林
對賭協(xié)議作為一種保護投資者利益的重要估值調整機制,在上市公司的投資收購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國目前缺乏因對賭交易收到業(yè)績補償后,進行企業(yè)所得稅處理的明文規(guī)定,導致產生了不同處理方式,使得各地時常發(fā)生稅企爭議,多繳稅、重復繳稅的情況時常發(fā)生。因此在現(xiàn)有稅收政策不明確的情況下,如何公正、合理地處理這類所得稅值得探討。為此,本文以A上市公司對賭交易為例,嘗試分析收購方因對賭形成反向股份回購的業(yè)績補償涉及企業(yè)所得稅的問題,并給出相應的處理建議。
一、研究背景與案例介紹
對賭條款是股權投資活動中的一種重要的估值調整機制,是收購方和被收購企業(yè)的大股東或管理層在初始投資時,鑒于對目標企業(yè)未來價值判斷的不確定,設計的一個基于未來目標企業(yè)價值變動,對目標企業(yè)實際擁有的價值或收益做出相應調整的機制。依據(jù)或有對價支付的時間,對賭協(xié)議分為正向對賭和反向對賭,其中反向對賭是指交易雙方先達成一個總價款,當目標公司未能實現(xiàn)對賭目標時,由被收購企業(yè)股東向收購方支付一定的業(yè)績補償。業(yè)績補償可分為現(xiàn)金補償和股份回購補償(收到回購股份需進行注銷)。正因為有業(yè)績補償機制的存在,使得對賭協(xié)議成為一種保護投資企業(yè)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投資與被投資市場主體間缺乏因對賭補償而產生的企業(yè)所得稅處理的明文規(guī)定,導致各地處理不一、執(zhí)行各異,稅企爭議凸顯,嚴重增加了企業(yè)的運營負擔,也使對賭協(xié)議無法完全發(fā)揮應有的效果。以下以A上市公司收購B公司為例,分析因對賭協(xié)議進行反向股份回購確認的業(yè)績補償對企業(yè)所得稅的影響。
2017年11月,A上市公司通過向B公司原28名股東發(fā)行股份及支付現(xiàn)金的方式收購B公司100%股權,此次交易以基于未來收益法對B公司的評估價約269999.92萬元成交。B公司的原股東魯某、游某、霍某、周某及RR中心作為第一順位補償義務人,NN投資、MM投資作為第二順位補償義務人,共同承擔B公司2017—2019年的業(yè)績承諾。若B公司無法完成承諾業(yè)績,以上7名補償義務人應就承諾期間累計實際利潤和累計承諾利潤的業(yè)績差額部分進行補償,且補償義務人應當就當期補償股份數(shù)已分配的現(xiàn)金股利作相應返還。交易情況如圖1所示。

圖1 A上市公司收購B公司交易流程圖
根據(jù)A上市公司與補償義務人簽訂的“補償協(xié)議”,B公司2017—2019年的業(yè)績承諾數(shù)約76608.00萬元,2017-2019年的業(yè)績實現(xiàn)數(shù)約46306.96萬元,因未完成業(yè)績承諾,觸發(fā)業(yè)績承諾人補償義務。A公司以人民幣1.00元總價回購7名補償義務人應補償?shù)募s2700.23萬股股份并予以注銷。
如表1所示,A上市公司產生了52208.92萬元的業(yè)績補償,被稅務機關要求征收7831.34萬企業(yè)所得稅(A上市公司為高新技術企業(yè)且符合減稅條件,企業(yè)所得稅適用15%稅率)。此結果產生了較大的涉稅處理分歧:企業(yè)認為該業(yè)績補償為回購本公司股份并注銷,不屬于企業(yè)所得稅應稅收入,無需繳納企業(yè)所得稅;稅務機關認為企業(yè)所得稅相關法律條文中無對賭協(xié)議產生的“營業(yè)外收入”免征企業(yè)所得稅的規(guī)定,故該筆“營業(yè)外收入”應征收企業(yè)所得稅。

表1 A上市公司的會計處理
下文通過對A上市公司因對賭協(xié)議進行反向股份回購形成的業(yè)績補償對企業(yè)所得稅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說明股份回購的業(yè)績補償不屬于當期應稅收入,當期無需就此事項繳納企業(yè)所得稅。
二、收到業(yè)績補償?shù)臅嬇c稅務處理
(一)收購方收到業(yè)績補償?shù)臅嬏幚?/h3>
按照企業(yè)合并或有對價會計處理的相關規(guī)定,如果在購買日后12個月內出現(xiàn)對購買日已存在情況的新的或者進一步證據(jù)而需要調整或有對價的,應當予以確認并對計入合并商譽的金額進行調整。但在實際對賭交易中,業(yè)績考察期通常超過3年,且在我國準則的適用下,對賭交易業(yè)績補償不是以購買日已存在的情況為基礎發(fā)生的,所以會計上不應對購買日初始投資成本進行調整,而應作為或有對價后續(xù)計量的變動。
1.收到現(xiàn)金補償。收購方收到現(xiàn)金補償?shù)臅嬏幚砟壳爸饕腥N方式:
(1)認為收到補償?shù)脑蚴窃谑召忞A段高估了標的資產,所以對初始交易價格做出調整,應在收到業(yè)績補償時沖減長期股權投資的原始成本,即貸“長期股權投資”。
(2)認為現(xiàn)金補償是企業(yè)非日常經營活動中發(fā)生的對賭勝利的利得,應在收到時計入“營業(yè)外收入”。
(3)認為現(xiàn)金補償是對企業(yè)購買虛高標的資產的補償,應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即貸“資本公積”。
本案例中收到的業(yè)績補償為股份回購,不涉及此會計處理。
2.股份回購并注銷。收購方回購定向發(fā)行股份并注銷,上市公司目前有兩種處理方式:
(1)上市公司在回購上述股份時,借記交易性金融資產,貸記營業(yè)外收入或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注銷時,借記股本和資本公積,貸記交易性金融資產,即將對賭收回原定向增發(fā)股份記入“營業(yè)外收入”或“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此為A上市公司的會計處理方式。
(2)市公司在回購上述股份時借記交易性金融資產,貸記資本公積;注銷時,借記股本和資本公積,貸記交易性金融資產,即將對賭收回原定向增發(fā)股份記入“資本公積”過渡,注銷時再將其沖銷。
(二)收購方收到業(yè)績補償?shù)亩悇仗幚?/h3>
1.分別稅務處理。在實際征管過程中,稅務機關多采用分別稅務處理,將初始股權收購與后期收到業(yè)績補償作為兩項獨立交易,即業(yè)績補償按照非公益性捐贈業(yè)務處理,捐贈方不得在稅前扣除,受贈方確認應稅收入。
2.合并稅務處理。借鑒部分地區(qū)的先進實踐及專家學者觀點,認為對賭交易的實質是對初始交易價格的調整,應將初始交易與對賭交易合并處理,追溯調整初始交易中被收購企業(yè)原股東的收益和收購方取得長期股權投資的計稅基礎,轉讓方按最終股權交易價格,對此項對賭交易業(yè)務涉及的企業(yè)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進行清繳,多退少補。
三、案例分析
1.A上市公司回購B公司股票并注銷,企業(yè)凈資產未增加,不屬于當期稅源事項。從會計核算角度分析,如不考慮計提的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A上市公司2019年收到補償義務人歸還的股份時,交易性金融資產和營業(yè)外收入同時增加,2020年核準注銷收到的股份時,沖銷交易性金融資產,同時沖減資本公積。此兩筆會計分錄對企業(yè)財務報表的最終影響是資本公積減少,未分配利潤增加,屬于所有者權益內部的變動,最終企業(yè)的凈資產并未增加。企業(yè)既無經濟利益流入,也就無須繳納企業(yè)所得稅。如考慮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本案例中資產減值損失119949.92萬,遠大于確認的營業(yè)外收入52208.92萬,導致企業(yè)凈資產大額減少,更不涉及繳納企業(yè)所得稅。
企業(yè)收購交易涉及金額往往巨大,如因該筆實質上無經濟利益流入的營業(yè)外收入繳納企業(yè)所得稅,很可能造成企業(yè)經營現(xiàn)金流斷裂,對企業(yè)正常生產經營造成極其不利影響。
2.因業(yè)績補償確認“營業(yè)外收入”應屬稅會差異,會計處理確認資產減值損失與營業(yè)外收入,而稅收并不認可減值準備則不應確認補償收入為應稅收入。根據(jù)企業(yè)所得稅法精神,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yè)財務、會計處理辦法與稅法規(guī)定不一致的,應按照企業(yè)所得稅法規(guī)定計算。企業(yè)所得稅法規(guī)定不明確的,在沒有明確規(guī)定之前,暫按企業(yè)財務、會計規(guī)定計算。A上市公司按照《企業(yè)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和《企業(yè)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的規(guī)定,在對業(yè)績補償款確認“營業(yè)外收入”的同時確認了對B公司長期股權投資的資產減值損失。企業(yè)財務報表確認營業(yè)外收入的同時資產損失增加,當期會計利潤是準確的。
而從企業(yè)所得稅納稅調整來看,長期股權投資的減值損失不能在企業(yè)所得稅前扣除,需做納稅調增,但對該業(yè)績補償確認的營業(yè)外收入是否繳納企業(yè)所得稅沒有明確規(guī)定,如僅僅依據(jù)會計核算確認的“營業(yè)外收入”就判定需要繳納企業(yè)所得稅(這是目前許多稅務機關的征收口徑和觀點),那么企業(yè)所得稅則不符合配比原則。按此邏輯推論,如企業(yè)回購股份時會計核算計入資本公積,而非“營業(yè)外收入”,那么是否就無須繳納企業(yè)所得稅了呢?筆者認為,不能僅依據(jù)某一會計核算科目的列支來判斷是否屬于“應稅收入”,而應把握業(yè)務實質。
此外,如果將A公司以1元收回本公司的2700萬股股票按公允價計入應稅收入,則回購股票的計稅基礎就是該公允價值,那么在該項資產消失(股票注銷)時,就應允許按其計稅基礎作資產損失扣除,如此也才能符合配比原則。但目前的企業(yè)所得稅法涉及的資產損失稅前扣除并未對此進行規(guī)定,這就導致稅務機關根本就不認可企業(yè)將此損失稅前扣除。
3.該項稅會差異屬時間性差異,該業(yè)績補償款涉及的稅收應遞延至股權處置時繳納。A上市公司應將回購原定增發(fā)股票的業(yè)績補償約52114.41萬元調整長期股權投資初始成本,即A上市公司持有B公司100%的股權計稅基礎變?yōu)?17885.51萬元。待A上市公司將來實際轉讓B公司股權時可扣除的長期股權投資成本為調減后的金額即217885.51萬元而非原始成本269999.92萬元,按照股權轉讓價款與股權計稅基礎之間的差額確認股權轉讓所得交納企業(yè)所得稅。因此該業(yè)績補償款的稅收遞延在股權處置時繳納,僅為時間性差異,并未造成稅款流失。
4.發(fā)行股份購買資產與收到業(yè)績補償實為一筆交易事項,稅收上應把握業(yè)務實質,調整長期股權投資的計稅基礎。《關于確認企業(yè)所得稅收入若干問題》(國稅函〔2008〕875號)規(guī)定,確認企業(yè)銷售收入應當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即如果形式上課稅要件未滿足,而實質上已經滿足,則課稅要件應視為已經滿足。反之如果形式上課稅要件已經滿足,但實質上并未滿足,則應視為課稅要件不滿足。“形式上不符合課稅要件但實質上滿足課稅要件”是為了解決避稅問題,“形式上符合課稅要件但實質上不滿足課稅要件”則為了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若采用分別稅務處理方式,被收購方股東需要就初始交易價格全額納稅,在支付業(yè)績補償后無法稅前抵扣或申請退稅,而收購方又需要就收到的業(yè)績補償全額繳納所得稅,這勢必造成重復征稅和多征稅問題。
對賭協(xié)議產生的最初目的就是調整企業(yè)估值,是對股權交易暫估價格的最終結算。根據(j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35條,采用基于未來收益預期方法對上市公司擬購買資產進行評估定價的,交易相對方應當與上市公司就相關資產實際盈利數(shù)低于利潤預測數(shù)的情況簽訂明確可行的業(yè)績補償協(xié)議。由于補償協(xié)議規(guī)定的或有價款是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但與最初的購買資產行為具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因此不能將或有補償款單獨進行稅務處理,即對賭協(xié)議雙方不能將收到的或支付的補償款視作利得或虧損,而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調整最初交易對價,從而調整轉讓方交易收益和所得,并調整投資方的投資計稅基礎。
5.各地的稅收案例有益實踐。根據(jù)《海南省地方稅務局關于對賭協(xié)議利潤補償企業(yè)所得稅相關問題的復函》(瓊地稅函[2014]198號),海南省地方稅務局對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賭協(xié)議收到的業(yè)績補償視為對最初受讓股權的定價調整,即收到利潤補償當年調整相應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根據(jù)南京全信傳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報告,其在2018年末確認了股份補償對應的營業(yè)外收入以及交易性金融資產,同時確認了遞延所得稅負債,在2018年此筆營業(yè)外收入并未進行納稅處理。2019年6月,其完成對賠償股份的回購注銷,并與當?shù)囟悇詹块T進一步溝通,當?shù)囟悇詹块T明確該筆收入不計入2019年度企業(yè)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應沖減長期股權投資計稅成本,并將2018年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負債進行了沖回。根據(jù)廣東銀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披露的《關于收到興科電子科技原股東部分業(yè)績補償款的公告》可知:興科電子原股東(三位自然人股東)依據(jù)相關協(xié)議向銀禧科技進行了業(yè)績補償,并由銀禧科技就業(yè)績補償事項向東莞市稅務局辦理了個人所得稅退稅申請。根據(jù)《稅務文書送達公告(李菊蓮稅務處理決定書)》,廣州稅務稽查局認定邦富軟件原自然人股東李菊蓮在華聞集團對邦富軟件的股權收購中,未就轉讓邦富軟件股權的事項足額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應補繳相應稅款。在計算應補繳稅款的過程中,廣州稅務稽查局減除了原自然人股東李菊蓮因邦富軟件未完成業(yè)績承諾而補償華聞集團股票對應的金額。
四、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為了完善稅制,維護國家和納稅人的合法利益,本文從稅制的公平性原則出發(fā),提出以下建議:
1.國家稅務總局要根據(jù)經濟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出現(xiàn)的稅收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作出反映。完善和細化對賭補償相關稅收政策,確保政策統(tǒng)一、執(zhí)行一致,避免各地執(zhí)行不一、處理各異的問題。對企業(yè)因反向對賭收到的現(xiàn)金補償及股份回購,視為對最初受讓股權的定價調整,在收到業(yè)績補償?shù)漠斈暾{整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2.為避免重復納稅,同時防治稅款流失,建議對包含業(yè)績補償?shù)墓蓹噢D讓協(xié)議按照先預繳后清算的方法。轉讓方在收到股權轉讓款時先就暫定的股權轉讓款預繳企業(yè)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后續(xù)收到或支付業(yè)績補償時再進行個人所得稅或企業(yè)所得稅的清繳。此時清繳不產生滯納金和罰款。
3.在反向對賭協(xié)議相關稅收政策明確之前,建議采用正向對賭交易模式,即收購方先向轉讓方預付部分交易對價,當目標公司完成對賭目標時,收購方再向轉讓方追加交易對價,同時以履約保證金的方式將后續(xù)可能會追加的交易對價預先支付給轉讓方或交由第三方進行共管或公證存款。如目標公司未完成業(yè)績承諾,轉讓方將履約保證金或共管資金返還給收購方。這樣既避免了稅收爭議又滿足了新型交易模式的需求。當然,這是假定以現(xiàn)金或非股票資產收購為主的交易方式,若本案例是以股票發(fā)行收購為主的交易方式,受我國股票發(fā)行管理機制的影響,正向對賭交易模式無從實施。如需采用反向對賭交易模式,建議收購方收到業(yè)績補償時計入資本公積,而非營業(yè)外收入,由此減少稅企爭議。這樣處理需要企業(yè)充分評判和權衡會計準則風險與稅收風險,同時做好稅企爭議的溝通與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