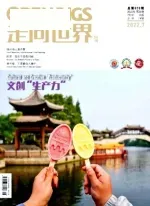煙火人間 至味清歡
張智輝

濟南東部曾有一個“五花八門市場”紅極一時,最終消失在城鎮(zhèn)化洪流中。但地方名吃、熟食、街頭小吃、時令食品從未走遠,且花樣日繁,有的看一眼就令人怦然心動,垂涎欲滴,拔不動腿兒,直白些叫“饞”。
“饞”到極致,梁先生出國3年歸來,可以將行李寄存車站直奔餐館,連吃3種爆羊肚,直呼“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尤不能忘”。“饞是一種生理狀態(tài),也可發(fā)展成近于藝術的趣味。”他的這段話可概括為“極饞近藝說”。
無肉不歡的人,濟南可讓你美夢成真。“瘦肉鮮明似火,肥肉依稀透明,佐酒下飯為無上妙品”“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真文人所見略同,梁先生和千年之前的蘇子似心有靈犀,這用來描述“濟南把子肉”的色、香、味和制作工藝再恰當不過。如今街頭超意興一日三餐可供,經(jīng)二緯六還有專門的把子肉店。來濟南不吃“把子肉”不成游也。
“隴饌有熊臘,秦烹唯羊羹。”濟南豬肉美,羊肉更是特色,最著名的當屬羊肉串。我突發(fā)奇想,以濟南為主題,以“泉城”為上聯(lián),對應下聯(lián)的話有很好的絕對,即“串都”,不知當否?夏日黃昏,街頭,光膀子擼串,已是昨日風景,業(yè)戶多“退避三舍”,但陣勢不減。
位于經(jīng)三緯四的“便宜坊”老店懸掛著一幅對聯(lián)“情切切登堂調(diào)五味,意綿綿入室宴八方”,很有兼濟天下的文化情懷。這鍋貼可謂面食極品,包制時兩端留口,微微露出餡料,煎烙時,先在鍋里淋油,然后把鍋貼緊挨著放齊,淋上清水悶煎。端上桌時,色澤黃白相間,底部酥脆、周邊稍軟,熱氣騰騰,令人垂涎。
雖屬小吃可登大雅的還有“油旋兒”,一種餅,由多層面皮壘起壓成圓形,經(jīng)油煎、烙烤而成,顏色金黃、層多松軟、蔥味香濃、又酥又脆,到口就碎。清代顧仲編著《養(yǎng)小錄》記載:“和面作劑,搟開。再入油成劑,搟開。再入油成劑,再搟如此七次。灶烙之,甚美。”
有道是“南米北面”,各有絕技,濟南四里山的“亮亮拉面”,那面摻的勁道,甩的地道,辣子又剛剛好,可能一次不去,但去過便不會只一次。
“作為一個吃貨。吃零食不是因為餓了而是因為嘴巴寂寞了!”為口腹之欲找盡千般理由的梁先生,“為解寂寞”酷愛糖葫蘆和桂花煮栗子,稱其為無上佳品。如果你是“三月里的下雨”,來的正是時候,在濟南同樣會吃到滿街飄香的糖炒栗子,攪動你味蕾的冰糖葫蘆,不小心在馬路拐角會有“纏蜜”會纏住你,讓你欲罷不能。時令性的產(chǎn)品還有滿口生香的蝎子豆,預示著一個新節(jié)氣的來臨。星羅棋布的薛記炒貨,桿石橋的五香花生米,如濟南人醇厚的特質(zhì)很有“嚼頭”。
如果你意猶未盡,且有閑暇,來一個“商河老豆腐”和“牛肉燒餅”組合,會五味俱全。一大食物店的糕點魅力不減,就在大明湖畔。商河“將夠本”燒餅,可贈友人。這就是濟南。

熟食中的“翹楚”屬“魯味齋”,前身是“魯香齋”,創(chuàng)辦于1927年,以燒制扒雞扒蹄而聞名,燒雞、豬蹄等香爛可口、肥而不膩、瘦而不散。天橋凈香園熟食名震天橋,蒿家扒雞、周記熟食、芙蓉、俊記牛肉等老字號都各具風味。
歲月匆匆,“我在故鄉(xiāng)的泥土中,尋找兒時的指印”。早年間老濟南街頭,有大明湖“三美”:蒲菜、茭白、白蓮藕。“紅花蓮子白蓮藕,說與詩人仔細吟”,白蓮藕,個大、雪白,質(zhì)細、脆嫩、味甜,可生吃,食之無渣,沸水一焯,姜末涼拌白蓮藕,味道絕佳。而茭白餃子、蒲菜奶湯,那更是滋味鮮煞人。大明湖里有魚并不稀奇,奇的是還有一種錦鯉,就是金尾鯉魚,那“錦鯉四作”(紅燒魚頭、糖醋魚腰、清蒸魚尾、酸辣魚湯),就是名菜了。錦鯉秋肥,最宜于秋天品嘗。過去大明湖畔有家小酒館,精于此道,賞明湖秋色,酌菊花佳釀,品錦鯉四作,備菊花水洗手,用荷葉打包,真可謂滿眼秋色,滿口清香,豈一個爽字了得。
更遠的記憶中還有匯泉樓外賣羊肉串,泉城賓館外賣膠東大包,南大槐樹南街的鍋餅,草包包子的炒肥肉片,白馬山啤酒廠的北冰洋啤酒,老茂生的月牙糖。或隱或退,紅塵中的美食也有興衰史。
“客到無供給,家醞香濃野菜春。”白居易給出了春日待客的美食——野菜。“湯蒙蒙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蘇軾吃野菜也能吃出花來。

在濟南,春日踏青之余,刨、購、嘗野菜很有情調(diào),苦菜蘸醬是農(nóng)家樂的硬菜,炸菊花芽、薺菜小豆腐等很受歡迎。生活中常見的野菜有很多種,例如蒲公英、薺菜、魚腥草、馬齒莧、苦菜、灰灰菜、車前草、蕨菜、苜蓿菜、榆錢、槐花、莧菜、水芹菜等。它們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都比較強,分布廣泛,且食用價值高。其中蒲公英又叫婆婆丁、黃花地丁、華花郎等,它的葉子和根都可食用,還可做茶飲。
李清照 “看彩衣爭獻,蘭羞玉酎。祝千齡,借指松椿比壽”,以松樹和香椿為喻體。香椿在濟南“椿”丁興旺,是木材也是食材。周邊縣區(qū)特別是南部山區(qū)盛產(chǎn)香椿芽,形、色、味“三絕”,玲瓏嬌嫩,色澤紅黑,味濃鮮美,內(nèi)含多種礦物質(zhì)、維生素及微量元素,極富營養(yǎng)價值。香椿食用花樣繁多,鹽漬香椿、香椿拌雞絲、油炸椿芽魚等。香椿炒雞蛋,老少咸宜,煎蛋的焦黃、香椿的青綠、馥郁的綿香、入口的清爽,色香味俱佳。將洗凈的香椿和蒜瓣一起搗成泥狀,加鹽、香油、醬油、味精,制成香椿蒜汁,用來拌面條或當調(diào)料,別具風味。深植在味蕾中的還有香椿拌豆腐,“嫩香椿頭,芽葉未舒,顏色紫赤,嗅之香氣撲鼻,入開水稍燙,梗葉轉為碧綠,撈出,揉以細鹽,候冷,切為碎末,與豆腐同拌,下香油數(shù)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汪曾祺先生描述很是經(jīng)典傳神。“壽堂已慶靈椿老,年年歲歲,重添嫩葉,頻長繁枝。”這樹神奇之處,在于椿芽越掰越旺,大有不破不立的架勢。
南山有“三寶”——香椿豆腐和年糕。香椿領先,豆腐是傳統(tǒng)工藝,酸漿點制,豆香十足。年糕,當?shù)厝私小包S面糕”或“黏黏糕”,寓意年年高,熟小米面用地鍋燒火頭蒸制。
面對食物的誘惑,如許衡 “梨無主心有主”需要近乎自虐的定力。“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坐役七尺軀。”“役”下之心各有視覺,“美食和風景,可以抵抗全世界所有的悲傷和迷惘。”這是美食家近乎狂熱的溢美。“知己難,知味尤難”,袁枚之說聊做一觀。最灑脫的還屬蘇子“人間有味是清歡!”
繁華落盡,四方食事不過是煙火人家,心心念念的不過是家家諸君安好、戶戶燈火可親。
“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山河遠闊終為煙火人間,咸有咸味,淡有淡味,無論咸淡莫不是人間滋味。
《味道》電影中,遠在異鄉(xiāng)的晨微最撫慰人心的是媽媽常做的“臊子面”。不知是哪家餐館的廣告詞耐人尋味 ,“媽媽的味道”,溫暖溫馨溫情,人間至味莫過于此吧。

All the pleasure will be gone, but the longing for the peace, safety and tranquility for all families never stops.
There’s a simple wish that the ordinary?dishes?can?fill?us?up,?a?small? house can make a comfortable home. There’s always a wide selection of delicious meals that shows a passion for life and a taste of life
Being away from home, the most comforting thing is the noodles with ingredients made by mom. A restaurant’s advertising slogan - “mom’s cooking is offered here” - makes the atmosphere touching and w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