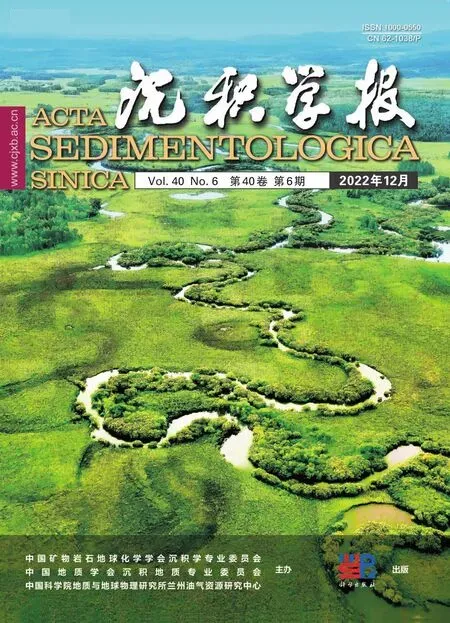裂陷盆地初始階段構造—沉積協同機制
——以蒙古塔木察格盆地塔南凹陷銅缽廟組為例
葛家旺,朱筱敏,王瑞,談明軒,趙曉明
1.西南石油大學地球科學與技術學院,成都 610500
2.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地球科學學院,北京 102249
3.廣西大學海洋學院,南寧 530004
4.河海大學海洋學院,南京 210098
0 引言
裂陷盆地蘊含豐富的油氣資源,是全球重要的含油氣盆地。據統計,世界877個大型油氣田(探明地質儲量大于5億桶油當量)中約31%的油氣田位于裂陷盆地[1 ̄3]。我國東部內陸及近海分布約230個各具特色的中、新生代陸相伸展裂陷盆地,是世界上最大的陸相含油氣盆地聚集區,在這類盆地中均發現了不同規模的油氣藏[4]。長期勘探實踐表明,分布廣泛、物性優良的砂體儲層是規模油氣聚集成藏的物質基礎,亦是盆地構造—沉積及源—匯系統領域的熱點研究對象。
我國東部中—新生代裂陷盆地多數具有典型的“下斷上坳”的二元結構特征,即早期裂陷構造層到晚期坳陷構造層[3,5 ̄7]。一個完整裂陷旋回的盆地往往經歷了構造活動由弱變強再減弱的過程;根據構造沉降史及沉積地層記錄,可劃分為初始裂陷期(幼年階段)、裂陷高峰期(青壯年階段)及裂陷萎縮(老年衰弱階段)等三個階段。初始裂陷期,低構造沉降條件下形成較低的可容納空間,該時期常常表現為沖積或扇三角洲—局限湖盆沉積環境[3,6 ̄7];裂陷高峰期,湖盆加速至最大沉降速率,湖闊且水深廣泛發育厚層優質烴源巖層;最后裂陷盆地進入老年衰弱階段,構造沉降弱,該時期盆地逐步填平補齊,最終演化進入坳陷熱沉降階段[6 ̄8]。
同裂陷期生長斷裂體系建造是控制盆地結構、地貌單元、層序地層構型的根本因素;其邊界斷裂生長、交互、聯結和消亡過程動態塑造了盆地內部斷塊的沉降或者抬升、剝蝕狀態,進而決定了剝蝕地貌高低及平緩程度和源區匯水面積[9 ̄11];盆內次一級同生斷裂在演化歷程中則相互作用并形成多種組合樣式,并通過斷距上的變化調節盆內地貌形態并嚴格控制水系湖盆入口位置、沉積物分散路徑方式及搬運距離,最終決定了砂體沉積類型、發育規模及儲層質量[12 ̄13]。裂陷盆地從青壯年演變到老年階段,斷裂作用與可容納空間、構造地貌、沉積組合及物堆砌樣式關系已被廣泛關注;在裂陷高峰期盆地受控于統一的邊界斷層,斷塊高幅度掀斜并伴隨斷層上升盤形成多個點狀水系供給體系(近岸扇體或重力流砂體);在裂陷高峰晚期以及裂陷衰弱期湖盆底形變得平緩均一,利于軸向水系攜帶碎屑進入湖盆內部形成大型軸向源—匯系統[14 ̄15]。
比較而言,前人針對初始裂陷階段源—匯系統及大型規模砂體成因研究則相對薄弱,其與油氣勘探密切的構造動態演化響應機制尚不明晰。初始裂陷期斷裂解析及沉積響應規律研究相對缺乏的原因主要有:1)遭受晚期構造疊加往往使得早期裂陷層系埋深大,地震資料信噪比低且分辨率低;2)深層的鉆井造價高、數量少而野外露頭較為缺乏[16 ̄19]。目前,初始裂陷盆地砂體分散方式多樣性給優質儲層預測及儲層評價帶來嚴峻挑戰。因此,加強初始裂陷期斷裂作用轉換下的砂體分配機制研究,不僅對揭示裂陷盆地構造—沉積演化及源—匯系統耦合關系具有理論參考價值,而且對裂陷盆地油氣勘探開發亦具有積極意義。因此筆者系統調研前人文獻并總結湖盆初始裂陷階段的構造—地層特性及一般規律;以蒙古塔南凹陷銅缽廟組為研究實例,綜合利用地震、測井和巖心資料,明確其沉積體系類型及分布規律,建立入湖水系與斷層活動演化歷史之間的演化模式,以期對裂陷盆地早期階段砂體成因預測提供科學依據。
1 盆地初始裂陷階段構造—地層特性
大量的實例研究表明,一次裂陷過程往往包括裂陷初始、裂陷高峰和裂陷萎縮三個階段,每個構造階段的構造沉降和沉積物供給存在特定的配置關系,并形成對應的地震層序樣式和盆地充填類型(圖1)。Prosser[20]認為,在初始裂陷階段,物源供給速率往往大于構造沉降速率,形成補償型盆地充填樣式;裂陷高峰期構造沉降速率大且遠遠超過沉積物供給速率,則形成退積型準層序組,以欠補償型盆地充填樣式為特征。裂陷萎縮期構造沉降減弱,沉積物持續供給形成補償型盆地(圖1c),或者缺乏物源供給則形成欠補償型盆地。

圖1 典型裂陷盆地構造演化階段及地層響應特征[20](a)裂陷初始期;(b)裂陷高峰期;(c)裂陷萎縮期Fig.1 Tectonic evolutional stages of rift basins and diagnostic stratigraphic stacking pattern[20]
控盆邊界斷裂的生長和連鎖使得湖盆構造沉降速率發生陡然變化。例如典型的埃及Suez rift中新統初始裂陷期盆地沉降速率僅為8.4 m/Ma,而斷裂發生連鎖以后裂陷高峰時期盆地沉降速率可達137.5 m/Ma[21]。Cowieet al.[22]通過數值模擬認為,裂陷盆地初始階段到高峰期沉降速率的陡然增大,歸因于盆地的應力反饋機制(stress feedback mechanism)。即在盆地形成的初始階段,眾多小斷裂分散了應力作用;伴隨盆地演化進程,應力開始集中于特定的邊界斷裂上,因此部分小斷裂發生交互并連鎖形成控盆邊界大斷裂,而另一部分位于應力屏蔽區的小斷裂不再活動,從此湖盆發生構造沉降速率的陡增并進入裂陷高峰期。值得說明的是,這一過程并不特別需要區域伸展應力方向的變化,恒定應力場下斷裂連鎖過程導致的應力分配差異是初始裂陷到裂陷高峰階段轉換的根本原因[23 ̄24]。
2 盆地初始裂陷階段構造—沉積協同機制
裂陷盆地邊界斷層系演化一般經歷區段式斷層的擴展—生長、聯結—貫通和最后停止的歷程;為突出其斷裂演化特點,Gawthorpeet al.[23]將裂陷盆地演化劃分為四個階段:孤立斷裂作用、相互作用、聯結—貫通和斷層衰亡階段。其中孤立斷裂作用階段對應于Prosser[20]方案中的初始裂陷階段,該時期盆地表現為低構造沉降速率特征。受基底屬性包括基底先存構造及巖性物質非均質性等影響,區域應力拉伸作用下初始裂陷時期盆地結構可表現為分散孤立和寬緩碟狀的盆地形態,對應不同的水系網絡及沉積充填特征。
2.1 分散孤立的湖盆結構
盆內主要斷裂系統的幕式活動及其活動性沿走向的遷移深刻影響了盆內構造古地貌特征,依據斷層活動特征可分為孤立斷層發育和斷層相互作用—聯結兩個階段。前裂陷層先存斷裂/構造或復雜巖性基底條件下,區域性伸展作用下發育復雜裂陷結構。該階段由于應力分散作用到數量眾多的正斷層上,這些斷裂破裂露出地表形成相互獨立的小洼陷群。還有部分“盲斷”正斷層隱伏于地表之下,往往形成生長單斜或撓曲褶皺[11]。因此,斷層孤立發育階段眾多的分割小型盆地內可識別出①典型的加厚楔形地層樣式,以及②向上盤撓曲向斜加厚撒開且向斷層端部撓曲背斜變薄等兩種地層結構樣式[23]。此階段,沉積物輸送體系主要受控于前裂陷層的先存水系網絡。裂陷初期,地層撓曲褶皺和斷層作用聯合形成“地形漏斗”可引發先存水系網絡向盆地一側偏轉(圖2a)。同時,盆地邊緣發育一系列側向短軸的陡坡帶及緩坡帶水系;流域面積與徑流量及沉積物輸出量關系密切,進而控制了盆內扇體分布面積[25]。
隨著裂陷作用進行,區域應力逐漸“選擇性”作用在某些特定的斷層之上,這部分斷層區段側向拓展并相互作用聯結在一起,擴大形成更大范圍的湖盆面積。與此同時,其他斷裂不再活動。初始裂陷第二階段,斷裂下降盤陡崖和緩坡區面積擴大,形成一系列不同類型的陡坡和緩坡區側向供給水系(圖2b),構成多套大型源—匯沉積系統。相對于短而陡崖帶匯水區,緩坡帶匯水區長而緩,進而發育高流量、高沉積物供給沉積體系類型和配置關系。陡崖區形成高流量、低沉積物供給體系,發育小規模扇裙體系(圖2b)。

圖2 先存水系主導的幕式裂陷構造—沉積響應關系[23](a)斷層孤立發育階段;(b)斷層相互—聯結階段Fig.2 Antecedent drainage dominated tectono ̄sedimentary relationship during initial stage of rift phase[23]
2.2 平緩碟狀的湖盆結構
與上述典型分散孤立的湖盆結構不同,McLeodet al.[26]在研究晚侏羅世北海盆地北部Strathspey-Brent-Statfjord半地塹認為,該地區初始裂陷期構造—沉積表現出以下特點:1)盆地拉張形成寬緩的向斜盆地結構;2)地層朝盆地中心方向增厚;3)眾多旋轉和非旋轉正斷層的位移量相似且位移速率極低;4)斷層延伸距離短(小于2~5 km)且無明顯的優勢斷層走向(圖3a)。形成這類寬緩向斜的初始湖盆結構主要與其較為均一的基底巖性或構造屬性有關。應力分布均勻背景下,盆地具有斷裂分布相對連續、極低構造速率、盆內開闊且極平緩地貌等特征[27 ̄28]。與典型的孤立分割的小洼陷群的盆地地貌迥然不同,此階段該類型地形地貌起伏極低,缺乏典型的陡坡帶及緩坡帶水系發育條件。這一類的盆地往往具有非常低的沉降速率,近源水系則相對不發育;在低新增可容納空間(A)/沉積物供給(S)比值條件下難以記錄較深水沉積,以濱淺湖或者淺海沖積平原為主,易發育干旱鹽湖沉積。
裂陷高峰期,盆地內數量眾多的小規模斷裂開始停止活動,部分大斷層發育并相互影響,構造沉降速率增大且差異性明顯增強,上盤形成連片的沉積/沉降中心,盆地演變為類似的半地塹結構(圖3b)[26]。盡管該時期盆地海平面升高,但沉積物供給速率高且超過盆地沉降速率。陡坡帶斷裂掀斜形成局部重力流沉積物,淺海/湖的高能環境下缺乏富有機質泥巖沉積。

圖3 初始平緩碟狀湖盆結構的裂陷期水系演化模式[26](a)初始裂陷期密集的位移量小的斷裂活動,斷裂幾乎沒有控制湖盆地形地貌,殘留盆內高地貌,但改變了水系流動路徑;先存水系提供物源使得盆地物質快速堆積,海/湖平面變化是主要沉積控制因素;(b)裂陷高峰期湖盆具有半地塹結構,斷層活動形成①陡坡帶逆向水系,②緩坡帶水系,③盆地內局部高地貌供給水系及④斷層上盤重力流水系Fig.3 Rift ̄related paleomorphology and drainage dispersion patterns in the initial rift basin of a broadly saucer ̄shaped basin structure[26]
3 實例研究:蒙古塔木察格盆地塔南凹陷
3.1 工區地質背景
塔南凹陷位于蒙古海拉爾—塔木察格盆地的南端,凹陷面積約為3 510 km2,基底埋深最大達4 500 m。塔木察格盆地前裂陷層為上侏羅統中酸性火山噴出巖及碎屑巖,火山基底總體表現為高低起伏的地勢[29]。在早白堊世區域性北西—北北西向拉張應力體制下,海拉爾—塔木察格盆地伸展盆地群形成。在塔南凹陷內發育了一系列北東和北北東向控盆控洼斷裂系統,這一類斷裂帶具有發育早、延伸長和長期活動等特征,常常斷穿基底并控制凹陷或凸起展布。研究區內有11條主要斷層,自南向北命名為塔南凹陷1號至11號斷層。塔南凹陷屬于并聯式復合半地塹結構,并具有繼承性疊加特征[30 ̄31]。塔南凹陷由三個半地塹次凹組成(圖4a),次凹本身也是復式斷陷,自西向東可分為東部鼻狀隆起帶、東部次凹、中部斷裂潛山帶、中部次凹、西部斷裂潛山帶、西部次凹和西部斜坡帶等次級構造單元[32]。
塔南凹陷裂陷期下白堊統自下而上發育銅缽廟組(裂陷初始期)、南屯組(裂陷高峰期)和大拐河組(裂陷萎縮期)。前人通過古生物、巖礦、井—震資料可將下白堊統劃分為四套三級層序(自下而上命名為SQ1~SQ4[6,31 ̄32])(圖4b)。其下白堊統銅缽廟組頂底和內部可識別T5、T3和T31等三個不整合界面,其中T5和T3是廣泛的削截和上超面,為區域性的不整合面(圖5);T5和T3界面分別代表了銅缽廟組頂界面和底界面。在銅缽廟組內部識別局部削截面T31,該界面上下的地震相差異明顯[18,33]。銅缽廟組記錄了塔南凹陷裂陷層系第一套沉積信息,該時期氣候較干旱—半干旱,古生物組合為Bayanhuasporitessp.?Hailarsporasp. ̄Concentrisporitessp.Ass.(145~139.4 Ma)[6]。銅缽廟組下段(SQ1,145~143 Ma)發育一套雜色富礫含砂的混雜巖性組合,常見凝灰巖和角礫巖;銅缽廟組上段(SQ2,143~139.4 Ma)主要為灰白色砂礫巖、粗砂—中細砂巖夾薄層粉砂巖[32 ̄33]。研究區三維地震工區約1 500 km2,地震品質較好,豐富的鉆井和取心資料為探索初始裂陷階段的構造—沉積響應模式奠定了良好基礎。

圖4 塔木察格盆地塔南凹陷工區綱要圖(a)及構造—地層演化綜合柱狀圖(b)Fig.4 (a) Tectonic subdivision, fault distribution and (b) tectono ̄stratigraphical context in Tanan Depression,Tamtsag Basin, Mongolia

圖5 塔南凹陷層序地層格架及地震—地層發育特征(地震測線AA’和BB’見圖4a)Fig.5 (a) Seismic reflection and (b) stratigraphic sequence framework of Tanan Depression(location of seismic line AA’ and BB’ shown in Fig.4a)
3.2 沉積體系及分布
基于大量巖心觀察描述結果,結合測井曲線、地震反射特征及前人研究成果[6,18,31 ̄33],認為塔南凹陷下白堊統銅缽廟組主要發育沖積扇、扇三角洲和淺湖等三種沉積相類型。
3.2.1 沖積扇
沖積扇主要表現為砂、礫、泥混雜堆積的特征,主要在塔南凹陷西北部地區SQ1發育;由于北部隆起帶的發育,在6號斷層和7號斷層的下降盤發育沖積扇沉積。沉積物主要為大套粗碎屑的凝灰質礫巖、角礫巖和凝灰巖等(圖6),砂礫巖層厚度可達百米。測井曲線形態顯示為高幅箱形特征,由于凝灰巖頻繁互層,GR曲線顯示高值(>100 API)。目前,研究區的少部分鉆井資料顯示紅色泥巖和砂礫混雜特征,以及雜亂的地震相特征[18]。

圖6 塔南凹陷銅缽廟組連井沉積相帶及巖性特征Fig.6 Depositional facies and lithology for wells Y19 ̄41, T19 ̄30 and T19 ̄46 ̄1 in Tanan Depression
3.2.2 扇三角洲
銅缽廟組沉積時期,凹陷周緣的沖積扇進入湖泊形成扇三角洲沉積體系,主體為扇三角洲平原和扇三角洲前緣(圖7,8)。
(1) 扇三角洲平原
該部分為扇三角洲的陸上部分,其單層厚度一般大于2 m,包括水上分流河道微相和分流河道間微相(圖7,8)。

圖7 塔南凹陷銅缽廟組扇三角洲沉積特征Fig.7 De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an ̄deltaic system in Tongbomiao Formation, Tanan Depression
水上分流河道:巖性主要為顆粒支撐礫巖和砂礫巖,底部見侵蝕沖刷界面,礫石呈疊瓦狀排列。巖石分選差,呈次棱角—次圓狀,成分復雜。其內發育大型交錯層理、塊狀層理、遞變層理,單層厚度可達5~10 m。自然伽馬和電阻率曲線呈箱形或鐘形。分流河道內可發育碎屑流,巖性主要為雜色礫巖和灰色凝灰質含礫砂巖,發育塊狀層理和正遞變層理,礫石顏色多樣、成分復雜,分選差,磨圓差。
分流河道間:巖性主要由灰黑色碳質泥巖與灰色粉砂巖組成,與河道砂體呈突變接觸。
(2) 扇三角洲前緣
扇三角洲前緣亞相巖性主要為灰色、深灰色的砂礫巖、砂巖和泥巖。包括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間、河口壩和席狀砂微相(圖8,9)。

圖8 塔南凹陷扇三角洲地震反射及沉積分布特征(地震測線CC’位置見圖4a)Fig.8 Seismic reflections and depositional signatures of the fan ̄deltaic system in Tanan Depression
水下分流河道:巖性主要為凝灰質砂巖和礫巖,垂向上呈正韻律(2~4 m),底部常見沖刷界面,發育塊狀層理、槽狀交錯層理和平行層理等。沉積物分選中等,次棱角—次圓狀,顆粒支撐。測井組合以中高幅箱形或齒化箱形、鐘形為主。其與水上分流河道的差別主要體現粒度偏細、分選較好,且水下分流河道底部滯留沉積物中泥礫多為灰色,水下分流河道頂部的細粒沉積多為淺灰色泥巖,而水上分流河道多夾薄層碳質泥巖。
河口壩:巖性主要由灰色凝灰質中粗砂巖和細砂巖組成,常見平行層理、脈狀層理。砂巖分選較好,次棱角—次圓狀,顆粒支撐。呈下細上粗的反韻律特征(1~3 m)。自然伽馬和電阻率曲線以中幅漏斗形或齒化漏斗形—箱形組合為主,表現為下部多齒化、上部齒化或光滑、頂部多為突變的反粒序結構。
席狀砂:巖性主要為灰色細砂巖、粉砂巖,見蟲孔構造。分選好,次棱角—次圓狀。自然伽馬曲線與電阻率曲線呈中低幅齒化指形,厚度一般介于0.5~1 m。
水下分流河道間:由淺灰色、灰色泥巖、粉砂巖組成,夾薄層的細砂巖,含植物莖桿化石和植物炭屑,發育塊狀、水平及波狀層理。
3.2.3 濱淺湖
濱淺湖是指浪基面以上湖相沉積的部分,巖性主要為細粉砂巖夾灰色泥巖,發育灘壩、湖泥等沉積微相[18],但分布較為局限;測井曲線上呈反韻律及低幅度鋸齒狀,剖面上單層厚度較薄,一般小于0.5 m。
3.2.4 沉積體系分布
在巖心相、測井相和地震相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銅缽廟組沉積體系展布規律。
(1) 銅缽廟組下段(SQ1)
SQ1時期每個次級洼陷為一個獨立的沉積單元。東部次凹和中部次凹主要發育扇三角洲和濱淺湖沉積體系。該時期在T19-53-1井以北地區SQ1均被剝蝕,該井以南發育扇三角洲沉積,地震剖面上見典型前積反射特征。中部和西部次凹連為一體,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為主要物源,受斷層的控制分別發育規模不等的沖積扇—扇三角洲體系,這一類三角洲規模均不大,向前延伸距離一般小于6 km(圖8)。在西部次凹北部還發育沖積扇和洪泛平原沉積體系[18,33]。
(2) 銅缽廟組上段(SQ2)
SQ2時期湖泊水域面積向北擴展,湖盆逐漸擴大并連為一體。該時期發育廣泛的扇三角洲砂體,淺湖沉積物局限。平面上發育三套大面積扇三角洲沉積體系:第一套扇三角洲體系位于1號和2號斷層疊覆區,向西南方向推進距離約20 km;第二套位于2號和3號斷層疊覆區,向西南方向延伸約15 km。第三套位于4號和7號斷裂疊覆區,重礦物組合主要為鋯石—磁黃鐵礦—白磷礦,西南方向砂地比逐漸降低,綜合前積反射方向指示三角洲向西南方向推進(距離可達18 km;圖8,9);該處持續發育扇三角洲體系,扇三角洲平原分布面積廣泛,地震同相軸上表現為弱振幅低連續的反射特征,T19-342-t200取心井扇三角平原特征表現為大套礫巖發育的辮狀水道沉積。西部次凹發育多套扇三角洲體系,砂體疊合連片且分布面積大(圖9)。東部次凹受邊界斷層控制在陡坡帶發育呈“裙狀”的扇三角洲沉積(向湖推進距離小于8 km);6號和7號斷層下降盤發育扇三角洲沉積,說明此處沉積環境由陸上向水下的變化。另外,在中部次凹和東部次凹的緩坡帶發育砂席(灘壩)沉積,主要位于扇三角洲的側緣或局部隆起區,呈席狀、土豆狀分布[34]。

圖9 塔南凹陷SQ2時期同沉積斷層分布及沉積物分散示例圖Fig.9 Active fault arrays and deposition of sequence SQ2, Tanan Depression
3.3 初始裂陷階段構造—沉積模式
將前述沉積體系分布規律研究結合斷層演化及地層分布特征分析,對銅缽廟組構造—沉積發育模式歸納總結如下。
3.3.1 初始裂陷第一階段
塔南凹陷斷層幕式活動第一階段(SQ1沉積期),北東東向控洼斷層開始形成使得塔南凹陷被分割成幾個獨立的洼陷。1號斷層的南部和2號斷層中段活動速率可以達到222 m/Ma,東部次凹基底古落差超過700 m。控制東部次凹帶的3號斷層活動速率次之(約148 m/Ma),中部4號斷裂活動速率約為200 m/Ma,東西兩端斷層活動速率較低。該時期,6號、7號、8號和9號斷層共同控制了西部次凹帶的形成;其中,6號斷層和7號斷層活動速率相對較小,多在20 m/Ma以下,8號斷層活動速率相對較大,該斷層中南部的活動速率可達72 m/Ma。其他次一級斷層活動速率多數小于20 m/Ma(圖10)。

圖10 塔南凹陷銅缽廟組主干斷裂生長歷史Fig.10 Fault displacement and growth history during Tongbomiao Formation deposition, Tanan Depression
該時期地層厚度中心比較分散且面積局限,SQ1最大厚度約為400 m。3號斷層控制了中部次凹的形成,從南至北差異活動性明顯,共形成四個次一級的沉降中心。其中,4號斷層中心位置最厚(T19-52井附近,殘留地層厚度可達300 m,而最南端地層厚度則小于200 m)(圖11a)。總體而言,裂陷活動的第一個階段沉降中心主要位于東部次凹的南洼和北洼以及中部次凹的中部。

圖11 塔南凹陷SQ1(a)和SQ2(b)層序地層厚度分布圖Fig.11 Stratigraphic thickness of sequences in Tanan Depression(a) SQ1; (b) SQ2
塔南凹陷初始裂陷期在伸展體制下發育新生的北東向系列洼陷群,與基底斷裂及火山“高山深谷”[29,33]的先存地貌一起構成該時期獨特的源—匯系統:孤立的小洼陷群之間分割不連通,洼陷邊緣斜坡長度均小于10~15 km;盆地邊緣短程水系向四周的盆地低勢區供源,無明顯優勢的水流方向,盆地邊緣發育面積局限但數量眾多的沖積扇—扇三角洲群。總體來講此階段斷層剛開始活動,先存的基底構造對物源和沉積格局影響十分關鍵,與新生湖盆結構一起,發育小規模物源(盆內和盆外)、搬運距離短的粗粒沉積體系(圖12a)。
3.3.2 初始裂陷第二階段
塔南凹陷裂陷幕式活動的第二階段(SQ2沉積期),斷層活動強度幾乎不變但長度明顯擴展,盆地的范圍快速擴大且三個次級洼陷連為一體,塔南凹陷的盆地形態基本定型。整體上斷層活動具有繼承性(圖10),1號斷層的南部和2號斷層中部斷層活動速率較大,其中前者活動速率可達200 m/Ma,后者的最大活動速率可達230.7 m/Ma。該時期,3號斷層活動速率略有減弱,其中部活動速率最大為115 m/Ma,南部和北部活動速率減少到30 m/Ma以下。6號、7號、8號和9號斷層的活動也具有繼承性,其活動速率較小。其中,6號斷層和7號斷層活動速率最大達38.4 m/Ma,9號斷層整體活動速率略有變大,其中南部活動速率可達96.2 m/Ma。5號斷層活動速率較大,可達200 m/Ma。
相比SQ1,SQ2時期地層厚度中心位置變化不大,但地層展布面積擴大且向北擴展,地層厚度達500 m。其中4號斷層上盤發育統一的厚度中心,地層最厚約400 m(圖11b)。初始裂陷第二階段,伴隨控洼斷層活動性和長度增大進而發生斷裂軟聯結(圖11b):1)塔南凹陷連通變為較為寬而淺的盆地結構;2)1號斷層北端和2號斷層的南端,2號斷層北段和3號斷層南段,4號斷層和7號斷層交互疊覆,疊覆距離約10 km;3)形成低坡降的構造轉換帶(圖10),地貌低地勢區捕獲水系形成三套大型構造轉換帶三角洲體系,轉換帶疊覆區匯水面積均大于50 km2;4)西北側的緩坡地貌長度增至28 km,西部緩坡帶物源供給發育大規模的扇三角洲體系(圖9)。據匯水面積(A)與斜坡長度(L)之間的關系[35](L=1.4A-0.6),認為該時期低坡降的構造轉換帶和快速得到建設的緩坡帶有能力捕獲大型水系網絡。遠離剝蝕物源區的湖盆區,主要發育濱淺湖沉積,盆內相對局限高地貌區由于波浪作用可發育一定規模的灘壩砂[34]。此外,1、2和3號主干斷層下降盤發育斷崖短程水系,發育小規模的扇三角洲沉積(圖9)。該時期源—匯系統特征:斷裂快速拓展交互聯結,形成大型低地形坡度的構造轉換帶,同時緩坡帶長度增加;發育大面積展布的轉換帶及緩坡帶水系供給型扇三角洲沉積體系(圖12b)。

圖12 斷裂早期聯結型盆地結構及沉積分散方式響應(a)初始的孤立斷層階段:斷裂規模小位移量低,以孤立、分割的小半地塹群為特征;由于高低起伏的先存火山巖基底,缺失先存成熟的水系,盆地以短程水系供給為主,形成數量眾多且規模小的沖積扇/扇三角洲沉積體系;(b) 斷裂早期快速聯結階段:斷裂快速拓展交互聯結,形成規模較大的低坡降轉換帶且緩坡帶得到建設延長,發育大套包括轉換帶水系(②)和緩坡帶水系(③)供給的長距離搬運富砂沉積體系;軸向物源體系(④)及陡坡帶水系(①)延伸距離相對較短Fig.12 Conceptual model of (a) fault growth; and (b) sediment dispersal pattern in the early rift basins
4 初始裂陷階段源—匯系統的多樣性
裂陷盆地不同構造演化階段,斷裂位移、形態及其相互作用關系的轉換,主導盆地形態和展布規模發生變化,必然會導致入盆水系網絡、沉積物類型及砂體分散方式的轉換或遷移。研究表明,在一個完整的裂陷旋回周期演化過程中,響應于斷層初始活動、斷層交互和聯結過程,初始裂陷階段以短軸水系為主,而在裂陷萎縮期長軸供給體系逐漸占據主導。
受前裂陷層基底構造性質影響,初始裂陷第一階段新生湖盆剛剛打開,其結構形態可表現為寬緩碟狀或典型半地塹結構,其充填樣式與先存水系密切相關[23]。例如在北海盆地晚侏羅世初始裂陷期,先存水系攜帶充沛的碎屑使得盆地過充填。相反地,在塔木察格盆地塔南凹陷早白堊世初始裂陷期缺失先存水系網絡,孤立的窄湖盆(寬度小于10~15 km)缺乏規模化的新生水系網絡(圖12a)。由此可見,初始裂陷盆地充填樣式受控于先存水系,與盆地初始地貌建設亦有緊密聯系,這種聯控機制加劇了這套地層沉積體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19]。綜合調研以及研究區分析結果,初始裂陷的第一階段源—匯系統大致可分為以下3類(表1)。

表1 陸相盆地早期裂陷階段構造—沉積演化及源—匯系統Table 1 Tectono?sedimentary evolution and source?to?sink systems during the early rift phase in continental basins
類型1:先存成熟水系主導的孤立分割型湖盆群,即在裂陷盆地形成前期盆地地貌已經夷平,大型長源性河流水系已然建成,例如晚侏羅世北海盆地北部Lofoten地區[23]以及希臘Corinth裂谷盆地[13]。該時期,近源新生水系與長源先存成熟水系同時發育。盆內同時記錄河流—三角洲砂體以及近源扇體沉積物因而滿盆富砂[36]。
類型2:先存成熟水系主導的寬緩盆地,該盆地往往缺乏年輕的近源水系,例如晚侏羅世北海盆地北部Strathspey-Brent-Statfjord地區[26],該盆地以長源先存水系供給河流或三角洲砂體為主,該盆地可容納空間低,物源供給(A)遠遠大于新增可容納空間(S),湖盆亦具有滿盆富砂過充填特征。
類型3:發育年輕的短程近源水系主導的小湖盆群,屬于陸內裂陷且具有明顯的內流性質;該盆地往往缺乏先存水系網絡,新生短程水系提供近源沉積碎屑,往往發育小規模的沖積扇、扇三角洲碎屑物和火山巖碎屑物,其沉積物分選磨圓差,成分異常復雜,例如蒙古塔南凹陷下銅缽廟組(圖12a)。
初始裂陷的第二階段,盆地內應力開始集中作用使得同生斷裂發生相互作用并發生聯結(圖11b),其聯結方式對盆地結構及沉積物分散體制影響重大[22,24],可形成兩類迥然不同的源—匯系統(表1)。
類型4:若斷裂體系為早期聯結型,使得長度快速增加而位移量緩慢增加(或幾乎保持不變),即斷層聯結早于位移變化[22],那么該盆地往往具有連通的、寬淺的地塹或者半地塹結構;斷裂的交互作用不僅形成大型轉換帶富砂體系,還形成快速建設的緩坡帶供給沉積體系(圖13b)。該類源—匯系統下發育規模優質油氣儲集體的概率大,可作為勘探地質學家重要關注對象。
類型5:若斷裂體系為晚期聯結型,即孤立斷層側向呈放射性拓展并發生交互聯結,邊界斷層位移量和長度同時協調增大[22],最后形成的盆地結構分割型較強[37],難以形成大型匯水體系或水系難以通暢輸送至盆地中心區域,則常常以短程斷崖或小型轉換帶水系為特征,盆地整體具有“近源”快速充填特征。
在地表環境,相比陡坡或者陡崖帶,低角度或者平緩的地貌背景水系的侵蝕供源能力增強,更容易捕獲大型的水系及豐富的碎屑風化產物[38]。斷層早期聯結并迅速伸展改變盆地邊緣及內部構造地貌,這些地貌特征有利于捕獲大型的水系或作為砂體有效傳送通道。本實例研究表明,斷裂早期聯結型盆地以大型匯水體系及多套大面積展布的粗粒三角洲砂體,盆地整體具有“富砂”特征(圖12b)。這些富砂的沉積特征可能是邊界斷層快速伸展但位移量緩慢增大的特性,類似的沉積特征還在其他裂陷盆地可見[39 ̄40]。
根據實例分析及調研成果,筆者分階段建立了可供參考的初始裂陷構造—沉積構架,以及基于是否與先存水系溝通總結了五種源—匯系統類型。誠然,源—匯系統發育控制因素眾多,例如氣候變化、物源母巖類型及組合差異[41],使得相同湖盆結構的沉積充填樣式出現明顯差異。溫暖潮濕氣候背景下裂陷盆地初始階段主要發育河流—濱淺湖沉積體系建造(圖2a),而在干早和半干早氣候下則易記錄鹽湖或風成沉積物。盆地邊緣新生水系流域面積受構造斜坡長度所控制,亦與匯水區基巖的巖性和抗風化能力有關[23]。例如,碳酸鹽巖母巖主要供給形成溶解質顆粒,而花崗質母巖風化進入水體形成固態顆粒質碎屑[42]。初始裂陷階段,多斷裂體系活動形成各具特色的裂陷盆地結構導致水系類型及沉積響應的多樣性。
5 對裂陷盆地深層油氣勘探的啟示
經過幾十年的勘探開發,許多裂陷盆地已經進入勘探后期或開發階段,深層地層—巖性油氣藏已經成為該類盆地商業勘探的重要領域。塔南凹陷初始裂陷層油氣勘探實例顯示,深層銅缽廟組下段發育短程源—匯系統形成富礫含凝灰巖的沖積扇—扇三角洲沉積物,該套沉積物分選磨圓極差,儲層物性條件差,鉆井揭示均為干層(圖6)。相比而言,銅缽廟組上段發現多套斷塊或地層—巖性油氣藏,是塔南凹陷主力產油層。該時期,由于斷裂相互作用聯結形成寬緩連通復合半地塹結構及緩坡帶快速拓展形成中—大型水系網絡,在整體沉降弱的構造背景下發育推進距離遠的轉換帶及緩坡帶供源型扇三角洲砂體儲層,為油氣規模成藏提供良好物質基礎。銅缽廟組之上為南屯組裂陷高峰期厚層深湖泥巖,因此銅缽廟組上段優質扇三角洲前緣儲層側向接觸或上覆厚層烴源巖,形成“旁生側儲”和“上生下儲”兩類典型生儲蓋組合。
勘探開發實踐已經證實,塔南凹陷在初始裂陷第二階段發育厚層扇三角洲前緣砂體,該段具有滿盆含油、高部位富集及斷裂控藏特點,其探明石油地質儲量占整個凹陷儲量的87%[43]。初始裂陷第二階段發育的大型轉換帶及緩坡帶三角洲砂體具有毗鄰優質烴源巖、砂體規模大、儲層物性好及蓋層封閉性強等有利成藏條件,特別是后期遭受斷裂活化或者斷塊掀斜地區,極易溝通上覆或側向溝通充足的油源并為油氣聚集提供良好場所,可作為裂陷盆地深層油氣勘探優先關注目標。
6 結論
(1) 盆內同沉積斷層活動演化及其橫向差異性決定盆地的結構與地貌特征,深刻影響新生水系網絡建造及沉積充填演化過程。實例解析結合調研結果表明,先存水系和盆地地貌結構聯合控制初始裂陷盆地的充填樣式及源—匯系統,初始裂陷期構造—沉積協同機制及源—匯動態演化過程是當前國際地學盆地分析的難點議題。
(2) 塔南凹陷下白堊統銅缽廟組主要發育沖積扇、扇三角洲和淺湖三種沉積相類型。初始裂陷第一階段以新生的分割型小洼陷群為特征,與前裂陷層“高山深谷”地貌背景聯控下形成年輕的短程水系并發育數量眾多的小規模沖積扇—扇三角洲沉積體系。
(3) 塔南凹陷初始裂陷第二階段伴隨控洼斷層長度迅速增大發生軟聯結,形成連通及寬而淺的盆地結構,發育三套低坡降構造轉換帶以及西北側緩坡水系供給型大規模扇三角洲富砂體系,軸向物源體系及陡坡帶水系延伸距離相對短。
(4) 初始裂陷第一階段盆地廣泛富砂(溝通先存水系)或者饑餓沉積(不溝通先存水系),年輕短程水系主導的孤立小湖盆群則主要發育小規模近源碎屑沉積物。初始裂陷第二階段發育以短程斷崖水系(晚期斷裂聯結型盆地)或大型構造轉換帶及緩坡帶三角洲砂體(早期斷裂聯結型盆地)。斷裂早期聯結型盆地發育大型富砂型源—匯系統,是石油工業界關注的重點目標。致謝 審稿專家及期刊編輯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