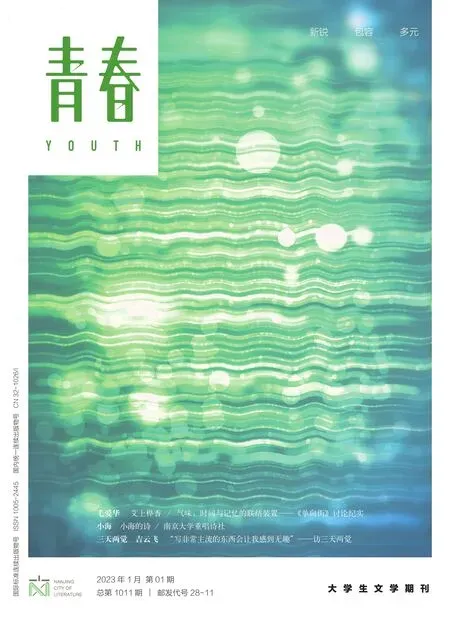瑪雅游樂園
上海電影學院 謝京春
朵朵光著雙腳坐在游樂園的滑梯上,她張開雙臂,示意我伸手接住她。我搖搖頭,鼓勵她自己滑下來,不應該每一次都依靠別人的幫助。兩個小男孩在后面的空地上為了爭奪一只藍色的皮球而大打出手,他們的母親,兩個身材走形的年輕婦女正嘰嘰喳喳地談論著一些什么,時而笑得前仰后合。把守游樂園入口的女孩睡著了,她的腦袋埋在雙臂中間,只露出高高的馬尾。太陽快要落山,估計不會再有新的客人進場。
下午的時候姐姐把朵朵交到我的手里,讓我帶著她到瑪雅游樂園玩滑梯。
“我可沒有帶孩子的經驗。”
姐姐一臉憤怒:“你遲早也要結婚的。”
見勢不妙,我只好抱著朵朵難為情地來到了游樂園。四周一個成年男人也沒有,這里是女人和孩子們的天堂。
朵朵是這里的常客,她已學會熟練地在會員登記簿里尋找自己的名字。負責人是一個年輕的女孩,樣貌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卻依然讓我心情大好。像在流水線上檢疫生豬一樣,女孩在我和朵朵的手背上各蓋了一枚紅色的印章,表示合格,可以通行。我們脫下鞋子,越過護欄,真正進入游樂園。
游樂園在人民商場三樓的東北角,地方并不大,有三架滑梯、一張小型蹦床、幾間泡沫房,地上散落著許多五顏六色的氣球。這已經算是縣城里最大的兒童游樂園。朵朵光著腳爬上其中的一架滑梯,等我伸手迎接后她便順勢滑下,笑聲清脆猶如風鈴。如此重復數次。后來她逐漸適應了一個人爬上爬下,我得以騰出時間來,悠閑地坐在空地上發呆。
我和朵朵在游樂園待了幾個小時,姐姐還沒有回家。她發來短信,說韓曉東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一下午都沒有找到。我覺得姐夫是故意躲著不見她,盡管姐姐口口聲聲說著要去話劇團鬧個底朝天,可是見不到韓曉東她絕沒有底氣貿然前往。
游樂園已經沒有其他顧客,朵朵的耐心正在一點點消失。女孩歪著頭看向我們,她已經睡醒了,或許就要下班。
“你們要回家嗎?”女孩沖著我們喊道。
我站起來,看見朵朵無精打采地坐在滑梯頂部,回答說:“我姐還沒有回家,我們想再玩一會兒。”
女孩說:“可是我們要關門了。”
我只好抱著朵朵從游樂園里出來,分頭去找各自的鞋子。朵朵的紅色小皮鞋不知被誰狠狠踩了一腳,鞋頭癟了,我用手倒騰了好一陣子才終于使它盡可能地恢復了原貌。
商場里的員工已經脫下了工作服,正陸陸續續地走進電梯。女孩把電閘拉下,瑪雅游樂園的招牌一下子暗下來。在一片花花綠綠的老年服裝攤位之間,很難想象這里還會有一家熱鬧的兒童游樂園。女孩邊走邊把身上的工作服解開,里面是一件深灰色衛衣,頭頂的馬尾被她一把揪散,烏黑茂密的頭發順勢披下來,把脖子整個地遮住。于是我們三個人同時朝著電梯走過去。
走出商場門口,我禁不住跟她道別:“很不好意思,耽誤了你下班。”
女孩很有禮貌,只是微笑。
我說:“這是我姐姐家的孩子,她以前經常來這里。”
女孩點點頭,說她認識。她沖著朵朵揮揮手,算是告別。
到家后,姐姐還沒有回來,我們只好坐在門口的樓梯上一直等。朵朵讓我打電話,無人接聽的語音傳出來,然后是“嘟嘟”聲,朵朵顯得很失望。我又打給姐夫,鈴響了很久,對面終于傳來一陣沙啞的聲音,我氣急敗壞地質問道:“你們還管不管孩子了?”
姐夫的聲音很小:“你先受累,幫忙照看一會兒,單位太忙了,我實在沒時間。”
人在氣頭上,我感覺有一肚子話想說,姐夫卻突然掛了電話。我像一只突然泄了氣的皮球。坐在門口的樓梯上,朵朵的眼睛忽閃忽閃,又大又亮。我不知道該跟她說些什么才好。
姐姐回來了。朵朵已經趴在我的大腿上睡了很久,聽見開門聲她還是一下子睜開了眼。
我說:“你怎么才回來?”
姐姐看了一眼朵朵:“你們吃飯了嗎?”
朵朵搖搖頭。

東良 《飛行小屋》
姐姐把朵朵抱進臥室,問她在游樂園玩得開不開心。朵朵繼續搖頭:“我的鞋子被別人踩臟了。”
我說:“你什么時候跟姐夫離婚?”
姐姐低著頭不說話。
“下午我給他打過電話,說單位里很忙。他要是躲著不肯出面,我可以幫你去。”
姐姐點點頭,問我要不要吃點什么。
我擺擺手算是拒絕,便關了燈各自回屋睡覺。
臨睡前,打開手機,看見姐夫發了一條朋友圈,是一張話劇團演出的預告海報,復排劇目《雷雨》。姐姐剛結婚的時候曾拉著我們全家去話劇團看姐夫表演,看的就是《雷雨》,姐夫當時飾演魯大海,一個意氣風發的罷工工人。當時看完,我們大受感動,覺得當話劇演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結婚后,縣里的劇團總是拖欠工資,姐姐幾次三番跟姐夫商量能不能換個工作,姐夫卻始終不為所動。
我干脆把姐夫的朋友圈屏蔽了。我知道他們兩個離婚也是遲早的事情,想到這些我就心煩意亂。
第二天是星期六,朵朵待在家里,我一個人出去圍著縣城閑逛。三中門口新開了一家手機店,專賣二手蘋果手機,趕上周末,店里擠滿了穿著藍色校服的男孩,他們的口袋里裝著一沓一沓的紅色鈔票,讓我自愧不如。想起上高中的時候,我算是班里的優等生,打心眼兒里看不起學習成績落后的同學,當時的那種優越感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正一點一點消失。
走著走著就到了人民商場。瑪雅游樂園果然生意紅火,入口處已經開始排隊。依然是昨天的女孩,她正認真地接待顧客,輪流在每個人的手背上蓋上紅色的印章。可惜朵朵沒有跟我一起出來,我不能一個人進去,這里是女人和孩子們的天堂。我只好躲在商場角落里遠遠地觀望。后來顧客慢慢變少,女孩又趴在桌子上睡起來,我才打算回家。
星期天一大早,我便自告奮勇要帶著朵朵一起出門。臨走的時候姐姐叫住我,囑咐我應該認真找工作,不要整天在縣城里閑逛。我答應一聲,沒再多說什么。下樓后便抱起朵朵直奔人民商場。
女孩還在,她翻開登記簿找到朵朵的名字,又例行公事一般在我們的手背上蓋好紅印章。她的手又軟又涼,讓我禁不住心跳加速,我想自己大概已經臉紅,便沖著她不自在地笑了笑。
朵朵并不需要我悉心照看,她已對這里的環境十分熟悉,事實上,我的心思也并沒有停留在朵朵身上,所謂的照看更像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游樂園里人滿為患,朵朵很快結識了其他的小朋友,看上去玩得十分愉快。女孩把守著游樂園的入口,此刻難得清閑,我鼓起勇氣朝著她走過去。
女孩的脾氣很好,我們很快攀談起來。我終于知道了她的名字叫薇薇,游樂園是小姨開的,大學放了暑假就來這里幫忙。說起我的情況,她看上去很感興趣,我只好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剛剛大學畢業,事實上我已經畢業兩年多。繼而問起我的工作,想到姐姐半年以來的責備,我決心對她撒謊,于是介紹說自己在縣里的話劇團上班。她問我是不是話劇團的演員,我搖搖頭,只說自己在那里什么都干一點。
“話劇團效益不好,過一陣子我準備辭職。”想到姐夫的遭遇,我為自己此刻的陰謀感到羞愧。
說起游樂園,我問她:“這里為什么叫瑪雅?一個兒童游樂園。”
薇薇搖頭說不知道:“一開始就是這個名字,是小姨起的。”
我說:“這個名字很好聽,聽上去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薇薇說:“小孩子可能不會這么想。”
看著頭頂的招牌,霓虹燈管讓“瑪雅”兩個字變得光彩奪目,我想起遠古的神秘預言,想到巨人石像、玉米和原始部落,我對此知之甚少,此刻卻浮想聯翩。
走的時候我們互相留了電話,我夸下海口說,話劇團再有演出的時候請她去看。
“你可不能騙我,到時候我真要去的。”
我點點頭,拉著朵朵走進電梯。
回去的路上我問朵朵喜不喜歡去游樂園,朵朵不說話,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一群高中生穿著藍白相間的校服,騎著自行車向我們迎面過來,他們車速飛快,前進的過程中言談甚歡。我嚇得把朵朵抓緊抱起來,直到過了路口,看見小區門口的噴泉,才又把她放下。
回到家,姐姐已經做好了飯,她看上去輕松了不少。不免又說起韓曉東,姐姐佯裝鎮定。她說已經托人聯系好了律師,過幾天就會有結果。
“你不用擔心,到時候我給你幫忙。”
姐姐嘆了一口氣:“再說吧,你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
晚飯后躺在床上,窗外的天空不時有雷電閃爍,空氣變得愈加黏稠。雨一直不下,讓人心里煩躁。我很想給薇薇發條短信,問問她在忙些什么,可我擔心這樣做會讓她以為我是個輕浮的人。我想明天還可以繼續帶著朵朵去游樂園,這樣就能夠名正言順地見到她……
周一上午,姐姐約了律師見面。我說我可以帶著朵朵去人民商場玩滑梯。朵朵死死抱著姐姐的胳膊不肯撒手,說什么也不要跟我一起。
姐姐說:“算了吧,還是我帶著她。你不要整天閑逛,要抓緊找工作。”
我蹲在地上,摸著朵朵的腦袋,問她:“游樂園不好玩嗎?”
朵朵不說話,把頭深深埋進姐姐的懷里。
我再次一個人出門。圍著縣城逛了半天,實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去處。其實我的心里早已經預設好了出行的目的地,可是沒有朵朵的陪伴,我成了逃票的乘客,想要去,又怕理由不夠正當。我越來越感覺到游樂園的好處。
逛了很久,最終還是到了瑪雅游樂園。出了電梯,一眼就看見游樂園里只有女孩一個人在。這讓我更加緊張。我想好了來的理由,就說話劇團演出,問她要不要去,她要是同意,我就給姐夫打電話,讓他幫忙搞兩張票,這不是多難的事。要是她說最近很忙,恐怕沒有時間,我就說沒關系,等你有時間了再約。
我一個人走向游樂園的門口。看見我出現,薇薇立刻站起身來迎接,問道:“怎么沒帶著朵朵一起?”
我說:“她跟著媽媽走了。”
薇薇說:“周一沒什么人來,你要進去玩嗎?”
我說:“算了吧,我太胖了,會把滑梯弄壞的。”
薇薇抿著嘴笑,然后翻進游樂園扛出來一個粉紅色的塑料小馬,讓我坐在上面休息。我坐在小馬的屁股上,跟薇薇聊起天。她沒再繼續追問我為什么一個人來,我花了幾個小時為這個問題做準備,想不到全是白費功夫。
我們面對面聊了好幾個小時,薇薇看上去比我還要開心。她已經在這里干了很多天,很少有人陪她一次說這么多話。直到有一個小男孩到這里玩兒,我才從小馬的屁股上站了起來。告別的時候我心情歡暢,我很想再陪她多待一會兒,又怕一次說得太多會讓她厭煩。
走的時候我問她要不要去看話劇,想起姐夫前幾天在朋友圈里發的海報,那是我唯一看過的話劇,我可以帶著薇薇重新看一遍,屆時我會像一個話劇團的老員工一樣坐在她的身邊為她講解劇情。
我說:“你什么時候有空?”
薇薇說:“我什么時候都有空。”
我說:“等我消息吧,到時候我給你發短信。”
薇薇說:“好,一言為定。”
于是我心滿意足地離開了瑪雅游樂園。
晚上我給姐夫打電話,想問問他什么時候有演出,一連打了三四個才打通。姐夫的聲音孱弱無力,全然沒有了往日的活力。想起幾年前他開車拉著我到中醫院幫姐姐拿藥,停車的時候跟別人起了爭執,彼時的他口齒清晰,聲音洪亮,心底坦蕩蕩,三五句話便讓對方節節敗退。
我問他:“話劇團是不是最近有演出?”
姐夫“嗯”了一聲,像在試探我的心思。
我說:“你能幫我弄兩張票嗎?我想去看。”
“你姐也來嗎?”他提高了警覺。
“她不去,我跟一個朋友。你放心,我姐不知道。”
姐夫答應下來,說明天下午就有一場,一會兒把電子票發到我的手機上。我的心里突然有些難過,說不上是因為什么。我覺得應該說幾句好聽的話安慰他才行。
“你別難過,姐夫,其實也沒什么,現在離婚的人很多。”
姐夫說:“我知道,就先這樣吧,有事兒你再找我。”
掛完電話,姐姐正好帶著朵朵回來了。我們什么話也沒說。悶熱潮濕的天氣讓我食欲不振,落地扇來回搖晃著腦袋,嗡嗡的聲音像是發起抗議。躺在床上,我抱著手機給薇薇發短信,說好了明天下午一起去話劇團。
一天就這么過去了。
話劇團在縣城的東南角,多年以前縣里的房地產生意還不像如今這樣紅火,劇團的二層紅色小樓被幾棵高大的杉樹環繞,算是縣城里的標志性建筑。現在高檔小區建的多了,二十幾層高的樓房到處都是,話劇團光彩不復當年。
我提前半個小時就到了,等了不一會兒就看見薇薇從路那邊走過來。話劇團門口很冷清,臺階上方擺了兩張并不醒目的宣傳海報。想起上次來這里還是幾年前姐姐剛結婚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從出租車上下來,姐夫早已在門口等候多時。那時候看話劇的人多,有孩子也有老人,但更多的是年輕人。此刻,薇薇已經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上了臺階,我們一前一后走進了劇場。
劇場里只零星坐了十幾個人,大幕還沒有拉開,舞臺上的燈黑著。姐夫給的兩張票,位置并不好,我心里有點嘀咕,懷疑他根本沒有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臨開場一兩分鐘的時候,薇薇扭過頭來問我:“應該沒有人再進來了吧?”
我說:“應該沒有了,這幾年劇場的效益不好。”
薇薇說:“那我們換個位置,到第一排的中間去,你看,那里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彎著腰急匆匆地跑到了最前排,剛坐下,劇場里的大燈便“唰”的一聲全部熄滅了,幕布緩緩拉開,好戲開始了。
薇薇安靜地坐在座位上,看得饒有興致。隔著潮濕的空氣,我聞見她身上淡淡的香味,看見她的胸脯高低起伏,眉頭時而緊鎖。我的注意力全然不在舞臺之上。有幾次我嘗試著悄悄靠近她的耳朵,想把舞臺上的故事給她解釋清楚。薇薇總能輕而易舉地發現我的小動作,她把食指貼在自己的嘴唇上,扭頭看向我說:“噓,不要說話。”
過了不知多久,我竟昏昏沉沉地睡著了。我夢見薇薇穿著肥大的戲服站在瑪雅游樂園高高的滑梯上迎接我。
我張皇失措地警告說:“這是我姐夫的衣服,你怎么穿上了?”
薇薇對我的話置之不理,她從滑梯上緩緩滑下來,笑聲清脆,猶如風鈴。
她說:“你的紅色小馬呢,我不是把它送給你了嗎?”
我說:“那不是我的小馬,是瑪雅游樂園里的,游樂園是你小姨開的,你是不是要走了?”
聽見我的話,薇薇突然蹲在地上哭起來:“你騙我,你根本就不在話劇團工作,票是你姐夫買的,位置一點也不好。”
我很想辯解,想說清楚自己并不是故意要騙她,我張大了嘴拼命呼喊,卻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看見薇薇蹲在地上號啕不止,我心如刀絞。
過了沒一會兒,薇薇把我從座位上晃醒。睜開眼,我看著空無一人的舞臺,長舒了一口氣。演出已經結束了,大幕重新恢復成原先的樣子,劇場里同樣空空蕩蕩,觀眾都已經退場。我揉揉眼睛,看著眼前的薇薇,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薇薇說:“想不到縣城里的劇團還能排練得這么好。”
我說:“那個魯大海,是個組織工人罷工的頭頭,他演得很好。”
薇薇說:“我知道,在大學的時候我從頭到尾看過三遍,還是覺得今天的演出最棒。”
聽見薇薇說她早已看過三遍,我突然有些失望,覺得自己不該帶她來看。這時候,身后突然傳來一聲大喊,是劇場的管理人員,讓我們抓緊離場。門外的光明亮得刺眼,讓我看不清那人的長相,我們兩個人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沖著門口大喊:“韓曉東今天沒來嗎?”
遠處的人停頓了一會兒,像是自言自語了幾句,又對著我們大喊:“抓緊走吧,我們要關門了!”
我們離開話劇團,各自打車準備回家。臨走的時候我對薇薇說:“對不起,我今天太困了。”
薇薇笑了笑:“沒什么,你一定是看了很多次,才覺得無聊。有機會我們再見吧!”
回到家,我依然為當天的事情感到內疚。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女生約會,很可惜,被我搞砸了。朵朵跑過來,問我今天出去干嗎了。我知道,這一定是姐姐派她前來打探消息。
走進廚房,姐姐正坐在板凳上削土豆。我說:“我今天去了話劇團,沒看見韓曉東,你們是不是見面了?”
姐姐頭也不抬地說:“你去那里干什么,他早就不在那里干了。”
我有些吃驚,明明幾天前還看見他在朋友圈里轉發劇團的宣傳海報,于是又緊接著問道:“我怎么不知道?”
姐姐說:“你該多操心一下自己的事情,再找不到工作怎么辦?”
我說:“我想好了,再不行我就走得遠一點,到外面看一看,縣城里機會太少。”
姐姐抬頭看了看我,不一會兒又繼續干起手頭的活,她說:“協議擬好了,過兩天就去離婚,房子歸我,朵朵跟著韓曉東。”
“朵朵不跟你嗎?”我立馬想到薇薇,想到瑪雅游樂場,想到自己以后再難有機會順理成章地前去,“為什么不問問我的意見呢?”我的語氣近乎斥責。
姐姐把土豆扔進菜盆里,抬頭說道:“你能幫上什么忙?到時候我去上班,朵朵都沒人看。”
我說:“我可以幫你帶朵朵,帶她去游樂園,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縣城我很熟。”
姐姐說:“沒人愿意整天去游樂園,你抓緊找工作,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我說:“你總是喜歡自作主張,是你先要離婚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韓曉東有哪里配不上你的?”
朵朵聞聲跑進來,姐姐的眼淚已經吧嗒吧嗒掉在地板上。
那天晚上我離開了姐姐家,正如姐夫韓曉東在某個初春的夜晚走出家門再也沒有回來一樣,我暗下決心,自己將永遠離開這里。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縣城里游蕩了很久。遠處的驚雷伴隨閃電預示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天氣太熱了,如果下一場雨,就會涼快很多。這樣想著,雨點竟然就吧嗒吧嗒落下來。
出租車往來的頻率正逐漸加快,商店陸陸續續地關門。大雨來勢兇猛,不一會兒,街面上就再也看不見一個人。人民商場也已經打烊,保安下班了,只剩下樓頂的彩燈在一片激烈的閃電中發出五顏六色的微弱光芒。雨淋在身上仿佛冰冷的子彈。我想,我已經身負重傷。
穿過地下車庫長長的陡坡,順著消防通道一路往上爬,雷電的聲音早已經聽不見了,漆黑的樓道里只剩下安全指示牌綠色的光和刺耳的滴滴聲。在黑夜的掩護下,我再次來到了瑪雅游樂園。
憑著記憶,我熟練地翻過護欄。沒有了薇薇的紅色印章,我成了一名偷渡者。躺在游樂園中央的滑梯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不光因為這偷渡的欣喜,在被大雨淋濕的空氣抵達之前,我明白,這里依然殘留著薇薇的香氣。我拼命地大口呼吸。
遠古的神秘預言似乎在此刻向我召喚,讓我開始想象人類誕生之后第一次新建的家園,場景正如同我眼前的游樂場。在語言被發明以前,愛情是一場難以言說的游戲……
滑梯底部的優美曲線貼合著我的身體,躺在這里,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明天一早,薇薇會來這里繼續上班,她一定不會想到,我曾在暴雨侵襲的夜晚光臨瑪雅游樂園,并把其中一架不起眼的兒童滑梯當做自己的床。
這樣舒適的夜晚總是讓我想入非非,我接二連三地想起從前的許多事情。想到父親的離世,他曾是縣城里一名誠實的鎖匠,在母親去世之前,對于生活他從未有過絲毫抱怨。想起姐姐的婚禮,那一天,意氣風發的韓曉東出盡了風頭,他是話劇團的知名演員,享受著無數年輕女人的愛慕。想到薇薇,我跟她的第一次約會,她是個如此開朗又善良的女孩子,我內心篤定這樣一個事實:凡是來過瑪雅游樂場的男孩,沒有一個不愛她。
這是我一天之內第二次進入夢鄉。瑪雅游樂場消失了,眼前是一片長勢茂密的玉米地,玉米穗金黃飽滿,綠色的秸稈高大粗壯幾乎擋住我的去路,大雨剛剛過去不久,太陽光炙熱刺眼。薇薇穿著新娘的衣服輕快地從遠處走來。
我問道:“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在這里?”
薇薇笑靨如花,說:“你看見韓曉東了嗎?我找了他很久都沒有找到,他已經不在話劇團工作了。”
我說:“我早就知道了,他是我姐夫。”
薇薇說:“上次你騙了我,以后你可不能再騙我了。”
我說:“好,以后我再也不騙你了。”
薇薇又問我:“朵朵怎么沒跟你一起來?”
我說:“我不知道,我已經很久沒見她了。”
薇薇臉色一變,呵斥說:“是你把她弄丟了,你以后不準再來這里。你看,這里只有女人和孩子。”
這時,玉米林里突然傳出巨大的聲響,原本堅硬挺拔的玉米秸稈紛紛倒地不起,無數的陌生人正從四面八方向我們涌來。
薇薇說:“你抓緊走吧,再晚就來不及了。”
我揮舞著雙手急于離開此地,兩只腳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抬起,低頭看時,我才發現它們已經變成玉米根莖深深扎進了地里。這下我再也跑不掉了。
千鈞一發之際我睜開了雙眼。天亮了,游樂園已經開門營業。兩個孩子正拼命拖拽著我的雙腿,企圖將我搬下滑梯。周圍人聲鼎沸,兩個小男孩在后面的空地上為了爭奪一只藍色的皮球而大打出手。把守游樂園入口的中年婦女跟一個懷抱嬰兒的母親高談闊論。
薇薇沒有來。
從滑梯上慢慢滑下來,我感到有些頭暈目眩。翻越護欄的時候,中年婦女看了我一眼,問:“你是怎么進來的?”
我說:“我認識你,你是薇薇的小姨。”
中年婦女不再說話,直到我走出很遠,回頭看見她側著腦袋跟那名母親指指點點。
走出商場,我的心里感到有些遺憾,剛才應該問一下,薇薇為什么沒有來。韓曉東突然打來電話,說他跟朵朵在瑪雅游樂園,問我要不要過去見一面。
雨后的縣城變得格外清晰,柏油馬路烏黑發亮,新鮮的空氣吸進肚子里令人產生飽腹感。我想都沒想就把電話掛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