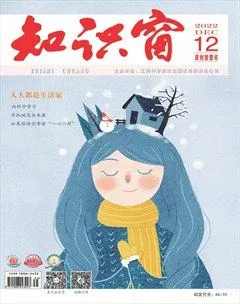以雌鷲為師
程應峰

詩人史蒂文森除了寫詩之外,還在一家保險公司上班,他每天上下班都安步當車,就算刮風下雨也難得坐一次車。他這樣做,目的是一邊走路,一邊作詩。他若左搖右擺,步伐緩慢地行進,那一定是在構思詩篇。
作家吉爾回憶說,有一次,一位朋友看見史蒂文森從門前走過,只見這位詩人腳步越來越慢,后來還停了下來,站在那里身體搖晃一兩下,然后后退一步,猶豫一會兒,接下來便挺起胸膛大踏步前進。看他的樣子,如同將一句詩再審讀了一次,刪掉了一個不滿意的字,換上了更優美的詞,并且續寫出了下一句。
托爾斯泰對普希金的小說極為推崇,甚至認為比普希金的詩歌還要好。托爾斯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時,想了幾十種開頭都不滿意。一天,10歲的兒子謝廖沙給托爾斯泰的姑媽朗誦普希金的小說。謝廖沙順手拿起書,剛念完第一句:“客人們紛紛來到別墅……”托爾斯泰聽到后,贊不絕口地說:“寫作就應當是這個樣子,普希金是我們的老師……要是換個別人,就會先把客人和房描繪一番,而普希金卻開門見山。”
19世紀,俄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果戈理,對自己的作品相當苛求。有一次,果戈理給詩人茹科夫斯基朗誦自己剛寫好的劇本。朗誦是在午飯后開始的,茹科夫斯基有午睡的習慣,難以改變,他一邊聽著果戈理朗讀劇本,一邊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而果戈理并不知道詩人有這個習慣,還以為是自己的劇本沒有魅力。
等茹科夫斯基小睡一會兒后,果戈理說:“您瞧,我請您批評我的作品,現在你的瞌睡就是對它最好的批評。”說完就把手稿扔進火光閃閃的壁爐。次日,一位朋友問起這個劇本的事,果戈理只是擺了擺手。
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福賽斯,走上專業作家道路后有一個習慣,每寫完一部作品,總要先讓6個人過目:妻子、父親、母親、出版商和兩位代理人。他認為,父母代表一般讀者的閱讀水平,如果他們看不懂某一情節,就說明作品不夠通俗,需要改寫。如果妻子感到某個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脫離實際的,他就會改寫部分情節或對話。最后,再由6個人投票表決,假如4票贊成,就算通過;假如3票反對,3票同意,那么由他自己投票決定該書的命運。
有位青年很喜歡寫作,卻怎樣也寫不出好作品,便埋怨靈感不登自己的大門。一天,青年走在路上時,偶遇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他正一邊走路,一邊構思新詩。青年趕上前去,對馬雅可夫斯基說:“先生,聽說您非常富于靈感,而我為什么總得不到呢!”馬雅可夫斯基停下腳步,打量著這位青年,幽默地回答說:“噢,靈感需要磨蹭,它大概不喜歡風風火火的趕路人吧!”
一位詩歌愛好者問詩人特拉亞諾夫:“怎樣才能獲得靈感,寫出好作品?” 特拉亞諾夫笑了笑,說:“一只雌鷲一次要生出三只蛋。它丟掉其中一只,只孵另外兩只。待雛鳥出世后,雌鷲又只給其中一只哺食。以雌鷲為師,專注些,何愁寫不出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