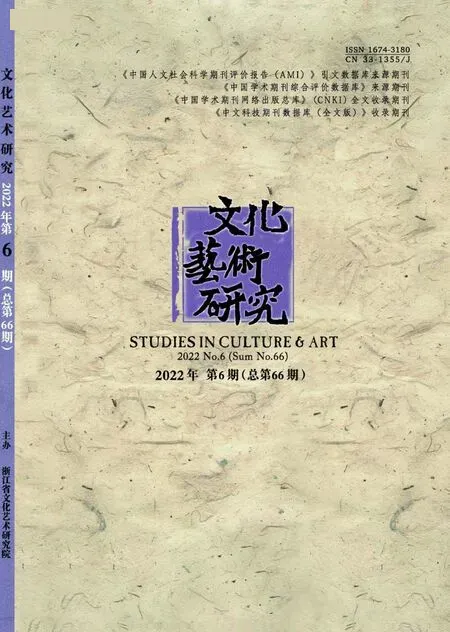藝術真理唯一性的哲學解構
蔡 靚
(澳門科技大學 人文與藝術學院,澳門 310023)
隨著各種新的科學技術、電子機械影像、美學理論、政治文化的出現,以及對傳統古典藝術規則的瓦解,藝術的本質問題在圖像泛濫的時代中逐漸被淹沒,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討論“藝術作品是什么”這一本質問題。其實也就是要回答“什么是藝術?為什么是藝術?”的問題。在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理論以后,藝術作品的原創性和唯一性被消解了,原作和復制品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引發了藝術的本質問題,即藝術的本源性問題和真理性問題。本雅明認為,新的作品被現代機械無限復制,作品的獨一無二性便不復存在,從而導致靈韻的消失,藝術價值也隨之發生變化。古典的傳統藝術在宗教層面上具有膜拜價值,但機械復制后只有展示價值,并且欣賞價值和效果也發生了變化。海德格爾從物性的存在主義角度出發,提出藝術作品中真理的自行置入與建立是藝術作品之本源。這與本雅明的立場有所不同,但也有相通之處。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在身體理論中提出藝術是有意義的身體的呈現,即從藝術的感知和體驗出發回到人本身,藝術的樣式和空間都與身體發生作用,是心與眼、身與心的關系。人的知覺都以身體化為其存在的真實,藝術起源于肉體感知客觀世界后的身體運動,于是一個真理就發生在作品與畫家、作品與觀者之間,這一“具身性”的提出對當代工業化時代的藝術是有其意義的。但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依舊提出了身體性這一藝術的本質論,正如海德格爾提出的藝術真理的本質論一般。這三人提出的理論都指向了藝術的本質性,即主體性。那么,什么是藝術本源的主體性?藝術本源的主體性在當代是否依舊成立?本文試從哲學層面做出解釋,并解構藝術本源之主體性。
一
海德格爾在《藝術的本源》一文中對藝術作品中的物性與藝術性、形式與質料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追問與闡釋,提出藝術作品中真理的自行置入與建立是藝術作品之本源。海德格爾對藝術的思考有別于美學、哲學、文藝,并不屬于現代學術思想的領域。他提出“讓事物回歸到事物本身”,即讓存在者在存在中實現其自身的本質,也即現象學所說的讓事物直接呈現的方法論。這在他的《藝術作品的本源》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該著作明確表述了海德格爾對藝術的思考不屬于美學范疇,而在于對存在之本質的思考的路徑上。[1]藝術既不被設想為文化成就領域中的現象,也不被設想為一種精神現象,藝術歸屬于成已發生,即“存在的意義”只能由此而得到規定的成已發生。
存在是什么?在傳統意義上的存在論那里,存在是具有“自身同一性”“永恒不變性”“連續同一性”等的狀態,比如柏拉圖的“理式”、基督教的“上帝”、笛卡爾的至上“上帝”、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而海德格爾的“存在”是指在去蔽與隱蔽沖突中呈現出來的被日常世界“去蔽”而具有有用者狀態的“無蔽狀態”,或者被科學世界“去蔽”所呈現的“客體狀態”以及被科學技術去蔽所呈現出來的“被訂購者的狀態”,也可以是被藝術世界去蔽而呈現出來的“自身鎖蔽的狀態”,所以存在是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的,具有多種可能性。藝術與存在主義有著密切的關聯。海德格爾將藝術本源定義為世界與大地的爭執后出現的裂隙與真理的自行置入的自我的確立,將藝術作品之真理的自行置入作為藝術本質的根源問題,顯現了海德格爾所認為的藝術之本質是主體性的,也是唯一性的。
海德格爾在書中探討了梵高的那雙“鞋”。雖然梵高的“鞋”在歷史上引起了爭議,但人們都是在對物本身進行追問,最終關注的都是藝術再現中的真理問題是否具有科學性和普世性。海德格爾認為,梵高所畫的《鞋》(圖1)是農夫腳下的鞋,是農夫生活狀態的凝固的表現形式之物,也是超時空的自在之物。而夏皮羅認為,這是梵高的私人物品——鞋,是梵高的自畫像,梵高是自圓其說并欺騙了自己。對此,我們沒有證據也無法判斷誰對誰錯,但是為什么海德格爾可以如此富有激情而自信地去描述這是農夫的鞋?因為海德格爾對藝術作品的關注并不是落在藝術作品的表象,而是藝術作品的真理問題,也就是說,通過藝術作品去理解物之外的其他東西,即物外(something else)。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藝術作品“物性”的問題。

圖1 《鞋》,梵高(1853—1890),1886年,油畫,37.5cm×45cm,荷蘭阿姆斯特丹梵高藝術博物館藏
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的物理因素承載著藝術作品的本質屬性。這一論斷顯現了其對藝術作品本源的分析落在作品的“物”上。藝術作品之所以成為藝術作品,是因為其超越了自身原本作為物的功能而產生了“隱喻”,這種隱喻的內容正是藝術作品在制造過程中自行置入的,或者說是“被融入”的,所以藝術作品就是“符號”,這與結構主義之父索緒爾提到的“能指”和“所指”原理有類似之處。海德格爾說的“物”是索緒爾說的能指,海德格爾說的“物外”是索緒爾說的所指,“物”和“物外”的結合就是藝術作品,這是具有隱喻或象征性的“符號”。對于“物”有三種解釋:第一種是質料物(純然物,如石頭、水泥、金屬等自然物質),這種解釋忽略了人與物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二種是感知之物,感知是人的思維意識,這種理解過于強調人的主觀意識;第三種是造型之物,即對物本身的擾亂。海德格爾所討論的物是其存在主義哲學中具有象征意義的物,和莊子《齊物論》里所說的物是不一致的。一件物品從何而來,成其所是并如其所是?第三種對物的解釋“造型之物”其實與藝術作品相關。造物是對物的本身外在形式的擾亂,改變物的形式而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如同亞里士多德早期的“四因說”提出的“質料因”到“目的因”的轉變。海德格爾認為,雖然這是藝術作品里呈現的器具,但除了器具的功能外,還有器具之“非物”的器具性,藝術家造物的結果即藝術作品具有物和物外的“雙重性”,這種物外就是特定的物具有特定承載的“物性”,當它顯現的時候就是符號出現的時候,那就是藝術作品之“藝術”的呈現。
在現實物中無法找到藝術,藝術是一種現象,并沒有對應于現實的物,所以藝術必須依附在現實的作品之上才可以顯現出藝術本身。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不在于模仿與表現物的普遍性,而在于揭示那個作品里所展示的物的“真理”,也即那個作品中實體的本性是什么,“創建”了什么,如何“創建”。他通過對梵高的《鞋》的論證來展現繪畫里的“真”。從表面上看,該畫作只是描繪了一雙普通的農鞋。如果我們僅從表象上看,那藝術理論就會陷入類似模仿論、再現論等的流行性言說;如果我們認為這只是一雙農夫的鞋之外形描繪,那就陷入了藝術“模仿說”;如果我們認為是藝術家借此鞋表達對農夫的情感,那就陷入了類似“表現主義”情感情緒之范疇;如果我們認為畫面上的鞋是某種象征物,那就陷入了藝術的象征論言說。海德格爾認為,這都不是藝術的“真”。按照他的“此在”理論邏輯解讀,這不是單獨的、孤立的鞋,而是一雙與世界發生關系的鞋,“鞋”只是一個符號,符號的功能是“物外”,這不僅是可見的鞋,同時還自然帶來不可見的“無蔽狀態”,是敞開自身的真實性。海德格爾在鞋性的解讀中呈現了農夫與大地的關系,農夫穿著這雙鞋行走,使農鞋得以在大地與世界的關系中堅固其有用性。人和器具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人靠著器具而生存,器具在使用之中而存在。通過對農鞋的解釋,海德格爾還揭露了存在者的“無蔽狀態”是如何發生的,藝術作品之“藝術”又是如何發生的。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有兩個特點:其一,建立一個世界,同時以大地為基礎;其二,作品中所建立的世界和自然涌現神秘物之大地的沖突生發了存在者的“無蔽狀態”,簡單地說,是世界與大地的對立來創建“真理”。可見海德格爾對藝術詮釋的出發點不是藝術本體論,而是以對“存在”本身的研究為核心的本體論問題,這有別于沃爾夫林、李格爾、潘諾夫斯基、夏皮羅等西方正統藝術史學家以藝術作品為中心的客體研究。
不妨借鑒海德格爾的藝術本源理論對米開朗琪羅的雕塑作品《大衛》(圖2)做進一步解釋。《圣經》寫到年輕人大衛決定出去和腓力斯的勇士哥利亞作戰時,把大衛的年輕描繪成近乎天真,比如他丟棄了國王給他的保護身體的盔甲,因為他認為盔甲使他無法敏捷前進,所以只留下了手杖、投石器和光滑的石頭。這正是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塑所塑造的一個年輕人拿著他的作戰工具的形象。作品揭示了那個時期年輕人的天真,以他們的勇敢和無畏面對殘酷世界所顯現出來的真相。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他建立了一片空地,在那里遇到了指引方向的道路,這種無所顧忌、勇往直前的勇敢之心源于年輕時的天真與無畏,而構成一個人的心情和處境可能是因為“年輕”的一種假象。和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人物一樣,現實中,個人的很多決定源于年輕時的天真。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塑體現了對大理石這一物質重新排列后“真理”自行置入的藝術本源,即以物顯真的特性。

圖2 《大衛》,米開朗琪羅·博納羅蒂(1475—1564),1501—1504年,大理石雕塑,高3.95m,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術學院藏
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里指出,“藝術”是在現實世界里找不到對應物的一個詞,藝術作品里的物因素是藝術家創作的質料與基底。他認為,從作品的質料和形式出發,把藝術轉嫁到物上并呈現出來或敞開來的東西,是藝術的最終歸宿。但同時我們也發現,海德格爾對藝術本質的闡釋是建立在作品的物性之上的,其對真理置入作為藝術本源的主體唯一性的確立忽略了梅洛-龐蒂所主張的身體和肉體的存在,這是他早期受到質疑的關鍵問題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借梵高的《鞋》闡述自己的主張,是具有局限性的。
二
梅洛-龐蒂以對塞尚和克利兩位藝術家的藝術創作的揭秘,再次引領了對于藝術中的真理和真理的藝術的探索,他提出藝術的本質具有多樣性,豐富了海德格爾對于藝術本源單一性的理論闡述。
在梅洛-龐蒂這里,“真理的起源”是一個從未完全實現的話題,雖然在他的《可見與不可見的》中,考慮了兩個暫定的書名《真理的起源》和《真理譜系》,但最終都沒有完成,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他的晚期,哲學提供了對單一起源研究的批判。福柯的譜系學也為藝術提供了一個思路。進入歷史,會發現事物背后存在“完全不同的東西”,不是永恒的基本秘密,最真的秘密在于它們沒有本質,或者它們的本質是一種形而上的編造,對起源的追尋在時間上越走越遠,越來越趨于多重起源。所以,探尋梅洛-龐蒂的藝術作品真理的起源話題時,我們需要關注“起源”的關鍵性作品,其實就是對海德格爾的藝術的“真”之自行置入這一本源問題提出質疑:藝術是否真的存在唯一性的本源?
什么是藝術中的真理起源?更確切地說,一個或多個關于真理的問題如何構建?這其實是關于認識論的問題。梅洛-龐蒂認為,它與感知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和肉身運動的真相有關,對真理的呼喚還涉及動作真實的感覺。多納德·蘭德斯(Donald Landes)通過對梅洛-龐蒂的《眼與心》的研究認為,梅洛-龐蒂從現代繪畫的歷史演變中挖掘出了豐富的存在論意義。梅洛-龐蒂對繪畫的哲學思考使存在論在藝術中得以鮮活呈現,其繪畫理論也被稱為“繪畫存在論”[2]。作為法蘭西學院候選人時,他在提交的文稿中寫道:“我們永不止息地生活在知覺的世界中,但在批判思維中我們卻繞過了它——竟至于遺忘了知覺對我們的真理觀念所作的貢獻。因為批判思維面對的只是它或討論、或接受、或反對的空洞命題。批判思維已經粉碎了事物的素樸明證性……”[3]梅洛-龐蒂的早期著作《知覺現象學》(1945)和《塞尚的懷疑》(1948)對保羅·塞尚的藝術作品和著作的研究,以及后期著作《眼與心》,顯示了保羅·克利的藝術作品和著作對他晚期本體論和美學思想的深刻影響。
我們對塞尚的一只耳朵的自畫像印象深刻,其實保羅·克利在他的自畫像中就顯現了藝術家的“向內看”,以緊閉的眼睛和沒有耳朵為象征符號表現全神貫注的沉思。人們會詢問:這種“向內看”或“內向看”可能意味著什么?克利認為,他的畫作反映了內心深處,他畫的臉比真實的臉更真實。在筆者看來,這不僅是畫家保羅·克利的內心深處,還是“創造之心”,因為克利對準確反映表面現實的畫沒有絲毫興趣。
梅洛-龐蒂也認為,現代藝術家不希望繪畫與現實世界的真理有任何相似的關系。在《眼與心》中,他提到了自畫像中藝術家與鏡子之間的關系。這里的“鏡子”與所謂的“鏡像功能”不同,或者說消解了鏡子的實用性功能,而轉為向自己展示這個人,鏡像功能旨在表達圖像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在鏡子中,“我”的外部性變得完整。梅洛-龐蒂特別強調了鏡像的外在性,認為鏡像是我們的身體和我們自己處在與他人共存中的揭示,而不是按照拉康的說法,鏡子與利己主義甚至自戀有共同關聯。同樣,克利對鏡子的真相的描述也否認了鏡子的功能,其所謂的內在真相是內心的真相,他向我們展示了比真實的面孔更真實的人臉。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內在性是畫家內在神秘性的顯現。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前言中說:“更確切地說,沒有內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認識自己。”[4]胡塞爾說,我們的生命體是我們在世界上的個人和個體錨,用于我們在空間中的運動和方向感——上、下、右和左,所以地球與身體也錨定我們的運動和方向感、平衡、重量和重力。
在克利的闡釋之后, 海德格爾對自己提出的藝術本源論有所動搖。在《關于克利的筆記》(1960)中,海德格爾再一次思考存在與藝術的關系,和德勒茲、利奧塔以及梅洛-龐蒂都關注“藝術如何讓不可見成為可見”。他認為克利并不像梵高一樣描畫了器具的世界,而是描畫了世界本身(在更廣闊的意義上,比如宇宙、生命)。這是由克利作品的生成性決定的,唯有像克利這樣不斷生成和變化的藝術家,才能了解到世界的本質是變動不居,使世界最容易被理解的表達,就是將生成生長而不是生成最終之物展現在作品之中。海德格爾認識到“生成”是克利藝術的關鍵點,他評價道:“運動的自由在于無限的生成。”①轉引自蘇夢熙:《使不可見者可見:保羅·克利藝術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頁。這與德勒茲“任何一種解域都伴隨著另一種建域”的藝術發展理解同理。可以說,海德格爾以對克利的闡釋來反對傳統美學之“形而上”。
從克利1924年的作品《演員面具》可見,他通過線條的聚攏和分散來呈現臉部的五官與神情。但對臉部造型的呈現并不是克利的目的,他所要表達的是從二維到三維“力”的運動之變化。線條向內的力出現了層疊,向外散開的線條呈現了分散的力,線條分散后聚集的一個點成為一個新的起點,這種力的存在是一種力的運動形式,可形成多樣化的視覺表征,除了線條的兩對力之外,也同樣體現在色彩之間,向內的色調是深色,向外的為淺色。開始,宇宙的相反力是不存在的,只是因為光的出現,世界呈現了運動和生命,光喚起了對黑暗的對抗,于是我們找到了重力與引力內部對抗的中間點,也就是力的平衡處,也是生命內部和外部的交界。所以,可以判斷的是,克利在他的藝術中尋求的真理是“運動”。他的一幅水彩畫Physiognomic Genesis(1929)展現了橙色、棕色和黃色的節奏,前景部分可能被認為是地球土壤中的沉積物,從中升起類似于植物芽的中間區域,展開一朵花。在地球和植物上方,一個遠離地球的位置,是另一組沉積著黃色、綠色、藍色和紅色層的設置,支撐著一個向天空移動的黑球。這幅畫以描繪地球史前史和歷史中看不見的過程,很好地說明了克利將藝術稱為“地殼形成的寓言”所包含的意味。他的另一幅水彩畫Physiognomic Lightning(1927)展示了兩種異質元素:一個是圓形的,另一個是平面系列的褶皺。曲折的閃電主動沖擊畫面的中部,異質元素之間的張力帶出動感,這也證明了運動與流變是藝術的起源之一。
克利在魏瑪(Weimar)與德薩(Dessau)的授課中也說道:“所有的造型就是運動,因為他們會在一個地方開始,到一個地方結束。從世界觀到形式再到風格,風格是概念的判斷標志,風格是人對于凡世(靜態)與來世(動態)這樣的問題之態度。”[5]莫里斯·梅洛-龐蒂在《符號》前言中表示:“人只是在運動中。同樣,世界只是在運動中,存在(Etre)也只是在運動中。”[6]他所說的運動,不是A到B的位置的挪移,而是銘刻在場的“形狀或品質的紋理”和“景觀內部動態”的變化。其實海德格爾也曾指出,藝術的起源問題不在于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藝術的本質問題,而在于克服一種將存在(being)作為再現的客體對象的美學解釋。[7]即,藝術要脫離對物與人的主宰,其實質是背離傳統的形式和顏色等物化性質的游戲,使其關注視覺現象中身體-主體與世界的關系,這也正是梅洛-龐蒂在身體現象學中所提出的主體間性的問題。
作為時間的空間是梅洛-龐蒂在《眼與心》中對繪畫意義總結的背后的東西,即用時間的變化創造藝術的空間。“既然繪畫已經創造出了潛在的線條,它可以通過振動或輻射表現出某種沒有移位的運動……繪畫向我的雙眼提供的東西有點接近于真實的運動向它們提供的東西:適當搞混的一系列瞬間景色,以及,如果涉及到一個有生命之物的話,一些停留在先與后之間的不穩定姿態。”[8]梅洛-龐蒂在《對塞尚的疑惑》中說,對塞尚來說,要畫成一幅靜物畫必須工作100次,而畫成一幅肖像畫則要對人物的姿態改動150次,也就是在不同的時間中體現真實的視覺空間。因此,我們認為,他的作品只是對繪畫的不斷嘗試,也是對肉眼真實的逆反,是對印象派的反抗,對肉眼之一瞬間的可見世界的不信任,重返事物的本身,對自然極端地尊重和重視。
塞尚在作品中呈現的透視規律是有悖于以往透視學的,是一種感官的“透視”,而非幾何學或照片的透視。所以,在他的繪畫中有一種二律背反:不離開感覺來尋找真實,在直接的印象中只以多次自然視覺為向導而拒絕其他,沒有幾何透視與輪廓,也不調配顏色,這就是貝爾納所說“塞尚的自我毀滅”之所在。他追求真實,卻又禁止自己去使用達到真實的手段。在1870至1890年間,在塞尚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畫面呈現物的“變形”,放在一張桌子上的碟子或高腳杯從側面看應該是橢圓形的,可是橢圓的兩個頂點卻被展高了,橢圓被擴張了。塞尚在對物體的100次凝視中發現了每次物象的不同,這印證了阿恩海姆在《沉思與創造力》中探討的日本心理學家所做的實驗。阿恩海姆通過實驗指出,隨著人的眼睛長時間的觀察,感覺器官的某些電化反應開始下降,當眼睛暴露在不變的刺激下,對視力至關重要的光敏物質就會耗盡,也就是說眼睛長時間聚焦后,新的模式就會出現,支配結構開始瓦解,眼睛也從支配結構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于是一種看不見的模式開始出現,如對象的對稱性結構破壞,次要細節的變化以及形成不同組合的整體感覺。塞尚的100次作畫正是在不同時間段,通過拉長時間過程,用大量的視覺觀察時間去看一個物體,而非第一眼的視覺感覺。對物體的多次觀看與長時間的反復觀察,目的是實現事物在視覺表象之外的真實。他為居斯塔夫畫的肖像是違反透視規律的,但是塞尚醉心于感覺的混沌或者說知覺的疊壓和對幾何透視心理的停止,來產生物體在視覺“流變”中的“真相”。塞尚希望把二者結合起來,并把這種統覺放在幾次堆積的感覺當中,并求助于智慧,把它組織成作品。可見藝術是一種個人的統覺,萊布尼茨說,這種統覺是由內心狀態反射出來的意識與認知。而康德認為,統覺是自身的意識活動的再現,也可說是一種經驗統覺,每個人的身體在不同時空中經驗著現實世界,這種經驗的統覺就意味著真實的世界是運動與流變的,模棱兩可與混沌的,這證實了我們的肉眼在第一時間所見的東西不是物體最真實的一面,我們的身體所經歷的也不是真實的,肉眼所見的“真實”具有欺騙性。
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強調流動性、運動性與不確定性作為藝術本質的起源,即,藝術本源不只是真理創建之唯一性,而是建立在界定主體性的關系之中,即主體間性中。主體間性是對主體性的背反,主體間性是由自身存在的結構中的“他性”界定的,也就是說藝術的本源不是由主體性來界定的,“他性”的影響會使主體性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遇見塞尚圣維克多晚期的水彩畫后,海德格爾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了另一個走入繪畫的真相:藝術的本質將是存在者將自己投入“工作”的真理,藝術“工作”是關系到認識主體在創作藝術中以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先驗的影響,藝術創作正是藝術家再現自身對藝術的理解的各種外在方式。這就表明,如果我們只抓住作品的物性的話,是看不到作品本質的,要發現作品中某種未曾顯現過的東西,實則是基于現象學基礎之上。現象學最真實、最本真地顯現了事物存在的原因和方式,透過事物本身的現象與個體的感知來發現我們視而不見的隱秘的東西。這也避免了藝術模仿論、功能論,回到對事物本來面貌的探索,即:主體對事物本身認識上的“流動”與“運動”所引發的真相介入藝術創作。這種對主體性的哲學解構是主體間性對藝術本質的塑造,這種主體間性也決定了藝術的本質具有流動性、不確定性和多樣性的本源。
三
藝術在古希臘被理解為“美的藝術”(手工藝藝術),后來,又被理解為“詩的藝術”,是自行涌現的藝術。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學術界,陳述者與被陳述者符合一致性的藝術才被理解為藝術作品,即作品與其所表象者(作者創作意識、經驗、觀念、超驗等事物)相一致(再現、表現、象征等)。現代藝術以藝術表現論、再現論、象征論等話語權展現于藝術界,其本質都是在宣揚藝術的本體性,但其實沒有真正涉及藝術的本質秘密,藝術的本質論至今還是一個不可言說的“謎”。雖然海德格爾對藝術的看法是,藝術創建存在者的“真”(無蔽狀態)本質上有別于再現、表現和象征,但他早期從物性分析到真理——真之質的置入,依舊是陷入了藝術的主體性單一論中,因為藝術的本質的唯一性在梅洛-龐蒂、海德格爾(后期)、拉康那里已經轉向。基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之言說,藝術作品應該離開功利性和實用性而去找回事物原本的樣子。從克利關于他畫的臉比真實的臉更真實的陳述,以及塞尚的作為時間的繪畫空間告訴我們真相開始,我們知道藝術作品或藝術活動是人的主體意識自行運動、相互關系的結果。這也啟示我們,對藝術本源的解釋要避免進入主體性一元論范疇。藝術本源意義是世界、主體間性、言語和虛擬化的網狀交織,有其持久性、流動性、敏捷性、微妙性和深度,它在各種運動、創造以及創造的欲望中存在多種起源,不能以單純的邏輯性的“真理”概之。
藝術的主體性是被解構了的,主體性走向虛擬或虛構,藝術的本真性也并非存在于主體唯一性之中,而是建立在界定主體性的關系之中,即主體間性中。這種主體間性是指此意義并不存在于主體中,而是存在于界定主體性的關系中,這種關系是多元和虛擬的。本雅明、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從不同的主體維度論述了藝術的生態場景和問題的發展,由此,主體間性決定藝術的本真性是一個連續的、流動性、多樣性的網狀交織狀態。藝術真理的唯一性解構也為藝術提供了一種新的哲學認知。當下政治文化邏輯對藝術本真的綁架引起了藝術家的現實焦慮,對藝術本質模糊的焦慮也影響了藝術創作的純粹性。如何使創作者與創作、創作者與觀看者、作品與受眾者之間的焦慮轉嫁出去?對藝術中世界與大地對抗“無蔽(真理)的再次解密”,我們要以發展的角度給予更好的解釋與完善,這也是對德勒茲眼中的藝術——去中心化、綿延、流動性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