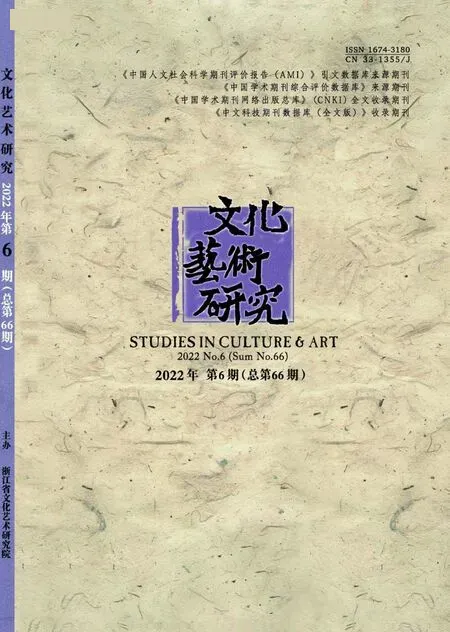回到“云南”:中國民族器樂“創新性發展”的路徑與可能
——以中阮《云南回憶》為例
張碧云
(上海音樂學院 民樂系,上海 200031)
優秀傳統民族音樂的承繼是現代音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然而,如何“承繼”?是蕭規曹隨地繼承舊日曲譜,或是自出機杼地進行多媒介混搭?藝術理論界似乎迄今還缺乏自覺的認識。20世紀初,歐風美雨為中國音樂的發展打開了一個新窗口。新音樂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音樂的實踐帶來了“古今”“中西”“雅俗”間的不同張力。如何面對傳統音樂和外來音樂文化以及當下新音樂,無疑是每一位中國音樂家面臨的至為重要的課題。如今,中國的發展站在了新時代的坐標上,音樂家應如何在當代新音樂的發展歷程上,解決“中西”“古今”兩大關系呢?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的“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1]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何以可能,如何實現?
阮是一個極具個性的民族樂器,曾一度陷入沉寂,劉星的《云南回憶》可謂給它創造了一個復興的機會,使中阮的發展出現了一次重大轉折。由解讀其人其作入手,可以重新認識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樞機。
一、橫空出世的阮樂《云南回憶》
阮,古人稱之為“秦琵琶”,是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彈撥樂器,相傳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它起源于秦漢,鼎盛于唐宋,沒落于明清。民國時期,鄭覲文等人曾以各類古樂文獻作為依據,嘗試對古代阮予以復原,但限于各種客觀條件,各類仿制阮都未能得到較好的推廣,業界對其的關注度也不高。新中國成立后,王仲丙、張子銳、王勇等阮樂演奏家、教育家對阮這一樂器進行了復原與再造。他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再造并完善了我們今天通用的現代阮。現代阮既繼承了古代阮的文人品格,又體現了當代國樂家對于西方十二平均律律制的吸收,成為了一件融匯中西的現代民族樂器,為其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現代阮出現后的數十年里,它一直未能擺脫伴奏樂器的身份,表現力有待深入開發。人們對于阮音色的審美理解和認知,大多沒有脫離古代詩詞中關于阮樂表演場面的描述,“非琴不是箏”①“非琴不是箏”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和令狐仆射小飲聽阮咸》,該詩描寫了唐代樂人演奏阮技驚四座的場面,其中對阮音色“非琴不是箏”的描述成了后人對古代阮樂展開想象和重構的重要依據。仍然是人們對“理想阮樂”的定位和要求。直到1987年,青年音樂家劉星的中阮協奏曲《云南回憶》問世,才使得民族音樂界重新認識了阮。協奏曲以幻想式的曲風、迷人的風情、超脫的意境、渾厚的音色、多變的節奏,令人耳目一新。
《云南回憶》首演之后,其鮮明的革新性引起了學界和中阮業界的高度關注。不少音樂理論家圍繞《云南回憶》的創作手法、文化立意等方面對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兩年后,趙詠山在《人民音樂》上撰文高度評價,認為《云南回憶》“不僅為中阮打開了新局面,并且是民樂創作新階段的代表作品”[2]。此論為《云南回憶》的歷史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調。隨著《云南回憶》的傳播越來越廣,不少演奏家基于自身表演實踐對《云南回憶》的表演技巧進行了深入的論述,但基本沒有跳脫出趙詠山一文的立論。2013年,喬建中在《中國藝術報》上發表《劉星與他的中阮協奏曲〈云南回憶〉》一文,以眾多一手資料對《云南回憶》的創作過程和創作特色予以了深入的發掘,指出該作品的成功與劉星與眾不同的“隱者”人格有著密切的關系。喬建中毫不吝嗇對《云南回憶》的贊譽之詞,指出“《云南回憶》獲得成功所產生的效應是長遠的、多方面的。毫不夸張地說,二十多年來,它已成為所有阮樂演奏家最喜歡的曲目”,《云南回憶》的出現,“為阮樂劃出了一個新時代”。[3]此外,黎家棣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古代阮與現代阮的比較》中,以《云南回憶》為個案,就西方音樂因素對現代阮樂創作的影響進行研究,指出該曲的出現“代表了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后,阮曲目創作的目的開始回歸到音樂上,政治影響開始變得模糊”,在創作上則體現了對流行音樂元素和中國傳統音樂因素的雜糅運用。[4]據筆者檢索知網發現,截至2022年9月20日,以《云南回憶》為篇名的論文有46篇,這些研究大多是從作曲技術和演奏技術兩個方面對作品展開論述,至于《云南回憶》的命名原因、創新路徑等依然有待深入思考,比如:《云南回憶》何以命名為“云南回憶”,只是表達“表現對那雖已逝去,卻久不能忘懷的歲月所產生的深切眷戀與啟示”嗎?《云南回憶》樂句究竟是如何與樂器互相生發的,或者說樂句如何發掘出樂器的潛能,舊樂器如何創造出新語言?《云南回憶》的成功只是一個孤例抑或可以成為一種范例?
二、云南回憶:何為“云南”,何以“回憶”
標題通常被稱為作品的心靈之窗。要對《云南回憶》這一阮樂創作個案的創新路徑予以深入的剖析,自然離不開其標題的能指和所指的分析。
我們從字面上理解《云南回憶》,就會自然聯想到這是創作者劉星對故地云南的美好回憶,的確有一些評論者是如此理解的。可事實上,劉星出生在東北,學習在上海,在創作該首樂曲之前,并沒有去過云南。他對云南的認知,大都來源于其妻子陳文的講述。既然從未到過云南,那么劉星在樂曲中的“回憶”又從何而來?
(一)何為“云南”:交疊時空的文化符號
作為少數民族聚居的中國西南邊陲省份,云南有著獨特的自然地貌和文化傳統。從亞熱帶雨林到雪山高原的復雜地理空間成就了其豐富的生態景觀,而漢族與幾十個少數民族聚居更形成了其多元的文化景觀。
在交通尚不發達的20世紀80年代,云南對身處北京的劉星而言,無疑是橫亙著時間和空間阻隔的遙遠存在。因此,與其說“云南回憶”中的“云南”是地理意義上現實存在的云南,不如說它是劉星想象中的烏托邦。云南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對劉星來說,并非是“親歷”的,但唯其并非“親歷”,才更容易激發“想象”,從而成為其馳騁藝術想象的最好場域。
劉星描繪的“云南”,是他心中的“云南”。這個“云南”,既是“自然”的,更是作曲家本人的,不僅是劉星用主觀能動性對自然本來面目的還原,更是他借助自我心靈的想象和創造。“云南”,既可以說是遠古時代里布滿神秘圖騰的無垠曠野,也是逐步融入國家現代化浪潮的少數民族文化匯集地。這是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并在藝術表達上充滿各種可能和張力的文化符號的場域。
這一藝術場域的創造和產生,和劉星奔放不羈、向往自由的性格有著密切關系。劉星曾經在一次訪談中指出,藝術是精神的產物,創作者唯有在廣闊的精神空間中才能獲得自由的思想,進而創作出別具一格的音樂作品。這也解釋了劉星為何會在20世紀80年代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樂團,成為了一位“自由音樂人”——在劉星看來,唯有自由,才能使他無限接近他心中的烏托邦式的“理想國”,而這樣一個遠離世俗的理想國正是他構建“云南”這一文化符號的靈感源頭。為此,劉星不惜辭去了體制內的工作,成為了一位自負盈虧、自謀出路的獨立音樂人。這樣的做法,即便在今天看來,他也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沒有對音樂的絕對熱愛,“出走天涯”絕非是理想之舉。[3]從這一層面來看,劉星奔放不羈、向往自由的人格,是他創造“云南”這一跨越時空之文化符號的原初動力。
《云南回憶》是筆者演奏的保留曲目之一。演奏時,筆者似乎在四弦的阮上,看到了這樣的一幅畫面:點點阮聲,猶如湖上閃爍的霞光,管弦樂隊營造的巨大音墻,如同霞光映照的平靜湖面。隨著阮的聲音越來越密集,音樂也隨之不斷向觀眾釋放出更大的張力。那面由管弦樂隊構建的恢弘音墻,如同自然界中有著不同面貌的湖面,這面湖既是深沉淵博的,也是光芒四射的。在劉星的精心編織下,這面湖成了阮的最美舞臺,承載了阮演奏家無窮無盡的音樂想象。全曲到了最后,所有的樂音匯為一點,用水沖刷調色板后傾瀉而下的色柱,使一切顏色都復歸自然,成了渙散在天地間與世無爭的泛音。劉星以阮的迷幻光影、管弦樂隊的恢弘音墻,達成了他本人的抒情,同時也為演奏家提供了抒情的靈性空間。
正是由于“云南”這一文化符號在劉星的筆下擁有了超越時空的特質,因此它所能容納的就不僅僅只有現實中云南的聲色情境,還有存留于劉星腦海中的對音樂的理解和思考。這個潛藏著無限張力的文化符號,不僅能容納中國源遠流長的國樂文化,更能融匯具有全球視野的音樂創作技術,因而為劉星的音樂創作及聽眾在聆曲后產生的想象,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而要理解“云南”這一文化符號中潛藏的可能性,需要我們再次解讀劉星的“回”與“憶”。
(二) “回憶”何為:回歸原點的音樂價值追尋
若從書面上來理解“回憶”一詞的意義,它指代的是我們恢復過去經驗的過程。但是既然劉星未曾在創作該樂曲之前親身前往云南,那么“回憶”一詞的原意在此處顯然是不成立的。與其將“回憶”直接理解為劉星對于往事的回想,不如將“回憶”分拆為“回”與“憶”二字進行單獨解釋,進而闡釋劉星在創作該樂曲時的原初理念。在筆者看來,“回”指代的是劉星回歸音樂以及中阮音色本原的嘗試和實踐,而“憶”則指代劉星對于過往音樂經驗的回顧和整合,劉星以別具匠心的“回”和“憶”,為他構建的文化符號“云南”添上了骨與肉,成就了《云南回憶》中別樣的音樂世界。
劉星對于音樂本原和阮樂原本樣貌的追尋,構建了他對于標題中“回”的理解和實踐。歌、舞、樂三者合一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音樂形態,在遠古時期,音樂承擔了祭祀儀禮、傳播信息的重要作用。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音樂承載了人的喜怒哀樂,見證了人類歷史變遷的悲歡離合,人類對于情感迸發和表達的主體追求,構筑了音樂的本原存在。盡管持自律論觀點的漢斯立克始終認為,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音樂的美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容的美。[5]但事實上,一定的音樂形式體現了作曲家的內在思想,音樂形式在“聯覺”的作用下,承擔了表達特定情感內容的作用。就此而言,音樂不僅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音樂具有承載內涵、表達情感的功能不言而喻。在筆者看來,追求音樂對于情感的表達,就是對音樂的本來面貌的追溯和還原。站在這一立場上,劉星充分發掘了阮的可能性,并透過阮這一樂器,完成了情感的抒發和表達。在劉星眼中,阮既可以是一把文人阮,更可以是一把逸發當代知識分子內心情思的現代阮。《云南回憶》的阮既帶有傳統的意味,更具備了如同吉他般的現代氣息。劉星以自己對于音樂本原的純粹追求,再次發掘了阮這一傳統樂器的無限可能,拓寬了阮樂的表演性能。而凡此種種,皆為劉星對于“憶”的實踐奠定了基礎。
劉星作為一位有著豐富音樂實踐經歷的作曲家,不僅精通月琴和阮的演奏,還在業余時間里接觸了鋼琴、吉他等西洋樂器。辭去黑龍江省歌舞劇院的工作之后,他只身來到北京,成為了一位自由音樂人。其間,劉星開始接觸流行音樂,并通過借鑒吉他的演奏手法,大膽地進行了阮樂演奏技術的創新嘗試。劉星在創作《云南回憶》之前形成的這些音樂積累,共同構建了他對音樂的理解,組成了其豐富的音樂世界。《云南回憶》作為一部充分體現革新性的作品,其中對民族調式的運用體現了劉星對傳統音樂的理解,而對西方流行音樂元素的使用則是劉星對現代音樂的思考,劉星的豐富多元的音樂世界,映射在了這部被冠以“云南回憶”之名的作品之中。因此,標題上的“憶”,其實就是劉星對自己的音樂世界的呈現,在這個呈現過程中,劉星過往的音樂經驗被不斷整合,進而形成了他獨有的音樂創作風格,造就了《云南回憶》盛演不衰的經典地位。
劉星對音樂本原和阮樂原本樣貌的追尋,既發掘了阮的無限可能,更為我們呈現了他內心音樂世界的繽紛多彩。《云南回憶》的“回”與“憶”,體現了劉星力圖回歸原點,追問音樂價值和可能性的努力。
三、可能世界的探索:《云南回憶》對國樂傳統的超越與再造
劉星在20世紀80年代《云南回憶》的創作中大量吸收了西方音樂創作技術的合理因素,在不拋棄阮樂以及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基礎上,大力挖掘阮的可能世界。
在對阮樂的可能世界的深入探索和積極創造中,筆者認為作曲家劉星在《云南回憶》中主要是從“西方協奏曲體裁結構的中國化探索”“創新運用特殊和弦和現代節奏型”兩個方面,拓寬了阮樂藝術的表現力。
(一)對西方協奏曲體裁結構的中國化探索
《云南回憶》作為一首大型民族器樂協奏曲,劉星對該曲結構和布局的設計體現了他力圖在音樂創作中內化中國音樂的風味,并使西方音樂體裁“中國化”的藝術構想。全曲由三個獨立的樂章組成,分別為:中庸的中板,呆滯的慢板,機械的快板。在結構上,劉星打破了過往中國傳統音樂中“散—慢—中—快—散”的布局模式,但也沒有一成不變地照搬西方協奏曲的程式化結構,使樂思得以在高度靈活的格局中自由回響。協奏曲作為西方重要的器樂體裁,凸顯“競奏”關系的特點,突出了西方文化中強調戲劇性表達的特質,而劉星對于協奏曲的運用和理解,始終未忽略這一體裁中鮮明的“競奏”屬性,這樣的做法強化了音樂的張力,為過往強調主從關系的中國音樂的審美帶來了新的沖擊。可以說,劉星以《云南回憶》這一作品,表達了自己對協奏曲這一西方體裁的理解和改造,為協奏曲中國化進程的探索獻上了寶貴的智慧。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中國樂壇上出現了專為民族器樂而作的協奏曲。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利用中國的民間音樂素材創作了民族器樂協奏曲《二胡協奏曲》、《琵琶協奏曲》、《貴妃之歌》(二胡與樂隊,衛仲樂首演)和《夜曲》。這位來華西人音樂家拉開了民族器樂協奏曲創作的大幕。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器樂的協奏曲作品盡管時有出現,但整體來看仍有不少缺陷——如配器單一、主題單一等。經過數十年的曲折發展,中國民族器樂協奏曲創作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劉星的《云南回憶》正是重要代表之一。《云南回憶》讓阮這一原本甚少被人關注的民族樂器,煥發出了新的生命色彩。它在充分凸顯阮這一樂器的表現力之余,還在保持中國音樂民族色彩的前提下,突出了協奏曲的“競奏”色彩,因此其價值不僅體現在阮這一樂器上,還在中國協奏曲創作的歷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為第一部專為阮樂創作的多樂章協奏曲,《云南回憶》借用了西方協奏曲的框架,為中國器樂創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云南回憶》盡管借用了西方協奏曲的“型”,但依舊內化了中國音樂的審美。它挖掘并創造了阮樂器更為廣闊的可能世界,為后來民族器樂協奏曲的創作帶來了寶貴的啟示。
(二)對特殊和弦與現代節奏型的創新運用
除借用西方協奏曲外,劉星還在《云南回憶》中創造性地運用了多個特殊和弦與現代節奏型。這些和弦與現代節奏型的運用,使樂曲具有更多的現代氣息,彰顯了阮的藝術潛力,拓寬了阮在音樂語言表達上的可能性。
1.特殊和弦的運用
《云南回憶》一曲大量運用了功能性以及色彩型和弦,其運用的密度在第三樂章中尤其高,展現了阮這一彈撥樂器極強的音樂表現力。在傳統創作中,七和弦、九和弦以及其他高疊和弦的使用并不多見,大多樂曲即便為了渲染氣氛,也只是運用掃弦的技術完成“音塊”的呈現。但是在《云南回憶》中,劉星為了凸顯樂曲的情緒,運用了大量橫向和弦、七和弦(見圖1)。這些和弦的運用大大拓寬了阮在音樂語言表達上的豐富性,挖掘了阮的舞臺潛力,提升了阮作為獨奏性民族樂器的地位。

圖1 《云南回憶》第三樂章
2.布魯斯節奏與新世紀音樂風格的嵌套
《云南回憶》除在特殊和弦的運用上可圈可點外,對布魯斯節奏和新世紀音樂風格的嵌套也頗為成功。新世紀音樂為追求平和的氛圍,大多摒棄了傳統的節奏模式,打破了音樂本身的平衡感。為了凸顯自然隨性的風格特征,新世紀音樂很少使用強烈的節奏,節奏的應用大多具有循環和模糊的特色,而《云南回憶》便體現了這一特點,凸顯了自身的新世紀音樂的特征。但值得指出的是,劉星對新世紀音樂風格的借鑒是巧妙的,選擇以重復布魯斯節奏以凸顯音樂的新世紀風格。(見圖2)

圖2 《云南回憶》第一樂章
這樣的做法為新世紀音樂添加了新的元素,同時也體現了劉星對兩種不同音樂風格的糅合能力。在《云南回憶》中,shuffle是劉星運用最為廣泛的布魯斯節奏型。作為爵士樂中常見的一種布魯斯節奏類型,shuffle常會以三連音的形式變化組合,來打破以往節奏規律的平衡。在樂曲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這一節奏型,這一方面固然和劉星在青年時期愛好吉他有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在音樂創作上不拘一格的風格特色。這種節奏型在樂曲中基本上都是以六連音的形式出現的,其中第一、三、四、六個音符是節奏的重音點,因此演奏者需要在演奏六連音的過程中將其理解為兩個三連音的組合,并突出每個三連音的第一個音和最后一個音。在演奏的過程中,需要突出節奏重音的第一、三、四、六音須以技法“彈”來完成,而相對較弱音位置的第二、五音則需要由“打音”或“滑音”來演奏,這樣的技法安排能將原本譜面上的六連音分解為兩個三連音的組合,并有利于突顯音樂中的布魯斯節奏風格。演奏者需要在練習演奏的過程中,逐步把握音樂“不平衡”的律動特點,從而更好地回歸、還原作者音樂創作的本意。
在《云南回憶》出現之前,鮮有阮樂作品如此頻繁地運用布魯斯節奏與七和弦,因此不難想象該曲在問世時給人們帶來的沖擊。如今這些和弦與節奏的應用在阮樂中已經不再罕見。但在數十年前,它們確實為阮帶來了新穎的音樂色彩,不難想象首次聆聽該曲時觀眾感受到的震撼。在香港首演時,《云南回憶》不拘一格的創新精神打動了一眾音樂評論人,有職業樂評人在《信報》上撰文高度評價,指出其全曲聽不見一個“例行公事的樂句”,但“滿溢中國音樂的韻味”。[3]受《云南回憶》啟發,此后出現的阮樂作品大多沿襲了這種從和弦與節奏音型入手,凸顯阮樂創新性的做法。可以說,劉星在節奏音型、非常規和弦上的積極探索,完成了他對阮樂的可能世界的第二重發掘。
阮樂是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不斷發掘并創造其可能世界,才能拓展其表現力。劉星以一曲《云南回憶》,探索并創造了阮在當代的可能世界,對國樂傳統的繼承與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從這一點來看,劉星創作的《云南回憶》通過對阮樂的可能世界的探索和創造,完成了對國樂傳統的超越與再造,而這一過程正蘊含了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真義。我們今天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可從《云南回憶》身上獲得寶貴的啟迪。
四、《云南回憶》對當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啟迪
《云南回憶》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阮樂作品創新的典范,是因為劉星始終堅持站在傳統的立場上,以海納百川的姿態吸納了來自國外的音樂創作技術和觀念,這樣的做法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難能可貴,劉星及其《云南回憶》為我們在當下認識并實踐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借鑒學習的模范。
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習近平文化觀的重要思想。[6]當下,我們要努力對優秀的傳統文化予以轉化和改造,使其得以承續和發展,并走向世界,成為傳播中華文明、展示中華民族“軟實力”的使者。音樂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中國音樂創作者需要在努力繼承、發掘傳統音樂文化的基礎上,努力吸收不同音樂文化的精髓,創作出雅俗共賞而又內涵深刻的經典作品。《云南回憶》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但其創作者劉星卻以超前的眼光,較為成功地處理了繼承傳統音樂文化和吸收外來音樂文明之間的關系。
在國門重新向世界敞開的20世紀80年代,劉星盡管也被歐美流行音樂文化所吸引,但他并沒有舍棄伴隨他長大的中國音樂。在當時新潮音樂迭興,中國音樂界再次掀起對西方音樂文明的崇拜之風時,劉星仍舊選擇拿起手上的阮,追尋中國音樂的“根”和“源”,用深藏著中華音樂審美品格的民族調式,彈奏出了奔放綺麗的《云南回憶》。可以說,劉星不忘傳統的音樂觀念,為他創作《云南回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劉星作為一位對阮樂有著獨到理解的作曲家,并沒有止步于對傳統音樂文化的照搬和挖掘,而是選擇匯入中國新音樂立足傳統、放眼世界的創作潮流。在《云南回憶》中,劉星選用了“協奏曲”這一西方音樂體裁來承載他營造的文化符號“云南”,并且打破了協奏曲固定的程式[7],使音樂體裁真正成為音樂抒情述志的途徑,推進了西方音樂體裁的中國化進程。劉星基于自己對阮這一中國傳統民族樂器的認識,將吉他等西洋樂器的演奏技術,成功地移植到了阮上,傳統的阮因此獲得了鮮明的現代色彩,拓寬了自身的變現力。借助《云南回憶》中布魯斯音型的廣泛運用,阮發出了不羈怒放的鳴響,為中國傳統器樂藝術的發展樹立了新的標桿。《云南回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離不開創作者劉星繼承傳統、超越傳統的堅持,更離不開他放眼世界、海納百川的大膽嘗試。劉星這種以辯證態度面對傳統音樂文化,并與時俱進地站在中國立場上吸收外來文化,創造當代中國“新音樂”的做法,與我們今天提倡“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事實上別無二致。
相比20世紀80年代,當前中國正以更為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敞開大門,同時也對傳統文化的傳承采取了更為珍視和中肯的態度。黨和人民無時不在呼喚具有中國氣派,同時又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文藝作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天的作曲家顯然更能夠接觸到來自各國的音樂文化,完成傳統音樂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創作出人民滿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音樂作品。《云南回憶》問世已近30年,但它作為一個頗具“先見之明”的成功個案,其創作經驗依舊能為我們實踐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寶貴的經驗。
在中國傳統藝術的“創造性轉化”過程中,我們在敞開胸懷學習并繼承傳統經典作品的形式的同時,要積極開拓全新的多媒介融合方式。我們要回到“原初”,如同我們的先人從無到有發明中阮一樣,面對過去的傳統,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其潛在的各種可能,不斷豐富我們的當代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