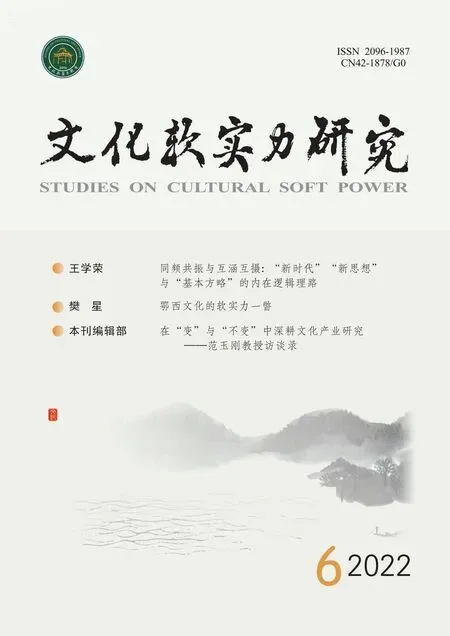走向城市發展學的我國工業遺產研究(2002—2021)
——基于中國知網中文學術期刊論文的知識圖譜分析
韓 晗
(武漢大學 景園規劃設計研究院,湖北武漢 430000)
一、導論
工業遺產是近五十年來的熱門研究領域與不可忽視的學術增長點。谷歌學術統計,自1970年以來,以“工業遺產”(industrial heritage)與“工業考古學”(industrial archaeology)為主題的中文、英文、日文、德文、俄文與法文學術論文,多達10000余篇,與其他相關研究主題相比,工業遺產研究在全世界特別是工業發達國家,已經獨樹一幟并自成體系,變成了一個越來越無法忽視的存在[1]。
“工業遺產”這一概念最早由時任劍橋大學助理講師的皮特·馬蒂亞斯于1958年在《英國釀酒工業:1700—1830》(ThebrewingindustryinEngland,1700-1830)導言中明確提出,“過去一百年的工業遺產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島嶼歷史的方方面面”[2]。嗣后,英國學者肯尼斯·修森在1965年發表的論文《工業考古學的發展之痛》又從工業遺產的角度提出了“工業考古學”這一概念[3]。
顯而易見的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源自于理論的跨國旅行,最早可溯自于東北工業大學教師呂強1986年發表的文章《要重視工業考古學》,但此文并未使用工業遺產這一概念。“工業遺產”作為學術概念最早進入中國,是1994年斯蒂潘納克《旅游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一文的譯介入華,此文指出:“在歐洲,Canbury World則是這方面的典型,它是一個工業旅游點,并以此促進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利用”[4],但上述兩文影響有限且主要為概念介紹與譯介,可視作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先聲(1)截至2022年1月,《要重視工業考古學》一文在中國知網被下載100次,被引8次,《旅游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被下載104次,被引2次。。
嚴格來說,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始于2002年,時由深圳大學教師李蕾蕾在《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發表《逆工業化與工業遺產旅游開發:德國魯爾區的實踐過程與開發模式》一文,此文是她在德國訪學的研究成果,也是中文學界第一篇以“工業遺產”為標題的學術論文,還是目前有案可查最早一篇系統論述工業遺產概念及其經驗路徑的論文。截至2021年12月,此文被引700次,而且發表次年就在國內掀起“魯爾區”的研究潮流,也是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領域第一高被引論文。此文可以被視作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邏輯起點。
自2002年至2021年二十年間,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經歷了從小到大、由點而面、自譯介而原創的發展,形成了蔚為大觀的工業遺產研究體系。據不完全統計,二十年來,以工業遺產為主題的單篇中文論文超過4000篇,著述也超過百部,就其體量而言,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一些規模中等的建制化二級學科。從總體格局上看,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切合時代、風格鮮明且體系豐富,有著走向城市發展學研究的大趨勢。
從全球工業遺產相關研究來看,近年來工業遺產研究已經呈現出了走出工業考古學,與城市發展密切結合的學術大趨勢,當中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與城市規劃研究的緊密結合[5]。我們研究發現,2017年以來,非中文語種的高被引工業遺產研究成果大約有60%以上發表于《城市》(Cities)、《環境與城市化》(EnvironmentandUrbanization)、《土地》(Land)、《城市科學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Sciences)與《城市事務雜志》(JournalofUrbanAffairs)等城市研究的期刊上,可見面向城市發展學的學術轉型并非為我國所獨有,而是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本文所言之“城市發展學”是集合李維斯·霍普金斯的“城市發展理論”、穆瑞·克欽的“城市界限理論”與我國學者李文彥、朱鐵臻與仇保興等人關于城市發展觀點而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1984年,穆瑞·克欽立足城市發展與土地利用的關系提出了“城市界限理論”1980年代,李文彥提出如何處理工業區規劃與城市發展的關系問題,受到學界矚目,到了1990年代,仇保興就城市形象、城鎮化動力問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引起較大反響。人類進入到21世紀以來,城市發展學逐漸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準學科,當中以李維斯·霍普金斯的《城市發展學:規劃的邏輯》(Urbandevelopment:Thelogicofmakingplans,2001)與朱鐵臻的《城市發展學》(2010)為個中代表,中外學者共同認識到:城市發展學是一門因城鎮化、城市治理與城市建設而生的學問,與城市規劃、建筑學、風景園林、人口學、管理學與歷史學等傳統學科關系密切,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我國學者在當中的耕耘,反映了我國城市發展研究與世界的同步性,彰顯出了具有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研究視角,從其學術貢獻來看,是事關人類命運未來發展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新興研究領域。我國作為后發優勢大國,現代城市源自于工業技術的轉移與發展,產業結構轉型與城市更新、土地再利用等關系密切[6],因此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當與城市發展學更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本文擬借助CiteSpace軟件與中國知網平臺的數據分析程序,對2002年以來國內學術期刊發表的4324篇(截至2021年12月)“工業遺產”相關主題的中文學術期刊論文進行知識圖譜分析(2)“工業遺產”這一概念旅行入華之初,其概念定義尚不明確,多將工業遺產、工業遺存、工業遺址甚至工業文化遺產等四種不同概念混用,這一現象持續至2014年左右,因此本研究即以上述四種概念為主題,通過中國知網中文學術期刊總庫檢索有關學術論文發表情況。。并結合目前我國學術研究話語體系建設的實際需要與國際相關研究的總體大勢,對二十年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總體狀況與發展趨勢進行梳理。
二、二十年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總體狀況
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實現了從無到有、由有而優的進步。具體而言,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 研究譜系:兩大傳統學科“雙引領”
從論文發表的平臺來看,本文所研究的4324篇論文分別發表于1192家不同的刊物,當中絕大多數期刊都只刊發2次以內關于工業遺產的論文,且多出現在自由來稿或專題當中。根據中國知網論文的學科分布情況,當中屬于包括建筑學、城市規劃學在內的“建筑科學與工程”學科的論文引領性地占據半壁江山,其他學科則多達近四十個,呈現出了被建筑學與城市規劃學兩大傳統學科“雙引領”,而其他學科廣泛參與的研究譜系(見表1)。

表1 4324篇論文學科分布圖
具體來看,緊隨其后的“旅游”、“工業經濟”與“文化”等學科,在跨學科、新文科與新工科的大環境下,與建筑學、城市規劃兩大引領學科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若算廣義上的“雙引領”,其學科成果占比份額要高于49.94%,達到總成果的一半以上。如果從建制化的傳統學科的角度來考量,目前工業遺產的主要研究者也來自于這兩大傳統學科,可以說,工業遺產研究是一個自帶“工科血統”的新文科研究領域。
我們通過對被研究文獻的分析進一步發現,在4324篇論文的作者所在機構歸屬中,數量排名第一的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緊隨其后的為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北京建筑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天津大學與重慶大學等“建筑老八校”以及中信建筑設計總院、四川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等專業規劃機構,此外還包括吉林建筑大學、沈陽師范大學、山東建筑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等在城市規劃領域頗有聲望的高校,其學科呈現與發表論文的學科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圖1 170篇高被引論文發表期刊分布圖
此外,高被引論文也往往作為衡量一個領域研究狀況的重要參考。中國知網相關數據顯示,4324篇論文均被引數為0.032次,如果將“工業遺產”相關主題論文視作一個學科內成果,以ESI的判斷標準年度被引前1%論文則可以視作高被引論文。但工業遺產領域是一個逐漸發育的領域,年度標準顯然不適用于其總體發展水平的判斷。因此將2002年以來所有論文按被引前1%進行歸納,并排除大量零引論文或書評、會議綜述等非嚴格意義學術論文后發現,工業遺產的高被引論文正好是單篇累計被引率超過30次的論文,計有170篇(見圖1)。
研究顯示,170篇高被引論文分布在62家不同的學術刊物中,涉及建筑、城市規劃、人文地理、經濟、文化產業、歷史學、哲學、材料學、物理學、冶煉學等不同學科,當中有13篇發表于《建筑學報》,居于其次的是《工業建筑》,有11篇,該刊也是二十年來發表“工業遺產”相關主題論文最多的期刊,在4324篇中占有238篇(含正刊與增、特刊),《城市發展研究》與《城市規劃》位居第三位,各為9篇。
總體上看,在170篇論文中,有54篇論文集中發表于《建筑學報》《工業建筑》《新建筑》等建筑學期刊中,而另有56篇論文集中發表于《城市規劃》《上海城市規劃》《規劃師》等城市規劃學專業期刊,這與之前提到的“雙引領”具有一致性。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他各只發表一篇論文的“其他期刊”則由《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與《中國名城》等城市研究專業期刊所構成,加上發表9篇論文的《城市發展研究》,可見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學術成果在高被引論文中占了絕大多數,這與研究總體趨勢存在正相關性。
(二)關鍵詞共現反映城市發展議題導向牽引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軟件針對4324篇論文進行了關鍵詞共現歸納,研究顯示,一方面,“工業遺產”已經成為了不同歷史階段顯示度均最高的關鍵詞(見圖2),另一方面,與“城市”有關的議題,也與工業遺產研究息息相關。

圖2 4324篇學術論文高頻關鍵詞共現示意圖
事實上,城市發展議題在工業遺產研究領域的出現,正是在“工業遺產”進入中國不久的2006年,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開始集中關注城市更新、城市記憶等議題(見圖3),在2010年之后,城市復興、景觀更新、老工業城市、歷史街區與城市雙修等事關城市發展的議題開始緊密地與工業遺產研究發生聯系,反映了二十年來學界從單純注重于工業遺產概念闡釋到關注城市發展議題的趨勢變遷。

圖3 4324篇論文高頻關鍵詞分時共現圖
“拆與保”是我國工業遺產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其與城市發展議題相聯系的關鍵。自2002年以來,“保護與利用”“保護利用”“活化利用”與“保護再利用”等關鍵詞一直貫穿于學術研究的視野當中。中國知網主題高頻關鍵詞共現也反映,在單篇論文中最常出現的主題是“工業遺產”,而最常同時出現的一對主題是“工業遺產”與“工業遺產保護”(60次),其次相繼為“工業遺產”與“保護再利用”(52次)、“工業遺產”與“再利用”(42次)以及“保護再利用”與“再利用”(30次)(見圖4),它們普遍與“城市”有關議題共生,這充分說明學界對工業遺產命運的關注,建構在對城市發展的關切上。

圖4 4324篇論文高頻關鍵詞總體共現示意圖
不言而喻,立足城市發展相關議題構成了學界探討工業遺產研究的一個重要認知,這也體現了工業遺產研究學以致用的特征。如果仔細來看,則不難看出,工業遺產的命運實則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從宏觀上看,“拆”則涉及到城市空間、土地的完全更新,而“保”則涉及到城市空間、土地的再利用,無論走哪條路,都離不開城市規劃、城市未來決策等城市發展議題。
近年來,“文化創意”“三線建設”“景觀改造”與“公共空間”等議題被提上日程,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了工業遺產研究領域的關鍵詞,得到了學界的積極響應,如“文化創意”作為目前工業遺產保護再利用的一個重要渠道,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引擎,實現“廠區-園區-城區-社區”的空間變遷,形成了“文化創意+工業遺產”的再利用路徑。就相關實踐而言,如創意產業園、文化創意產業、旅游開發、工業遺址公園與工業旅游等議題也廣泛受到學界關注,這都是與城市發展緊密相連的部分,對相關問題的局部深研也拓寬了城市發展的研究思路與視野。
(三)總體趨勢:以理論創新走向城市發展學
歷史地看,工業遺產這一概念傳入中國,是理論旅行的結果,即對國外當時已經較為成熟的工業遺產、工業考古學等知識譯介進入我國,并實現了“中國化”發展。筆者將本研究所涉及的4234篇學術論文進行了高頻關鍵詞分時共現研究(見圖3),可見二十年來工業遺產研究在中國次第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是理論旅行期(2002—2009年),期間主要是建筑學、城市規劃學譯介國外工業遺產有關名詞、概念并介紹國外工業遺產保護的經驗與研究觀念。一部分學者開始關注我國工業遺產的命運,但期間工業遺產概念尚不完善,如工業文化遺存、工業遺址等提法都普遍存在。
在這一階段,學界多關注于廣義上的工業遺產概念,屬于理論旅行入華的初肇期,如對工業文化、保護利用、景觀設計、城市記憶與旅游開發等概念的探討,以對舶來理論的回應與思考為主,并開始初步探討我國城市發展當中所共存的一些議題。
從研究方法來看,這一階段的工業遺產研究并沒有太大的原創性,而是主要集中在對相關舶來觀點的譯介、討論上,但需要重視的是,當時我國工業遺產學界對于西方工業遺產相關理論存在著取舍,比如對于工業考古學、工業遺產美學理論等基礎知識關注不夠,而多關注與城市發展有關的經世致用之學。
二是理論自覺期(2010—2017年),期間除了建筑與城市規劃學之外,科學史、歷史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也開始參與其中,短短四年間,形成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一個小高潮。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設立了工業文化發展中心,湖北黃石也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地級市政府直屬的工業遺產管理單位——黃石工業遺產保護研究中心,逐漸形成了對城市發展議題的主動關注,打下了重要的研究基礎。
這一期間,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界開始認識到我國工業遺產的優勢、特征以及其自身關鍵屬性,初步通過跨學科研究范式凝聚了一批在工業遺產研究領域學有所成、學以致用的學者,從而推動我國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研究的理論耦合與實踐指引。
三是理論創新期(2018—)。2017年12月20日,國家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獲得認定的國家工業遺產名單,2019年11月2日至3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浦江兩岸,對“銹帶”變“秀帶”提出了重要指示,這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在理論創新期的重要思想指引。自此,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開始真正與城市發展學緊密相連,并與城市發展實踐聯系緊密,服務于我國城鎮化建設與城市治理決策,真正進入到了“以我為主,理論自覺,問題出發,中國方案”的研究格局。
就關鍵詞所呈現的勢態來看,這一時期新出現了文創產業、城市雙修、老工業城市等新興本土化概念,大大豐富了我國城市發展學研究。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階段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彰顯出了與世界同步研究、同頻思考、同等對話的學術景觀,許多成果在國際同行當中處于引領性水平,成為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國際化建設、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二十年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主要成就
走向城市發展學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二十年的發展趨勢。從總體特征來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大致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以時代感服務城市發展學理論建構
通過二十年的努力,國內學術界逐步形成了以關注城市發展為目標的工業遺產研究體系,相關研究立足時代命題,呼應時代所需,有非常鮮明的時代感。
工業遺產相關概念旅行進入中國時,我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還處于起步期,明顯遲發于歐美國家,隨著我國城市化發展加速,旅行入華的工業遺產概念不斷與我國城市發展實踐相結合,這也是城市發展學理論建構的重要動力。
具體而言,這一理論建構還由如下兩個方面所反映并決定。一是以立足城市發展大局談工業遺產問題,形成了立足于中國國情的保護更新及再利用方案,尤其是對大沽濱水工業遺產、東北老工業基地工業遺產、上海浦江兩岸工業遺產與“三線”工業遺產的保護更新再利用,均提出了較好的研究對策;二是與城市發展頂層設計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如城市雙修、公共文化服務、老工業(資源枯竭型)城市振興、文旅融合等國家層面的政策,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均有較深介入或系統闡釋,體現了與時代脈搏共振的學術追求。
從時間上看,我國工業遺產研究與我國城市發展研究同步起步,因此工業遺產研究界也成為了我國城市發展研究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的理論參與者。在4324篇論文中,2100篇都涉及了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兩百余個我國重要城市,特別是一些處于更新中的城市如武漢、重慶與沈陽等等,反映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經歷了一個與城市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建構之路。
(二)以豐碩成果建立健全城市發展學話語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高度重視,習近平同志多次指示要重視話語體系建設[7]。學術話語體系的建立,一般而言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基于本土經驗對基本概念的詮釋;二是通過比較研究方法的創新實現學術話語的轉換與更新;三是以開放的心態開展海外研究。[8]縱觀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發展二十年,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通過豐碩的成果,建立健全城市發展學話語體系。
我國城市發展學起源于1980年代,但真正形成廣泛的學術影響則是在本世紀之初的城市化浪潮之下,當中以仇保興為代表的學者結合我國城市化實踐,就我國城市軟實力、城市形象與城市文脈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這與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具有時間上的同步性。在這個過程當中,工業遺產作為實踐性強的研究領域,在經驗上先行先試,以不斷產出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我國城市發展學的在地性內涵。
值得關注的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最初是關于國外工業遺產的介紹與研究,二十年發展中不斷吸收了國外城市發展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動了城市發展學的話語轉換與理論創新。譬如在2002年之后不久,國內迅速刮起一股“魯爾區研究熱”,開始關注我國老工業城市轉型,促進了城市發展學對于國內相關共性城市問題的關注。
在2000余篇個案研究論文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對國外工業遺產案例的研究,近三分之二為我國工業遺產的研究,盡管在體量上形成了“以我為主”的局面,但與此同時在數量上也構成了對海外工業遺產問題的關注,尤其注重對其他國家城市發展經驗的借鑒,當中多為對鹿特丹、柏林、倫敦、芝加哥、東京等國際重要城市工業遺產管理、工業社區更新等問題的研究,形成了中國學者看世界的獨特視野,這為建立健全我國城市發展學話語體系有著重要意義。
此外,我國工業遺產學界也是最能吸引海外學者投身我國學術研究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一,這在其他領域當中并不多見,如天津大學日裔教授青木信夫、北京科技大學西班牙裔教授胡安·曼努埃爾·卡諾·桑奇斯等等,這些學者既是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領域的高被引學者,同時也在國際學術界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果,促進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國際高水平參與。
(三)以研究多元化促進城市發展學有序發展
這里的研究多元化,指的我國工業遺產研究范式與路徑的多元化。研究范式在這里主要指的是以研究的目的為導向的研究形態。就目的而言,學術研究一般分為自由研究與課題研究。4324篇論文顯示,當中有2030篇沒有任何課題資助,其中不乏研究生或青年學人以及非高校或科研機構工程技術人員的自由研究或工作報告。在2294篇有明確課題資助的論文中,有348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71篇屬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其余分別為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全國藝術科學規劃課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河南省軟科學支持計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等課題資助,多達近100種,且基本處于平均分布的局面,皆為不同學科、不同層次、不同來源的科研課題。總體上呈現出了研究范式上自由研究與課題研究相結合,課題研究中又形成了目的多元的格局。
路徑多元則體現在研究成果的類型上。就4324篇研究論文而言,根據相關研究類型分類,具體情況如圖5所示。

圖5 4324篇論文研究類型分布示意圖
圖5的11個分類顯示了工業遺產研究類型,即仍以應用研究框架下的多元研究為主,當中以工程研究為大宗,并指涉技術、開發、行業、管理、政策等不同方面,這與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實踐所亟需的研究類型相契合。
研究多元化彰顯出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跨學科、去學科的特征,它直面我國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如空間利用、城市更新、棕地治理、城市記憶與社區改造等等,它們也是城市發展學的核心問題,其研究多元化勢必促進城市發展學有序發展。
四、結論:目前不足之處與發展愿景
我國工業遺產研究走過了二十年的櫛風沐雨,成為了“新文科”與“新工科”之下的“準學科”,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隊伍中一支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生力軍。但毋庸諱言,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的知識圖譜分析,發現仍有較為鮮明的不足之處,需引起學界同仁重視。從宏觀大局來看,共建城市發展學“中國學派”勢必是工業遺產研究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愿景。
(一)理論創新仍有不足
盡管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初步實現了學術理論創新化的嘗試,并形成了關于城市發展學的相關論說,但因為理論創新期時間較短,多數概念、理論與標準沿用舶來論說,原創性理論所用有限,“強制闡釋”這一問題依然未在根本上有所改善。
本研究所涉及的4324篇論文顯示,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基于工業建(構)筑物本體、土壤與水體的修復、更新及治理等工程技術層面的研究;二是工業空間更新與城市發展之間關系的探討;三是工業文脈與城市形象等議題的探討。這三種研究所依托的是近二十年來我國工業遺產保護更新再利用服務于城市發展的長期實踐,也是我國城市發展學理論創新的基礎。但它們也共同反映了: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多數時候依然借用舶來理論工具,思路多以“一文一事”的案例型研究為主,對于“元問題”的探索與理論提煉普遍缺乏。
工業遺產研究首先要回應的問題是:工業遺產何以具有美學特征?這是探討工業遺產價值的根本問題之一,也是工業遺產保護更新再利用的起始,弄不懂這個問題,工業遺產旅游無從開展,工業遺產再利用目的自然也模糊不清。但在漢語學界之外,關于工業遺產美學的研究實際上已非常豐富,但應當注意到,我國工業遺產的美學特征不只是西方學者所言的廣義普遍性范疇,更包括了自強求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與紅色文化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屬性,可惜的是,目前對我國工業遺產美學特征的探討尚未起步,多數論說只是照搬照抄西方學者的“廢墟美學”、“后工業文明”等陳舊說詞,難以有說服力。
目前的工業遺產領域的研究類型(圖5)也顯示了這一問題,盡管目前工業遺產研究路徑多元,但所有的研究幾乎都指向實踐性、對策性等應用研究。我國經歷了數十年城鎮化發展,已經形成了多個在國際上居于領先地位的城市群,城市發展的“中國經驗”亟需總結,“中國故事”有待講述,而城市發展學的“中國學派”也呼之欲出,工業遺產研究在理論自主創新當中不應缺位。
相關問題還暴露在目前工業遺產研究缺乏對普遍性價值的關注上。就目前所見而言,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個案的經驗介紹與對策建議,較少針對城市美學、空間媒介、場景再造與城市史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這與其他發達國家工業遺產研究的理論深度相比,仍有一定距離。當中一個很大原因在于,研究者因為受制于機構、學科的差異性,導致思維受限,形成了學科內部自我封閉的信息繭房,甚至還有大量的重復研究(如某個具體的工業遺產點、工業遺址竟然有十余篇大同小異的研究論文),這顯然不利于城市發展學今后進一步的理論創新。
(二)“遺產研究”轉向較為遲緩
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成果固然豐碩,形成了走向城市發展學的總體趨勢,但朝“遺產研究”(heritage studies)轉向較為遲緩,導致一系列重大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同時也滯后了城市發展學相關研究。
一是對工業考古學關注有限,造成城市考古學缺位。人類的工業遺產研究,源自于工業考古學,即以考古學的研究范式來研究工業遺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實踐創新必須建立在歷史發展規律之上,必須行進在歷史正確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9]
在研究的4324篇論文中,僅有32篇文章以“工業考古學”為主題之一(且當中只有8篇文章以“工業考古學”為篇名),另外只有部分論文提到“工業考古學”。雖然圖1顯示有294篇文章屬于“考古學”,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為研究工業博物館或工業遺產展陳的研究成果,按照我國學科規制隸屬于“考古學”范疇,實則與“工業考古學”關系不大,可見工業考古學與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目前并未形成強有力的關聯。
城市考古學是城市發展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它事關城市建筑保護、城市文脈賡續與城市形象構建,它與工業考古學有著巨大的交集。國外學界新興的“城市考古學”研究很大程度上與工業考古學同源,且構成了城市規劃、建設與更新等研究的基礎[10]。顯而易見的是,目前我國工業考古學發展水平束縛了城市考古學發展,也不利于城市發展學總體研究水平的提升。
二是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參與工業遺產研究仍然較少。工業遺產與城市發展議題緊密相關,它應當是“新文科”與“新工科”相結合的產物,從其學科歸屬上講,它理應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看,它也被視作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部分(3)如前文所列舉的《城市》(Cities)、《環境與城市化》(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土地》(Land)、《城市科學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與《城市事務雜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等期刊以及《工業考古學評論》(Industrial Archaeology Review),皆為SSCI(社會科學索引)或A&HCI(人文與藝術索引)期刊。。但就目前所見而言,我國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如中文、歷史、法學與哲學等學科的學者卻嚴重參與不足。正如圖3及圖4所顯示,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雖然對城市問題有頗多關注,但多浮于問題表面,較少對城市發展的文化建設、社區治理、遺產空間立法等復雜議題做理論深研,更不用說對審美、歷史、文化等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探討了。
工業遺產研究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事關城市發展,且與建筑學、城市規劃學等傳統學科以及風景園林學、材料科學、測繪科學、交通運輸等工程技術學科所涉及的議題息息相關,但它仍有較強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特征,這與城市發展學當中的城市史、城市文化與城市形象等領域有著較大的交叉性,因此,未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朝著“遺產研究”轉向,既是自我學術轉型,也是提升城市發展學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三)發展愿景:共建城市發展學“中國學派”
海外學界雖然沒有“城市發展學”這一概念,但“城市研究”卻普遍存在,“城市發展學”作為“城市研究”在我國的本土化發展,雖然已經枝繁葉茂,但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學派”應是未來目標,具體來說有如下幾點發展建議。
一是發揮好“新文科”與“新工科”的優勢,立足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需求,繼續保持對在地性、本土性議題的關注,一方面從我國城市發展實踐中探尋經驗,豐富研究內涵,另一方面真正地持續指導我國城市發展的實踐;二是往縱深理論深度挖掘,探討我國工業遺產研究領域的理論價值,從而形成具有公共闡釋能力的話語體系;三是注重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工業考古學的介入,推動工業遺產的“遺產研究”轉向,從根本上提升了我國城市發展學的研究水準。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研究仍有明顯的薄弱之處,除了前文所述存在著大量的重復性研究之外,涉及到工業考古、工業遺產美學乃至工業遺產旅游等方面仍然研究深度不足,上述領域構成了工業遺產研究的基礎邏輯與基本理論,它們之于我國城市發展學理論研究而言當然也意義重大。而且,至今為止我國尚無一部與工業遺產有關的教科書,所出版專著多以案例匯編、博士論文或會議論文集等為主,這不得不說目前研究還存在著的一定局限性,而上述相關不足顯而易見又是未來學界努力的方向。
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有非常強烈的實踐性,它走向城市發展學既是歷史必然,也因其研究對象、范式及其價值依歸使然。未來的城市發展學將會給我國工業遺產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視角與更豐富的學術內涵,從而指導工業遺產保護再利用工作與城市發展大局共生共榮。最終使我國工業遺產研究不但可以學以致用,而且真正地成為立足在地經驗并以內驅動力實現理論創新的知識體系。
一言以蔽之,努力共建城市發展學的“中國學派”,應是未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矢志不移的發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