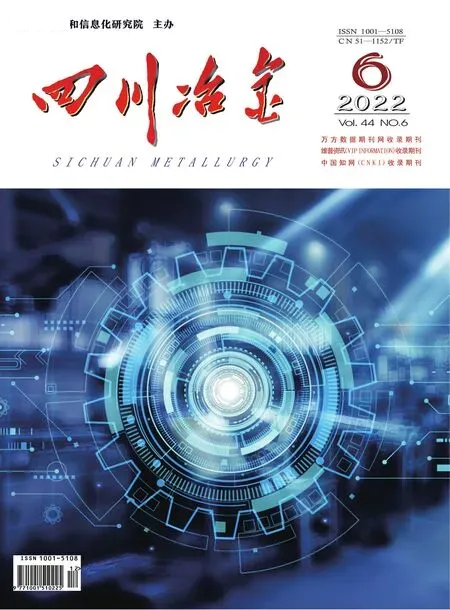四川省制造業集聚程度、專業化水平和區域布局研究
冉星妍,涂文明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 統計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3)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制造業發展,指出“制造業是國家經濟命脈所系”,強調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這無疑對作為實體經濟主體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成制造業強國,加快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制造業在空間的集聚有助于促進資源流動和技術共享,提高地區制造業專業化水平也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四川省作為西部工業大省,是我國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級,2020年,四川制造業增加值總量10746.8億元,工業總量排名西部第一、全國第八。《四川省“十四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規劃》提出“十四五”時期是四川省制造業乘勢突破的“關鍵五年”。四川省要全面提升制造業發展質量和核心競爭力,應實施制造業立支柱、強基礎、鍛長板行動,解決“大而不強”的隱憂,塑造四川制造業新格局。測算產業集聚水平現狀及演變趨勢,是制定產業布局與產業轉移政策的基點,因此,本文對四川省2011-2020年制造業各行業集聚程度和專業化水平進行分析,以期助力四川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1 制造業集聚理論及相關研究綜述
產業在一定空間內形成集聚的現象,是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產業集聚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杜能在《農業國》一書中闡述的農業區位理論,隨后馬歇爾基于外部性開啟了產業集聚研究的新視角,認為規模經濟會促使企業擴大生產,形成產值的地理集中;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確定了三個區位因子: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集聚和分散,明確提出了集聚經濟的概念。隨后,法國學者佩魯提出增長級理論,認為主導產業在特定區域或城市聚集,從而形成增長迅速且具有顯著經濟效益的部門。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認為,要素差異會導致勞動力和資金由臨近地區向增長極地區流動,從而導致地區產業專業化和產業集聚進一步加大,而當產業集中超過一定限度后,又由于規模報酬遞減,促使增長極的資金和勞動力向臨近地區流動,帶動周圍地區發展。克魯格曼在1991年發表了中心——外圍模型,模型形成的條件有:制造業份額足夠大而運輸成本足夠低,同時制造業的差異化種類足夠多,這樣由于規模集聚的作用就會導致制造業的空間集聚與分散。基于以上理論,現在認為制造業集聚原因主要有原材料、人口、市場、運輸成本等因素。Lee(2015)提出,人口流入既是產業集聚的原因又是產業集聚的結果。Coe和Kelly(2019)[1]等人認為地區原材料的分布、運輸成本、市場狀況等因素綜合決定了制造業集聚的最佳區位。劉鑫、毛熙彥(2015)[2]等學者發現交通設施對制造業的布局具有顯著的影響[3]。
當前對于制造業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集聚對于經濟增長、技術創新的影響以及制造業集聚的空間外溢性。原毅軍和郭然(2018)分析我國2008-2015年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發現中國中西部省份制造業集聚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范劍勇、馮猛(2014)[4]等人通過對中國縣級經濟的研究發現制造業集聚有助于改善技術效率,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范建勇還提出,在縣域層面上,制造業專業化能夠促進效率提高與經濟增長,產業轉移則會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潘文卿和劉慶(2012)[5-7]研究中國2001-2007年制造業HHI指數,發現中國造業的產業集聚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王立勇和呂政[8]研究廣東省制造業集聚情況發現,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受到交通運輸條件的影響,在交通運輸條件發達的地區,制造業集聚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張公嵬和陳翔(2013)[9]等人提出制造業集聚存在正的外部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影響。Piyali和Aparna[10]對印度各州制造業集聚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制造業集聚能有效促進出口,從而刺激經濟增長。Muratah和Nakajima[11]發現美國的研發實驗室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內,制造業集聚可以相互學習對方的技術而促進區域創新[12]。Hanlon 和 Miscio分析了早年英國制造業的數據,發現隨著制造業的集聚,當地經濟經濟增長更快,且制造業集聚存在空間外溢性,能夠帶動臨近地區增長[13]。關于制造業集聚空間演變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全國層面。安樹偉和張晉晉(2016)發現,2004年以來我國制造業集中度有所下降,市場化改革促進了制造業的擴散[14]。孫曉華和郭旭(2018)等人分析2004-2013年中國30個省份的制造業面板數據發現,中國制造業中西部省份的制造業集聚程度自2004年開始上升,制造業轉移與要素集聚相互作用顯著影響了地區經濟。季書涵和朱英明(2016)[15]等人也發現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資源錯配的改善效果更強。文東偉,冼國明(2014)[16]利用1998-2009年中國工業企業層面的數據發現制造業四位數行業的企業數量在減少,集聚程度卻在不斷加深。[17]目前對于省域層面制造業集聚空間演變的研究較少,著眼于省域內部的研究能更好地打破行政壁壘,更有效地實現省域內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優化。
2 四川省制造業演變的整體特征
四川省2020年制造業規上企業個數為13605個,實現營業收入40690.05億元,較2011年增長64.24%;全年平均用工人數為260.26萬人,較2011年減少15.88%。四川省制造業營業收入占全國制造業營業收入的比重十年間穩定在3.2%以上,自2016年開始,四川省制造業規上企業營業收入占全國的比重開始明顯增大,到2020年達到4.23%。

圖1 2011-2020年四川省制造業規上企業營業收入占全國營業收入比重
成都市作為四川省制造業的主要集聚地,在2011-2017年,營收收入占比增加了6.01%,此后又開始逐漸下降,說明制造業在成都市先集中再逐步分散。南充市、廣元市、廣安市和宜賓市制造業營業收入增長最快,首位城市為南充市,增長了176.65%;營業收入占全省比重也由2011年的14.07增加到2020年的21.34,說明四川省制造業在這些城市趨于集中;甘孜州、內江市和資陽市制造業營業收入不增反減,資陽市減少最快,為78.30%,主要是由于行政區劃變動導致的結果,但同時,這三個城市的營業收入占全省比重也由2011年的12.19減少至2020年的3.78,說明四川省制造業在這些城市趨于分散。
同時,四川省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營業收入占比連年增加,在2013年就已占比第一,十年間由30.01%增加到39.59%。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占比波動下降,分別由2011年的32.81%和36.38%下降至2020年的28.20%和32.21%。制造業全年平均用工人數的減少也暗示著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占比的下降。四川省制造業不同行業在不同城市呈現出差異化的集聚分散趨勢。

圖2 2011-2020年四川省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占比變化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
本文以四川省各地級市為研究區域,分析四川省制造業的集聚程度與專業化水平。綜合考慮數據的可得性,以四川省除達州市、阿壩州、涼山州的18個市州相關年份的制造業統計數據作為分析對象,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9年修改版標準,選擇了各市州30個制造業2位數行業的規上企業營業收入,為了統一數據統計口徑,2018年以后的數據選用主營業務收入。因煙草制造業具有較強的政策管制性質,不適用于產業集聚相關研究,因此本文將其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原始數據均來自2012-2021年《四川省統計年鑒》及各市州統計年鑒。
3.2 指標選取
3.2.1 空間基尼系數
空間基尼系數是由克魯格曼最初提出的用于測算產業空間集聚程度指標的一種指標,本文以四川省制造業為基準。其計算公式為:
(1)
式中:Si表示的是四川省i城市制造業某一2位數代碼行業營業收入占四川省制造業該2位數代碼行業營業收入的比重;Xi是四川省i城市制造業所有行業總營業收入占四川省制造業所有行業總營業收入的比重。G的取值在0到1的范圍內變化,G值越大,表示產業集聚程度越高,即該產業在地理上越集中,當G值為0時,表示該產業在地理上分布平均。
3.2.2 區位熵
區位熵又稱地方專業化指數,是衡量單一行業在某一區域的專業化水平的指標,用來比較區域中某類產業與整個地區相比是否具有比較優勢,是用來測度具體行業專業化程度的方法,其計算公式為:
(2)
式中:LQij為i城市j行業的區位熵指數;ei為i城市制造業內某一2位數代碼行業的營業收入,et為i城市制造業所有行業的營業收入;Ei為四川省制造業某一2位數代碼行業的營業收入,Et為四川省制造業所有行業的營業收入。區位熵的值越大,表示i城市j行業的專業化水平越高;當LQij大于1時,表示i城市j行業專業化水平高,集聚程度較高,與四川省其他城市相比具有比較優勢;當LQij小于1時,表示i城市j行業專業化水平低,集聚程度較低,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空間基尼系數和區位熵分別從空間和行業的角度測量了集中程度。
4 四川省制造業集聚程度
為了得到四川省30個2位數代碼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情況,根據式(1)計算了2011-2020年制造業各2位數代碼行業以四川省制造業為基準的空間基尼系數。
從表1可以看出,G值最大的是化學纖維制品業,為0.61,十年間平均G值為0.50,集聚程度最高。該行業在四川省內主要集中于宜賓市。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2020年G值為0.50,十年間平均G值為0.39,集聚程度較高。除此之外,截至2020年,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等7個行業G值大于0.10,剩余21個行業G值小于0.10,其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2020年G值僅為0.01,集聚程度最低。

表1 2011-2020年四川省各市州制造業營業收入占全省比重
30個行業中,G值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10年間增長0.21,2020年該行業空間基尼系數達到0.61;紡織服裝、服飾業10年來G值增長0.11,2020年該行業空間基尼系數達到0.11,有明顯的集聚趨勢。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紡織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3個行業G值增長大于0.01,呈現出產業在地理上集中的趨勢。橡膠和塑料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家具制造業等14個行業10年間G值減少,呈現出地理上分散的趨勢;其中家具制造業十年間G值減少最快,減少0.28,在2020年降至0.03;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十年間G值減少0.16,在2020降至0.06,有明顯的趨于分散的趨勢。
此外,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平均G值最高,集聚程度最高,其中化學纖維制造業、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等行業具有明顯的原料、市場和技術指向性。而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有趨于分散分布的特征。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的G值最大,在2020年為0.23;在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G值最大,在2020年為0.15,這兩個行業也都具有明顯的原料指向性。

表2 2011-2020年四川省制造業各行業空間基尼系數
5 四川省制造業專業化水平
采用式(2)計算了四川省18個市州30個2位數代碼制造業的區位熵值,對測算結果進行整理,繪制四川省制造業空間分布態勢圖(如圖3所示)。發現四川省制造業整體集聚水平呈現擴散趨勢,2011年四川省制造業區位熵值大于1.1的城市有個6,首位城市為資陽市,LQ為1.88;2020年區位熵值大于1.1的城市僅有1個,為德陽市,LQ為1.11。2011年四川省制造業區位熵值大于1.0,小于1.1的城市有5個,首位城市為內江市,LQ為1.08;2020年區位熵值大于1.0,小于1.1的城市有12個,首位城市為眉山市,LQ為1.11。2011年四川省制造業區位熵大于0.8,小于1.0的城市有5個,首位城市為宜賓市,LQ為0.95;2020年區位熵值大于0.8,小于1.0的城市有3個,首位城市為成都市,LQ為0.94.2011年和2020年四川省制造業區位熵小于0.8的城市有2個,LQ值最小的城市均為甘孜州。制造業整體從成都平原經濟圈向外圍擴散。

圖3 四川省制造業區位熵空間分布態勢
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農副食品加工業LQ值大于1的城市個數最多,在2020年分別為12個和11個,主要分布于四川省欠發達城市,說明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農副食品加工業在這些城市具有一定的空間集聚態勢與專業化優勢。化學纖維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LQ值大于1的城市個數較少。在2020年均僅有兩個,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經濟圈,這三個行業均為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對于技術資本要求較高。

表3 四川省制造業各行業專業化水平
6 四川省制造業區域布局政策建議
6.1 主要結論
應用空間基尼系數和區位熵分別對四川省2位數代碼制造業空間集聚程度和各城市專業化水平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四川省制造業各2位數代碼行業集聚程度不一致。化學纖維制品業的集聚程度最高,且在2011-2020年間空間基尼系數增長最快,集聚趨勢明顯;橡膠與塑料制品業集聚程度最低,其空間基尼系數僅為0.01;家具制品業的集聚程度下降最快,其空間基尼系數十年間下降了0.28。
(2)四川省各城市制造業優勢產業不同。如巴中市農副食品加工業的專業化水平最高,宜賓市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的專業化水平最高,攀枝花市金屬制品業專業化水平最高,區位熵值最大。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專業化水平較高的城市增長最快,LQ值>1的城市個數由2011年的2個增加到2020年的7個;紡織服裝、服飾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專業化水平較高的城市減少最多,LQ值>1的城市個數分別由2011的7個、8個減少至2個、3個。
(3)四川省制造業總體集聚程度下降,在地理分布上呈現分散趨勢。30個2位數代碼制造業行業中,14個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減小,其中家具制造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和其他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程度下降最快;儀器儀表制造業、造紙和紙制品業等5個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十年間幾乎無變化;11個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增大,但除化學纖維制造業和紡織服裝、服飾業外,其他產業集中趨勢不明顯,且四川省整體基尼系數減小。
6.2 政策建議
(1)家具制造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和其他制造業4個2位數代碼制造業10年間G值下降超過0.10,分散趨勢明顯。這4個產業均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應進一步推動這些產業由成都市向外圍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城市轉移,發揮這些城市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豐富的勞動資源優勢,加強其市場競爭力,加速接受產業轉移的城市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合理引導產業空間布局,同時有助于推動成都市等向外進行產業轉移的城市的產業升級。
(2)化學纖維制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紡織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5個2位數代碼制造業10年間G值增加超過0.05,集聚趨勢顯著。其中化學纖維制造業和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兩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進一步向宜賓市、自貢市;資陽市、廣安市等城市集聚,技術密集型產業集群有助于發揮其知識溢出效應,促進產業高質量快速發展;紡織服裝、服飾業,紡織業兩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向南充市、廣安市集聚,廣安市近年來積極承接沿海紡織產業轉移已取得不錯成效,同時南充市作為中國西部地區唯一的“中國綢都”,這兩個城市應把握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機遇,進一步發揮兩地勞動力優勢,積極推動產業協作集群,推動絲紡服裝產業高質量發展,打造“地理標志”品牌。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具有明顯的資源導向性,應充分發揮攀枝花市、內江市的資源優勢,推動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綠色發展。四川省要進一步加強這5個產業的園區建設,打造產業集群,增強各產業的知識溢出效應,積極進行相關產品“地理標志”品牌建設。
(3)四川省各市州應結合自身特色,依托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稟賦構建特色優勢產業集聚,充分利用現有專業化水平,合理優化四川省內制造業各行業空間布局。如宜賓市和瀘州市應依托其釀酒歷史和地理優勢,進一步優化白酒品牌建設,兩地要加強交流合作,攜手重振川酒。南充市和廣安市應積極打造紡織業“地理標志”品牌,建設絲綢紡織集群,打造中國西部最大的絲紡服裝加工制造基地。廣元市要充分發揮其資源優勢,進一步發展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和家具制造業,積極完善綠色家居全產業鏈,大力承接東部沿海和成渝地區家具制造業專業,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建設中國西部重要的綠色家居產業基地。攀枝花市和內江市要充分利用其資源要素稟賦,綠色高質量發展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和金屬制品業及其衍生產業,推動產業協作,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攻破重金屬綜合利用的核心技術問題。資陽市和遂寧市要進一步做好承接成都市產業轉移工作,爭當承接專業轉移的“領頭雁”。巴中市和甘孜州應做強做大農副食品加工業,打造生態食品產業鏈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德陽市和眉山市要充分利用其專業化水平,進一步發展設備和電氣機械制造業,積極吸納高技術人才,推動技術創新。成都市和綿陽市則應進一步利用其現有優勢,加大對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資本投入和政策支持,研發具有全國競爭力的計算機、通信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