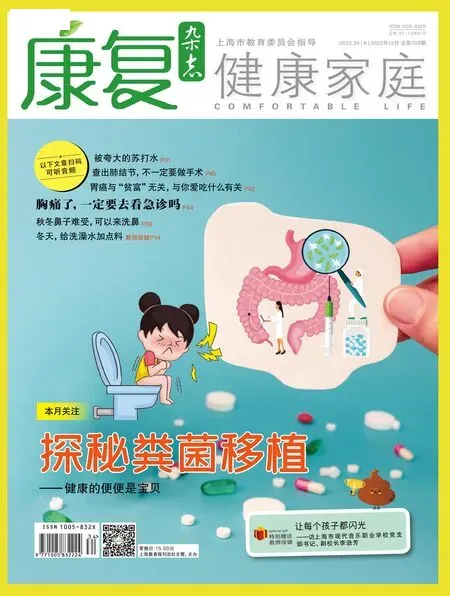常服避孕藥,會增加患乳腺癌的風險嗎
文/劉引
口服避孕藥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女性的命運甚至人類的歷史。有人撰書寫道:“避孕藥首次將性和生育分開,使得女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說,它改變了婚姻,改變了男女關系,改變了家庭的定義,使女性獲得更多就業和受教育的機會。然而,近年來,對避孕藥質疑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在道德層面,有人指責它是濫交、通奸的“幫兇”;在醫學層面,有人認為避孕藥含有性激素,會大大增加罹患乳腺癌的風險。事實真是如此嗎?
避孕藥致癌?事實并非如此
最早對“避孕藥致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 9 7年。國際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上刊登了一項包含16萬人的大型研究,該研究指出避孕藥增加了7%~24%的乳腺癌發病風險。這一數據引發社會上的軒然大波;緊隨其后,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避孕藥列入了一類致癌物。
然而,這項研究的對象是老一代避孕藥,雌孕激素含量很高,不符合當下情形和需求。新一代的避孕藥在改進了成分和工藝后,結果又是如何呢?
2 018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刊登了一項丹麥的全民研究,囊括了18 0萬育齡期女性,數據來自丹麥國家藥物產品統計注冊數據庫,其中包括1150 0多例乳腺癌的詳細信息報告,隨訪長達10年的結果。這項研究證實,2 0世紀9 0年代中期以來開發的新一代避孕藥,仍然會增加20%的乳腺癌發病風險。
這個數字聽上去很可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普通民眾乳腺癌發病率的原有基礎上增加2 0%;而人群中乳腺癌發病率并沒有那么高。如果進行換算,這代表8 0 0 0個女性連續服用避孕藥一年,其中有一個人會因此罹患乳腺癌。而且,使用年限小于5年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在停藥后會很快消失,而使用年限較長的女性風險則會持續較久。
新一代避孕藥或可降低患癌風險
其實,與服用避孕藥相比,不良的生活習慣更容易增加乳腺癌風險,如營養過剩、肥胖、高脂飲食、過度飲酒等。另外,千萬不要忘記一種情況,基因的胚系突變所帶來的乳腺癌風險。比如BRCA1/2基因,它們隸屬于同源重組修復基因,這類基因如果存在胚系(天生攜帶的)致病性突變,那么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高于普通人群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在這樣的基因背景下,如果再長期服用避孕藥,風險還是有點高的。除此之外,對于乳腺癌患者來說,應盡量避免服用避孕藥,而采取其他有效的避孕方式。

其實,避孕藥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可減少計劃外生育的不良后果。計劃外的生育不僅從心理上、精神上、輿論上會對女性造成巨大的壓力,如果處理不當還會導致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對于計劃外的胚胎而言,無論是勉強將其孕育下去,還是忍痛將其流產,都存在倫理上的困境和爭議,更不必提在某些所謂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女性甚至沒有選擇人工流產的自由。
除此以外,新一代避孕藥還可以減少一系列婦科腫瘤發病的風險:可以降低3 0%~4 0%的子宮內膜癌風險,3 0%的卵巢癌風險;甚至貌似毫無關聯的結直腸癌風險,也會下降2 0%左右。2 021年發表在《癌癥研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專門闡釋了長期口服避孕藥與各類癌癥風險之間的時間依賴性影響。該研究提示,僅在停止口服避孕藥后小于2年的時間內,使用避孕藥的女性其乳腺癌發病風險會提高;而對于預防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的作用,在使用者最后一次使用口服避孕藥后長達3 5年內仍然相當顯著。當然,這并非鼓勵大家為了防癌去吃避孕藥。
總結:“小藥丸”科學用,不必因噎廢食
作為一名乳腺科醫生,我仍然推薦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可以繼續科學地服用小藥丸,大可不必因噎廢食。同時,千萬不要忘記健康有效的避孕措施還有很多,比如安全套。畢竟,與做家務、養育孩子一樣,男性朋友也應該承擔起一部分責任哦。
延伸閱讀
避孕藥的出現,改變了女性的命運
人類自古以來,便有避孕、節育的意識和傳統,但這也困擾了人類幾千年,人們想出各種方法“折騰”自己。最早關于避孕的文字記載出現于公元前1850年,當時的人類使用蜂蜜、樹葉和獸皮等通過物理阻隔來進行避孕。古埃及人認為,鱷魚或者大象屬于“神獸”,在房事前服用神獸的糞便,有助于避孕。這種方法可能奏效,但絕不科學,更遑論舒適。
事實上,直到現代,人類才擁有健康有效且種類豐富的避孕措施:安全套、口服避孕藥、安全期避孕法、體外排精、宮內節育器、手術避孕法等。“小藥丸”(THE PILL)在英文中特指的就是口服避孕藥丸,即口服激素進行避孕。它從成分上可分為聯合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單純孕激素兩種,其原理是通過激素抑制排卵和增稠宮頸黏液來阻止受精。
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人類社會迫切需要重建以及發展生產力。彼時,號召廣大婦女解下圍裙,走進車間。因此,什么時候生孩子,要不要生孩子,需要服從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與此同時,避孕藥應運而生。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一個婦女平均孕育3.6個后代;到了80年代,這個數字下降到2個。在避孕藥誕生10周年之際,《時代》雜志專門記錄了一系列女性的心聲,講述避孕藥如何改寫了她們的人生,使得她們獲得受教育以及工作的機會,從而擺脫貧窮和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