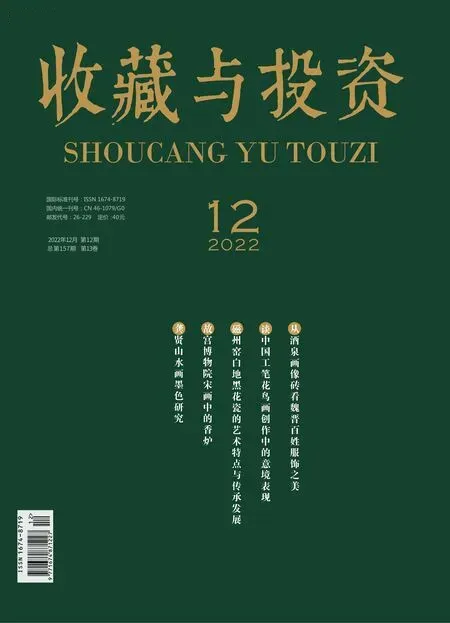顧愷之“傳神論”美學思想與當代價值重申
耿 媛(澳門科技大學,澳門 999078)
中國畫藝術作為一門純粹的造型藝術,深刻地依賴著二維的視覺形象與畫家的筆墨技法來構型整體作品,二維繪畫的局限性在中國畫藝術悠長的歷史縱深與深厚的文化空間之下經由各代創作者們的辛勤探索,從古代的樸素畫法演變到今日的百花齊放,已經逐漸演變為一門成熟且獨一無二的藝術。中國畫畫家們早在魏晉時期就開始了對于繪畫理論的探索與摸索。顧愷之作為中國歷史上首位留存下完整作品與系統理論的人物畫家,他的論作《論畫》集中于對魏晉畫作的評論,也是中國畫歷史上留存的第一篇繪畫理論,其間包含了顧愷之對人物畫的“神采”“形質”“形神兼備”等核心觀點,這些觀點對中國畫理論構建與后世創作具有深遠意義。
一、“形質”與“神采”的歷時性概念探牙賾
在中國傳統繪畫的各個種類中,人物畫具有較高的繪畫難度,同時也是最具歷史性和社會性的,畫中角色的軀體動作、服飾裝扮等無不承載著歷史性的信息元素,同時畫家對角色畫像的不同處理方式也反映出時代的癥候性畫法。東晉時代的顧愷之提出了“以形寫神”的繪畫原則,是中國畫早期對“形質”與“神采”的關系做出的第一次定義與認識,他是第一個將原本有多種含義的“神”這一概念引入繪畫的畫家,并將其與“形”相結合,從而開創了中國畫美學境界的新篇章。在當代視野之下對形神理論進行再認識,時空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由此不能割裂顧愷之提出這一理論時的具體語境,這些語境深刻地影響著何為形、何為神、形神關系、各自的存在狀態、主次關系等問題的發展,并反映這些問題背后的形成肌理。
顧愷之生活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四起、社會分裂,創造出了寬松的思想文化環境。儒學、佛學、玄學思想彼此交融、各自活躍,佛學與玄學的合流更是這一形神思想形成的直接來源。合流思想之下,士人們開始了對個性、主體性的追求。“以神至上”成為人物畫的評判標準,同時出現了以道德、品行、精神氣質等為品藻對人物作出分類評價的風尚。這些對人物的評價標準與人物的審美標準,都成為顧愷之形神論的思想淵源。神采成為人物注入精神氣質的重要構成部分,同時還講究人物內心的審美情感表露。顧愷之在《論畫》中曾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人物畫的難度不僅體現在對形狀的準確把握、人體結構的復雜性,還體現在對人物內心狀態的刻畫。只有將這些刻畫好了,才能達到形質和神采兼備的效果。總而言之,形質和神采作為中國繪畫藝術幾千年創作實踐出的結果,經過歷代畫家的不斷發揚與傳承,早已相互融合成為“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的境界,也逐漸演化為中國繪畫藝術的基本要求。
二、當代審美視野下重審“神采”與“形質”
(一)神采與形質關系的學理性辨析
上述理論已經對“神采”與“形質”的歷時性概念進行了一定闡述,如何將其重新放置在當代審美視野之下,形質論的內涵與外延又發生了另一重的認知變化。
在探索繪畫美學的道路上,魏晉時期的畫家注重描繪客觀對象的外表與造型,這就是形質。藝術之所以具有美的欣賞價值,不僅在于傳遞了文化內涵和思想情操,更在于它高于生活,中國畫作品通過藝術化的技法,給予了它們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形質作為中國畫精神的外化形式,承擔著重要的職責,只有具有美妙的外在形質,才能吸引欣賞者去深入領悟中國畫作品想要傳遞的深層次美學追求與精神氣度。
神采指的是中國畫作品中所彰顯出來的精神氣質與風采。一幅優秀的中國畫作品不僅在形質上具有審美價值,更在于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意蘊美,它會創造出獨特的審美意象,并引導欣賞者進入作品的意境中,讓他們領悟到藝術家在創作這幅中國畫作品時想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與美學追求,同時他們也可以感受到藝術家的修養、學識、精神等。藝術美之所以高于生活,一方面是通過藝術家精湛的技巧將生活中值得創作的事物提煉出來,另一方面是因為藝術家并不是簡單粗暴地搬運生活素材,更是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藝術家的思想和人生經驗,因此,中國畫藝術中的神采是一種虛無渺茫、抽象的東西,它依靠中國畫作品的形質和中國畫作品的內涵升華為神采。
二者不僅不能缺其一,同時要做好均衡二者的關系。如果形質重于神采,中國畫作品就會流于虛浮,空有華麗的外表,卻沒有深層次的內涵與感染力,也就無法打動欣賞者;如果神采重于形質,就會脫離實際,事實上沒有恰當的載體,神采根本無法獨立存在。因此,在中國畫藝術中,“神采”與“形質”的關系是相互兼容、相互均衡的,只有形神兼備,才算是一幅好的中國畫作品。
(二)以宋彥軍與羅寒蕾為例:重審當代神采與形質的關系
將神采與形質放在當代視野之下,若要對其關系進行重新定義,就要對各自的實質與其所包含的能指性關系進行現象學視域下“面向事物本身”的認知。以宋彥軍的人物畫為例,他是當代中國畫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線條運用方面,通過線條的細密精到、連綿不斷、悠緩自然表現人物的形神。在繪畫造型時提煉出能表現物象結構的線條組合,能準確、生動、迅速地表現形質,突出基本特征,達到畫面整體效果的和諧。宋彥軍在《都市麗影》作品中描繪了九位神態迥異的都市女青年在街頭穿梭的場景,她們的衣著能體現出時代的特征,是一種時代的剪影。都市人物題材涵蓋家庭生活、校園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面,都市女性在城市中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她們有的追求時尚靚麗,有的追求優雅自然,有的個性獨特,女性形象的多面化呈現,散發著青春的魅力。她們得體的衣著和精心的打扮充分展現了都市女青年對生活的熱情,帶有一種青春洋溢的氛圍。宋彥軍使用自身技法對肌理質感進行表現,例如女青年身著的牛仔褲,在表現面料質感的同時傳遞了真實的粗糲感。從女青年的衣著打扮中,可以看出他對都市女性的個人物形象的理解,從特殊的形象中挖掘出了特殊的形神。
東晉畫家顧愷之曾說過:“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他認為人物的神情意態,就在于這對眼睛,這句話體現著顧愷之對神采的理解。《都市麗影》中也傳達著這種含義,女青年目光中帶著堅毅,清澈而明亮。畫中人物的眼睛讓欣賞者感受到女子的自信與熱情。這些外部表象往往可以直接體現她的生活狀態,具備青年女性的特點,知性優雅、風姿颯爽,這一切都構成了整幅作品的意境與神韻。

圖一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摹局部) 27.1 cm×572.8 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人物畫作為中國傳統繪畫最早出現的類型,講究通過線條、色彩等二維平面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與西方繪畫的寫實風格不同,中國人物畫描繪的是自然的生活和人物原本悠然自得的狀態,通過人物的情緒狀態、氣質動作等特征傳遞出一種由內到外的神韻,從而透過畫面語言讓受眾對其進行精神上的關注與思考,正所謂由神入畫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羅寒蕾是當代視野下另一位重要的中國畫創作者,在羅寒蕾的《日日是好日》(圖二)中,可以看到三名青年女子身著時尚衣物。畫家通過勾勒描繪人物的形質,向欣賞者展現女子的行為動作,借助表象的“形”去捕捉女子的“神”。只見其中一位女子有著利落的短發,穿著優雅的高跟鞋,手持一束鮮花,快步走在街道上。女子身旁的植物為整幅畫增添了色彩。動植物有時也會作為一種特殊的性別意識符號出現在繪畫作品中。基于世俗大眾對于女性與動植物之間聯系的認知,花就如女子一般動人,絢麗綻放的花簇擁在女子身邊,襯托得女子更加嬌艷。

圖二 羅寒蕾 《日日是好日》200 cm×170 cm 2009年中國美術館收藏
羅寒蕾筆下的女性,通過造型的現實性、生動性、細膩地表現出呼之欲出的蓬勃氣息,線條的刻畫、濃郁的抒情性和女性的知性優雅和諧一致,讓觀賞者置身于畫面中讓人著迷的詩境,女子的神采風韻中洋溢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此外,在中國人物畫中,形神關系不僅體現在畫幅內容上,更應該是作者通過筆墨來抒發內心情感的一種方式,將對客觀物象的描繪與主觀精神的傳達交融,才能稱之為“形神兼備”。
在此,“神采”與“形質”成為當代人物畫的一種創作方法,它們不再是一種創作的規則與桎梏,而是擁有了更為多元的話語解釋權,采用一種現象學的視野,強調將物象從被壓制太久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從而擁有全新的本質形象,在物的本質中傳遞著神采,即創作者的自身審美趣味與元藝術的繪畫思想。
三、結語
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產物的繪畫藝術,中國人物畫歷來注重對主體精神的傳達。傳神寫照,即指人與物內在溝通的過程與結果。在藝術創作的審美觀念中,作品的“神采”不僅是表達作品的和事物所包含的內在精神,還在于傳達作者的涵養、精神等。
縱觀中國古代繪畫的發展史,神采與形質并存早已成為中國畫鑒賞的標準。就繪畫而言,“神采”不是對外在神態的描繪,而是反映了人物內心的精神。“形質”與“神采”不僅是孫子所說的“文質彬彬”中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那么簡單,更是外在形象與內在精神的傳遞。總而言之,形神兼備作為中國畫的最高境界要求,是歷代藝術家和美術家從觀察生活、實踐摸索以及傳承創新中收獲的,是經過辛勤耕耘和不斷沉淀所得到的藝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