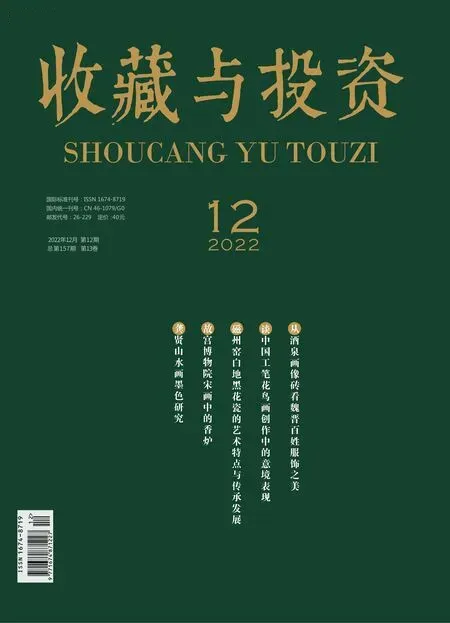芝華長生
——漢代裝飾所見靈芝文化信仰研究
蘆 倩(吉林藝術學院 藝術學研究所,吉林 長春 130012)
漢代是中國繪畫裝飾藝術的奠基階段,在經歷先秦時期由寫實到抽象化的發展,最終在漢代形成較為穩定的繪畫樣式及裝飾體系。在漢代尊崇厚葬、“事死如生”以及讖緯之說的社會觀念影響之下,給予了神話題材藝術創作極大的空間。神仙信仰、求仙問道等觀念長期存在于漢代社會觀念之中。正是因此,漢代所呈現的各類藝術形式之中,不乏神怪題材,這一現象在各類裝飾性器物之上尤為顯著。加之漢初黃老學說提倡休養生息政策,在恢復民生的影響之下,對植物類的藝術創作與內涵延展也日益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從先秦到秦漢時期,靈芝等菌類植物經歷了被神化其來歷再到逐漸被賦予長生作用的過程。人們將其視為仙藥,在應用中對靈芝等仙草圖式進行藝術化加工,運用至各類器物裝飾之中,寄托長生之愿,靈芝文化信仰便在此種社會氛圍之中逐漸發展。
一、漢代靈芝圖樣信仰概述
原始時期,泛神化現象廣泛出現,植物樣式圖騰的象征意味明顯。在漢代裝飾藝術中,對應漢代的神學思想,植物被神話思想所渲染,其中神話中所流傳的仙草也被應用于藝術創作。漢代人所信仰的“仙藥”與“瑞草”種類中,菌類植物是典型。靈芝文化自先秦時期便已萌芽,先秦典籍《高唐賦》中提及靈芝,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靈芝。”[1]人們將靈芝定義為由神女瑤姬幻化的植物,這一典故賦予靈芝神話色彩。靈芝文化發展至秦漢,隨著長生思想及天人感應學說的廣泛流傳,仙藥之說更甚,靈芝被賦予的神話意義愈發厚重。靈芝在秦漢神話體系中有長生的吉祥寓意,在認知過程中人們逐漸了解其功效,將其夸張演化為食之可長生的仙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記載:“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2]在社會普遍信奉的長生思想引領之下,靈芝逐漸被廣泛定義為可使人延年益壽的長生之藥,從而進一步使得靈芝信仰擴大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靈芝圖式經歷了由上至下的傳播過程,這一圖示的表現方式日益世俗化。
在各類裝飾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中,靈芝圖式的出現往往象征著對長生的追求以及對于神仙世界的探尋與思考,在漢畫或者其他藝術形式中以紋樣形式出現,亦代表著情緒與意念的傳承,因此這一圖示往往與意義相關聯的神怪圖式共存。甚至可以說,靈芝圖式依存于神怪題材。靈芝的神話故事以及祥瑞寓意凸顯,但靈芝這一圖式出現的時間相對而言并未與其信仰發展同步,靈芝文化雖誕生于先秦時期,卻在秦漢時期才初步確立仙藥地位,并在西漢時期才真正確立瑞草內涵,出現被定義為祥瑞的文獻記載[3]。在藝術表現上,靈芝圖式往往依托草葉紋以及神怪題材同步出現,但靈芝圖式的應用卻遲于靈芝意義的確立,直至西漢中晚期,靈芝圖式應用才廣泛出現。靈芝圖式與他類草葉紋飾有所差異,其形制較為規整,大致以一枝多果的形式呈現,菌蓋繪制也多以寫實為重,多用近橢圓形表現,形貌特征較為明顯,但也不乏他種表現形式。總體而言,在識認紋飾方面優于他類草葉紋。
二、裝飾化藝術中的靈芝文化呈現
(一)靈芝圖樣形制蠡測
當代對植物紋飾的研究,常存在圖樣界定不明的情況,面對此種現狀,進一步精確化草葉紋的歸屬問題與其文化內涵至關重要,需要對其圖式的文獻記載與所存文物的相關性進行著重分析。當代在對靈芝圖式演變研究過程中,最大的難題便是對其形式的辨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靈芝圖式最常出現在漢畫或裝飾中的神仙圖以及宴飲圖中,是所描畫的神仙托舉之物,即仙藥。識認時,須以畫面所傳達的神話思想為基礎,根據紋飾所附著的整體圖像來判別植物圖式在其中所擔任的角色并探尋其價值所在,同時通過與近似類型的草葉紋相結合進行觀察,從而探查仙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其形式不一,引發了學術界對于仙藥本質為何物的多重思考,學者提出的觀點包含靈芝、樹枝、嘉禾、茱萸、蓮花等植物,眾說紛紜。靈芝圖式往往是此類裝飾之中更容易為人接受的植物樣式。
在漢代神仙信仰體系之中,多種植物樣式被賦予了不同的神話寓意,各裝飾紋樣中均有不同形式的植物出現。發展至今,部分紋樣已有固定名稱與形式判別方案。但在對靈芝圖式的研究過程中,人們卻容易陷入思維定式。今人與古人所提及的“芝類”概念并不相通,從古人角度而言,芝類亦分屬于各類功效的植物,并非局限于菌類靈芝這一架構。擴大觀察視角,古人的靈芝文化信仰應包含由信仰仙草而誕生的多重文化理念。東晉葛洪所作的《抱樸子·內篇》中論及靈芝可分為五大類,稱為“五芝”。“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從其對芝類作的解釋,可見芝類形貌各異,種類多樣,或如蓮花,或如樹枝,形態各異,并非局限于當下所定義的三歧樣式。王仁湘在《漢畫芝草小識》一文中也提及對漢畫中神仙人物托舉植物的看法,他將其定義為靈芝屬,并歸納了靈芝類紋飾的幾大類別,即無菌蓋形靈芝、鹿角形靈芝、蓮花形靈芝以及花葉形靈芝[4],并將多種形式的植物歸為靈芝屬。在這一觀念被提出之前,學術界往往將不同于三歧靈芝的植物形態歸于早期蓮花紋、嘉禾紋、茱萸紋等它類具有祥瑞寓意的圖式,歸為靈芝者寥寥無幾。王仁湘在文中分析了不同于三歧靈芝的幾大類別的靈芝屬合理性,其例外之處是將神仙題材畫作中具備蓮花以及四葉紋形態的植物形象,根據畫作風格及環境的關聯性,視作靈芝之屬,并將其作為一種新的思考方向進行溯源。順其觀點延伸,四葉紋形象、蓮花紋形象、茱萸紋形象有與此前認知相偏移的可能性。當下廣泛認知的靈芝圖式為菌蓋,是近橢圓形的靈芝。
將菌蓋靈芝作為主要的存在方式,且當下人們廣泛認可的便是三歧靈芝樣式,但菌蓋靈芝之中亦存有雙歧或單歧的樣貌,不過較之三歧數量較少。在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的過程之中,筆者通過分析參考文獻以及文物實例之中的圖像特征、古籍記載以及當下對于靈芝圖示理解的裝飾紋樣,發現與靈芝紋最為相似且最為清晰的樣貌便是一枝三果形式。但在紋飾應用中,漢代對稱樣式更為顯著,“三”的象征意味顯得有所不同。在古籍中,靈芝又名“三秀”,《九歌·山鬼》中記載:“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漢代王逸作注稱:“三秀,謂芝草也。”[5]《爾雅》中也有記載:“苬,芝也。”晉郭璞注曰:“芝,一歲三華,瑞草。”[6]郭璞將靈芝視作一年開三次花的珍奇瑞草。古人將這一帶有祥瑞寓意的物象融入藝術化創作之中,取其一年開花三次之意,從而形成三歧靈芝的圖像。東漢班固也著有《靈芝歌》:“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7]東漢年間,在神學思想廣泛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將靈芝的出現與人性道德觀念體系和祥瑞出現的情況相關聯。對照這種情況,在三歧靈芝形制演變的過程中,古人還有可能賦予靈芝人性道德的象征意味,以增添人文氣息。在漢代思想中,天、地、人合一的觀念始終貫穿于藝術表現中。靈芝被賦予神話寓意之后,不僅是作為一種植物形式而獨立存在,還將“天”與“地”聯結,最終呈現“人”的世界。
草葉紋往往存在識別不明的情況。以漢代三歧靈芝這一范例為標準,以草葉紋成熟時期的紋樣作范本,根據已發掘文物中的相似圖案進行推導,將其串聯,亦可發現與三歧靈芝相關聯的圖式。靈芝等菌類因其同株多果的生長特征,人們在描繪它時,會對其進行寫實化與藝術化的再創作。同株多果成為菌類植物的代表特征之一。西漢早期的一些裝飾性紋飾亦有同株雙果,以柿蒂紋為代表的形似同株四果的紋飾,甚至還有同株多果的植物紋飾形式。此類紋飾雖與靈芝圖式相似,但根據植物特性而言,生長以及植物樣貌極具對稱性,故不可將其盡歸于此,應對其相似性進行梳理分析。一株三果式的靈芝圖式,其菌蓋往往根據生長特性被繪為橢圓形或近似于扇形。出土的系列西漢草葉紋銅鏡(圖1)之中,亦出現此類近似扇形的葉紋形象,且附有銘文“與天無極”等帶有一定神學與長生意味的字樣。該草葉紋銅鏡之中,兩近似水滴扇形的葉脈紋形象對稱分布于柿蒂紋兩側,且中央出現形似多重菌蓋相疊壓的圖式,有可能是靈芝圖式的早期形貌或他種形貌。雖仍無法得出該圖式為靈芝的結論,但結合整體裝飾紋樣看,該銅鏡的整體風貌、祥瑞寓意與神學意味明顯,且此類紋飾在這一時期成為風尚且廣泛出現,與時代特征相匹配,其植物紋飾意義有可能與長生思想相關。

圖1 西漢與天無極草葉紋銅鏡
總體而言,三歧形式作為目前爭議最少的靈芝圖式已被廣泛認定為靈芝,將靈芝作為紋樣裝飾并附于物品上,寄托著漢代人對長生的渴望。但對于它類未匯總形成體系的草葉紋形象,則有待進一步精確細化其發展脈絡,探察其是否與靈芝圖式有關聯。
(二)漢代裝飾中的靈芝圖式畫面分析
由于神學思潮的日益發展,在漢代裝飾藝術之中,靈芝圖式被應用于各個方面,西漢末年到東漢年間,更為廣泛地出現在各類神仙題材的裝飾繪畫之中。從藝術創新角度而言,靈芝圖式經歷了與漢代藝術相對應的從簡化到日益豐富的發展過程,并在神仙題材繪畫中以其富含的藝術美感以及價值體現,成為此類繪畫的重要標志。因目前僅有三歧靈芝圖樣是較為廣泛認可的靈芝圖式。在分析與判別的過程之中,人們對疑似圖樣不作過多可能性分析,仍主要選擇三歧靈芝圖樣作為重點來進行風格化與美學價值的分析,且大致主要為東漢年間所存文物的紋飾代表。在漢代的眾多藝術形式之中,神仙題材所覆蓋的靈芝圖式占比極高,靈芝圖式作為單一植物形式,往往與羽人、仙侍、鳳鳥、四神等形象相伴出現,且在所有存有靈芝圖樣的神仙題材裝飾性繪畫之中,靈芝圖式皆不作為畫面主體進行表達與呈現,在畫面所描繪的場景之中,則大多有羽人手持靈芝、仙侍手持靈芝側立于西王母等主要神仙身旁,鳳鳥口銜靈芝,靈芝于神仙身側獨立生長,用以象征神界氛圍等幾大類別。
畫像石作為起源于漢代的獨特藝術形式,其上所描繪的漢代民風民俗給后代提供了極高的參考價值。畫像石在藝術創作形式上風格多樣,存有靈芝圖式的畫像石更為普遍且內容豐富,幾乎囊括大多數靈芝樣式。仙人六博圖式作為漢代典型的神話象征,在畫像石以及墓葬之中較為常見。四川彭州出土的東漢時期仙人六博石函之上(圖2)便出現了典型的靈芝圖式。與上文所分析的典型三歧靈芝樣式大體符合,以仙人博弈為主要畫面,在畫面下方兩角處均布置有植物形象。兩仙人形象跪立于畫面兩側,左側仙人形象執棋落子之際,右側仙人作振奮之姿,興奮之余似欲起身,整體人物態勢似懊悔,亦似驚嘆之意,其中,兩仙人身上均有近似于羽翼的裝飾,是為羽人形象,畫面上方也呈現有不規則形狀紋飾,或為仙界飛禽一類。畫面下方兩側各繪有兩叢靈芝,均為三歧靈芝,這一畫面是以簡潔的形象對靈芝進行塑造,并未以規整橢圓形替代,而是遵照靈芝原始形象進行描畫,使得形象清晰,也使觀者易明晰其畫面所處空間環境與氛圍。

圖2 四川彭州仙人六博畫像石
此圖式僅作為三歧靈芝形象的簡易形式,雖同為一類型圖式,但在演變發展過程中,隨著對于畫面豐富性與美感的進一步追求以及神學思潮的進一步發展,圖式形象在畫面中也有所改變。從東漢新津崖墓中出土的仙人六博畫像石(圖3)中可以明顯看出此種差異[8],雖同為仙人六博,但后者不論是從畫面整體的細節刻畫還是從畫面整體的美感而言,均有極大提升。就靈芝圖式的塑造而言,與四川彭州仙人六博畫像石相比,新津崖墓出土的仙人六博石函中的靈芝體量明顯增大,且有分枝現象,雖有樹形結構的特征,但其并非為樹形,觀察菌蓋可以發現,對于菌蓋的塑造與此前畫像石上的菌蓋相似,且在遵照實物形體的基礎上有了更加明顯的指向性特征,即更具寫實特征,塑造中更加注重對菌蓋形狀的細節刻畫,故而因此排除其為樹形的可能性。

圖3 四川新津崖墓仙人六博石函
畫面中靈芝生長旺盛,擁有雙重分枝的結構,菌蓋飽滿圓潤,菌柄分支雖多于此前形式,但描畫方式仍采用纖細的光滑曲線,整體畫面效果盡顯柔弱迎風之感,柔弱卻非無力,反而生長態勢良好,卷曲的菌柄攀援向上,仿若有靈力滋養,使人望之便有飄然之意。結合畫面整體而觀,靈芝仿若飄立于云間,盡顯神界風采。分枝形式的出現也使得靈芝在畫面中的占比更大,圖中靈芝為雙重分枝的情況,靈芝大小已與跪姿仙人大小相近,與現實生活中的靈芝相對比,該畫面上的靈芝與石函上的大小以及生長形式并不相符。可見,此時的靈芝形象已逐步擺脫寫實描畫而進入藝術化創新的階段,同時也賦予了靈芝更豐富的神話價值與人文內涵。除仙人六博圖式之外,靈芝在以西王母、鳳鳥、四神等為主的神仙題材的裝飾性繪畫之中所呈現的樣式大多與畫像石中形象以及演化趨勢相一致。在畫面中,雖不把靈芝作為畫面主體形象塑造,但作為裝飾元素而言,其以特有的神話以及長生寓意來增添畫面的神話色彩,在整體畫面的完整性、寓意性以及人們所給予的期盼之上增添了信念感,共同豐富了漢人熱衷求仙問道,追求升仙逍遙的精神世界。
三、結語
在漢人所描繪的虛幻且未探知明朗的世界之中,充滿浪漫色彩且帶有人文氣息成為這一時期的時代特征,所接續演變并再度創作與構思的神話體系更是奠定了中國神話體系與信仰的脈絡與基調。靈芝文化信仰僅為其中一環,但作為漢代人對于長生思想的追求以及對于神仙世界及未知世界向往的象征性代表之一,承載著無盡的浪漫幻想與期盼。靈芝文化信仰的演變與發展,同樣也體現著漢代人對于生命起源的理解與探索過程。漢人將這一文化形式與藝術形式融合,用藝術的形式將這一構思進行實體化創作,融入并貼近現實生活,信仰的全民化同樣也推動了藝術的廣泛性。靈芝作為漢代長生思想最為典型的圖式象征,將人文思想與神文價值共同貫徹其中,并通過與神話人物、神獸題材的聯合創作,以畫面形式再現漢代人期望中的神仙世界,最終成為漢代人精神世界的現實寄托,更成為傳統信仰中一個浪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