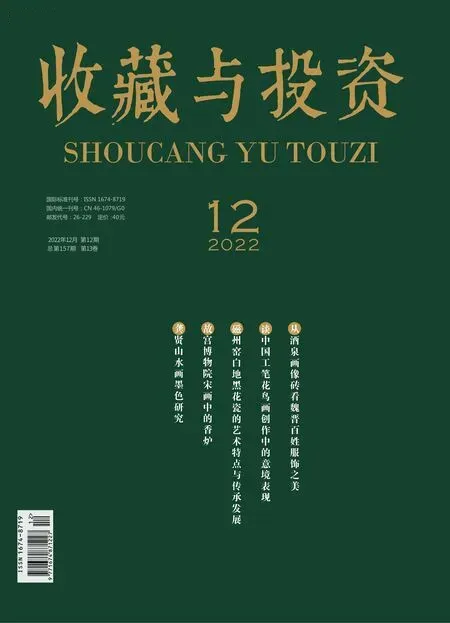淺談《益州名畫錄》中的“逸格”
王 菁(福建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宋代被認為是中國繪畫的繁榮時期,以蘇軾、米芾等人為代表,提出了許多關于文人畫的理論,其中“逸”的提出體現了文人畫家們不隨世俗、目標高遠的精神境界,極大地影響了古代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同時也為文人畫樹立了一個新的形象標準。“逸”作為一個美學概念正式被提出是在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的四格論中,主要表現為“逸品”,其藝術性要遠遠高于其他三者。然而這并沒有改變人們的繪畫審美,直到宋代黃休復對其作出了新的定位,將“逸”放在了四格之首,由此提升了“逸”在文人畫中的地位。
一、《益州名畫錄》“逸格”的提出及其內涵
在古代文字中,“逸”的本義是逃跑、奔逸,在謝靈運《會吟行》中,“逸”字被引申為隱居避世,這樣就能不受約束,悠然自得,所以“逸”又被解釋為豪邁、豪放的意思,這個意思在《滕王閣序》中也有應用。再往后又被引申為安樂、閑適的意思。北宋初期,畫家黃休復編撰了畫論著作《益州名畫錄》,該書主要以收錄為主,記載了從唐代到五代再到宋初時期成都地區的五十八位畫家及其作品,并將他們按逸、神、妙、能四格來劃分。在畫錄中,黃休復把“逸格”放在四格之首,是位于自由層面的最高層。畫錄對“逸格”作出了解釋,道: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一名優秀的藝術家想達到“逸格”,必須要在熟練掌握藝術技巧與技法的基礎上,對所要表達的對象有全方位的理解,擁有熟練的繪畫技法和極高的悟性才能達到。
畫錄中提到的“能格”是藝術繪畫的造型基礎,是達到“逸”的前提,但局限性在于太側重外在形象的精確度與相似度。“能格”之上的“妙格”是技巧層面,比“能格”多了些思考。因為每個人的閱歷、學識與修養以及生活學習環境都有所不同,所以每個人看待同一件事物,都會有不同的見解,他們所表達的情感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作畫的時候藝術家要善于表達自己的主觀情感,才能做到“各有本性”,而不是拘泥于客觀描摹,或者一味地學習他人的技法。“筆精墨妙”強調畫家要學會運用筆墨,能夠“以其一筆能藏萬筆也”。運墨則關系到藝術創作中從意韻到技巧的全部要求,最終要能夠達到“得意而忘形”“技進于道”的境界。比“妙格”更高的是“神格”,位于天才層面,歸于“神格”的作品,不僅有著成熟的技法,還能做到“氣韻生動”,即生動形象地反映對象所蘊含的神韻。
黃休復將“逸品”列于四格之首,也不是毫無依據的。首先,能夠達到“逸格”要求的畫家必然有著超脫世俗、不慕名利的精神,而他們的作品也總是給人一種清逸、簡約的感覺。而“神格”只要求傳達對象所蘊含的神韻,并沒有深入到創作主體的精神層面。從黃休復對“逸格之人”孫位的評價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具有豁達的生活態度和超脫世俗的精神,說明生活態度也與藝術息息相關。“逸”所追求的是一種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它超越了神采而達到了“天人合一”,最終歸于自然。綜上所述,不管是從審美境界還是從精神上比較,“逸格”均遠遠高于其他三格。
“逸”“神”“妙”“能”四格雖然在品評等級上是由高到低的,但這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位畫家的水平,可能有
的畫家更想要描繪出高度寫實的作品,更加尊重客觀事實,如唐代流行的青綠山水,畫家們都是根據真實的山水來寫生的;和精勾細描相比,有的畫家則更多以抒發自身情感為主,如趙孟頫、倪瓚等人。四格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承上啟下的,“能格”的作品要為屬于“神格”的作品奠定基礎,一件作品不可能跨過“妙”而達到“神”,就像鄭板橋的創作理論中,“眼中之竹”不可能直接達到“手中之竹”;能格也無法脫離其他三格而單獨存在,因為美術家所掌握的藝術技巧都是為了表現他們的思想情感,假如脫離了情感,那所謂的藝術就變成了玩弄技巧、玩弄筆墨,只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人也只能成為一個畫匠。同樣,“逸格”也不能脫離其他三格而獨立存在,它是作者通過藝術創作而表達的一種態度,一旦把它們區分開,“逸”就只剩下一種蒼白無力、平淡無味的意境。
二、“逸格”內涵的歷史淵源和發展
關于“逸”的美學命題往前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莊子在他的繪畫理論中便提出“技進乎道”的美學思想。意思是當一個人的技法無法再超越時,再進一步就會附和自然界的規律,也就是“道”,一旦到了這個階段,最終呈現出來的作品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整個藝術過程。通過這個過程,藝術家使自身與自然完全相融,求得精神上的自由,達到對心境澄明的追求。中國的藝術觀由此得到了解放,這也是“逸”的美學內涵最初的來源。
北宋黃休復提倡的“逸格”是對道家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追求的是自然美,是非人工的。老子《道德經》中提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為一個新的品評標準,它影響著中國繪畫的發展趨向,因此在唐代,人們所追求的一種豪放的生活狀態,逐漸變成了宋元時期的“聊以自娛”。在宋代“逸”逐漸被文人士大夫們所重視,繼續發展成熟并提出了“逸格”“逸筆”,一般能達到這個高度的畫家常常表現出高潔傲岸的氣質,如南宋畫家梁楷,他以逸筆滲入院體畫,作品富有個性,筆簡神具。
在畫錄中,黃休復稱“逸格”為最難達到的超高境界,在他看來作品能夠達到“逸格”的畫家僅有孫位一人。孫位是唐代的著名畫家,以御用畫家的身份隨皇入蜀,在人物、鬼神、山石樹林等材上題皆有所成。從畫錄中對孫位的介紹來看,他很喜歡飲酒卻很少有醉酒的時候;既有瀟灑飄逸的外表,又飽讀詩書,文化修養非常高,是一位評價極高的畫家。傳聞千金難得其一筆,由此也能看出他高潔的氣度。逸和氣韻的意思是一致的,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說: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可見畫家的精神境界在中國畫創作的過程中是最重要的,這也是自古以來書畫品評中最重要的標準。這種難能可貴的氣質恰好在孫位身上有所體現,他的畫面很好地表達了他的人生態度,這或許正是黃休復將他單獨一人列為“逸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孫位作品用筆飄逸灑脫、雄氣奔放,主要流傳下來的作品有《高逸圖》(圖1),現收藏于上海博物館。畫面描繪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七位賢人交談的場景。從畫面中可以看出孫位的技法高超,生動形象地描繪出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性情高逸”的共性,又通過肢體語言、動作神態來刻畫他們的個性。從圖中僅存的四位人物不難看出作者在描繪人物形象時,不僅追求外貌的逼真,還注重描繪人物外在的精神面貌,特別是眼神的刻畫。在注意眼睛之外,也注意到環境對人物性格和神情的影響,以細節襯托人格。例如畫中最左邊的阮籍面露微笑,側身靠在墊子上,雙腿盤坐著,神情灑脫傲然。他兩手拿著扇子,這是當時士大夫常用的“麋尾扇”,既能扇風又能代表領袖的身份,突出了阮籍在“竹林七賢”中的地位和風范。這種繪畫風格繼承了東晉顧愷之連綿不斷、悠緩自然的風格形式,既得了“阿堵傳神”之妙,又夾雜了唐人的精細筆墨。

圖1 唐 孫位《高逸圖》(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關于書法繪畫的藝術理論在我國歷史進程中不斷發展、不斷進步。張彥遠的繪畫理論中提到,在運筆連貫、生動有力的同時,要加強對筆墨的“逸”境的追求。宋元時期,書畫理論中對“逸格”的追求是文人畫家極力推崇的,他們將內心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復雜情緒物化到紙上,從而達到情感與形式的完美結合。文人畫從筆法上看,工謹中帶著清逸,設色濃麗中顯清雅,借此來尋求精神上的歸宿。倪瓚作為元四家之一,是元代“逸格”文人畫的代表。他的畫風清新脫俗,追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境界,備受后人贊美。倪瓚的繪畫風格與元四家其他三人有所不同,這也與他的性格和獨特的審美觀念有關。他有著鮮明的主觀色彩,在繪畫實踐上和繪畫思想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對后世的山水畫與寫意畫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漁莊秋霽圖》(圖2)為紙本水墨畫,縱96.1 cm,橫46.9 cm,現藏于上海博物館,是倪瓚在友人王云浦漁莊居住時創作的。在畫中,近景有六棵樹木,枝葉蕭疏,錯落有致。遠景為平緩的山巒,與近景遙相呼應。中景為較大面積的空白,表現的是平靜遼闊的水面。該作品采用了獨特的“河兩岸,三段式”構圖方式,融入自己內心的“逸氣”,將筆墨和畫面的意蘊進行提煉,畫格天真,意境遼闊。這種筆墨、構圖、意境的創新都為中國山水畫提供了典范,由此作品我們可以窺見元代文人的主體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色即是空,是實又虛,是動還靜,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獨有的審美境界。

圖2 元 倪瓚《漁莊秋霽圖》 上海博物館藏
三、“逸格”理論的歷史貢獻和影響
自古以來,中西繪畫的審美觀念與表現形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在藝術創作中,中國畫家感性大于理性,以寄托情懷為出發點,甚至一草一木都透露著情感,作品中表達的意境正反映了作者對生活的態度。西方繪畫總是離不開“理”字,畫面中透露著一種理性思維,不那么注重人的情感,認為自然科學是首要的。這樣的觀念差異導致中西繪畫產生了不同的著重點和表現方式。中國畫中所謂的“意境”指的是在創作過程中經過理性的思考,最后用簡練的線條表達出準確的形體,這便是“筆簡形具”。假如我們一味學習西方的繪畫體系,卻忘了中國繪畫所要表達的“意境”初衷,那么只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對此,“逸格”的提出是尤為重要的,它作為一種崇尚清淡、樸素的繪畫觀念,時刻警醒著人們要保持中國繪畫的本體意識,謹記在學習西方的繪畫方法時,仍要以本土意識為出發點。中國美術界的一代宗師林風眠,早期接觸的大都是西畫,但他仍以固有文化為基礎,將中西繪畫調和,把神韻、情趣表現在畫面上。如果沒有這種對傳統繪畫觀念的思考,較少關注甚至放棄關注中國畫,只是單純地套用西畫框架,那么畫面是無法得到完整呈現的,也無法表現民族傳統藝術的精髓。
因此,“逸格”不僅是一種書畫的品評標準,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對于今天我們學習民族美術也有著積極的指向作用。
四、結語
本文對于《益州名畫錄》的研究主要是對該書的相關內容進行的研究,對其進行了自己的思考。黃休復所說的“逸格”從畫面上的審美情趣上以筆簡形具,崇尚筆墨,書法入畫,詩情畫意這幾點主要因素,“逸”的精神內涵與自然的關系密切,追求天人合一,要求畫家不僅要表達個人情懷,更重要的是要與自然產生共鳴,將自然景物與自己的情感融合。自然與“逸”是相通的,是非人為的、非勉強的。人是通過天地萬物來取法道,宇宙萬物順應生長規律的狀態,自然而然,天人合一。天等于自然,天人相應,應該順應自然。南朝謝赫的“六法”中便將氣韻生動放于首位,注重的是繪畫的神韻,追求的是捕捉萬物的神態,使其畫面達到生動的境界。“逸格”是文人畫作為欣賞的最高標準,筆簡形具、崇尚水墨、以詩書畫為一體,已經成大寫意的一個理想的追求,“逸”潛移默化成為文人畫家的最高的審美追求,推動寫意畫的發展,對后世繪畫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