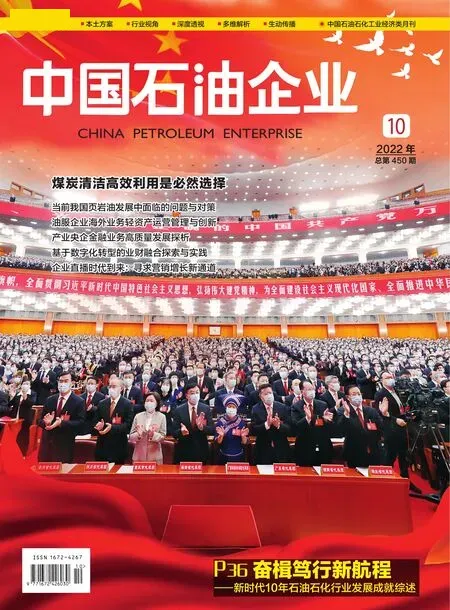“創新是一種樂趣,也是科學家的責任”
——訪中國工程院院士、有機化工專家汪燮卿
□ 文/唐大麟

記者:汪院士您好,我看到您正在電腦上閱讀外文資料,是在查找資料嗎?
汪燮卿:“雙碳”目標里提出今后的石油除了將繼續作為燃料使用外,更多地將轉化為化工原料,雖然石油作為化工原料從重質油轉變成低碳烯烴的生產技術已有將近30年了,但未來仍會有一個規模不斷擴大、內容不斷創新的轉化過程。所以,我們今年準備出版一本這方面的英文書,我正在組織大家趕稿,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做這件事情。
記者:您提到把重質油轉化為低碳烯烴,我了解到目前我國正在大力發展重油制乙烯丙烯,結合我國國情,您覺得我們在重油轉化這條道路上還有哪些可以優化的方面?
汪燮卿:從我國資源稟賦來看,重質油偏多,輕質油偏少且不夠用,所以國家領導層和權威學者歷來重視用重質油生產烯烴,因為它可以緩解輕質油的短缺,提升劣質油利用效率,提高經濟附加值。從重質油生產低碳烯烴的開發技術來講,我們做的比較早,國際上第一套重質油生產低碳烯烴的工業化裝置是我國生產的。從石油化工和煉油技術角度來講,國內第一套出口到國外的成套技術就是低碳烯烴,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是有一定基礎的。至于優化發展這個問題,我認為現在首先應該在原有發展基礎上找到新的突破口,這樣才能找到下一步優化工作的方向。具體來講,把重質油轉化成低碳烯烴不可能像石腦油一樣蒸汽裂解,因為它是一個催化過程,沒有催化材料是做不成的。但是在催化過程中,它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無論催化材料的開發還是催化工藝的開發,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與成套技術的配套,都應該統籌考慮,這也是目前大家也正在努力的方向。
記者:精細化工正在成為我國石油化工產業主要發展方向,您對此您有何展望?
汪燮卿:精細化工的產品非常多,可以說它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無論是國民經濟發展,還是工業與國防建設,都離不開精細化工產品。如果讓我對精細化工的未來發展做展望,那就是“三精”——產品要精雕細刻、工藝要精耕細作,成本要精打細算。例如焦炭,我們現在生產的焦炭很多,污染也很大,但是好的石油焦很缺。不僅我們缺,全世界都缺,所以我們能不能通過精雕細刻、精耕細作、精打細算來生產高附加值的優質焦炭,而不是消耗了資源卻沒有達到資源最大化利用。
記者:上世紀80年代我國石油產量突破1 億噸時,國家曾組織力量研究“如何用好1 億噸油”;現在我們要把2 億噸的油氣牢牢端在自己碗里,您覺得在新形勢下,這2 億噸油氣該如何合理利用?
汪燮卿:雖然現在我國石油產量達到了2億噸,但仍需大量進口以滿足國內需求。這個客觀現實我們想努力扭轉,石油行業也在下大工夫找油,但是誰也不敢保證結果。當時國家提出研究如何用好1億噸油,是基于石油可以自給的形勢;現在思考如何用好自己的2億噸油,形勢已發生很大改變。這自產的2億噸也僅僅是我們石油消費量的30%。石油既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物資,又是國家的戰略物資,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全面的考慮。我之前沒有認真思考過,但覺得深度加工利用肯定是個很重要的方向。因為深加工可以提高石油的經濟效益,提升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我們既要看準技術前沿上的一些問題,更要下工夫去攻克。比如我們剛才談的重油制烯烴,烯烴下面還可以生產乙烯、丙烯,還有PX,這些都是基本的化工原料。所以我們現在就需要考慮怎么讓劣質的重油盡量多地轉化為乙烯、丙烯等,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最小的碳排放,實現低碳化。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在新形勢下就發展不了,這需要引起大家重視,要在深度加工上有一些和過去所不同的新概念。

圖為本刊記者采訪汪燮卿院士。
記者:20年前,在由侯祥麟院士負責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研究”報告中,您負責起草了“油氣節約使用”“大力發展石油替代產品”等建議措施。從目前我國油氣資源發展現狀來看,當年提出的一些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實。結合當前國家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您是否依然主張以上兩點建議?有何新的建議?
汪燮卿:“油氣節約使用”和“大力發展石油替代產品”這兩點,我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比如要發展石油替代產品,明確講就是用清潔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這就需要提高成本投入。這件事我們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但結果我始終不太滿意。以前德國用植物油生產航空煤油,這是清潔燃料,但是它的成本是普通航空煤油的3倍以上,這就需要國家層面的政策與資金支持。最近中國石化鎮海煉化用地溝油生產出來的航空煤油,獲得國家有關部門頒布的適航證書,這種生物航煤是以餐飲廢油等動植物油脂為主要原料,與傳統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其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減排50%以上。所以我相信油氣節約和能源替代在我國是一定有發展前途的,這兩個方向也是不容懷疑的。
目前“雙碳”目標的樹立,也為以上兩點的實施樹立了新的奮斗目標。過去石油工人說“井無壓力不出油,人無壓力輕飄飄”,這個新目標是壓力也是動力。我們現在把二氧化碳埋入地底或用它驅油,這肯定是一個方向。但我也經常發散思維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能不能把本來屬于破壞環境的二氧化碳通過光合作用利用起來,讓它負排放。我們在大西北的這些油田,太陽能資源非常豐富,是否可以探索在二氧化碳排放時結合一些條件產生化學反應,使其變廢為寶。現在大家可能覺得這是天方夜譚,就像我們現在說發明5納米的芯片一樣,但我想如果全世界共同努力,將來這些技術都會實現的。
記者:您剛才描繪的場景,在技術上已經有突破的苗頭了嗎?

汪燮卿:我還沒有看到,這只是我在“鼓吹”。過去這種“鼓吹”會被人說是異想天開,我覺得異想了,天不一定能開,但是不異想,天一定開不了。這句話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有根據的。“文革”期間石油部軍管,1972年5月石油部軍管會給我們單位來電話要我出差,去長沙馬王堆。我那時搞油品化學分析,軍管會代表告訴我,石油部計劃從四川鋪條輸氣管線到武漢,輸氣管線肯定會存在腐蝕問題。他在內參上看到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女尸保存完好,沒有腐蝕,就希望我去把棺液里的成分搞清楚,看是否能應用到油氣管道防腐中。我當時一聽就覺得這簡直是異想天開,但后來再仔細一想,又覺得這個軍代表不簡單,有想法,也敢想,我很佩服他。所以現在我也鼓勵大家要有異想天開的精神,鼓勵大家創新,但不能沒有科學依據的瞎想。
記者:歐美很多轎車都是柴油發動機,這種車更節油環保,為什么柴油轎車不能在我國大規模推廣?
汪燮卿: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國內轎車現在的發動機技術還有待提升,我們現在普通的柴油貨車發動機技術掌握的還是比較好的,但柴油轎車發動機技術難度比柴油貨車大多了,所以它需要投入的成本就大,這對于汽車制造企業和消費者而言都是一個大問題。其次因為國內柴油機在排放上與汽油機相比還是有差距。歐洲柴油發動機之所以搞得不錯,一是它原來就有基礎,柴油英文名“diesel”,就來自于德國工程師狄塞爾,他發明的柴油發動機取代了之前的蒸汽機,這是他們在技術上的基礎優勢。二是在技能方面,其各種零部件配合后與環保的配合度非常好,高效能低排放。但我們國家目前只有汽油機能做到,柴油機排放整體還差一些。三是國家政策調控,過去我們說要提高柴汽比,現在要降低柴汽比,把柴油使用量降下來。雖然柴油機功率大,但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要什么事情都做到全面超越恐怕還有困難,所以還需統籌考慮,重點研究。
記者:您在自傳中記錄了自己顛沛流離的青少年生活,那段生活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汪燮卿:我覺得那段艱苦歲月對我最大的幫助,是讓我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就是遵循自己內心的喜好選擇,不人云亦云。那個時候,雖然國家處于戰爭時期,條件艱苦,但是國家對國民的教育并沒有放松,那種啟發式的教育使我們每一個人的專長都能夠得到發揮,這種教育也讓我受益終身。可能現在大家對我們的教育都不是太滿意,但我也不悲觀。之前我看新聞,有一個偏遠地區的女孩考上了北大,但她報志愿的時候沒有填大家都追逐的金融、經濟等熱門專業,而是報了考古,因為她想去敦煌研究古代文物。我覺得她很不簡單,突破了常人想要升官發財的傳統路徑,而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我總在想,中國這么大,天地很廣闊,如果大家都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把專業分散開來,而不是老擠在一個地方內卷,那么我們的人生機遇都會很多,這樣各行各業也就都能做到百花齊放了,那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定會早日實現。
記者:您在德國待了將近5年時間,您覺得這段留學時光對您日后科研工作的影響是什么?
汪燮卿: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就是培養了我嚴謹的科學作風,這5年時間對我科研思想的轉變很大。我是1956年去德國留學的,兩年后國內就開始“大躍進”。在德國第一年我們都在學習德語,“大躍進”開始后大家都很羨慕在國內的同學,因為“1天等于20年”,所以我們當時總跟德國人說讓我們去工廠實習一下就回國吧,德國人就會狠狠地批評我們一頓,說你們來這里主要是學方法的,如果實習一下就回去,那有什么意義。當時國內的基礎教育還沒有那么嚴格,所以我們在大學畢業去到德國之后,又從分析化學、微積分開始重新一門門地補課。德國人對那些反應方程式太清楚了,就像我們過去背四書五經一樣信手拈來,所以到現在德國都處于全球化工領域頂端位置,這和他們扎實的基礎及科學求實的作風密不可分。我們國家在這方面與之相比差距還很大,所以我一直提倡加大對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投入,這個投入不一定會有產出,但關系戰略發展。我最近看一個資料,美國用天然氣中的甲烷制乙烯和丙烯。看了以后感受很深,他們通過對天然氣氧化來實現這個技術,在實驗室里已經研究了40年,經歷了兩代人,到現在都沒有工業化。我想我們國家如果干這件事,估計干不到10年就解散了,因為沒有利潤且前景不明確。所以我覺得,我們基礎研究一定要轉型,它確實需要付出,有的研究可能立竿見影,很快就有成果,能產生經濟效益。有的可能需要非常長時間,但并不是說沒有效果這些研究就白做了,我們國家應該加強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戰略部署,這樣才有希望在全面的國際競合中立于不敗之地。
記者:今年是侯祥麟院士誕辰110 周年,您在清華求學期間就已認識他,侯老讓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回顧過去,是否還有其他影響您一生的人和事呢?
汪燮卿:我是1951年認識侯老的,那年他回國在清華當教授,而我剛考進清華。在新生迎新晚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他。侯老個頭不高,穿身紅衣服,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但真正接觸是在1961年工作以后,1965年我當了研究室副主任,他常對我們幾個業務骨干說,你們不僅自己要做好工作,還要幫助周圍的人做好工作和研究,8小時是出不了科學家的,應該經常思考。我最敬佩侯老的,還是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特別是在政治運動中能依然堅守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這很不容易。其他對我有較大影響的,我認為是我的中學老師。講一個故事,那時候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在我們老家農村買不到白糖和紅糖,但是有一種麥芽糖做的糖餅。下課后,我們就花幾分錢買一塊麥芽糖回教室吃,但這種糖用手掰不開,我們就在桌子上一拍,讓它碎成幾塊,然后大家一起吃。這時候我們的物理老師就會啟發我們,你們知道麥芽糖掰不開但可以摔開是什么原理嗎?蘋果掉下來讓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那你們是不是也可以發現一個糖餅定理呢?所以我在中學時通過老師們的啟發,在遇到問題時能把學到的知識串聯起來思考,多問幾個為什么,從而可能產生新的思索。這種思維方式的培養,對我日后科學研究思路的打開非常關鍵,我很慶幸能在思維的孕育期,遇到能啟發我靈活思考的老師,這對我一生都很重要。
記者:您曾主持和參與過許多重大化工工藝的研發和生產,回首過去,您覺得自己最驕傲的作品是什么?如果讓您總結成功的秘訣,您覺得是什么?

汪燮卿: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就知道了。咱們國家現在會進口含酸原油,因為它便宜,每桶差十幾塊錢,所以進口含酸原油進行加工可以賺錢。但含酸原油多了以后,會腐蝕設備,所以一個煉廠里面只能進口一部分含酸原油,把它跟普通原油混合稀釋以后,可以減少腐蝕性,大部分煉廠都是用稀釋的辦法來加工含酸原油的。中國海油在惠州煉廠專門安裝了一套全不銹鋼設備煉含酸原油,但這樣投入就很大。所以我就想,是否可以把這個含酸原油的成分搞清楚,以后通過技術改進,在普通煉廠用普通碳鋼來煉,這樣有多少原油就能煉多少。我把我對這個問題的具體思考路徑告訴了我的一個研究生,讓他去做試驗,結果很圓滿,工業化實驗也成功了,在上海高橋煉廠也建了加工裝置,大家都很高興。當時中國石化總工程師曹湘洪院士,對這個技術改進也很感興趣,他就向中國石化主要領導匯報說應該報獎,領導十分支持并希望保密這項技術。但我的上級領導認為,雖然這個技術改造的思路很好,但其技術訣竅一聽就明白,太簡單了,所以不予上報。很多人都覺得可惜,但對我來講得不得獎并不重要,并不是因為我已經當了院士,無所謂了,而是我覺得如果自己的一些想法能解決實際問題,這就是最大的獎賞。所以當時我帶的這個研究生做答辯的時候,去了100多人聽他的答辯,而以前的答辯都是在一個小房間里,最多十幾個人參加。我覺得創新是一種樂趣,創新也是科學家的責任,我們要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至于成功的秘訣,我覺得是不存在的。但作為一名科學家,在探索客觀真理的過程中,首先要對這個探索有興趣,沒有興趣做不好事情;其次就是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應該窮盡所能,讓所有學到的知識都能產生聯系,取得應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讓二氧化碳負排放。我有時候晚上睡不著覺,就會想這些東西,這個思索的過程充滿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