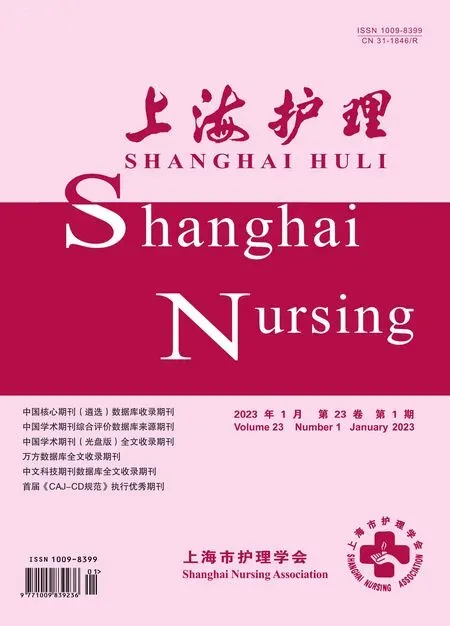云南省高校實習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及影響因素分析
熊尹詩,王 娜,張 穎,胡俊霞,張 穎
(1. 大理大學護理學院,云南 大理 671099; 2. 云南大學附屬醫院,云南 昆明 650000; 3. 云南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4. 昆明醫科大學護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臨終關懷(hospice care)是通過早期識別、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積極評估、控制疼痛和其他不適癥狀,以預防和緩解患者的身心痛苦,從而改善患者及家屬生活質量的一種有效方式,與終末期患者的“死亡質量”密切相關[1]。我國已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隨著老齡人口增加,患有惡性腫瘤及阿爾茨海默病等不可治愈性疾病的人數不斷增加,人們對于優化臨終生命質量的需求也愈發強烈[2]。我國護理人員的臨終關懷知信行現狀不容樂觀,即使是腫瘤科護士對臨終關懷的認知仍處于中低水平[3],因此臨終關懷教育需做大范圍、有深度的普及和推廣。實習護生(以下簡稱護生)可塑性強,進行良好的臨終關懷教育無論是對自身或是服務對象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4]。目前國內針對護生臨終關懷態度的研究較少[5],相關研究更多關注臨床醫護人員。本研究對護生臨終關懷態度進行調查,并探討影響護生臨終關懷態度的相關因素,為今后開展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調查總體為云南省12所醫學院校實習護生:昆明市7所院校共196名,安寧市1所院校27名,曲靖市1所院校33名,大理白族自治州1所院校354名,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1所院校224名,楚雄彝族自治州1所院校219名,實習護生總數為1 053名。其中,來自地級市實習護生占實習護生總數的24%,來自各自治州護生占實習護生總數76%。納入標準:全日制在校實習護生;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無嚴重疾病。排除患有精神疾病、意識行為障礙者及無法正確理解問卷內容者。課題組于2020年7-11月,根據云南省地級市和自治州的劃分,通過分層抽樣的方式,最終納入樣本量為780名護生。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調查卷由兩部分組成。①自制一般人口學特征問卷。包括年齡、性別、生源地、獨生與否、宗教信仰、接受臨終關懷教育的情況、過往臨終關懷照護經歷等。②Frommelt臨終關懷態度量表(Frommelt Attitude Toward Care of Dying Scale Form B,FATCODB)。該量表由Frommelt于1989年編制[6],用于測量護士臨終關懷態度。王麗萍[7]于2016年形成中文版FATCOD-B,總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69,6個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610~0.863。研究者已獲得王麗萍對于本量表漢化版的授權。該量表共有29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記為1、2、3、4、5分),條目1、2、4、11、15、17、19、20、21、22、23、24、26、29為正向計分,其余條目為反向計分。中文版FATCOD-B量表滿分145分,得分越高表明臨終關懷的態度越積極。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5。
1.2.2 調查方法研究者與12所院校的相關負責人取得聯系,并向其解釋研究的目的、意義等,課題組成員(經過統一培訓)采用線上+線下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昆明市區內的護生由各實習組長組織學生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其余地區,各個學校在限定時間內召集本校護生使用問卷星完成線上調查。問卷剔除標準:條目缺失值≥10%。共發放問卷780份,回收有效問卷771份,有效回收率為98.8%。
1.2.3 統計學方法利用Epidata 3.0軟件建立數據庫,雙人雙錄入核查數據的一致性與邏輯性,運用SPSS 22.0軟件進行統計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統計推斷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對數據先進行方差齊性檢驗,若方差齊以ANOVA檢驗結果為最終結果,多重比較以Bonferroni’s為最終結果,若方差不齊以Welch、Brown-Forsythe為最終結果);計數資料以頻數或構成比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實習護生中文版FATCOD-B量表得分情況771名護生的中文版FATCOD-B量表得分為(102.98±9.66)分,得分最高的維度是“針對家屬支持必要性的態度”,得分較高的條目有“家屬應關心和幫助臨終患者讓其更好地度過生命剩余的時光”“臨終關懷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得分最低的維度為“針對照顧臨終患者出現恐懼不安心理的態度”,得分最低的條目為“醫務人員沒有責任對家屬進行關于死亡及臨終的教育”。各條目得分情況見表1。

表1 實習護生中文版FATCOD-B量表得分情況(N=771)
2.2 實習護生一般特征及其對臨終關懷態度的影響本次調查實習護生771名,年齡最小者17歲,最大32歲,平均年齡(20.56±1.62)歲。83.3%的學生明確表示愿意照顧臨終患者;59.3%的學生表示選擇護理學是自己的意愿。不同特征實習護生中文版FATCOD-B得分比較見表2。

表2 不同特征實習護生中文版FATCOD-B得分比較(N=771)
2.3 實習護生臨終關懷相關經歷及其對臨終關懷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以往有照護終末期患者及其家屬經歷的護生中文版FATCOD-B得分高于無相關經歷者(t=8.90,P<0.05);不同當前經歷的實習護生FATCOD-B得分比較,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F=3.05,P<0.05)。兩兩比較顯示當前有處于終末期的至親者得分高于當前沒有處于終末期的至親者。見表3。

表3 不同臨終關懷相關經歷實習護生中文版FATCOD-B得分比較 (N=771)
2.4 實習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影響因素多重線性回歸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6個因素作為自變量,以中文版FATCOD-B得分為因變量,建立多重線性回歸模型。最終有4個變量——性別(男=1,女=2)、學歷(大專=1,本科、研究生及以上=2)、愿意照顧臨終患者(是=1,否=2)、以往照護終末期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有=1,沒有=2)進入模型,Durbin-Watson統計量為2.002,認為回歸模型中殘差之間相互獨立,自相關問題不顯著,對應的VIF值均小于1,說明不存在共線問題。結果見表4。

表4 實習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影響因素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實習護生對臨終患者照顧態度的現狀云南省受調查護生FATCOD-B總分水平高于倪娟等[8]對昆明市(含未實習本科護生)及湯寅瀅等[9]對湖南省(包含未實習護生)護生的調查,與郭奕嬙等[10]在河北所做的調查總分水平接近。這可能與護生參與實習工作后,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對臨終關懷理解更為深刻,更能體會患者的心理,喚起了護生的同理心有關[11]。且本次調查的時間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后,護生經歷過防疫、隔離,更有護生經歷喪親之痛。與此同時,護理人員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行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高度贊揚,使護生使命感增強。加之隨著我國對人文關懷教育及臨終關懷教育的重視逐漸增強,與死亡教育、臨終關懷相關的教育普及增多,對臨終關懷照顧者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得護生臨終關懷的態度也較以往更為積極。本研究中,得分最低的維度為“針對照顧臨終患者出現恐懼不安心理的態度”,最低的條目為“醫務人員沒有責任對家屬進行關于死亡及臨終的教育”,提示護生在進行臨終關懷的過程中,尚缺乏同理心,對于家屬陪伴的重要性認知不夠,后續可通過質性訪談等研究進一步探討。在今后的教育中要強化這方面的觀念,使護生明確臨終關懷的目的和意義,同時注重護生與家屬溝通交流的技巧培訓。目前,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對臨終者的照護需求不斷增加,護生作為我國護理行業未來的中堅力量,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來提升其臨終關懷態度的積極性。
3.2 高校實習護生臨終關懷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3.2.1 一般人口學資料分析本研究中絕大多數受調查護生為女性,女護生的均分稍高于男護生,兩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女性更為感性、細心、體貼有關。工作經驗和患者死亡經歷都不是護生臨終關懷態度的重要因素。雖然較長的臨床經驗有助于鞏固護理知識從而樹立更為專業的護理態度,但共情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品質,可能在護生實習初期對臨終關懷態度產生更大的影響,這與希臘學者Dimoula等[12]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顯示,有無宗教信仰對于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沒有影響,這一結果與顧志華[13]、張晗等[14]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反,與黃昆等[15]研究結果一致。研究結果不同的原因,可能與地區差異及護生對宗教的理解不同有關,后續可以對護生使用訪談[16]及敘事研究等方式進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中納入了大專、本科及研究生三類不同學歷層次的護生,結果顯示三者有統計學差異,研究生及本科護生得分高于大專護生。分析原因:不同教育階段的培養方向和培養能力的出發點不同,學歷層次更高的護生在臨終關懷護理工作中遇到問題時處理得會更專業、更系統,對于臨終患者的心理洞察得更為透徹。這也提示我們在研究生教育的專科培養階段可以進行臨終關懷方向的專業指導,為我國培養一批優秀的專業人才;在本科階段要更注重人文教育的熏陶,為臨終關懷護理教育的普及奠定有力的基石;對于大專護生,應該積極開設相關課程或臨終關懷服務志愿活動,讓他們對臨終關懷的理解更為全面、深刻。本研究結合前人研究[7,17-19],納入云南省各高校實習護生家庭結構、生源地、照顧臨終患者的意愿、過往接受臨終關懷教育情況等可能影響臨終關懷態度得分的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護生家庭結構、來源地、宗教信仰、過往接受臨終關懷教育情況以及以往的喪親經歷對臨終關懷態度得分均沒有影響。分析原因:一方面,隨著國家脫貧攻堅和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深入推進,城鄉差異逐漸減少,醫療教育資源相對平均。另一方面,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可能對死亡有自然崇拜[20],但本次研究納入的實習護生大部分為漢族學生,擁有宗教信仰的占極少數;而且,隨著馬克思主義關于死亡的思想等死亡教育進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21],實習護生對生存狀態與意義具有較高的認同感。對于臨終關懷教育情況的進一步調查發現,即使開設了臨終關懷課程,但存在專科實習護生的相關課程課時少、本科及以上學歷實習護生臨終關懷課程僅作為選修課程學習的現象,這可能是造成其對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影響不顯著的原因之一。這一現狀提示我們在課程設置過程中,應將臨終關懷課程納入必修課,并適當增加課時。
3.2.2 照顧臨終患者的意愿本研究結果顯示,是否愿意照顧臨終患者與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有關,與Laporte等[22]研究結果一致。護生照護臨終患者的主觀意愿能夠讓他們在護理臨終患者時發揮主觀能動性,在面對死亡的情景、接觸重病或瀕死患者的態度上更為積極主動。由于臨終關懷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護生在臨終關懷的護理過程中也會得到相應的情緒調節鍛煉,增強心理彈性,實現一定的個人成長[23]。在我國傳統習俗的影響下[24],死亡教育開展情況不盡理想[25]。結合本次研究結果,提示我們應在課堂上和實習帶教過程中,引導醫學生接受死亡、正視死亡,系統灌輸死亡觀教育,減少他們對死亡的抵觸情緒,用自身的護理專業素養去照護臨終患者,以提升護生應對死亡的能力和實施臨終關懷的技能。
3.2.3 以往照護終末期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本研究顯示,以往是否有照護終末期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與護生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有關,這與Hagelin等[26]研究結果相反。Hagelin表示以往在照護臨終患者的過程中有不愉快的經歷,可能會導致在臨終關懷照護中失去信心和耐心。本研究發現,受儒家傳統觀念影響,家中有親人患重病有過類似照護經歷的護生更能夠體會到臨終患者的痛苦,也更能理解臨終關懷工作的重要意義,從而對臨終關懷態度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提示在護生的教育中,可以通過改編真實案例進行護理劇本的角色扮演,進行類似于巴林特小組學習[27],構建護生臨終關懷教育培訓方案,加強護生對于臨終關懷內容的真實體驗,提升其共情能力,進而激發護生照護、關愛臨終患者的愛心和責任心,從而更好地為臨終患者提供照護。
4 小結
本次研究表明,護生的臨終關懷態度雖較為積極,但仍存在對于臨終患者同理心缺乏、死亡觀念較薄弱、不理解家屬陪伴的重要意義等問題,有待在今后的教學中加以改善。如何引導學生科學、客觀地認識和對待死亡,應該是日后護理教育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護理本專科教育應加大對護生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并為其提供臨終關懷實踐機會,護理研究生教育應專科化、細致化,為我國臨終關懷事業儲備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