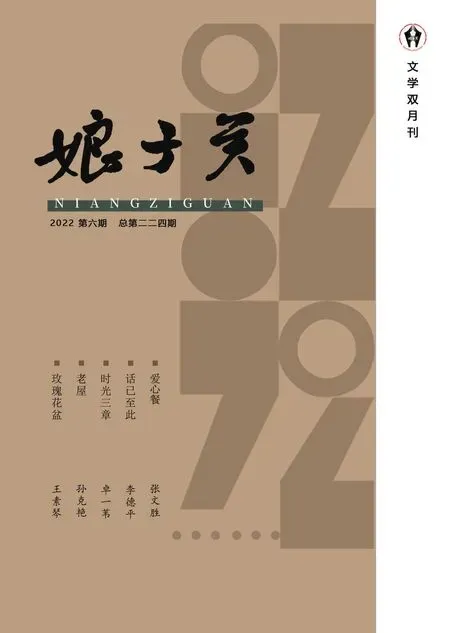窗口品云(外一篇)
◇柳林
如果大自然以天為封面,以地為封底,云便是最活躍最生動的文字,是情緒、是詩、是心象、是畫。
坐在窗下,竟思慕起山居生活的明靜清澈,懷念山中那些云絮、云靄、云帶、云海。在城市,總覺云很遙遠;在山里,卻很貼近,云與我相互凝望、對語。有時,就在面前佇立,登上山頂,又在足下繚繞,歸去,它掛在屋檐期待,未閉門窗,它會悄悄入室叩訪;有時,追著云趕路,枕著云睡覺,不知不覺,云就成了伴侶。
山居的歲月,天地打開它們的書卷,讀了山川、森林、花鳥這些實文,又讀云這種虛文。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這千古名句,不過是讀云的一點心得,云,才是超凡的美學家。畫家米芾、倪云林、八大山人,誰不是在云意中悟出美而再現與表現,誰不是云的弟子?當我們聽見古典樂曲《彩云飛》或流行曲《故鄉的云》,云又化為音符,在我們心里回旋,化為歡快和惆悵在我們心里彌漫。
讀云,既有“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意義,更有一種審美的情趣與感悟。有時,云會很自然地再現你讀過的那些詩的意境。孟郊的“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過去,被視作終南山風景,而當我走近云,又走出云,心想這詩句怎能用風景二字解釋,分明隱隱含蓄著一種人生哲理,此刻,云,好像又是哲學家了。而“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當我做了游子后,又千百次凝望過山里浮云,驚訝除云之外,再難有這樣貼切的對應物,這時,云不是理性,而是情性與物性了。
這么以詩悟云和以云悟詩,悟得的,還是古人的意境,這山中的云,豈是古人在詩中畫中樂中能包攬與包涵?不僅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候,它儀態萬千,在晨昏或陰晴,更是景象各殊,在風里、雨里、雪里,也是不同的情調。云的面容、身影、色彩、性格、情趣、流韻,真是大千世界的大千氣象,在無窮變幻中,展現造化的無窮。崛于千仞的峻峰,堪稱雄奇了,云在峰巔,也作山勢,更偉岸地升高,使高峰在它足下變成侏儒似的小丘。有時,又拉出大幅帷幕,遮住山的身體,只顯出山頂,或者懶懶地睡在山谷里,做著自己的夢。它十分敏感,又很調皮任性,有時,同風在天空賽跑,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馳過,恍惚馬鬃飛揚,草原上的馬群,在天空馳騁。也許是敗在風的手里,禁不住淚雨滂沱起來,痛快淋漓地宣泄,又永遠揮灑不盡它的感情。雨后,總飄出云帶,系在山腰,或浮出云朵,掛在樹枝,表現它的情感,既是奔放的,又是纏綿的。這種纏綿甚至與奔放匯合,如錢塘大潮無聲地鋪天蓋地涌來,淹沒了大森林,我真懷疑,這是云海與林海的一種戀愛方式。云海與林海,不都是以“海”為其共性嗎?它們有相同的氣質、品性與襟懷,怎能不心心相印?一到拂曉,曙色初萌,云就在天邊鋪開產褥,迎接新的一天降生的孩子——太陽。
更多的時候,在山的那邊,它是縷縷云煙,裊裊地升騰,使我懷疑山中有位仙人在煉丹,于是遐思不輟,聯想山中每天吐出的日月,豈不是煉出的不老仙丹,育萬物生生不息嗎?天地這本大書中的云語,真是百讀難盡,百讀不厭。
隔窗觀天
笠翁有言:“人之不能無屋,猶體之不能無衣。”即是古人房舍筑于山間澤畔,雖蓬門蓽戶,依窗而眺,往往生出隱居山林,超凡脫俗之愜意。
如今,人們大都入住仿佛密林般的水泥鋼筋造就的擁擠、高大樓群之內,樓外樓,窗對窗,上仰一線天,下視一片雜亂無章。誰也無法享受“窗中列遠岫”“列綺窗而瞰江”之情調,更領略不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鳴禽響瀑,茅屋板橋”(清·李漁《閑情偶寄卷四》)之山居窗外勝景。蝸居一隅,窗外則寂寞冷清;雜宿鬧市,又喧囂嘈雜。《釋名》曰:“窗,聰也;于內窺外,為之聰明。”站在窗前,聽到的是大呼小叫,看見的又是人如蟻陣,此時能耳聰目明嗎?恐讓人不置可否。
現代人多以居于城市為幸,且越大越好。想在山野中筑屋,非一般人所能及:一則缺少大量資金;二則不安全,擔心做無謂犧牲;三則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那生計不可或缺的諸如煤水電之類怎么辦?于是,能在城中覓得一席地理位置不錯,面積大些,樓層又滿意的棲身立命之處,也算一種福分了。誰還敢生出其他奢望?至于窗外如何,怕是由不得你挑選,也顧不得那許多,只好聽天由命了。
“窗,穿壁以木為交窗,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說文》古人的這一說法,大抵是“在墻曰牖,在屋曰窗”的意思。“窗”“牖”盡管叫法不同,但功能想必無什么大的區別。小時生活在北方農村,家中三間房屋每間都辟有南北兩窗。雖居于泥土陋室,難以同當今城中的高樓廣廈相媲美,但視野寬闊,滿眼“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之美景,讓人心醉。南窗外,有兩株高大的棗樹,一簇茂盛的果樹,隨著栽種的黃瓜、豆角、西紅柿及各種一年生草本花卉的出土、長高、含苞欲放,再到結出累累之果,窗外便成了一座“花枝草蔓眼中開”的小小花圃,花草的清香沁人肺腑,果實的豐碩使人欣慰。歸巢燕子呢喃,蜜蜂花間采蜜,小鳥枝頭鳴唱,常有“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宋·楊萬里《宿新市徐公店》)的景象發生,那兒童便是我和我的同伴了。北窗外則是一個很大的園,這不免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話:“我家的后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做百草園。”我家后面的這一園中雖無什么雅致的名稱,更無百草園里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槐樹、縈紅的桑葚和輕捷的叫天子(云雀)、纏繞著的何首烏藤和木蓮藤,更沒有赤練蛇等。但螳螂舞刀,蟋蟀彈琴,顏色各異、大小不同的螞蚱蹦來跳去,蜻蜓小憩于柵欄的枯樹枝頭等等,卻是常見的。北面有一行高大的柳樹,郁郁蔥蔥,樹下一條潺湲的小溪流向村西的一座大池塘內,是“聽取蛙聲一片”的好地方。碧綠的菜畦倒有一大塊,在園中的西面,均是供一家人飯桌上的各種蔬菜:白菜、生菜、蘿卜、茄子、辣椒、蔥蒜等,春夏秋三季不斷。東邊的一大片便是蔥郁的玉米地,長勢很旺。閑來無事我便跳過北窗,在園中轉來轉去,欣賞田園美景。在與鄰居相隔的東柵欄下,以枯木為柱,野草、玉米葉子為蓋,搭起一座足可容身的茅棚,經常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里面,炎熱天防曬,刮風時躲風,下起雨來又可避雨,可謂望晴空麗日,聽風聽雨,聽鳥蟲吟唱,想必其中亦有詩的意境。只是那時年幼,說不出什么,雖無詩句吟成卻有無限的樂趣。那感覺即是踏入城中的娛樂城、游戲廳、兒童樂園,抑或風光旖旎的名勝古跡、公園里,也無法尋覓到。
我如今棲身于人煙稠密的樓群之內,居住條件比兒時家中的泥土房不知好多少倍。屋中獨辟一室作為書房,窗前置一案,或書或畫,或讀書,自有無言的情趣。然窗外的景致絕沒有梁實秋先生寄身四川的“雅舍”時窗外的空曠,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遠望過去是幾抹蔥翠的遠山,旁邊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糞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更比不得其旅居海外的“白屋”,窗前有花有草,有藍天有碧樹,有活潑蹦跳的兒童,有手捧花傘的男男女女,足以怡人倦眼,充溢情懷。
如今,我閑時佇立窗前,盡管有煙有酒有茶,但俯仰天地之間,眼前窄狹的一條通道,僅僅一線似的不再清亮的藍天,不要說花草,就連像樣子的樹木也無幾棵,人群的匆忙,商販的叫賣,物欲的涌動以及人心的不可測……令人心煩意躁。無奈中只得關窗閉戶,把這一切阻隔在外,且回到案前,任寂寞與孤獨籠罩,揮毫欣成佳制,把卷喜得佳句,心遠而淡泊,陋室自然清靜,必沉醉于無牽無掛、閑適素心的大安詳之中。每遇此時,便想起家鄉泥土房窗外的迷人景致,還是梁實秋先生說得好:“臨褚凄愴,吾懷吾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