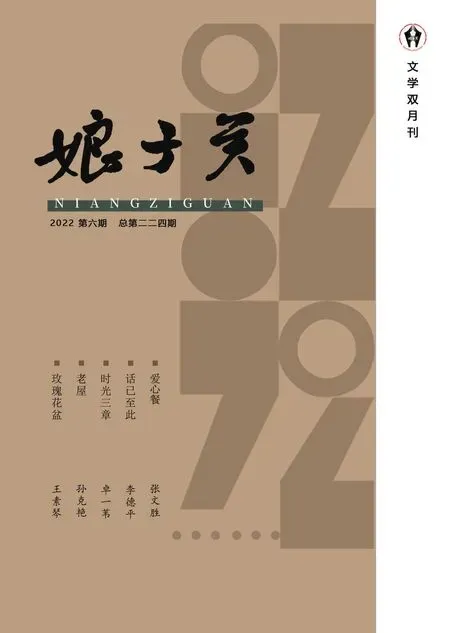荒院之魅
◇蘭青
最近幾天,小雨淅淅瀝瀝地下著,門前的石階上隱隱約約有綠色的青苔迎著雨水生長。遠處的山蒙上一層薄紗,呼吸的空氣都是濕漉漉的,有些透不過氣,本已不快的心情增添了幾絲憂愁。這天,午飯過后,趁著小雨初晴,便想著去荒廢的舊院看看。回憶過去,突然間發現自己竟然有五六年的時間沒有去過舊院了,這雨后的小院是否有另一番景象。
走在鄉間獨有的小路上,看著那陌生又熟悉的景色,心中的感慨一如這陰晴不定的天氣。未至小院,空氣中遠遠地飄來淡淡的、甜甜的味道,混雜著點點青草、泥土的氣息。幾個晃神間,已步至小院門外,石頭砌成的院墻早已看不出本來面貌,石頭縫中散落倒掛著幾棵干枯的藤蔓,新冒出的小草試圖在風中站穩腳跟。大概是很久沒有人光顧這個小院了,兩扇紅木門歪歪斜斜地倚在門框上,像個裝飾品。蛛網橫在眼前,阻擋去路,幾滴殘留的雨滴掛在細細的絲線上,對著陽光觀望,像一個個五顏六色的水晶球,微風一吹,碎落滿地銀光。拿掉門閂,“吱嘎”一聲,推開紅木門,滿眼的綠色竟給這廢棄的小院增添了幾分色彩,幾分樂趣。
我側著身子,從蛛網的旁側穿過去,緩緩地抬著腳往里面深入。幾棵洋槐挺立在墻角邊,背靠院墻而生,樹根拱出地面及至院墻外,殘缺不全的石頭墻多出幾條溝壑。粗壯的主干上半部分分出若干枝杈,細密的葉子下面一串串白色小花正吐蕊納香,遠遠看上去,那朵朵小花如一串串銀色風鈴隨風擺動,迷亂了我的眼。背靠著樹,微微抬頭,閉目凝神,仿佛能聽到花朵綻開的聲音和鈴兒叮叮作響。此刻,我不敢吟出贊美之詞,或大聲呼吸,打破這優美和諧的旋律。
年幼時,菜園里的蔬菜沒有現在的品種豐富,種來種去只有那幾樣,早已索然無味。每到槐花盛開時節,我最愛的一道美食便是用新鮮的洋槐花做成的槐花餅。每年槐花開,我都會到外婆家住上幾天,外婆家門前有幾棵高大的洋槐樹。那時,我最大的樂趣就是看著外婆拖著不夠靈敏的身體,舉著又細又長綁著鐮刀的竹竿,動作遲緩地把槐花從樹上一串串地鉤下來,我在旁邊喊著、指揮著。然后,再和外婆一起把一朵朵小花摘下來放在簸箕里備著,給我做槐花餅。
荒院里的幾棵洋槐,是外婆家的老槐樹從根部衍生出的幼苗。外婆見我喜歡洋槐花,而洋槐花開時滿村飄香,風靡一時,綠白相間,甚是好看。那年春末夏初,洋槐花含苞待放時,我剛到外婆家住下沒兩天,就逢刮風下雨,大風大雨持續一個多星期才停歇。等天氣徹底放晴,洋槐花早已敗落,樹下滿地是風雨之后殘留的枯枝敗葉和濺上泥點子的花瓣。我搬來木墩,坐在院門口,望著旁邊被雨水洗劫一空的槐樹,靜靜地發呆、冥想。
當時的我在想些什么呢,或許只有那時的天空和逝去的洋槐花知道。
村子里的人忙著耕地耙田,栽秧播種。天氣的原因耽誤了幾天的農時,外公外婆和其他村民一樣從早起忙到天黑,中午回來潦草地做一頓飯,隨便吃幾口便急著下地干活。
據說,我家和外婆家原來是一個村的,村子中間相隔著一條河,我家在村南,外婆家在村北。后來不知怎么回事,村子以河為界分為兩個村,遙遙相望,看似相鄰,相距大約有二里腳程。
我坐在門口,拿著一截樹枝在地上圈圈畫畫,時而抬頭看看遠處的天空,仿佛我與這村莊格格不入。為什么這樣說呢,是有原因的。大人們忙著農活,在村子里面游蕩一圈也見不著幾個人影,為數不多的幾個小伙伴跟隨著父母下地去了,只有我閑著,坐在院門口無所事事。外婆沒什么事需要我幫忙的,她一度認為我太小幫不了她什么忙,干脆讓我留在家里看家,自己玩耍。殊不知,這特殊的一份寵愛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與村莊的忙碌相比而不知所措。
等到這一陣子的農活忙完,洋槐樹的葉子更加綠了,也是我回到自己家的時候。這年由于雨水較多,我在外婆家多住了一段日子,母親遲遲不來接我回家,外婆也不主動送我回去,我知道,這是娘倆之間的默契。外婆忙時是起早貪黑下地,而背著“上有老下有小”的母親何嘗不是分身乏術。我從最初的不情愿,又逐漸釋然,習以為常,到最后的依依不舍。臨別時望向樹梢綠葉下面一片空蕩,為沒有吃到新鮮的洋槐花而感到悵然若失。
后來年齡長些,我也入了學校,周六日習慣蹲在家里讀書寫字,外婆家漸漸去的少了。從以前愛湊熱鬧的“假小子”變成“鄰家女”,可以安安靜靜地獨處一隅,消磨時光。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自己都忘記了洋槐花的味道,倒是外婆還惦念著我兒時的那口槐花餅,每年槐花開了摘了新鮮的槐花做好餅,以及一些還未處理的槐花一起送過來。直到后來外公因病離世,外婆因睹物思人身體每況愈下,又不忍拖累兒女,經別人介紹改嫁到別的村子,精神頭才稍好些。
外婆在臨行前,從門前的槐樹根部拔了幾棵幼小的槐樹苗給母親,讓母親栽下,許是那幾棵樹苗命不該絕,奇跡般地活了。生活總是越過越好的,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村子再也沒有回來,有的在城里買了塊地皮自己建了房,有的搬到其他交通方便的村莊居住。慢慢地沒出幾年,村子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我家是最后一個搬走的,從這一個山溝里搬到另一個山溝,選了新址,蓋起了新瓦房。同樣都是山里,只是新的村莊多了條蜿蜒曲折的土路,交通便利很多,拉了電線,通了電話。
而今,槐花依舊,離去的人早已不在。看著蕩漾在風中的洋槐,花朵恣意地開放,吐露芬芳,仿佛槐花餅的香味依然在唇齒間縈繞,有關外婆的記憶漸漸浮上心頭,那些美好快樂的時光將會陪伴我走過余生。
鄰著槐樹,倚著院墻根堆放的是幾截板栗木料。在我們那里,上了年份的板栗樹是做棺材的好木料,杉木并不常見,板栗樹是家家戶戶都有的。松木做的棺材分泌油脂易開裂,梧桐樹木容易腐朽蛀蟲,而板栗木結實耐腐,就是比較沉重。外婆家有兩棵活了很多年的板栗樹,兩棵樹挨著相依而生,雨露均沾,粗細大小需兩個人環抱。曾經有行走商人出高價收購那兩棵樹,外公都沒舍得賣掉。每次路過樹下,外公都要在樹底下轉上幾圈,左拍拍右瞧瞧,在拱起的樹根上坐上一會兒。然后,拿出一張泛黃的紙,慢慢折疊好撕成一小張一小張的長條,卷上自己種的烤煙葉,點燃吸上幾口滿足了再閉上眼瞇一會兒才離開。兩棵板栗樹一面挨著山腳,一面是兩塊地,一大一小,分地時剛好分給了外公家。有幾次我隨著外公他們一起下地時,外公都會指著那兩棵板栗樹對我說:“妮兒啊,看見那兩棵栗樹沒,那是我和你外婆以后的房子,一人一棵,給多少錢都不賣。”那時我還不太懂外公口里的“房子”是什么意思,隱隱約約覺得不是件好事,并沒有追問下去,外公說的次數多了,“房子”這事也深藏在我心里。
那幾年,我在鎮上上初中,一個星期回家一次,我從家里到外婆家一頓飯的時間就可以跑個來回。那天是周末,我去給外婆家送雞蛋,看見外公指揮著村里的人往院子里拉木頭。我看著那些木頭有些熟悉卻沒敢開口詢問,還是外婆走出來說是外公找人把兩棵板栗樹放了一棵,先拉回來放著,回頭找個好木匠做好擱那兒備著。當時我心里便有種不好的預感,我放下雞蛋,以作業沒有寫完為由匆匆離開外婆家。就在棺材做好的第二個月,外公因突發腦出血搶救不及時,沒有救過來。那一刻,我才徹底明白外公所說的“房子”是怎么回事,直到今天,我依舊把外公曾經對我說的那些話,深深地埋在心里,沒有對任何人講過。
外婆因為改嫁,那邊又有兒女,棺材不好提前備著。外婆走的時候是夏天,一次重病就撒手人寰,誰也沒想到她會走得那么著急,“房子”也沒提前準備。外婆改嫁后唯一的念想是陪伴她走過幾十年風雨的板栗樹,外婆離開后,剩下的一棵板栗樹也被放倒了,卻沒來得及做成棺材,只能從鎮上買了一口上好的杉木棺匆匆下葬。外婆的遺愿沒有完成,而那棵板栗樹的生命卻和外婆一起終結,外婆也算此生無憾了。放倒的栗樹最終沒被賣掉,被鋸成一段一段的堆放在這個荒廢的小院里,伴著院中的草木、老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默默守護著逝去的光陰歲月。
木頭散亂地躺在地上,外面的一層樹皮早已不見蹤影,縫隙里夾生著一些不知名的小草,又細又長,不似其他地方的草壯實青翠。挨著墻壁的那一根木頭上,生滿了綠色的青苔,縫隙下面的土壤表層棲息著黑殼蟲、蚰蜒、潮蟲等看著嚇人的小蟲子。當然,在土窩里長大的我是不懼這些蟲子的,我嘗試著翻開木頭,看著暴露在陽光下的小蟲子爭先恐后地逃跑、隱藏身影,這也是年幼時經常做的一件事。
村里的孩子不似城里的孩子精心養著,在我們那老一輩人常掛在嘴邊的“放養”,一般情況下父母是不會管孩子們的游戲方式,只要安全就行。那兩年,村里的人越來越少,我的玩伴也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獨處。有段時間,我瘋狂地迷戀上了各種小蟲子,家里有個生銹的炒菜用的鐵鏟子,它成了我最順手的工具。房前屋后,雜草叢生的老屋遺址、稻場邊緣、池塘河岸邊,只要是潮濕、土壤疏松、或雜草雜物覆蓋的地方,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小驚喜。蜈蚣是我不喜歡的最常見的一種節肢動物,甚至連我家的小白、小花都不喜歡它。小白、小花是母親養的老母雞,母親喜歡養些家禽,雞鴨鵝每年都是必養的,屬雞的數量最多。幼小的雞崽兒得以快速成長,除了母親的精心飼養,我也功不可沒。每次拿著鐵鏟出門,我的身后總是跟著一群雞大軍,有我起了名字的,還有一些沒來得及起名字的,黃的、白的、花的、麻的,爭先恐后地想要擠入最前列,緊緊地跟在我的腳后邊。我努力地用鏟子扒拉開表層的土,小白小花尖尖的嘴在翻開的土里來回翻找著,很多次比我更先發現隱蔽起來的小蟲子。我們翻過這一片,接著再翻另一片,沒多會兒身后一片狼藉。
翻木頭的過程,是一個費體力的活兒,對于長時間不干重活的我來說,有些力不從心。滿懷驚喜,也存在一絲驚嚇,荒廢了多年的舊院,肯定有未知的生物存在,只是我沒有發現罷了。我就像一個闖入者,偷偷摸摸地尋找著一切可疑的東西。沒有稱手的工具,就地隨手撿了一截小樹枝扒開腐爛的落葉和堆積的雜物,除了那些以前見過的小蟲子,還在墻根上發現了一只蟬殼,看樣子應該是去年留下的,還沒有被風化,這算是一個小小的收獲了。
蟬的幼蟲,富含高蛋白,營養很豐富。在盛夏來臨之際,尤其是下雨之后的晴天里,楊樹林里、池塘埂上的土壤里,藏著很多的蟬寶寶。它們在等待同伴的召喚,一個個鉆出地面爬上樹梢放聲高歌,燃燒生命。曾經聽村里老一輩的人說過,蟬卵到幼蟲的生長期在地底下可以潛伏很多年,直到將要蛻變時鉆出地面,脫去一層外殼,長出翅膀才會以成熟期蟬的形態生活在炎熱的夏天。蛻變之后的蟬生命周期非常短暫,只有一個夏天。在蟬的世界里,夏天就是它們的高光時刻,放開自我,用生命彈奏贊歌。我曾親眼看見一只蟬的幼蟲從土里鉆出來爬到最近的樹干上,一點點脫去透明的殼,說是透明卻是接近土的顏色,直到軟軟乎乎的肉身全部出來,慢慢地長出一對翅膀,身體變色、硬化后就是我們經常在樹上看到的樣子。蟬,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完美蛻變,想想,簡直是不可思議。
挖蟬蛹,也是需要技巧的。首先要選對地方,蟬蛹喜歡生活在土壤透氣性好的沙質土,表面會有一個個細小的圓孔,那是蟬蛹挖出的通道,有圓孔的地方地底下肯定會有很多蟬蛹。這時,鐵鏟就不管用了,需要用鐵鍬,一鏟子下去能挖出很深、鏟出來一片土,再用樹枝把翻上來的土扒拉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蟬蛹一般藏在土里二十多厘米深的地方,挖起來有些費力。獲取蟬蛹最好的方法是在夏天的晚上,白天用透明膠帶在村前屋后、楊樹林的樹干上纏上一圈,高度在伸手可以夠著的位置就行。等到吃過晚飯,乘涼片刻,大概八九點、十點鐘的樣子,一手提著裝著水的塑料桶,一手拿著手電筒一棵樹一棵樹地照,在纏上膠帶的下方總是有大大小小的蟬蛹正在蛻變。捉到的蟬蛹要立刻放入水桶里淹死,不然等到蛻變完成長出翅膀的蟬就不能吃了,也沒有人收購。
村子里的夏夜是熱鬧的,也是我比較忙碌的時候。白天里天氣炎熱,除了下地干活大多數人都縮在家里不出門,只有我們這些不怕熱的皮猴子跑到小河里玩水摸魚。夜里吃過晚飯,微微的夏風吹來,熏上一把艾草或板栗花穗編織的繩子驅蚊,三三兩兩地坐在院門口,或村頭的楊樹下,嘮家長里短。而我,在村子里穿來穿去,拿著手電筒一棵樹一棵樹地搜尋著遺落的蟬蛹。蟬蛹在過去,直到今天都是一道營養豐富的美食,一個夏天下來靠賣蟬蛹,也足夠滿足我這個好吃的“小饞貓”了。
那時的我們,簡單、快樂,真誠而努力地活著。
鄉村生活的簡樸、純真的笑臉,至善至美,是繁華都市里難以追尋的記憶,是回不去的白月光。行至今年,那情那景,又有幾人識得呢?
有時候,懷念過去,是獨處的一種消遣方式,抑或是真的內心孤獨,需要慰藉罷了。
木頭的邊上是小石塊圍著的花圃,想當初還是我提出來的。母親本意想在院里多種幾棵果樹,經不住我的鬧騰,在院子的一角用石頭簡單地圈了一個小花園。美人蕉是我親手種下的,當初搬家的時候沒有把它移走,任它自生自滅,沒想到今天仍然冒出一棵一棵嫩芽。它的生命力超乎了我的意料,與這滿院的草木爭奪養分,依然存活至今,繁衍生息。想當初移栽時只有小小的兩棵,而今已然一大片了。花園的四周是到處可見的艾草、車前、茼麻、蒼耳、狗尾巴草、苦菜、灰灰菜……還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
院子的左邊有一口人工挖的水井,井口用一塊大石板給蓋住了,以防有生物不小心掉落井里。井邊的地面比其他地方更加潮濕,幾塊石板圍著井口鋪了一圈,石板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紋路,密密麻麻長滿了青苔。站在水井邊上,伸手可夠著從院墻外伸進來的楝樹枝,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帶點白,懸掛在墻頭上,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楝樹是村里常見的樹木,路邊、山腳邊到處都是,枝杈不多,樹的形狀像傘一樣向四周張開,遠遠望過去如一頂綠色的帳篷。楝樹的果子成熟后黃黃的,曾經一度被我們當作“子彈”,用自制的彈弓打偷吃糧食的小鳥。地上跑的雞,池塘里游的鴨,樹上停歇的鳥兒都成了我們游戲的目標。子彈用完了,拿一根竹竿往楝樹上胡亂敲打一番,黃色的楝果就呼啦啦地落滿一地,只需要裝滿滿一口袋,足夠我們戲耍半天了。
水井旁邊是一棵很老的櫻桃樹,樹苗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從集市上買來的。母親當時買了兩棵,只成活了一棵,那唯一的一棵櫻桃樹在以后的多年里,成了我零食的來源之一。每年春天櫻桃花開時,我就滿懷期待地站在樹底下,仰著頭祈禱著不要刮風下雨,一旦在花期遭到風雨的洗禮,意味著今年的櫻桃沒有往年結的果子多了。等到櫻桃從青果逐漸發黃變紅的那段日子,白日里我就搬個小凳子坐在櫻桃樹下,手里拿著一根竹竿,竹竿的一頭系上彩色的塑料袋,不停地驅趕偷吃果子的麻雀。櫻桃成熟后,是我最忙的時候,一邊忙著和麻雀搶奪枝頭上最紅的果子;一邊要應付前來討嘴吃的小伙伴;還要防著以找母親有事為由的大人們順手順走一把小櫻桃。那段時間的我成了村里小伙伴們羨慕的對象,種植的家櫻桃在我們那邊很稀少,山上也有野櫻桃樹,結出的果子都不如我家院子里的櫻桃又大又甜。母親把櫻桃樹看護得很好,一年比一年長勢喜人,結出的果子也越來越多。
小院荒廢之后,櫻桃樹也不再有人來打理照顧,樹根周圍雜草沒過膝蓋,院墻外的樹越長越高,遮住了所需的陽光,逐漸衰老,干枯而死。而今,老去的櫻桃樹還殘留著半截木樁子立在那,占領著屬于它的位置,從老樹根部生長出來的幾棵半人高的小幼苗仍在努力向上生長,頑強地抵抗著風雨,汲取地底不多的養分。櫻桃樹在等著我,等我為它恢復昔日的風姿,卻等到樹葉凋零,化為養料被其他的植物抽走養分。這么多年來,我竟然忘記了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忘了自己親手撫摸過的每一寸土地。
櫻桃樹的旁邊是一個坍塌的雞舍,雞舍也是石頭蓋的簡易的兩層小房子。最下面一層是鋪的石板用黃泥土抹平的地面;中間一層是木棍搭建的隔層;頂棚是松木,松木上鋪了幾層白色的塑料雨布,再繕上厚厚的茅草。村里的雞舍大多是這樣的構造,下雨地面過水,雞可以棲在上面一層。我家的雞,有時候更喜歡棲在櫻桃樹枝上,有風襲來,隨著枝頭擺動,別有一番趣味。
這些年,它們在這個小小的院里,以獨有的姿態生存著,而我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虛度光陰。它們都在等著我來,等著和我再次相遇,等著等著,風又吹落了樹梢上最后一片樹葉。等到風吹化了院墻上的巖石,樹上棲息的鳥兒離開了又來,來了又再次離去,我還站在回憶的路上,徘徊著,遲遲不來。
搬家的時候,我正在鎮上上學,母親只搬走了常用的家具和糧食,一些古老的家具和老物件統統塵封在老屋里。剛搬走的那幾年,每逢假期我還會來老屋轉上幾圈,看看有沒有可以帶走的東西,結果來了數次都空手而歸。最初的時候,村子里還有人往來走動,整理一下房前屋后長出的雜草,再后來,慢慢地就很少有人踏足這里了,包括母親,也是在下地的時候才會去老屋轉上一圈。這幾年,年輕的人們都在外地打工,老一輩的人沒有更多的精力種地,很多的田地都荒廢了,也有的人家覺著荒廢了可惜,栽上楊樹苗后任其自由生長。母親就近打理著二畝地,種些蔬菜糧食,不忙的時候去給別人做工,維持著日常開銷。
老屋離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并不是很遠,大概有五六里路的樣子,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冷冷清清,四周山林茂盛,雜草叢生,昔日的小路也被一些草本植物覆蓋。除了幾間衰敗的老屋佇立在那,隱沒在一片青翠之間,誰還會想到那里曾經也是人聲鼎沸,人和牲畜和諧相處,一片祥和呢。
突然間想到這里來看看,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早有打算的,只是被一場雨耽擱了些時日。所幸來得并不算遲,一切正好,滿院子草木競相生長,欣欣向榮。有各種昆蟲棲息在草林里;土壤里還有許多爬行動物;野蜂嗡嗡地在花朵間飛來飛去;一只早蝶在我面前扇著翅膀,而后飛過院墻,隨著路過的風遠去了。荒院,并不荒涼衰敗,井井有條,所有有生命的,以最原始的姿態生長在這片土地上。
除去老屋里的小門上著鎖,我沒法進去,屋檐下、窗臺上蛛網遍地,大大小小的蜘蛛代替我守護著這幾間老屋。母親并不知道我來這里,她只是單純地以為我在家里悶了幾天想出去走走。我喜歡獨處,這是小時候養成的習慣,至今仍然喜歡一個人待在無人的角落里靜靜地發呆、熬煮時光。在我獨處的時候,母親無事絕不會去打擾我,只有在做好飯的時候才會大聲喊我的名字。因此,在母親眼里我是個比較省心的孩子,即使一個人的情況下也不會離開村子太遠,只在周邊活動。如果當年,我們沒有搬離這個小院,時至今日是不是有另一番景象呢。
這些未知的事,我曾經在心里幻想過無數次,也假設過好幾種結果。我想,所有的假設最終的結果都躲不過“歲月不饒人”這句話。我把母親現在的背影和多年前的背影放在同一個角度去看,卻再也找不回流逝的青春年華。我也從一個懵懵懂懂無知少年,成為別人的母親,繼續延續著母親的使命。
站在這個荒院里,此刻,我可以想象著自己還是個孩子,可以任性地做著不屬于我這個年齡的游戲。忘記工作、忘記社交、忘記一切讓自己心煩的東西,再回到懵懂時代,眼里只有花草樹木、鳥兒昆蟲。不為他人憂,不為身后事而愁,一切盡在無言中,沉默,是對過去最好的緬懷方式。
我在小院的角落里,找到一把銹跡斑斑的鐵鍬,挖了一把苦菜,又掐了一把鮮嫩的灰灰菜,準備帶回去涼拌,正好解決了晚餐為吃什么菜而愁的困惑。野菜,是春天里的餐桌上最常見的一道菜,如薺菜、蒲公英、榆錢、蕨菜……還有一些一時記不起名字的草、樹上新生的嫩芽。在我爺爺那一輩年輕時,分的糧食不夠吃了,就挖野菜果腹。那些生長在路邊、田地里、山野里,看似不起眼的小草,在過去說不定就是救命的糧食,養活了很多人。
游走在小院里,輕輕地撫摸著每一株草、每一朵花、每一棵樹,我都想象著它頑強生長、抵抗風雨、不屈不服的樣子,多像現在的我呀,和生活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人們。我慢慢地走著,把向前抬起的腳步放到最慢,慢到不帶起一縷風,地面還是濕的,沒有揚起的塵土,只有鞋底淺淺的一層濕泥。我的后背拋給吹向山野,恰巧路過小院的風,捎去我曾到過這里的訊息。我的背后是一排樹,院墻之外還有無數棵樹,一一等待著我去認領。
生長在這片土地的人啊,如果有一天你路過這里,看見一個滿懷滄桑的人徘徊在老屋的門前,走在村里的每一個角落,請你不要驚訝,那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祭奠逝去的青春歲月。
簡單的,迎著風綻放
我視它們為自然里最純粹的生命
流走的歲月里
夭折的只是未干的淚痕
在腐朽的肉體上
打磨光潔的內心和堅硬的皮膚
風雨過后,飄落的葉
一半接住思念,一半接住風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