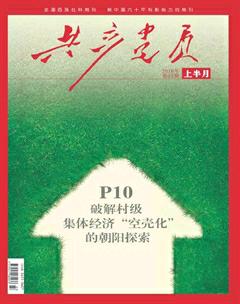習近平: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創新體制機制強化黨內監督
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于新的形勢任務,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正風肅紀,反腐懲惡,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中央紀委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遵循黨章規定,聚焦中心任務,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的重大成效。我們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夯實管黨治黨責任,創新體制機制、扎牢制度籠子,持之以恒糾正“四風”、黨風民風向善向上,強化黨內監督、發揮巡視利劍作用,嚴懲腐敗分子、加強追逃追贓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反腐敗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眾給予高度評價。
習近平強調,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關鍵在黨。“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立下的軍令狀。3年來,我們著力解決管黨治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的問題,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全黨同志對黨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上的決心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取得的成績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夠自信。
習近平指出,做好今年工作,重點要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尊崇黨章,嚴格執行準則和條例。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尊崇黨章。各級黨委和紀委要首先加強對維護黨章、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的監督檢查,確保黨的集中統一,保證黨中央政令暢通。二是堅持堅持再堅持,把作風建設抓到底。要用鐵的紀律整治各種面上的頂風違紀行為,有多少就處理多少。抓作風建設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在加強黨性修養的同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干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三是實現不敢腐,堅決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勢頭。懲治腐敗這一手必須緊抓不放、利劍高懸,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要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四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對基層貪腐以及執法不公等問題,要認真糾正和嚴肅查處,維護群眾切身利益,讓群眾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果。五是標本兼治,凈化政治生態。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從自身做起,廉潔用權,做遵紀守法的模范,同時要堅持原則、敢抓敢管,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促進政治生態不斷改善。
習近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各級黨組織要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要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開展紀律教育,狠抓執紀監督,養成紀律自覺,用紀律管住全體黨員。要增強領導干部政治警覺性和政治鑒別力,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站穩立場、把準方向,始終忠誠于黨,始終牢記政治責任。要堅持高標準和守底線相結合,既要注重規范懲戒、嚴明紀律底線,更要引導人向善向上,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變思想道德防線。
習近平指出,強化黨內監督,必須堅持、完善、落實民主集中制,確保黨內監督落到實處、見到實效。要完善監督制度,做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既加強黨的自我監督,又加強對國家機器的監督。要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要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要強化巡視監督,推動巡視向縱深發展。對巡視發現的問題和線索,要分類處置、注重統籌,在件件有著落上集中發力。要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讓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每個黨員、干部的必修課。要抓住“關鍵少數”,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領導干部責任越重大、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強監督。
習近平強調,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是管黨治黨的重要力量。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旗幟鮮明支持紀委開展工作。各級紀委要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帶頭尊崇黨章,把維護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作為首要任務,加強對遵守黨章、執行黨紀情況的監督檢查,嚴肅查處違反黨章黨規黨紀的行為,堅決維護黨章權威,做黨章的堅定執行者和忠實捍衛者。各級紀委要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紀律要求紀檢監察干部,保持隊伍純潔,努力建設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紀檢監察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