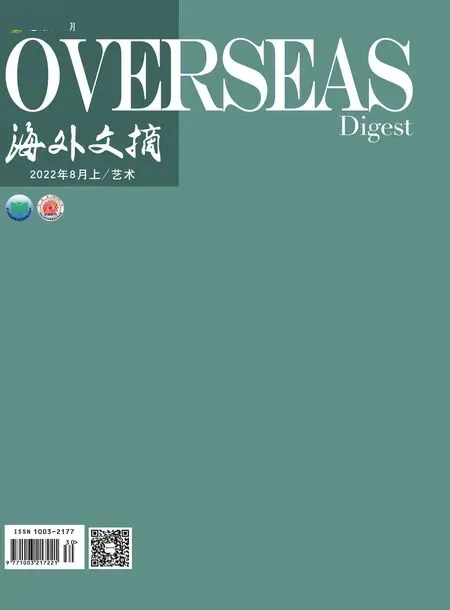老齡化社會(huì)生存圖景與多維關(guān)照
——論山田洋次電影《家族之苦》第二部
□俞閱/文
山田洋次電影《家族之苦》第二部,呈現(xiàn)日本超老齡化社會(huì)環(huán)境中老年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理狀態(tài),表達(dá)對(duì)完善老齡化社會(huì)相關(guān)體制的深入反思。本文根據(jù)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生存需求、愛(ài)和歸屬感需求、自尊自信需求、自我實(shí)現(xiàn)需求這四個(gè)層面,剖析此電影中老年群體的生命需求和現(xiàn)實(shí)困境,以及導(dǎo)演以愛(ài)為核心的解決方案和社會(huì)對(duì)策。
日本在發(fā)達(dá)國(guó)家中率先進(jìn)入超老齡化社會(huì),其快速老齡化趨勢(shì)在短期內(nèi)難以緩解。家庭形態(tài)轉(zhuǎn)變、人口高齡化、少子化、人口高度流動(dòng)和城市化所導(dǎo)致的與父母異地分居等社會(huì)變局,使老年群體貧困、孤獨(dú)死、低自尊、存在感衰退等老齡化社會(huì)問(wèn)題日漸顯現(xiàn)[1]。對(duì)老年生存狀態(tài)進(jìn)行探討,對(duì)老年精神困境進(jìn)行觀照,是當(dāng)代日本電影的重要主題。著名導(dǎo)演山田洋次執(zhí)導(dǎo)的系列電影《家族之苦》第二部,是呈現(xiàn)該主題的優(yōu)秀電影之一,榮獲2018年第41屆日本電影學(xué)院獎(jiǎng)最佳編劇提名。此片以爺爺因堅(jiān)持開(kāi)車而與家人產(chǎn)生的沖突為主線,以爺爺少時(shí)同學(xué)丸田的臨終遭際為副線,串聯(lián)起一個(gè)多元而生動(dòng)的老年世界,呈現(xiàn)老年群體的多層面生命需求與人生狀態(tài)。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家馬斯洛認(rèn)為,人類的本質(zhì)需求可以概括為從初級(jí)需求向高級(jí)需求逐漸過(guò)渡的需求體系,該體系自下而上包含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愛(ài)和歸屬感需求、自尊自信需求、自我實(shí)現(xiàn)需求這五個(gè)級(jí)別需求[2]。本電影雖未涉及安全需求,但以影像化方式深刻展現(xiàn)出老年群體除安全需求之外的四個(gè)級(jí)別需求,本文將依據(jù)這四個(gè)級(jí)別需求,剖析電影所呈現(xiàn)的老年群體生存狀態(tài)。
1 生存需求及現(xiàn)實(shí)困境
根據(jù)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生存需求是人類需求體系中的第一級(jí)別需求,如果無(wú)法被滿足,則難以上升到需求體系中的更高級(jí)別需求,生活質(zhì)量和生命狀態(tài)也難以上升到更高層面。“根據(jù)日本《高齡社會(huì)白書》的統(tǒng)計(jì)結(jié)果,2011年日本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為了‘收入’而工作的比例由5年前的9.9%增加到20.7%。[3]”許多日本老人因生存需求無(wú)法實(shí)現(xiàn)而被迫從事繁重工作,本電影對(duì)日本部分老齡群體生存需求的現(xiàn)實(shí)困境加以深刻展現(xiàn)。爺爺?shù)母咧型瑢W(xué)丸田為維系生存,于73歲高齡仍在建筑工地打工,付出巨大辛勞才能勉強(qiáng)滿足生存需求。丸田是日本泡沫經(jīng)濟(jì)的直接受害者。青年時(shí)代在房地產(chǎn)泡沫的誘導(dǎo)下將全部家產(chǎn)用于投資房地產(chǎn)項(xiàng)目,房地產(chǎn)泡沫全面破滅后,其資產(chǎn)瞬間付之東流,晚年依賴建筑工地的艱辛工作維持生計(jì)。導(dǎo)演以丸田在工地疏導(dǎo)交通時(shí)麻木疲倦的表情以及工地簡(jiǎn)陋粗糙的午餐環(huán)境,暗示生存壓力對(duì)他造成的精神重負(fù)和靈魂匱乏,他的生命已從當(dāng)年追尋自我實(shí)現(xiàn)時(shí)的豐富生動(dòng)狀態(tài)退化成只為衣食而活的貧乏枯槁?tīng)顟B(tài)。爺爺在丸田猝死后感嘆:“他也有好好交稅,也有好好工作,都是個(gè)七十幾歲的老人了,在烈日下?lián)]灑汗水,揮動(dòng)著紅棒子,這個(gè)國(guó)家,是要讓人工作到死嗎!”丸田形象代表日本底層社會(huì)因遭遇時(shí)代傷害和社會(huì)不公而在遲暮之年仍為生存需求而苦苦掙扎的老年群體,是對(duì)社會(huì)良知與公正的拷問(wèn),促發(fā)大眾對(duì)老年群體基本生存需求及其現(xiàn)實(shí)困境的重視,以及對(duì)建構(gòu)合理化養(yǎng)老體系和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思考。
2 對(duì)愛(ài)與歸屬感的需求及現(xiàn)實(shí)困境
馬斯洛認(rèn)為,對(duì)愛(ài)與歸屬感的需求是人類需求體系中的第三級(jí)別需求,若無(wú)法得到滿足,會(huì)導(dǎo)致孤獨(dú)感和孤立感。“日本學(xué)者青木邦男認(rèn)為,孤獨(dú)感是社會(huì)互動(dòng)作用不全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主觀感覺(jué),就老年人而言主要是由獨(dú)居生活、被社會(huì)孤立以及各種‘喪失體驗(yàn)’而引起的。[3]”隨著身體機(jī)能的衰老,老年群體與社會(huì)和家庭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日趨減弱,日益從社會(huì)和家庭中的主體地位向邊緣地位過(guò)渡,從而引發(fā)其家庭角色和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其家庭歸屬感和社會(huì)歸屬感逐漸弱化所導(dǎo)致的精神孤獨(dú)困境是老年群體心靈危機(jī)的重要原因。
本電影中的爺爺面臨歸屬感衰退的困境。爺爺因堅(jiān)持保留駕照并繼續(xù)開(kāi)車而與子女產(chǎn)生沖突,此代際沖突是本電影的核心沖突,而沖突的本質(zhì)恰恰是有關(guān)愛(ài)和歸屬感的延續(xù)或中斷。年老后繼續(xù)保留駕照并自己開(kāi)車,是爺爺維系殘存的社會(huì)歸屬感的重要方式。隨著與社會(huì)體系的疏離,爺爺與社會(huì)生活的關(guān)聯(lián)日漸衰減,而自己開(kāi)車卻能保障他最后的社交權(quán)利。他可以開(kāi)車去高爾夫球場(chǎng)或釣魚(yú)場(chǎng)和老友相聚,可以開(kāi)車去心儀的居酒屋,可以開(kāi)車帶著好友佳代去吃天婦羅。如果上繳駕照,這些社交生活及其所承載的社會(huì)歸屬感都將無(wú)法延續(xù),但爺爺頻發(fā)的駕車碰擦事故卻使家人多次組織家庭會(huì)議來(lái)勸說(shuō)他放棄開(kāi)車。家人的本意是出于對(duì)爺爺?shù)年P(guān)愛(ài),但因缺乏有效溝通以及深重的代際隔閡,導(dǎo)致家人并不重視也無(wú)法理解爺爺開(kāi)車行為背后的深層心理需求,爺爺也無(wú)法理解家人的勸阻是為他付出愛(ài)的特定方式,甚至誤認(rèn)為家庭會(huì)議的召開(kāi)意味著家人對(duì)他處心積慮的算計(jì)和缺乏親情的冷漠壓制,從而愈加喪失家庭歸屬感而倍感孤立無(wú)依,其社會(huì)歸屬感和家庭歸屬感雙重缺失所引發(fā)的深度孤獨(dú)無(wú)人理解。在家庭會(huì)議上爺爺對(duì)小兒子說(shuō)“你不讓我開(kāi)車就相當(dāng)于讓我一直待在家,讓我死一樣”,表露出這種深度孤獨(dú)對(duì)老年群體的精神折磨和損害,他們?nèi)諠u被命運(yùn)剝奪了曾經(jīng)擁有的精彩而充盈的人生,灰暗冷寂的晚年生命狀態(tài)無(wú)法得到社會(huì)和家庭的理解與扶助,這呈現(xiàn)出導(dǎo)演對(duì)老齡化社會(huì)的人本主義反思。
爺爺?shù)耐瑢W(xué)丸田不僅生存需求面臨困境,其對(duì)愛(ài)和歸屬感的需求更是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因泡沫經(jīng)濟(jì)而破產(chǎn)后妻子帶著女兒離開(kāi)了他,數(shù)十年獨(dú)居生活以及在社會(huì)底層受盡白眼的打工經(jīng)歷,使他的家庭歸屬感和社會(huì)歸屬感早已殘缺凋零。73歲的他下班后總是煢煢孑立地坐在老舊公寓的小桌前,桌上放著舊日的全家福以及女兒幼時(shí)的毛絨兔玩偶,從工地上摘來(lái)的一束盛開(kāi)的彼岸花與公寓房間昏暗敗落的氛圍格格不入,這一系列鏡頭語(yǔ)言,暗示他在無(wú)愛(ài)人生的困境里依舊懷著對(duì)愛(ài)和家庭溫暖的記憶與渴望。丸田在外猝死后那束彼岸花獨(dú)自枯萎,導(dǎo)演以萎謝的花朵這一鏡頭意象隱喻丸田對(duì)愛(ài)和家庭溫暖的眷戀與憧憬隨著他肉體的死亡而無(wú)聲無(wú)息地獨(dú)自熄滅,無(wú)人關(guān)注也無(wú)人憐惜,呈現(xiàn)日本“孤獨(dú)死”老人群體的終極生命狀態(tài)。丸田去世后只能由一名政府殯葬員為其送葬,導(dǎo)演以辦案警員的話“這種悲傷的事,常有的”,暗示在無(wú)愛(ài)漠視中離世是日本“無(wú)緣社會(huì)”獨(dú)居老人的潛在生命結(jié)局。
3 對(duì)自尊自信的需求、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求及現(xiàn)實(shí)困境
馬斯洛認(rèn)為,對(duì)自尊自信的需求以及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求,是人類需求體系中的第四級(jí)別和第五級(jí)別需求,是較高級(jí)別的生命需求。爺爺對(duì)開(kāi)車的堅(jiān)持,不僅呈現(xiàn)他對(duì)愛(ài)和歸屬感的需求,也呈現(xiàn)他對(duì)自尊自信和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需求。爺爺說(shuō)“我考駕照時(shí)的車,一握方向盤一動(dòng)手,人會(huì)有種和車胎一起前進(jìn)的一體感,可謂人車合一,現(xiàn)在的車都是電腦操縱,一點(diǎn)意思都沒(méi)有。”這表面上是對(duì)往昔車型的懷舊和對(duì)自己昔日車技的夸耀,本質(zhì)上是對(duì)自己曾有擁有的自尊自信的懷念。當(dāng)他決定將要購(gòu)買新越野車時(shí),衰老臉龐上洋溢著夢(mèng)回青春般的熱情和憧憬,如同孩子般期待著閃耀的明天。這組鏡頭語(yǔ)言暗示爺爺對(duì)延續(xù)自尊自信、延續(xù)人生希望和生命活力的渴求,同時(shí)也表露他對(duì)自我實(shí)現(xiàn)的渴求:他期望繼續(xù)施展自己的才智和潛能,保有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他在竭力堅(jiān)守那個(gè)真正的自己,他不能失去自我實(shí)現(xiàn)所能賦予他的存在感。然而年老的歲月逐漸剝奪了他繼續(xù)擁有這一切的可能性,他的車尾被迫貼上了高齡者標(biāo)志,奶奶去機(jī)場(chǎng)時(shí)他被家人剝奪了開(kāi)車送奶奶的權(quán)利,大兒子在丸田葬禮后嚴(yán)厲喝令他上繳駕照,他對(duì)這些遭遇的憤懣顯露著自我價(jià)值的失落,命運(yùn)的異化使他被迫轉(zhuǎn)變,他不愿妥協(xié)地注視這陌生的自己,無(wú)力對(duì)抗也無(wú)法與之和解。導(dǎo)演以此呈現(xiàn)老年群體試圖延續(xù)自尊自信和自我實(shí)現(xiàn)時(shí)的精神掙扎與尷尬境遇,希望喚起社會(huì)對(duì)老年群體較高級(jí)別生命需求的理解和保障。
4 針對(duì)老年群體多層面生命困境的對(duì)策
針對(duì)老年群體上述四種需求所面臨的困境,導(dǎo)演的根本對(duì)策是愛(ài)的付出,呼喚社會(huì)與家庭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chǔ)上為老年群體多層面生命需求的滿足提供更多愛(ài)的支撐,從而保證老齡化社會(huì)的和諧與公正,減少社會(huì)孤立與歧視。對(duì)于老人丸田愛(ài)和歸屬感的需求無(wú)法得到滿足的困境,導(dǎo)演安排他在孤寂生命的盡頭得到了一次愛(ài)的治愈和歸屬感的補(bǔ)償。相隔三十年的高中同學(xué)們?yōu)橥杼锝M織了溫暖聚會(huì),聚會(huì)后爺爺又為他安排了傾吐半生苦痛的酣暢酒會(huì),席間特意為他準(zhǔn)備炒白果作為下酒菜。白果意象具有隱喻性,隱喻丸田對(duì)親情和家園的回想,臨終前得以暢享白果,隱喻著世界對(duì)這位缺愛(ài)老人的愛(ài)的撫慰,使他缺失歸屬感的生命再次構(gòu)建起與家庭和社會(huì)的溫情聯(lián)系。丸田的深夜自語(yǔ)結(jié)束后,導(dǎo)演以酒杯里冰塊消融的輕響,暗示丸田的精神困境在愛(ài)的慰藉下實(shí)現(xiàn)了部分消融。丸田火化時(shí)身體上灑滿白果,隱喻導(dǎo)演期望以愛(ài)治愈老人靈魂創(chuàng)傷的誠(chéng)摯愿望。爺爺?shù)募胰藗冏罱K都克服困難來(lái)參加丸田的葬禮,為這位孤獨(dú)的陌生老人付出最后陪伴,導(dǎo)演以此表達(dá)來(lái)自社會(huì)的暖意最終為他送行。家人們的集體到來(lái),也使?fàn)敔旙w驗(yàn)到真摯親情與關(guān)愛(ài),融化了爺爺與家人的尖銳獨(dú)立,從而破解爺爺家庭歸屬感缺失而導(dǎo)致的心靈困境。導(dǎo)演表達(dá)出應(yīng)對(duì)老年群體愛(ài)和歸屬感缺失的根本對(duì)策,是家庭和社會(huì)愛(ài)的付出。
小兒子和小兒媳是承載導(dǎo)演對(duì)于完善老齡化社會(huì)的相關(guān)理想的重要人物形象。他倆主動(dòng)提出為獨(dú)居老人丸田送葬,滿懷同情地去丸田的舊居祭奠,小兒子還主動(dòng)提出更換一間大房子,將孤獨(dú)無(wú)依的丈母娘和患有老年癡呆的婆婆接來(lái)共同居住,并希望丈母娘未來(lái)可以幫自己照看孩子,從而實(shí)現(xiàn)愛(ài)的代際互援。在子女普遍與父母分居的當(dāng)代日本,這種回歸傳統(tǒng)家庭的舉動(dòng)無(wú)異于特立獨(dú)行,卻承載了導(dǎo)演以愛(ài)拯救老年群體多層面困境的構(gòu)想。社會(huì)化養(yǎng)老體系在深度老齡化社會(huì)的重壓之下顯現(xiàn)出資源不足和疲乏無(wú)力,導(dǎo)演試圖以傳統(tǒng)家庭模式的優(yōu)勢(shì)之處予以補(bǔ)充和完善,以傳統(tǒng)的三代同住的居家養(yǎng)老模式緩解社會(huì)化養(yǎng)老體系的壓力和缺陷。同時(shí)導(dǎo)演清晰表達(dá)出向傳統(tǒng)家庭的回歸必須以愛(ài)的付出為前提,否則只會(huì)是空洞的回歸,并不能解除老年群體的多層面困境,而小兒子和小兒媳恰恰是導(dǎo)演為倡導(dǎo)這份大愛(ài)而構(gòu)建的理想化人物形象。
奶奶是本電影中僅有的獲得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老人形象,代表導(dǎo)演對(duì)老年群體生命狀態(tài)的理想化構(gòu)想。她所加入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班組織,使她的潛能和愛(ài)好在晚年得以盡情舒展,靈魂充盈精神豐富,在暮年時(shí)刻依然憧憬著全新希望和未來(lái)。奶奶能擺脫老年群體普遍的生命困境而擁有健康飽滿的生命狀態(tài),除了她的生活理念與主觀能動(dòng)之外,更得益于家人和社會(huì)為她的愛(ài)的付出,親情的寬容、理解與協(xié)助為她創(chuàng)造了發(fā)現(xiàn)自我、追尋自我的自由空間。同時(shí)文化中心所提供的包含老年創(chuàng)作班在內(nèi)的老年服務(wù)項(xiàng)目,也體現(xiàn)了社會(huì)對(duì)老年群體較高級(jí)別生命需求的尊重和關(guān)愛(ài)。奶奶與同學(xué)交談時(shí)提及瑞典電影《野草莓》,此情節(jié)是導(dǎo)演對(duì)于愛(ài)的重要性的獨(dú)特暗示,《野草莓》中家庭悲劇的核心原因在于愛(ài)的缺失,導(dǎo)演以此暗示愛(ài)的支撐對(duì)于緩解老年群體多層面生命困境的重大意義。
5 結(jié)語(yǔ)
本電影呼喚對(duì)于老年群體多層面生命需求的認(rèn)同以及對(duì)其困境的重視,并提出以愛(ài)為核心的解決方案與社會(huì)對(duì)策。人口老齡化不僅是日本的社會(huì)問(wèn)題,也是國(guó)際性社會(huì)難題,本電影對(duì)各國(guó)老齡化社會(huì)的文化轉(zhuǎn)型和制度構(gòu)建具有啟發(fā)意義。■
引用
[1] 陸曉鳴.從電影《恍惚的人》看日本老齡化社會(huì)[J].電影文學(xué),2010(9):103-104.
[2] [美]亞伯拉罕·馬斯洛.動(dòng)機(jī)與人格[M].許金聲,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
[3] 張季風(fēng).少子老齡化社會(huì):中國(guó)日本共同應(yīng)對(duì)的路徑與未來(lái)[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