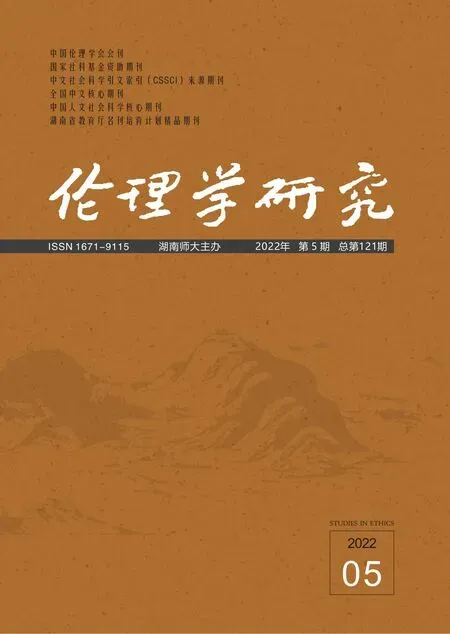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向度
儲德峰,何云峰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倫理向度可以考量。國家頒布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以下簡稱《新綱要》)從制度安排層面明確指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要“持續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1](4)。這表明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制度保障之于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性,體現了新時代高度的制度自覺。接下來,我們需要從實施和落實的角度思考如何將制度安排變成現實。對此,我們認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在進行制度安排的時候首先必須考慮制度的倫理向度。這是制度得以扎根的前提,也是決定制度建設成敗的關鍵。
一、制度倫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不可或缺的檢視向度
所謂“制度倫理”,是指針對制度的正當、合理與否進行的倫理評價和制度本身所內蘊的倫理追求、道德原則與價值判斷,以及指向制度的倫理屬性即制度的“善”或“好”的問題。在當代中國,如果說“‘制度倫理’問題緣起于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制度創新這一社會變遷基本路徑選擇的思考”[2](41),那么對于制度倫理與公民道德建設關系的探討則緣起于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經濟發展過快而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帶來的公民道德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公民道德建設“決不簡單地只是一個輿論宣傳教育的問題,更是一個生活實踐、制度化了的規范力量引導的問題,是一個價值引導與通過制度安排所呈現的利益誘導的一致性問題”[2](41)。在制度安排層面,公民道德建設需要創新制度安排并通過制度規范的剛性力量規約和引導公民道德生活實踐,推動和諧安定社會氛圍的形成。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遷,人們的道德生活實踐越來越復雜和豐富多彩。但無論人們的道德生活實踐多么復雜和多么豐富多彩,都可大致歸結為“道德理想”、“社會交往”和“心性修養”等三個基本層次。“道德理想”屬于道德信仰范疇即信仰倫理,“社會交往”屬于社會道德規范范疇即社會規范倫理,而“心性修養”則屬于道德品質范疇即美德倫理。道德理想主要強調的是對某種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追求,其最終指向道德理想主義即道德形而上追求;社會交往主要強調的是制度性道德規范體系對道德主體社會交往行為的引導和規約,其最終指向社會規范倫理即制度之善;心性修養主要強調的是個體內在德性之于道德建設的基礎性地位,其最終指向美德倫理即個體之善。對于公民道德建設而言,道德理想即道德形而上是方向和旗幟,具有內在的精神理想的意義;社會規范倫理即制度之善是他律之規則,具有保障意義;心性修養即個體之善是根基,具有根底意義。可見,三個方面彼此相互關聯、互相促進。
“在信仰倫理或道德形而上、社會規范倫理以及美德倫理三個層次之間,制度倫理是以社會規范倫理為基本理論維度的”[3](7),它一方面必須接受信仰倫理的指導,另一方面必須得到道德個體的普遍認同和接納。而社會規范倫理,就其具體物質形態而言,是既定社會已然形成的制度性道德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制度性道德體系是制度倫理的物質樣態,制度倫理融身于制度性道德體系之中。從公民道德建設的角度看,制度性道德體系即制度倫理“作為客觀的社會存在,不僅不為道德實踐主體的個人偏好所左右,相反卻對個人的偏好和價值追求起到矯正作用,把它們納入統一的社會秩序之中”[3](7)。制度倫理之于公民道德生活實踐的規范和矯正以及和諧穩定社會秩序的形成,具有重大價值和重要意義。一言以蔽之,公民道德生活實踐需要制度倫理的規范和引領。
從目的論角度看,公民道德建設就是通過人們的道德實踐將道德理想、道德原則以及道德規范等內化為人們的內在信念、外化為人們的實際行為,從而維護社會道德秩序,增益社會和諧。因此,如何將道德理想、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則構成公民道德建設的中心環節。傳統公民道德建設基于心性倫理,認為這一中心環節的實現必須依靠個體的道德自覺。因為,心性倫理認為個體“對道德在社會發展中的教化使命、倫理責任有清醒體認,能夠自覺承擔用先進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引領社會進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歷史使命”[4]。道德規范是“軟要求”并非“硬規范”。因此,個體的道德生活實踐理應是個體自覺自愿的行為,依靠的是道德自覺,帶有濃厚的志愿性。事實也的確如此。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許多善德義舉都是道德實踐主體的道德自愿行為,道德的志愿性是生成善德義舉的內在動力。因此,傳統公民道德建設強調要通過道德倫理教育提升公民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志愿性,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人的需要日益豐富多樣,人與人的交往日益普遍頻繁,人際利益沖突日趨多元,道德自覺的局限性也隨之日益凸顯。易言之,個體的道德理性都是有限的,難以應對日益復雜多變的道德生活實踐和社會交往,“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新舊倫理觀念相互沖突,善惡是非界限非常模糊,這就需要社會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確的社會道德規范,告訴人們什么是應當做的和什么是不應當做的,協助個體確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3](9)。此外,個體的道德意志同樣也是有限的。面對社會之中日益紛繁復雜且無處不在的各種誘惑,僅僅依靠個體有限的道德意志,顯然難以克制其本身所固有的自私欲望的膨脹,更談不上自覺承擔用先進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引領社會進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歷史使命。公民道德建設總是從現實的人出發,而作為現實的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都是有限的。
公民道德建設不能僅僅強調和依靠個體的道德自覺,還需要創新制度安排,加強符合倫理要求的制度建設,將道德理想、道德原則以及道德規范融入制度之中,使倫理要求成為集規范約束和價值引導于一體的、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制度力量。其實,制度倫理概念的出現和人們對于制度倫理的覺醒,意味著公民道德建設正在經由美德倫理(個體善)向規范倫理(制度善)轉向。從倫理視角考量制度的合理性、公平正義性以及屬人性,已在悄然之中成為公民道德建設不可或缺的向度。當前學界關于制度倫理的思考,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制度倫理即“制度的倫理和制度中的倫理”。這種認識或理解認為,“從概念上分析,制度倫理不外乎兩種:制度的倫理——對制度的正當、合理與否的倫理評價和制度中的倫理——制度本身內蘊一定的倫理追求、道德原則和價值判斷”[5](56)。“它所指向的是制度的倫理屬性,是關于制度的‘善’或‘好’的問題,它是要從倫理學維度關注制度,對實存制度進行價值分析。”[2](42)
其二,制度倫理即制度倫理化。這種觀點秉持的是“制度中心觀”[6](20),認為“社會體制的道德性,表現為內在于一定體制的制度、法律、法規、政策、條例等所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公平性和合理性”[7](37)。制度建設既要遵從特定社會體制的倫理原則、道德要求,也要符合人們對于制度正當以及合理與否的倫理評價,現有制度必須進行倫理道德審視才能確立其正當性和合法性。
其三,制度倫理即倫理制度化。這種觀點秉持的是“倫理中心觀”[6](21),認為“制度倫理就是一種制度化的道德規范和原則”[8](10),是“以強制性力量為后盾的明文化了的道德約束、監督及激勵機制”[7](37),主張要將社會廣泛認同的道德倫理規范和原則上升為具有剛性約束效力的社會性法典,現代社會倫理道德建設必須通過倫理的制度化增強他律性,才能將人們的多元行為統攝于統一的主流道德和價值觀念之中。
其四,制度倫理即對制度的倫理分析。這種觀點認為,“‘制度倫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倫理化’,也不是什么‘倫理的制度化’,而是對制度的倫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倫理屬性及其倫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個善的制度應該是怎么樣的’‘何以可能’‘有何倫理價值’等問題”[2](43)。
筆者以為,無論上述哪種觀點,均有各自理據、效能以及貢獻,所不同的只是關于制度倫理的價值訴求。第一種觀點即“制度的倫理和制度中的倫理”包含制度的外在倫理評價和內在倫理意蘊兩個方面,提出較早且對后來學術研究影響較大;第二種觀點即“制度倫理化”和第三種觀點即“倫理制度化”分別是對第一種觀點所內含的兩個不同維度的進一步展開;第四種觀點即“對制度的倫理分析”則是在對前三種觀點的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的創新性發展,其“以制度作為自身的關注點,并以制度的‘善’或‘好’作為其核心”,把作為人的自由意志實踐的具體樣式的制度和作為人對人性以及正義追求的倫理道德統一起來[2](43),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向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資源。
總之,公民道德建設離不開合理、良善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必然會涉及倫理的問題。如果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本身出現了倫理的脆弱性甚至矛盾性,那就可能會對制度本身的質量提出嚴峻挑戰。因此,從制度倫理角度審思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際上為人們的道德生活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性依據,意義重大且具有挑戰性。
二、兩難困境: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制度倫理的關鍵檢視節點
公民道德建設離不開制度規制,而制度規制又離不開倫理標準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審視。不符合倫理要求的制度無論如何健全和系統化都不是好的制度,最終也不會把公民道德引向人類文明的新高度。制度倫理融身于制度性道德體系中,制度性道德體系是制度倫理的物質樣態。在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設計中,很多的倫理問題會顯性或隱性地被牽涉到。而制度合倫理性的前提和基礎是要解決好制度可能帶來的各種兩難困境。具而言之,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設計必然涉及制度與價值、制度與規范、制度與意義等對應關系,而制度安排在處理這些關系的時候容易陷入兩難尷尬狀態,如“有制度無價值”[9](277)、“有制度無規范”[9](277)、“有制度無意義”[9](277)等,這就是制度倫理的兩難困境。公民道德建設本身必須要經得住倫理的拷問,而如何解決好這些兩難倫理困境,就決定著相關的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倫理追尋的要求。
1.滯后于新的社會生活實踐:“有制度無價值”
任何制度倫理“總是對生活世界內在秩序的具象反映與現實性表達,并從生活世界本身獲得存在合理性的證明”[10](243)。一方面,作為既定生活世界內在秩序的具象反映與表達,制度倫理一旦形成就必然會獲得相對的穩定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生活實踐本身總是處于不斷生成和變化之中,已然形成的制度倫理必然會經由與社會生活實踐的相適應而逐漸走向不相適應的狀態,滯后于新的社會生活實踐。也就是說,制度倫理相對于社會生活實踐本身的滯后性,是其自身的固有缺陷,其存在具有客觀必然性。但是,對于不斷發展變化著的社會生活實踐本身而言,如果制度倫理滯后于社會生活實踐,不僅會影響制度倫理本身的質量和水平,而且會降低制度倫理之于社會生活實踐的規范、約束和引領效能,對社會生活實踐本身形成非正向性的價值導向,甚至會讓社會生活實踐陷入“有制度無價值”的尷尬境地。因此,必須及時運用政治統治手段或治理工具對滯后于社會生活實踐的制度倫理予以調適或革新,以便最大限度地實現制度倫理和社會生活實踐同頻共振,降解其滯后性及其負面影響。如實施了五十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民法典的出臺等,就是根據社會生活實踐的變遷而對制度倫理作出的革故鼎新。
客觀地說,在社會生活實踐發展相對緩慢的歷史時期,制度倫理相對于社會生活實踐的滯后性并不明顯,不容易引發關注,即便被關注,人們也大多基于任何一種制度倫理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理性認知而予以寬容,并自覺將之懸置。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國內經濟社會深刻變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遷,使制度倫理的這種滯后性及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因此,分析制度倫理同社會生活實踐相適應到不相適應(滯后性)的變遷進程,不僅要著重于制度倫理和社會生活實踐的共時性分析,反思其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現代性,確保制度倫理的相對穩定性和獨立性,而且更要著眼于制度倫理和社會生活實踐的歷時性分析,反思其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敘事性,為推動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與時俱進提供內生動力。
2.圓融自洽障礙:“有制度無規范”
制度倫理作為社會普遍意志的現實性表達,本質地表現為經由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制度建設,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將制度倫理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最終目標。從制度倫理的生成過程看,制度倫理要滿足內外兩方面的要求:對內要求作為制度倫理的靜態結果的制度體系應當具有技術上的圓融自洽性;對外則要求作為決定和影響制度倫理的治理效能的制度運行機制與社會管理體制圓融自洽,因為任何制度體系都是在既定的社會管理體制下運行的。換言之,如果作為制度倫理的靜態結果的制度體系的運行機制受到社會管理體制掣肘,那么制度倫理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效率必然大打折扣。對于前者即對內的要求方面,由于制度體系作為一種技術性存在,本身很難做到絕對的圓融自洽,總是存在“制度作為一個系統所要求的內在耦合性,與系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頡頏性的矛盾”[10](244),也就是說,制度倫理在技術設計上難以做到盡善盡美,只能通過技術設計的自我革新不斷予以修正;而對于后者即對外的要求方面,從更加宏觀的制度倫理視野看,制度運行機制和社會管理體制都屬于制度倫理所應統攝的范疇,理應彼此相融而非相互矛盾。
事實上,當前一些制度運行機制受社會管理體制掣肘的現象客觀存在。這已經成為制約制度倫理的治理效能轉化的重要因素,需要予以高度重視。比如當前針對打擊制假售假的制度倫理:負責打擊制假售假的質檢機構和工商管理部門,不但在行政上受地方政府管轄,而且在經費支出上也受制于地方財政。在數字化考核日益常態化的年代,制假售假企業的“業績”往往和地方財政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績有著某種內在關聯。如果制假售假企業能給地方財政上交可觀的稅費,那么就有可能會有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政績考慮,非但不會對質檢機構和工商管理部門的打假行動予以支持,反而會對打假工作的開展設置重重障礙。再如對權力尋租進行有效監督的制度倫理:同級紀委既要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又要對同級黨委和政府進行監督,難免會有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嫌疑,難以確保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其監督效果很難令所有人滿意。這些機制受體制掣肘的現象都是制度倫理的自洽障礙的具象表達,如果不能及時予以消除,勢必會嚴重影響制度建設向治理效能的轉化效力,其結果可能會導致有制度無規范的現象出現。
3.價值結構失衡:“有制度無意義”
善的制度倫理或制度倫理的善,就其本質使命而言,在于通過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制度安排,克服由于人的因素造成有違公平的現象,保證人民平等發展的權利,實現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制度倫理的價值取向,從應然層面看,必然內含敗德報復正義(罰惡正義)和善德善報正義(賞善正義)兩重向度,既通過體現敗德報復正義的制度的剛性約束力對失范行為進行合理懲罰,彰顯敗德必受報復的正義價值,為社會生活實踐提供底線保障,同時還需通過體現善德善報正義的制度對善德良行予以激勵,彰顯善德必有善報的價值正義,為社會生活實踐提供價值指引。換言之,罰惡正義和賞善正義共同構成并維護制度倫理價值結構及其平衡。
但在實然層面上,當前我國制度倫理的價值結構失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存在。就其總體性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情形:一是罰惡和賞善的單向度發力與制度倫理總體價值結構平衡的脫節現象時有發生。盡管敗德報復正義(罰惡正義)和善德善報正義(賞善正義),都有其重點,但從價值結構平衡角度看,單向度的局部發力,往往與制度倫理的目標和初衷相去甚遠,有的甚至會發生某種程度的蛻變。二是當前的制度倫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敗德報復和善德激勵之間的張力失衡現象。這種失衡通常會有兩種表現:其一是有制度無效力,如當前客觀存在的諸多明明有制度的禁止仍要公然冒犯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存在制度約束力不強所導致的失范成本較低的因素,但其深層次的根源卻在于制度倫理的敗德報復和善德激勵張力失衡。敗德報復重在事后懲戒,雖然可以對主體的失范行為形成威懾,但卻難以從根本上消除主體可能存在的損人利己的行為動機,更談不上塑造主體品質。善德激勵則重在通過對善德義行的激勵推動善德必有善報心理機制的形成,從而達至消除主體可能存在的失范動機、塑造主體品質、形成人人向善社會氛圍的目的。缺少善德激勵向度,制度倫理只能治標而難以治本。其二是無制度無規范,如近年來屢屢出現的見義不勇為、見倒不幫扶、見困不援助、見死不施救等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其說在于人們的道德良知的麻木,不如說在于制度倫理中善德激勵向度的缺失。由于缺少彰顯善德善報正義的制度倫理,見義勇為、見倒即扶、見困即助等行為則可能就純粹意味著奉獻、犧牲,有的施行者甚至存在被誣陷的風險,一度甚囂塵上的道德爬坡論與道德滑坡論的論爭就是最好注腳。
三、三重邏輯: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制度倫理的基本檢視理路
從上述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可能出現的兩難困境的分析可知,以時代為關照,以回應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倫理訴求為重點,以增進制度倫理之于人民美好生活實踐的規范、約束、引領和價值導向效能為目標,遵循與時俱進的發展邏輯以完善和發展新時代公民道德的制度體系,遵循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以增進制度倫理的圓融自洽性,遵循賞善罰惡的價值邏輯以推動“不敢失范、不能失范、不想失范”三位一體有效機制的形成,是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走出“有制度無價值”、“有制度無規范”和“有制度無意義”等兩難困境的應然選擇。
1.與時俱進的發展邏輯
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1](11)。這是黨中央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遷所作出的科學論斷。這一科學論斷表明:“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并不局限于‘生存’和‘享受’層面對于物質文化生活的‘硬需求’,其重心已經悄然轉向‘發展’層面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軟需求’”[12](56)。社會主要矛盾作為社會生活實踐樣態的高度凝練和科學概括,表征著社會生活實踐的倫理價值訴求,是制度倫理的重要依循。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換,既意味著新時代社會生活實踐發生巨大變遷,同時也預示新時代社會生活實踐的倫理價值訴求發生變化,一些既有制度倫理已經或即將滯后于新時代的社會生活實踐,此外,還有一些新的領域迫切需要制度倫理予以規范、約束和引領。如果任由這種情況自行演化,那么一些社會生活實踐領域就可能陷入“有制度無價值”或“無制度無規范”的尷尬境地。
因此,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要遵循與時俱進的發展邏輯,按照《新綱要》所提出的“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的原則,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為邏輯起點,推動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對既有規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制度體系進行全面梳理和倫理審視,對不符合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倫理訴求的制度予以革新或廢除,推動既有制度倫理及其制度體系創造性轉化,消除既有制度倫理之于社會生活實踐的滯后性,確保制度倫理之于社會生活實踐的價值引導和規范約束,避免“有制度無價值”現象的出現;另一方面,要以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安全以及環境等方面為重點,完善和發展新時代的制度倫理,抓緊制定“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13](180),加快制度倫理及其制度體系的再生產,推動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及其制度體系的創新性發展,避免“無制度無規范”現象的出現。唯有如此,方能實現制度倫理與社會生活實踐的同頻共振,確保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的生機和活力,擔負起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任。
2.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
正如前文所說,制度倫理的圓融自洽具有二重性,對內要求作為制度倫理的靜態結果的制度體系應當具有技術上的圓融自洽性,對外則要求作為決定和影響制度倫理的治理效能的制度運行機制與社會管理體制圓融自洽無礙。就制度倫理的起源及其本質來說,制度倫理是人們通過運用理性能力設計出來的理性建構,是人們的有限理性能力的技術性存在。因此,任何制度倫理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難以做到絕對性的圓融自洽無礙,總是在某種程度或某種層面上存在某種內在裂隙或外在掣肘。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的圓融自洽性追求,就其絕對意義而言,確實難以實現。但本文所說的制度倫理的圓融自洽性并非上文所說的絕對性追求,而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因為,當我們說某一制度倫理存在圓融自洽障礙時,事實上不同程度地蘊含著一個主觀情感判斷——對這個制度倫理在總體上是基本認可的,只是這個制度倫理在圓融自洽性方面還不盡如人意,存在調適的空間和可能。如上文所提到的對打擊制假售假的制度倫理以及對權力尋租進行有效監督的制度倫理等。
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必須遵循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內含完善和發展兩個方面的致思:其一,調適存在圓融自洽障礙的既有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及制度體系,提升制度倫理及制度體系的規范效能;其二,以圓融自洽為標準創設新時代急需的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及制度體系,發展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及制度體系。對于前者,既要按照制度必須合乎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倫理訴求的原則,調和制度體系的內在耦合性與系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頡頏性的矛盾,使其處于能夠被容忍或被接受的范圍內,也要用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倫理訴求對標社會管理體制,增強社會管理體制的治理意蘊,減少社會管理體制對制度運行機制的掣肘,增強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及制度體系的治理效能,從而避免出現“有制度無規范”的尷尬現象。對于后者,是基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和社會生活實踐的變遷所帶來的新的社會倫理訴求的思考,也就是說,新時代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和新期待倒逼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必須進行創新性發展,新的制度倫理的創設同樣要遵循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否則,就會出現新的“有制度無規范”。
此外,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要遵循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從有益于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制度倫理建設的地方實踐來看,具有迫切性和現實必要性。如《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的施行、道德糾紛調解機制、道德回報機制的運行等,由于受到社會立法滯后、制度配套令出多門以及體制機制條塊分割的掣肘,要么僅停留在試點,制度化難,要么機制受體制限制,法治化難。這些已經嚴重影響了制度倫理的治理效能,迫切需要遵循圓融自洽的生成邏輯,提升其圓融度和自洽性,確保其規范效力和治理效能,方能避免陷入“有制度無規范”的困境。
3.賞善罰惡的價值邏輯
對于制度倫理必須遵循賞善罰惡的價值邏輯,鄧小平同志有過經典論述:“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4](333)這句話切中制度倫理理應遵循的賞善罰惡的價值邏輯。“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意味著好的制度倫理必須遵從敗德報復正義原則,即通過體現敗德報復正義的制度倫理對社會主體失范行為予以懲戒,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則意味著好的制度倫理還必須遵從善德善報正義原則,即通過體現善德善報正義原則的制度倫理對善德義行進行褒揚和激勵,為好人充分做好事提供剛性保障,樹立善德必有善報價值理念,引領社會主體行為,催生更多的善德義行。總而言之,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必須兼具敗德報復正義(罰惡)和善德善報正義(賞善)兩個價值向度。
人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的終極對象,總是現實性存在。而現實性存在的人總是有欲望和沖動的。換言之,任何以利己為目的的失范行為,其根本誘因都在于現實的人與生俱來的利己欲望和沖動。敗德報復正義通過對失范行為的事后懲罰(敗德報復)威懾人的利己欲望和沖動,但難以消除人的欲望和沖動。就此意義而言,敗德報復只是制度倫理的手段而非目的,僅僅依靠敗德報復顯然難以達至制度倫理的終極目的,即難以形成信任、合作、和諧、向善的社會生活秩序。進而言之,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的最終目的即信任、合作、和諧、向善的社會生活秩序的形成,不僅需要敗德報復正義,即通過規制治理懲罰已經發生的失范行為,為社會生活實踐劃定行為邊界,構建不敢失范和不能失范的威懾機制,而且還需要善德善報正義,即通過對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善德義行進行褒揚和激勵,形成善德善報的價值導向,構建不想失范的價值認同和價值引領機制。也就是說,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必須同時兼具敗德報復和善德善報兩種價值取向,唯有在敗德報復和善德善報兩種價值取向的張力中,方能產生不敢失范、不能失范和不想失范的有效機制,確保制度倫理的價值正義特質,提升公民道德建設的能力和水平,從而推動信任、合作、和諧、向善的社會生活秩序的形成。
結語
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必須要有完善的制度體系加以保障,而制度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又必須遵循人類倫理建構的基本原則。換句話說,真正促進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不是任意設定的制度倫理,而是符合人類倫理價值基本標準、能夠保障公平正義和人性進步的制度倫理。利奧·施特勞斯說:“寥寥幾代之前,人們還是普遍確信人能夠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能夠知道什么是正義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會秩序……在我們的時代,這個信念已經回天乏力了。”[15](86)現代社會的市場倫理日益強調能力本位,社會個體以社會人的方式而存在,個體在自己的生命區間內對自己的行為按照“權責利險對稱平衡”的原則承擔無限責任,道德觀念相對比較貧乏的人們內心相對比較空虛,或焦躁不安,或行色匆匆,或遲鈍麻木,或自命不凡。基于德治規范論的傳統公民道德建設,強調以德治規范的軟要求引導生成社會主體的道德自律,顯然難以滿足能力本位時代的公民道德建設的他律要求。隨著“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理論的提出及其實踐的全面推進,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對于加強制度倫理建設發揮制度保障作用的訴求呼之欲出。
從道德哲學層面看,對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向度進行分析和探討,蘊含著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必須加強制度倫理建設以發揮制度保障作用研究的兩大學術維度:現實意義和終極價值。在現實意義層面上,制度倫理是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發揮制度保障作用不可或缺的必然向度,加強制度倫理建設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提供信任、有序、穩定的制度環境,提升制度的治理效能,既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理念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領域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在全面推進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這一時代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設的邏輯演進之必然;在終極價值層面上,對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向度進行探討,其目的在于使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制度倫理能夠更好地體現公平正義原則,努力克服由于人的因素以及制度倫理本身的缺陷造成有違公平的現象,保證新時代人民的平等發展權利和美好生活需求,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重點追問的是制度倫理如何使新時代公民成為一個好公民的形而上問題。因此,制度倫理之于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既具有本體論意義,又具有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