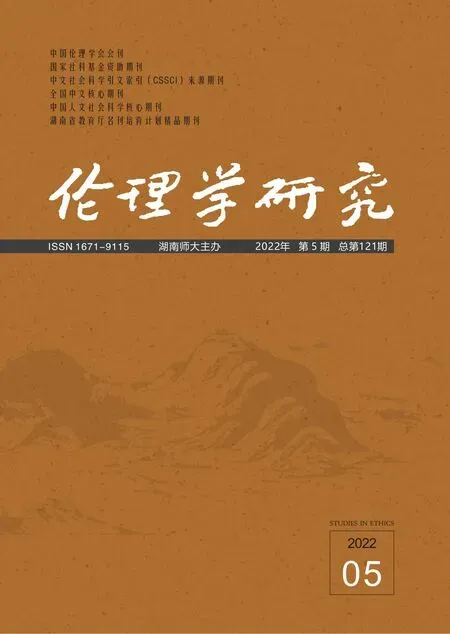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陰的教育倫理思想
朱玲莉,朱 懿
吉田松陰(1830—1859)作為日本江戶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以明治維新的改革派精神領袖形象為大家所熟知。他出生和成長在日本自然災害和社會暴動頻繁發生的天保年間(1830—1844),這一時期由于幕府的天保改革失敗,歐美列強頻頻扣敲日本的國門,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江戶幕府的統治之下,以吉田松陰為代表的改革武士派,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進行推翻幕府的倒幕運動。吉田松陰積極向西方學習,通過教育培養革新之士,他曾在松下村塾開展教育活動,培養了許多日本明治維新的精英人物,如木戶孝允等具有開拓精神的改革型人才。他的學生中有的是倒幕維新的核心成員,有的是明治新政府的領導力量,這些人才的培育積極推動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
一、吉田松陰的教育背景
日本江戶時代被稱作“教育爆炸的時代”。在江戶德川幕府倡導的“文武兩道”的文教政策的推動下,日本民族文化不斷發展且趨于成熟,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得到迅速的發展和普及。其間,教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一時期的學校教育機構主要分為官辦學校(德川幕府直轄的最高學府昌平坂學問所)、藩校(藩內武士子弟的教育機構)、私塾(漢學教育和高等教育機構)、寺子屋(初等教育機構)、鄉學(初等教育和平民的高等教育機構)等幾種形式,另外還有醫學館等專門的洋學教育機構。吉田松陰所主持的松下村塾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下孕育而生的。
吉田松陰從小過繼給作為長州藩兵學教師的叔父,并跟隨叔父學習山鹿流兵學。在學習兵學的同時,吉田松陰還在松下村塾學習一些傳統的漢學課程。其后他到長州藩藩校“明倫館”開始正式學習山鹿流兵學,后來成了藩校“明倫館”的兵學教師。1851 年吉田松陰到江戶游學,在學習期間,吉田松陰深感山鹿流兵學已經落伍過時,日本要想強大就必須學習西洋先進的技術,通過加強軍事力量來抵御外敵。1853 年,吉田松陰再次來到江戶正式拜日本著名思想家佐久間象山為師,決心學習蘭學和西方的軍事技術。同年美國佩里率軍艦“黑船”抵達日本,要求德川幕府開港通商。吉田松陰看到美國艦隊的船堅炮利之后,自感“吾國之弱小無抵御之力”[1](17)。1854 年,美國軍艦再次來日,強迫德川幕府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從此日本國門被打開。此時,吉田松陰再次痛感幕府的無能,企圖趁機搭乘美國軍艦偷渡留洋,事情敗露后被以“叛國罪”押送回長州藩,監禁于野山監獄[1](17)。在野山監獄,吉田松陰勤奮努力,翻閱了許多歷史哲學、文學典籍等方面的書籍,并著述了《野山獄讀書記》、《幽囚錄》和《獄舍問答》等書籍。在獄中,吉田松陰深刻地認識到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傳承自己的遠大志向。于是他在獄中就開始開展一些教育活動。1855 年出獄后,吉田松陰被圈禁在家“閉門思過”。1856 年9 月,為了弘揚自己的倒幕志向,吉田松陰進入叔父的松下村塾講學。私塾開始只有幾個弟子,到后來則聲名大振,各地前來求學的學生絡繹不絕。松下村塾改變了江戶時期教育的階級性,提倡士庶共學,摒棄了師生之間的繁文縟節,積極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和積極性,培養了自由質樸的新學風。1858 年6 月,幕府先后與美英等國締結不平等條約,日本國內矛盾不斷激化,倒幕運動迫在眉睫。吉田松陰號召武力討伐幕府,制訂刺殺幕府重臣的計劃。由于刺殺計劃泄露,他再次入獄。在幕府大佬井伊直弼為鎮壓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獄”事件中,吉田松陰于1859 年8 月被押解至江戶,同年10 月被殺害,年僅29 歲。吉田松陰作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雖然受其教育的弟子只有92 人,但是這些弟子在明治時期被授勛者多達37 人。大多數弟子成了倒幕維新和明治新政府的領導者和核心力量。
二、以維護封建秩序為主的道德價值論
眾所周知,日本在江戶幕府時期實行武家政權組織嚴密的幕藩體制。在兵農分離體制下,武士(兵)徹底脫離農業生產,離開村莊而遷居都市,成為統治階級。作為被統治階級的農民(農)世世代代束縛于農田,每年交納年貢來維系武士階級的生活支出。人們根據身份、門第等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和“四民”以外的賤民。他們在社會地位、職業、生活方式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受到嚴格限制,不可逾越,等級森嚴。
在這種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下,吉田松陰作為江戶時期的武士階級,即使在幕府處于風雨飄搖、“士風日下”即武士階級道德水平下降的時期,他仍然堅信維護封建倫理秩序是治理天下的關鍵,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語天下之至論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天下豈有不平哉。然則天下之不平者,在于君不君則臣不臣,臣不臣則君不君也,二者常相待而后天下不平”[2](94-95)。臣子始終是君主的臣子,為君主所用,做好隨時為君主獻身的準備。在吉田松陰看來,積極維護以往的封建等級秩序才是倫理道德教育的主要核心內容。
吉田松陰倡導的這一倫理道德教育的核心依據在于武士的職責是出仕于君,統治三民。他認為:“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3](99)吉田松陰堅持封建身份制的道德觀,肯定封建社會的身份等級制度的存在,強調士農工商各有其責,而作為“四民”之首、“三民之長”的武士階級不同于從事農工商那樣的職業,是統治階級。
到了幕末時期,武士的“士風”道德素質日趨下降,吉田松陰批判這種武士風氣,想竭力挽回武士在封建社會中的高大形象;同時,他也要求平民加強道德品質修養,試圖維護以往的封建統治秩序。他認為“志”為士的標準,有兩層含義:一是激勵武士成為理想的武士;二是要求庶民中的有志之士積極實踐“士”所要求的道德規范,使其為維護身份制社會秩序服務[4](121)。從這里可以看出,吉田松陰認為武士和平民的教育目標是不同的,即武士教育是為了培養更優秀的統治階級之“士”,而平民教育則是通過加強封建倫理道德教育,更好地維護原有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秩序。
同時,吉田松陰除了對武士和平民道德教育進行闡述以外,還強調武士和庶民在道德認知上是有差別的。因此,他認為不同身份的人的道德修養要求也各異。例如,“學問之道,要在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其所異者,無外乎五倫五常之得與失。失之則為庶民,勤而得之則為君子,從容自存者為圣人。雖云眾人,勤勵則為君子,至其功熟,即圣人也”[2](112)。他認為教育就是要培養圣人、君子等封建統治階級的理想人物,以此來維護正常的封建秩序。具體而言,吉田松陰認為武士和町人雖然同樣是社會之人,但對他們要求的道德內容卻各異。“夫屋宅極盡美麗,居間唯求便利,地板之置物,掛件,屏風,障子……商買町人者不苦之。茍為居于武士之籍而行搜集之舉,非誠為可恥之事乎?”[3](113)武士如果做了町人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就是可恥的,應當批判。吉田松陰強調平民教育可以不用太復雜,相對簡單就行。與平民內在的道德修養相比,吉田松陰更關心的是外在的平民對封建社會秩序的服從。由此可見,吉田松陰的倫理道德修養論最終也沒有超出封建教化的范疇[4](120)。
三、松下村塾的道德教育論
吉田松陰的倫理道德理念也在他曾執教過的松下村塾中充分地表現出來。松下村塾是日本江戶末期著名的私塾之一,因為培養了大批明治維新之士,曾被喻為“明治維新胎動之地”。它位于日本山口縣,1842 年由吉田松陰的叔父玉木文之進創辦,后由久保五郎左衛門在其私宅續辦。吉田松陰因思想激進,1855 年被幕藩勒令在家“閉門思過”,這期間大批塾生前來求教,于是吉田松陰成為該塾的教師,1857 年后成為塾主。1859 年吉田松陰被處死后,該塾由玉木文之進和杉民治等人繼續興辦,1892 年停辦。由于當時是幕末時期,日本處在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時代,吉田松陰時常憂國憂民,提出了“一君萬民”的號召,主張“尊王攘夷”的政治思想。在師匠決定私塾性質的江戶時代,松下村塾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內容,也是圍繞“尊王攘夷”這一主題開展的。由此可見,松下村塾是一個具有一定政治性的私塾。吉田松陰希望通過“村塾宣傳正義,培養國家之棟梁,維系天下之太平”[5](46),即“村塾雖簡陋,將成為神國之支柱”[6](224)。
首先,松下村塾十分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吉田松陰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強調道德教育至上。他提出求學即是求道,其中的“道”就是讓人明白何為五倫。因此,在教育活動中他始終堅持以倫理道德教育為中心,他認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動物,就是人明白倫理道德”[7](10)。吉田松陰認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上明君臣之義與華夷之辯,下不失孝義忠悌”。吉田松陰曾在松下村塾的題記中強調:“學,學所以為人也。”“為人”是“為人之道”,即“入則孝悌,出則忠信”的“為人之道”[3](52-53)。
吉田松陰在《士規七則》中的第一條便提到了“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為最大,故人之所以為人,忠孝為本”[8](227),以此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同時,他在“松下村塾規則”中規定:第一,不可違背父母之命;第二,應告知父母自己的行蹤;第三,要晨起洗漱,拜祖先,朝著城堡方向叩拜君主,朝東叩拜天朝,即使生病也不能懈怠;第四,對兄長年長且地位高之人,不得無禮,一定要恭順,要愛戴年幼的弟妹;第五,入塾、退塾以及塾內之間的交往都要禮儀端正。第一條為基礎,違者罰坐禪,其他則視情節輕重進行處罰[9](292-293)。這些規則不僅規定了弟子在私塾中的行為舉止,還規范了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和道德規范。
在教育評價制度上也體現了松下村塾教育對道德的重視。松下村塾根據弟子的日常品德,以及在學業上的勤勉程度設定了“三等六科”的評定標準,即“古人有月旦之評,今且為子弟,設立三等,分為六科,各標其所居,月朔升降,以念其勤惰。曰進德,曰專心,是為上等,曰勵精,曰修業,是為中等,曰怠情,曰放縱,視為下等。三等六科,志之所趨,心之所安,無為而不可,誠使邑人皆進為上等之選”[10](437)。思想懈怠、不精于學業的弟子為下等;精于學業并勵志的弟子為中等;品學兼優的弟子為上等。松下村塾的這種依據弟子道德品質的優劣和對學習的態度、不考慮學生的成績分數等其他因素而制定的“三等六科”的評價制度,是一種相對理想化的教育評價制度,充分體現了吉田松陰重視弟子道德思想教育和松下村塾教育自由性的特點。
其次,松下村塾十分重視教育平等。吉田松陰認為社會有身份等級之別,承認人性差別的存在。他指出:“人有三等。下等之人,不合于義,不信不果之徒,是妄人也。中等之人,必信必果,未必合于義之徒,是游俠之類也。上等之人即本文所謂大人,不必信,不必果,惟從義之所在而行之人也。若泛論人品,中等之人亦非易得,勿輕之。然至于為學者,舍上等何所學乎。”[2](108-109)人雖然天生有別,但他認為弟子無論天資如何,只要勤奮好學都能學有所長。他強調“人性皆善,圣人亦與我同類者也”[2](150)的“性善論”。他認為人不論身份高低貴賤,只要是有用之才都可以為國效力,對有志之士都歡迎接納。“人雖有賢愚之別,但每個人都有一兩個長處。因此,成就大事者要善于發現他人之長處,將這些長處發揮出來。”[11](158)同時,他提出:“天下之人皆為國之臣民,無論是誰,只要是有才干就應竭盡所能為國效力,在能力上不應有武士庶民貴賤之分。”[12](194)我們從松下村塾的弟子身份構成中也能看到這一點。從安政三年(1856)3 月到野山再獄的安政五年(1858)12 月,來松下村塾學習的弟子共92 名。其中武士有76 名,除此之外,還有醫生、僧侶、商人等[13](117)。弟子年齡不一,最小的9歲,最大的36 歲。松下村塾門生的平均年齡約18.6 歲[13](119)。松下村塾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無論年長年幼只要有志學習者均可入塾學習。在松下村塾中,與那些傳統儒家教學尊師重道不同,吉田松陰在教學上從弟子最感興趣的地方著手,因材施教,不斷啟迪學生,發現弟子們的長處,激發他們的學習激情,培養他們精誠團結的合作精神。吉田松陰的這種教育平等、積極招納各階層賢才的思想,在當時危機四伏的日本幕末時期,對日本教育沖破束縛并開啟近代化的進程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最后,松下村塾在教育的內容上也體現了吉田松陰的道德教育理念。在日本江戶時代,無論是幕府官辦的直轄學校還是地方各藩的藩校,都要求武士重視文武兩道。吉田松陰自己是武士出身,從小學習兵法,后來師從佐久間象山學習兵學,因此通曉文武兩道成為其后來執教松下村塾的宗旨。在松下村塾的教育過程中,他十分重視武道的學習,認為“習武藝,論武藝,閱武器”[3](105)這三件事是武士每天必須做到的事情。與此同時,他強調誦讀中國古典經書,提高自身修養和品性。他提出要學習真武真文[14](88),“不要形成無禮無法,粗暴狂悖的偏武”,同時他也警告弟子“不要只記誦辭章,浮華文柔,要學習真武真文”[3](98),只有掌握文武兩道才能為君主為國家做好隨時獻身的準備,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武士。松下村塾的整個教學活動一直圍繞吉田松陰的這一道德教育理念展開,它也成了日本私塾的典范。
在吉田松陰的這種重視文武兩道的教育理念指導下,松下村塾使用了大量的漢學教材,主要有《左傳》《資治通鑒》《孟子》《孔子》等,此外還有賴陽山的《日本外史》以及充滿“尊王攘夷”色彩的會澤正志齋(1781—1863)的《新論》等日本書籍。他還鼓勵弟子博覽群書。吉田松陰在《士規七則》里提出:“立志以為萬事之源,擇優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圣賢之訓。”[7](10)吉田松陰告誡弟子讀書,應讀圣賢之書,遵圣賢之訓,專心學道才能明曉事理,通達古今。在“村塾記事”中寫著“天下之書,蓋有四大別,曰經、史、子、集,通習四者,各究其精,是謂博學”[5](542)。他重點采用了“二十二史及資治通鑒各自為課”[5](542)的篩選方式,要求學生要用心去讀書,用心去理解“忠信孝悌”的真諦。吉田松陰認為弟子要勤奮努力,達到“為人之道”的標準,即“人唯一心,心唯一誠,以是事君則忠,以是事父則孝,以是事官長則敬,以是誨子弟則友,是其義也”[3](18)。松下村塾為豐富弟子們的學習生活還經常開展形式多樣的討論活動,涉及如世界形勢與日本現狀、藩政改革和幕府改革等具有政治色彩的話題。
為了更好地實施道德教育,他認為“人性教育作為高層次的教育,單純地通過語言教育是不夠的,還必須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因此,作為教育者必須要盡最大努力凈化和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7](10)。松下村塾力圖讓學生們在理想的教育氛圍中學習,并且通過老師合理的指導來達到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之道德教育目的。
松下村塾在教學環節中還安排了一些教育實踐活動,以此來提升弟子們的道德情操。教師除了傳道授業解惑、豐富弟子的學術知識以外,還經常開展射擊、劍術、操槍、登山、游泳等體育鍛煉,“定于每月十二日為野外郊游日,近則一二里,遠則五六里,大家一起練習擊劍和射擊而后回塾”[5](309)。吉田松陰因為當時待罪被圈禁在家,因此類似這種室外實踐活動無法參加,但是他率領弟子在私塾旁整隊操練,以竹刀代替槍炮進行射擊訓練[9](355)。通過這些野外鍛煉,弟子不僅提高了身體素質,而且鍛煉了堅強的意志。與此同時,他們也經常一起生產勞動,在共同勞動的過程中談論歷史、討論時事,從而達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營造了一個和諧、相互尊重信賴的學習氛圍。而且,吉田松陰注重個性化教學,因材施教,根據弟子們的特點,啟發引導弟子明確學習方向、確立學習目標。他經常通過書信對弟子進行個別指導。在松下村塾執教的一年多時間里,他給門生的書信約有70 余封[15](20),對弟子進行明確化的個性指導。
松下村塾的教育實踐活動不拘泥于本私塾內,他們還經常和其他私塾的學子進行學習交流。在日本江戶時代,私塾的學習生活也相對自由。弟子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在私塾學習的時間長短,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在幾個不同的私塾學習。松下村塾經常和育英館(阿武郡須佐村)私塾進行交流。育英館的館主益田彈正曾跟隨吉田松陰學習兵學,和松下村塾的弟子關系密切。兩個私塾的弟子不僅在學術上經常交流,還在政治領域等方面相互切磋。其后,松下村塾和其他私塾的弟子到日本各地游學,作為“吾黨之士”積極地開展倒幕運動。
四、吉田松陰的女子道德教育論
在江戶時代,日本出現了文化復興的新局面,各種學派百花齊放,學者輩出。尤其是江戶時代中后期,日本學術發展,教育機構林立,識字人數不斷增多。據不完全統計,江戶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識字,在婦女中有15%的人識字[16](85)。在日本幕末時期女子教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作為改革派先鋒的吉田松陰也十分重視女子教育。他所寫的《女訓》,收錄在其著作《武教全書講錄》的“子孫教戒”章中。在《女訓》中,他首先闡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女子道德教育不是一個個人問題,它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政治命運。“今世往往聞淫泆之婦,而至于貞烈之婦則寥寥乎絕響,然則禮儀雖聊存其舊,其義已泯沒。余常竊過憂之,以為亂亡之先兆。”[3](128)同時他還強調女子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夫婦乃人倫大綱,父子兄弟由此所生。一家興衰治亂之界,全賴于茲。故不可不先教誡女子。無論男子何等剛強秉直,恪守武士之道,婦人失婦道,則一家不治,乃至子孫之教亦廢絕,豈可不慎哉。”[3](129)“凡稟生于天地之間,無論貴賤,無論男女,不可使一人逸居,不可使一人無教,然后始可謂合于古道。”[3](129)吉田松陰雖然認為男女不論貴賤,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他也強調女子教育要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古道”。
為了保證女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吉田松陰建議設立女子學校[3](128-129),并且設計了一個女子學校的藍圖:“可于國中設一處若尼庵之所,號曰女學校,選士大夫之嬬婦數名,年四五十以上,貞潔素顯,通學問,能女紅者為女學校之師長,寄宿學校中。令士大夫女子,年八歲或十歲者,每日去學校,或依其愿許寄宿。專練習字,學問,女紅等事,教法要極嚴整。”[17](108)可以看出,他在女子學校教師的選擇、學生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設想。
在女子教育的教材方面,吉田松陰認為應“以柔順為用,以果斷為致”,兩者兼備才是最理想的教材。其中《武家女鑒》三卷甚佳,婦女讀之,無不受益。這本書由日本著名儒學家津阪東陽(1757—1852)所著,天保十一年(1840)正月刊行,分為三卷,其間還穿插著部分中國女性的故事。
吉田松陰還很重視婦女的言傳身教,他在給妹妹千代的信中強調了女性在教育十歲以下的幼兒時,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并且還應該進行胎教。具體而言,“但凡人之子,聰慧愚昧好壞,皆由父母教誨而養成。男子多受教于父親,女子多受教于母親。十歲以下的孩子不只是語言教育,還需有自己的言行示范給孩子看,就連胎教也不要放松,懷孕期間應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作為妻子應該孝敬公婆,應該崇敬神明,應該重視親族和睦”[17](108)。吉田松陰突出強調了女性對下一代的影響力。人的教育在于家庭,家庭的子女教育在于母親,由此可見重視女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吉田松陰作為日本幕末時期的思想家,深受中國儒學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始終銘記著時刻為君而生、為君而死的信念。他的教育思想影響著松下村塾的教育活動導向,也必然影響到每一個弟子的人生軌跡。他十分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強調道德至上,號召松下村塾的弟子獻身于“尊王攘夷”的大業。他在松下村塾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打破了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士庶共學。同時吉田松陰也重視女性教育,為女性教育設計了未來藍圖。但是,吉田松陰在教育中所提倡的“尊皇論”,認為國家的興衰盡在天皇,君臣關系才是“天下平”的關鍵,并提倡不論平民還是武士,都應隨時隨地竭力效忠天皇。吉田松陰的這些思想,在明治維新后持續發酵,成為后來日本侵略者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依據。因此,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吉田松陰的教育成果,取其精華,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