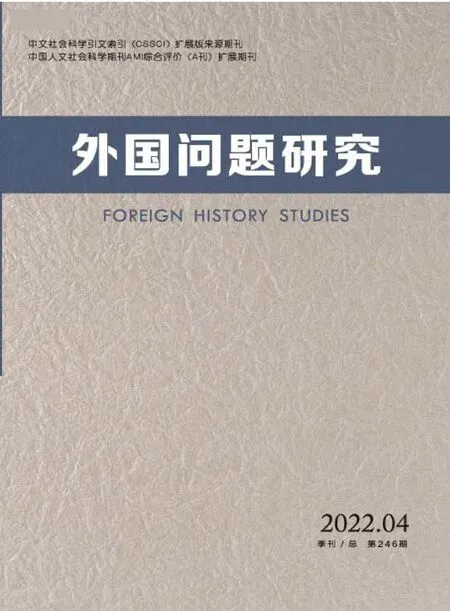阿根廷新左派對“第三世界”概念的闡釋
夏婷婷
(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444)
“第三世界”的概念起源于冷戰時期,在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下,許多發展中國家認識到自身處于殖民或新殖民的狀態,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第三世界”的概念成為他們團結起來的有力工具,也成為他們對世界秩序和地緣政治的新設想。1955年亞非國家舉辦的萬隆會議,從政治上定義了“第三世界”。相較亞非國家,拉丁美洲接受“第三世界”概念的時間更晚。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于19世紀初已取得了獨立,沒有參加1955年爭取民族獨立的萬隆會議,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加入不結盟運動。(1)Jaime Estévez, Crisis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y Tercer Mundo, México: CEESSTEM, 1983, p.27.隨著國際局勢尤其是美拉關系的變化以及古巴的積極推動,拉美國家于70年代紛紛加入不結盟運動。(2)高志平、肖曼:《冷戰時期拉丁美洲國家加入不結盟運動的歷程及影響》,《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6期。從這里,我們可以推斷出,拉丁美洲國家的地緣政治心態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變化,考察拉美的國家和社會團體對“第三世界”概念的闡釋與應用是理解這個過程的有效視角。
國內學界在研究拉美外交思想時,更多地關注外交家、著名思想家的對外戰略思想,主要內容是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獨立自主、拉美一體化思想或是反美主義,(3)洪育沂主編:《拉美國際關系史綱》,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徐世澄主編:《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孫若彥:《冷戰后不結盟運動與第三世界問題研究述評》,《理論學刊》2005年第7期;孫若彥:《獨立以來拉美外交思想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但是從社會群體角度和從歷史角度出發的研究較少。歐美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第三世界”概念起源和應用的考證,一般不涉及拉美。(4)對第三世界概念史的梳理,參見Erik T?ngerstad, “Between Metaphor and Geopolitic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the Third World,” in Helge Jordheim and Erling Sandmo, eds., Conceptualizing the World: An Exploration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pp.79-93;“第三世界”概念的起源,如Marcin Wojciech Solarz, “‘Third Worl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 Concept that Changed Hist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3, No.9, 2012, pp.1561-1573; 對概念的爭論,參見S. D Muni, “The Third World: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1, No.3, 1979, pp.119-128;對概念的使用,參見Vicky Randall, “Using and Abusing the Concept of the Third World: Geo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1, 2004, pp.41-53.拉美學界對“第三世界主義”(Tercermundismo)有零星的研究,更多的是針對以“第三世界主義”為名的運動或左翼組織的研究。(5)對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第三世界研究所的研究,參見Julieta Chinchilla, “El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73—1974),” Icono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No.51, 2015, pp.47-63.具體到阿根廷,有關于文化界知識分子群體對“第三世界”概念的接受和傳播的研究,(6)Germá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Vol.19, No.35, 2013, pp.211-228.也有針對以第三世界為名的機構和運動的單個研究,(7)Germán Alburquerque, Tercermundismo y No Alinea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urante la Guerra Fría, Santiago de Chile: Ediciones Inubicalistas, 2020.還有學者從情感層面解析阿根廷新左派認同“第三世界”的共同路徑。(8)Valeria Manzano, “Argentina Tercer Mundo: Nueva izquierda, emociones y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en las décadas de 1960 y 1970,”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54, No.212, 2014, pp.79-104.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從微觀層面考察阿根廷新左派中的不同群體基于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闡釋該概念的不同路徑。具體而言,將通過對其出版的雜志,如《聯結》(ElEnlace)、《基督徒與革命》(CristianismoyRevolución)、《第三世界人類學》(Antropología3erMundo)、《第三世界問題雜志》(Revistadeproblemasdeltercermundo)、《過去與現在》(Pasadoypresente)等進行文本分析來考察。本文借鑒了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思考和分析“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在阿根廷的流轉,在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團體中獲得的具體含義。
一、“第三世界”概念在世界和阿根廷的傳播
“第三世界”是冷戰時期的產物。1952年,法國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第一次將冷戰的美蘇兩極之間的欠發達的國家稱為第三世界國家(Tiers Monde),(9)這個說法模仿了法國歷史上的“第三等級”(Tiers état)的說法,Tiers比序數詞第三(Tróisieme)更加強調等級的高低,那相應,第三世界(Tiers Monde)是低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本意是聯合這些國家來對抗冷戰,并沒有質疑殖民制度。1955年舉辦的萬隆會議盡管沒有明確使用“第三世界”這個詞,但被普遍認為是“第三世界”的誕生地。1956年,法國人類學家喬治·巴蘭迪爾(George Balandier)把這個概念放到了社會科學中,強調反叛的地理、去殖民化的進程。隨著法農的《世界上受奴役的人》和薩特的《辯證理性的批判》出版和傳播,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法語之外的其他語言中廣泛傳播,左翼激進分子將亞非拉三大洲聯系在一起,作為解放運動的堡壘。(10)參見Erik T?ngerstad, “Between Metaphor and Geopolitic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the Third World”, pp.85-88; Cristopher Kal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Third World Decol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Left in France, c. 1950—19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在中國,“第三世界”這一概念在學界被認為是由毛澤東提出的全球地緣政治概念。毛澤東是這樣區分三個世界的:“我看美國和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國家。”“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拉美也是。”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是依靠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對抗第一世界的霸權主義。(11)羅時平、朱維紅:《關于第三世界概念和三個世界理論的考釋》,《晉陽學刊》1991年第5期;胡佳虹:《毛澤東“三個世界”思想綜述——作為一種戰略和一種理論》,《蘭州學刊》2010年第1期。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定義與西方國家存在差異,即不按照國家制度來劃分,而是基于反帝和民族解放的共性。
拉丁美洲國家相比亞非國家較早取得獨立,但是殖民時期遺留下的思想,依然在各個層面阻礙著拉美國家實現真正的獨立。20世紀中葉之前,拉美國際戰略的參照系只局限于歐美,與亞非的聯系較少。20世紀中葉,拉丁美洲國家尤其是阿根廷這樣的地區大國比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更為富裕、城市化程度更高,再加上其主導文化又是西方文化的分支,因而更為抗拒“第三世界”的理念。它們靠近和最終加入第三世界陣營的需要一個心態的轉變,也需要通過想象和創新來找到合適的路徑。
拉美左派知識界找到了一個可行的理論路徑。冷戰時期,拉美經委會(CEPAL)、 拉美社會學系(FLACSO)、拉美社科委員會(CLACSO)等機構的成立帶來了社科的繁榮,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發展,讓拉美國家開始研究自身的發展狀態,意識到發展的不足。這些機構中的知識分子也逐漸思考出“依附論”這樣的解釋框架,將拉美的不發達歸結于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依附性的邊緣地位,強調如果不去除這種依附,就很難得到真正的發展。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拉丁美洲國家處于一種“新殖民”的狀態,與亞非殖民地國家之間有了共同的聯系,需要通過第二次民族解放運動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
另外,拉美國家中也出現了靠近“第三世界”的領袖國家——古巴。1959年爆發的古巴革命真正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讓拉美國家看到希望,革命可以在拉美以不同于蘇聯共產主義模式的面相出現。古巴的國際主義精神推動其制定向外輸出革命的政策,協助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開展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軍事、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援助。(12)Germán Alburquerque, “Cuba en el Movimiento de Países No Alineados: el camino al liderazgo. Causas y motivaciones. 1961—1983,” Caravelle: Cahiers du monde hispanique et luso-brésilien, No.109, 2017, pp.179-193.1966年,古巴主辦了“三大洲會議”,隨后成立了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他們定義的“三大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范圍非常類似。格瓦拉在會上發表著名的宣言,號召創建“兩個、三個、許多個越南”,他撰寫的文章中強調“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是一個整體,它們的經濟力量被帝國主義行動扭曲了”。(13)Che Guevara, “Táctica Y estrategiade la revolución latinoanerican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1, Nov,1968, pp.19-25.古巴推動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加速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英雄形象和理念在拉美地區的廣泛傳播。(14)Aldo Marchesi, Hacer la revolución. Guerrillas latinoamericanas de los 60 a la caída del Muro,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2019, pp.71-104.
除古巴外,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魯等國也或多或少地踐行第三世界主義的外交政策。墨西哥人阿爾瓦羅·法利亞斯(Alvaro de Farías)于20世紀50年代在拉美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這個詞匯。(15)Ezequiel Martínez Estrada, Diferencias y semejanzas entre los países de la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90 (1962), p.16.1974年,墨西哥埃切維里亞總統起草《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Carta de Derechos y Deberes Económicos de los Estados),嘗試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75年,拉美25國通過《巴拿馬協議》,正式成立“拉丁美洲經濟體系”。智利的阿連德總統推行社會主義改革,與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建交。
具體到阿根廷,學者赫爾曼·阿爾布爾科科(Germán Alburquerque)將這一概念在知識分子階層接受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1—1967年,塞爾吉歐·百谷(Sergio Baigu)是阿根廷第一個引入這個詞匯的學者,他宣布阿根廷也位于這一陣營。(16)Sergio Bagú, Argentina en el mundo, Buenos Aires: FCE, 1961, p.175.1964年開始,許多與“第三世界”相關的出版物出現;(17)雜志《第三世界之聲》(Voz del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之書》(Libros para el Tercer Mundo)、《拉美問題與第三世界》(Problemas Latinoamericanos y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的事實》(Hechos del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的人》(Hombres del Tercer Mundo)等等。第二階段是1968—1974年,布大的第三世界研究所組織了第三世界電影委員會,阿根廷的《燃情時刻》(Lahoradehorno)電影宣告了“第三電影”(Tercer Cine)的誕生;(18)具體內容可參見魏然:《第三的意味:拉丁美洲“第三電影”理論及其播散》,《當代電影》2020年第12期。第三階段,1975—1987年,該概念遭到批判,逐漸沒落,在民主轉型時期,這個術語沒有再興起。(19)Germá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No.19, 2013, pp.211-228.從這個傳播過程的分期可以看出,阿根廷對這一概念的接受對象主要是社會團體,沒有上升為國家政策。
實際上,早在40年代,民眾主義領袖庇隆執政后就提出的“第三立場”(Tercera Posición)的國際戰略,反對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和教條國際馬克思主義,意圖在美蘇爭霸過程中保持中立,維護國家的利益。但是,庇隆的民眾主義政策造成了政治的極端化,“第三立場”并沒有得到左派知識分子的推崇和認可,反而淹沒在了稱庇隆政府為法西斯的反對聲中。1955年,庇隆流亡之后,部分左翼知識分子將庇隆主義看作民族解放的力量,庇隆派中的左翼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兩股力量通過第三世界的理念匯合。(20)Juan Perón, “La nueva generación debe continuar la lucha,” in Roberto Baschetti, ed.,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p.258-259.庇隆本人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他認為許多爭取民族解放的國家都是第三世界,而且民族解放的實現需要聯合起來。“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實現解放,但如果我們不加入第三世界,這一解放便無法得到鞏固。”(21)“La conferencia de presidentes de Punta del Este,” Fragmento de América Latina, ahora o nunca, Montevideo, 1967.
庇隆支持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劃歸到蘇聯式教條主義的行列,認為中國提倡的“第三世界”是可以包容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毛澤東以國際社會主義為基礎提出的反對剝奪和殖民的共同事業,可以與不同的社會民主制度共存。民族主義不一定必須是社會主義的,兩者共同的目的都是民族和人的解放。”(22)Roberto Baschetti,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353.庇隆政府非常欣賞中國獨立自主的國際政策,并在不結盟運動中,重申阿根廷的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政策,同時絕不允許外國勢力對拉美經濟和政治的干預。(23)“Carta de Peron a la Conferencia en Algería del Movimiento No Alieamiento, septiembre de 1973,” in Roberto Baschetti, ed.,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571.
但可惜的是,庇隆流亡期間提出的“第三世界”理念沒有得到充分實施,僅在短暫的第三任期內(1973—1974年)得以部分推進,隨后的軍政府(1976—1982年),也主動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交往,但主要是基于實際經濟利益做出的實用主義決定,與意識形態無關。總體而言,20世紀大多數中右翼政府在外交上沒有真正認同第三世界,還沉浸在自己是“第一世界”強國的美夢之中。(24)參見Mario Rapoport, Histori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Octubre, 2015.左翼政黨執政期間,外交政策靠近第三世界國家,而中右翼政黨執政期間,會立刻調整這一政策。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概念在阿根廷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應用,但是,“第三世界”理念在阿根廷甚至整個拉美是一種分散性的思想,不成系統,同時,這一概念也遭到了諸多的批判和抵制,難以長期實施,也無法形成長期戰略。(25)反對第三世界立場的主要是自由派,如阿根廷社會學創始人基諾·赫爾曼尼(Gino Germani)在著作《現代化的社會學》(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中提醒,把阿根廷列為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是錯誤的,他認為阿根廷算是“中產階級”國家。他批判這些大學生知識分子享受了現代化的紅利,還依然將國家定位為第三世界國家,是不道德的。可參見Gino Germani, 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estudios teóricos, metodológicos y aplicados a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Paidós, 1971, pp.12-14.也有部分傳統左派,胡安·何塞·塞布雷利(Juan José Sebrelli),他給“第三世界”貼上了“資產階級神話”(Mito Burgués)的標簽,認為這個說法很容易被理解成為冷戰兩極中的一個中間立場,從而掩蓋阿根廷的主要矛盾,即反帝國主義和反寡頭,他相信解決辦法在于國際無產階級的聯合。可參見Juan José Sebrelli, Tercer Mundo, Mito burgués,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e, 1975, pp.32-34,轉引自Germa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Vol.19, No.35, 2013, pp.211-228.可見,對這一概念的接受與理解與個人和團體的政治立場和利益息息相關。在認同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新左派中,這一概念成為新左派各個團體嘗試團結起來的工具之一,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即便如此,在新左派內部,不同的政治立場也影響了概念闡釋的路徑。
二、阿根廷新左派對“第三世界”觀念的闡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軍政府與有限民主的政府交替統治下,阿根廷的政治左翼、社會科學、先鋒藝術、文學批評等各個領域等都開始關注現代化的陰暗面,要求變革。(26)參見Leticia Viviana Albarracín, “Arte y Política: El caso del ‘Tucumán Arde’ (1968—1969),” Revista nuestr América, Vol.1, No.1, 2013, pp.102-117; Javier Campo, “Filmando teorías políticas: dependencia y liberación en La hora de los hornos,” Política y cultura, No. 41, 2014, pp.65-88.歐化的傳統左派中有部分青年接受了新思潮,對庇隆主義、古巴革命、民族解放運動充滿好感,逐漸從中分裂出來。同時,庇隆主義群體中的一部分青年,也開始認同古巴革命和世界其他的民族解放運動,學習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27)Silvia Sigal, Intelectuales y poder en la década del sesenta, Buenos Aires: Puntosur, 1991, p.193.天主教中受到革新天主教影響的教士和平信徒的政治立場也開始向左轉。馬列主義左派、庇隆主義左派和神學左派匯合成“新左派”。阿根廷學界用“新左派”來指稱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傳統左派中出現的不認同蘇聯道路的異見派,以及認同武裝革命的民族民眾主義派和宗教人士。(28)夏婷婷:《拉美新左派的特殊性——以“全球60年代”中的阿根廷為例》,《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阿根廷新左派有許多共同點,其中之一就是具有“第三世界”的共同情感,這些情感的產生有一個共同的路徑,即義憤。新左派青年接觸這些現象的路徑是“新旅行”(Neo-turismo),(29)這種新旅行有別于休閑度假式的常規旅游,是深入偏僻省份的農村觀察工人,可參見Félix Luna, “El neoturismo,” Clarín, 9 de febrero de 1970.參觀城市貧民窟或去東北部和西北部省份參觀貧困的鄉村,通過與大城市生活的強烈的對比,產生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和內疚。這樣的情感框架展現了一種不可估量的動員能力。阿根廷白人歐化的形象越是鮮明,民族自豪感越強,這些新左派青年在見到貧困時的沖擊就越大。他們在世界性的革命與解放浪潮的影響下,號召立即解決這些貧困與不公的現象,而實現民族解放是唯一的途徑,在這點上,阿根廷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站在同一條戰線上。(30)Valeria Manzano, “Argentina Tercer Mundo: Nueva Izquierda, Emociones y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de las décadas 1960 y 1970,” pp.79-104
盡管義憤帶來了新左派對阿根廷“第三世界”的身份和民族解放需求的共識,但是新左派中不同的派別對“第三世界”的接受路徑和側重點也有細微的差別。在展開論述之前,需要說明三點:首先,這三個派別闡釋 “第三世界”的路徑多有重疊,并不能完全徹底地區分開來,這里僅強調其側重不同;其次,盡管神學左派中很多人最終轉向庇隆主義左派,但兩者在理論和思想背景以及社會動員范圍上是可以區別開來的;再次,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社會群體,大多沒有參與執政,他們的第三世界國際戰略基本沒有在國際關系中得以實踐,但其影響卻延續到21世紀的左翼政府。
(一) 神學左派:貧困與革命路徑
20世紀60年代,阿根廷部分青年教士受到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的革新思想的影響,簽名支持《第三世界的十八位主教的信函》,贊同教皇保羅六世的通諭《為了人民的進步》,從“窮苦的人民”和“人民的窮苦”角度出發,重新審視教會的作用以及與人民的關系。“所有貧困的國家,都意識到自己是剝削的受害者,本信函給所有受苦的人、為正義而戰的人以鼓勵,這是實現和平的必要條件。”(31)“Mensaje de 18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p.221-230.從這點可看出,進步教士主要強調第三世界的貧困,強調救助因剝削和貧困而受苦的人。支持這封信函的阿根廷進步教士發起了“為了第三世界的教士運動”(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他們被稱為“第三世界教士”。
雖然名為“第三世界教士”,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國內的貧困問題,因而對第三世界的定義非常籠統,沒有做更為詳細的區分。“第三世界國家面對的沖突不只是東西方的沖突,而且是三個主要的群體之間的沖突:西方富裕的強國,兩個共產主義大國,最后是第三世界國家,尋找如何脫離大國的控制,自由地發展,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獨立和自由。”(32)“Mensaje de 18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221.隨后,該運動在1969年發布的文件《我們的基礎共識》(Nuestras coincidencias básicas)中闡明了他們對第三世界的看法:“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有一些國家(特別是亞非拉國家)和一些國家的某些部門,遭受了不公的境遇,遭受了饑餓、教育缺失、不安全、邊緣化等。這一現狀導致他們被稱為第三世界……我們,基督徒和基督的使徒,我們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為其需求而服務。”(33)“Nuestras coincidencias básicas,”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74.
隨著部分神學左派成員思想的激進化,其出版的雜志《基督教與革命》從最初幾期的神學理論開始轉而論證第三世界革命的必要性。(34)《基督教與革命》由神學院學生胡安·加西亞·埃洛里奧(Juan García Elorrio)于1966年創辦,最初是從神學角度論證革新和革命的必要性,后期成為聯結各種意識形態的游擊隊的平臺。對此雜志的研究,參見Esteban Campos,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El origen de Montoneros: violencia, política y religión en los 60, Buenos Aies: Edhasa, 2016.雜志第一期在總結第三世界的悲劇時,指出了拉美的定位與特點,“拉美與第三世界國家非常親近,但拉美也有天主教基底”。(35)C.James Snoek, “Tercer Mundo: Revolución y Cristianism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septiembre 1966).第六—七期合集中的《第三世界主教的宣言》一文,強調第三世界的寬闊地域包括“拉美國家如哥倫比亞、巴西與大洋洲、中國、再到撒哈拉、南斯拉夫、中東”一樣,“福音的光照揭示了這些地區同樣的問題,窮人意識到被壓迫,認識到自己是受害者。上帝不想看到這個世界上永遠有窮人”。(36)“Manifiesto de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 (abril 1968), pp.42-46.雜志從貧困和壓迫的角度來定義阿根廷和第三世界,強調阿根廷的天主教底色,中國和中東這樣的非天主教國家因其貧困和壓迫也被列入第三世界。
該雜志對阿根廷貧困現狀的揭示主要集中在北部圖庫曼、查科、薩爾塔等省份,將貧困歸因于這些地區的制糖業、伐木公司對人民的殘酷剝削,控訴外國資本對當地經濟和人民生活的破壞。(37)“Informe de la agrupación de estudios sociales de Córdob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0 (oct. 1968), pp.8-12; “Los hecheros,”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 8 (jul. 1966), pp.3-13.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外部強加的依附狀況導致的。這些特點由兩個層面的因素造成,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即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衛星國),另一方面是內部因素,國家內部集團的關系(地區、階級)”。(38)“Teología: un análisis nacional interpretado por la visión de Medellín,”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4 (abr 1969), pp.25-27.這個內部集團是與外部利益勾結的,即“阿根廷國內軍政府獨裁,代表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剝削人民,剝奪財富”。在此基礎上,雜志將阿根廷看作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國家,認為阿根廷應該加入反帝反資的大陸革命進程。(39)“Estrategia política del peronismo revolucionari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3 (abril 1970), pp16-18.
神學左派認可,針對體制性暴力可以還以暴力,從這點上與第三世界站在了一起。“阿根廷處在了戰爭的腳下,但這不是內戰,而是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發起的對制度性暴力和新殖民制度的抗爭。那些用武力來壓制混亂和暴力的人,應該明白,勞動人民最后會以全部和絕對的方式收回權力。”(40)“Quién impone la violenci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5(sep.1970), p.2.這也就是神學左派遭到政府鎮壓的主要原因。此外,該雜志除了論證阿根廷與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具有革命的需求,還論證了共同革命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這樣,革命才能有效。“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我們明天就可能與今日越南和其他解放革命中的國家擁有一樣的需求。任何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打擊都是有效的。”“只有與被壓迫的民族共苦,最后才能同甘。”(41)“Escriben los guerrilleros de Salta, desde la cárcel,”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8 (julio 1969), p.34.
(二) 庇隆主義左派:文化殖民路徑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庇隆主義左派舉起了庇隆早在40年代就提出的“第三立場”的大旗,將其改造為“第三世界”立場。庇隆在流亡期間和掌權期間對該立場的使用有一定的區別。流亡期間(1955—1973年),他用此概念來團結各方力量,以期達到回國執政的目的。在回國后第三次執政期間(1973—1974年),除了在外交政策實踐上靠近了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內政策沒有更多地實施反殖民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理念,而是采取調和階級矛盾的保守做法。庇隆主義新左派中有激進群體想要開展階級斗爭,但終遭到庇隆本人和庇隆主義右派的排擠。因此,大量庇隆主義新左派加入第三世界的路徑只限于在文化上開展去殖民化的斗爭。
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第三世界研究所(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嘗試在教育體系中實現去殖民化,曾出版研究亞非國家的大量研究論著,推動了第三世界電影行動,如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電影方面的交流,舉辦各國電影界對談,阿根廷曾邀請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其他拉美國家參加,討論各國去殖民化的經驗、分析各國現實、復興民族文化遺產、電影的制作、發行和教學等。該群體一方面為人民攝制電影進行宣傳動員,另一方面為阿根廷民眾播放來自第三世界的電影。(42)Julieta Chinchilla, “El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73—1974),” pp.47-63
阿根廷社科領域也興起了“第三世界人類學運動”(Antropología del Tercer Mundo),這里的“人類學”泛指所有的社會科學。該運動旨在去除知識界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現代化理論,推動課程的本地化和民族化,給學生教授阿根廷屬于第三世界的理念。(43)Gonzalo Cárdenas, “El movimiento nacional y la Universidad,”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No.3 (noviembre 1969), pp.41-60.該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是庇隆主義左翼,因此反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認為唯一可行的聯合只有在為解放而斗爭的依附性國家之間發生。(44)“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No.2 (mayo 1969), p.2.
他們出版的同名雜志第二期專門討論“第三世界”的概念,強調“第三世界”指的是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不指這些國家的政府。“第三世界”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處于解放斗爭的某一階段(哪怕周圍沒有斗爭的環境),人民共同的敵人是殖民中介;二、獲得獨立的但在政治經濟上依然在爭取獨立的國家,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如阿爾及利亞;三、形式上獨立的但在政治經濟上依然處于依附地位的國家如拉丁美洲國家和一些非洲國家,他們都是遭受“新殖民”的國家。(45)“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pp.1-2.
值得注意的是,庇隆主義新左派的第三世界觀與毛澤東的看法最為相近,但他們在理論上也沒有完全處理好中國的位置。雜志中一篇文章認為,“在世界的兩極中間,有兩個群體,一個是殖民或新殖民的國家,一個是與兩極經濟緊密相連的發達國家,即西歐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除外),他們也參與對前者剩余價值的壓榨”。(46)“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pp.2.作者特意強調中國除外,這充分證明了庇隆主義新左派不將中國歸為毛澤東所說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是遭受完全剝削和處于依附狀態的群體,即上述第一個群體。作者強調,第三世界不是第三立場,不是對立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而是國際層面的被壓迫者為了對抗壓迫者形成的陣線,第三世界國家有團結起來實現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愿望,在這點上,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渴望是一樣的,但它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它不屬于第三世界國家。這里出現了一個論證上的空白,庇隆主義新左派既沒有將中國看作第一、二世界國家,也沒有將中國置于第三世界之內,出于對中國不了解或是理論上的格格不入,而將中國懸置了。
與下文要提到的馬列左派含混不清的立場相比,庇隆主義左派更為明確地將蘇聯列為兩個霸權之一。同時,他們贊賞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對中國是否歸屬第三世界的看法自相矛盾,認為這并不是阿根廷的道路,民族社會主義才是阿根廷可能的發展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庇隆本人雖然提到過社會主義,但在他回國執政后實施的政策與社會主義路線關系不大,還是注重調和勞資矛盾,在這點上,庇隆主義新左派與庇隆的意見是不一致的,這也導致庇隆主義新左派的“第三世界”戰略沒能在庇隆回國短暫執政時期得以完全實踐。
(三)馬列主義新左派:依附理論路徑
馬列主義新左派是從傳統左派中分裂出來的,支持中國、支持古巴革命、親近庇隆主義的左派群體。馬列主義新左派知識分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了大量的文化雜志,占據了阿根廷文化界的重要地位。這些雜志主要刊登文學批評、介紹歐洲的新理論新思想、對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也有很多的介紹和分析,但這些雜志很少采用“第三世界”這一術語,究其原因,大概是三個世界的劃分方法涉及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排斥。在馬列主義新左派的雜志中,以第三世界為名的有《第三世界問題雜志》。雜志第一冊的卷首就強調將阿根廷的定位列入第三世界陣營,第三世界是遭受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的國家,并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沖突在發生變化,但是對三個世界是如何劃分的問題進行了模糊處理。
馬列新左派知識分子因其豐富的理論知識背景,較為容易從理論角度與第三世界產生共鳴。他們向第三世界靠攏的第一條路徑是反殖民的理論,馬列新左派《書籍》(loslibros)雜志中有文章分析法農的理論,認為法農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和歷史決定論,反對線性的歷史進展,強調第三世界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層的共同背景,強調革命實踐,他認為“流氓無產階級”這個說法是激起革命意識的一個有效理論,這一階級的組織是能將理論落入實踐的唯一中介,而革命只有在搞革命的過程中形成,甚至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作者認為在這點上與毛澤東和葛蘭西相似。(47)“Franz Fanon: Alienación y violencia, más allá del tercer mundo,” Los Libros, No.13 (noviembre 1970), pp.24-25.關于這一點,作者沒有考慮發達國家的流氓無產階級與第三世界在理論上的矛盾。
著名的左派文化雜志《過去與現在》中《第三世界的問題》一文,對第三世界概念進行了專門的討論。文章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群不同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都遭受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之苦。這些問題阿根廷都有,阿根廷還有一些自己的特點,例如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共存。(48)Héctor N. Schumcler, “Problemas del Tercer Mundo,” Pasado y Presente, No,4 (enero-marzo 1964), pp.284-290.這里第一次強調了國家制度問題。同時,該雜志曾多次贊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強調各國應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
馬列新左派進入第三世界的第二條路徑是依附論。《書籍》雜志曾介紹岡德·弗蘭克(Gunder Frank)《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一書的理論,將拉丁美洲國家的不發達歸于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揭示了統治霸權即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集中、對本地工業的禁止或摧毀等等,認為只有打破這些舊制度,才能構建新社會。作者在開篇就提到,自從發現了“第三世界”以來,發展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討論,這一問題需要置于全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制度來討論,而不能只討論單個國家。從這點上說,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國家遭遇類似的發展問題和依附問題,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49)Hobert A. Spelding, “Gunder Frank: Capitalismo y Sub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Los Libros, No. 17 (marzo 1971) p.18.
在當時盛行的兩派依附理論中,馬列主義新左派更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50)拉美依附理論分為兩個流派: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將外圍國家的經濟依附擴大到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因此反對改良,倡導激進的社會革命。參見孫若彥:《獨立以來拉美外交思想史》,第119頁。強調拉美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處于一種依附性的地位,打破依附的地位、通過革命實現解放是第三世界共同的目標。他們認為,只有“民族解放后才能按人民利益組織社會,所以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是一體的。我們要與社會主義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階層一起。第三世界并不是區別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未來還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第三世界人民在反帝斗爭中最有效、最有活力,具有全球的影響力,我們要將阿根廷革命加入世界革命的浪潮,但我們也反對普世主義(Cosmopolita)的革命觀”。(51)“Por qué tercer mundo?” Problemas del Tercer Mundo, No.2 (diciembre 1968), pp.83-84.綜上,馬列主義新左派在三個世界的劃分界限上比較模糊,究竟是否按照國家制度劃分意見不一。他們的共識為,堅持認為阿根廷需要通過實現社會主義來擺脫殖民與依附,同時,這類革命還需要聯合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這體現了他們思想中長期存在的國際主義思想。
結 語
通過分析阿根廷新左派中三個群體對第三世界的論述,我們發現他們對“第三世界”的闡述路徑存在共同之處,也能分辨出他們不同的側重點:神學左派主要通過揭示貧困與體制性暴力,意欲幫助第三世界窮人來改變這些剝削和壓迫;庇隆主義左派主要通過揭示文化殖民、從民眾的知識結構上的去殖民化;馬列新左派主要通過論述反殖民和依附論等理論,加入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浪潮。
三者側重點的不同源于他們不同的知識背景和政治立場:神學左派以革新派教士為主體,通過社會網絡向平信徒青年傳播新思想,這些新思想主要來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和解放神學理論,強調要和窮人站在一起,優先揀選窮人,除了窮人之外再無救贖,第三世界是窮人最多的地方,一直遭受體制性的暴力,需要實現解放。從這一點上講,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陣營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更多考慮的是國內的壓迫性體制的問題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罪惡,沒有涉及美蘇對抗等國際戰略問題;庇隆主義新左派聽從庇隆的教導,接受了庇隆和庇隆派知識分子將“第三立場”改造成“第三世界”的做法,但受限于庇隆第三次執政時的保守立場,無法實施徹底的反殖民革命,只能從文化領域開展去殖民的批判和實踐;馬列主義新左派以知識分子居多,容易接受國際上的新思想、理論和分析方法,從反殖民思想和依附論等出發,強調人民遭到的壓迫、國家經濟上遭受的結構性的剝削等等,堅信阿根廷的出路是走向社會主義。他們的知識背景導致他們更為國際化和理論化,他們的“第三世界”立場更為強調國際戰略的設計,較少涉及國內具體的斗爭方案。
阿根廷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新左派對“第三世界”的理解有一致性也有不同的側重,三者中僅有庇隆主義新左派較為接近權力。庇隆短暫執政期間雖然采取了靠近第三世界國家的做法,但因國內的矛盾過于尖銳,“第三世界主義”的國際戰略也無法得以較好實施。20世紀六七十年代,除了古巴曾向外推廣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及通過不結盟運動反抗美國的霸權,“第三世界”思想在其他拉美國家較少有機會作為政府的整體性國際戰略得以實踐。“第三世界”的思想更多地應用于政界和知識界,來解決本國和地區的問題,這與歐洲同時期的激進左派想要領導全球斗爭的想法相異,與不結盟運動中的領袖國家的想法也不同。
蘇聯解體之后,“第三世界”這一概念也陷入了沒落。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更為自由,殖民的面相也在跨國資本的掩蓋下日益模糊。各國日益意識到,國家內部也存在貧富的差距,一個發達國家的落后地區不見得比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地區好,有些曾經的貧困國家也趕超了上來,成為富裕的國家,因此,難以用“第三世界”來囊括今日這個松散的多樣的發展中國家聯盟,在這個意義上,第三世界走向了消亡,甚至有被“南方國家”的說法取代的趨勢。
但是,“第三世界”的概念和理念曾經在團結發展中國家對抗帝國主義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其中蘊含的思想在今日依然有效。只要殖民主義沒有消失,只要有壓迫和不公存在,就會有第三世界的話語市場,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就有團結起來的必要。今日,中國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少拉丁美洲國家民眾甚至左翼知識分子在心態上會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聽從美國的教唆,將中國的投資行為視為“新帝國主義”,因此,重審“第三世界”的概念,研究“第三世界”概念在拉美的流變,對今日中拉關系的提升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可以為應對美國的“新冷戰”戰略帶來的新挑戰提供更多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