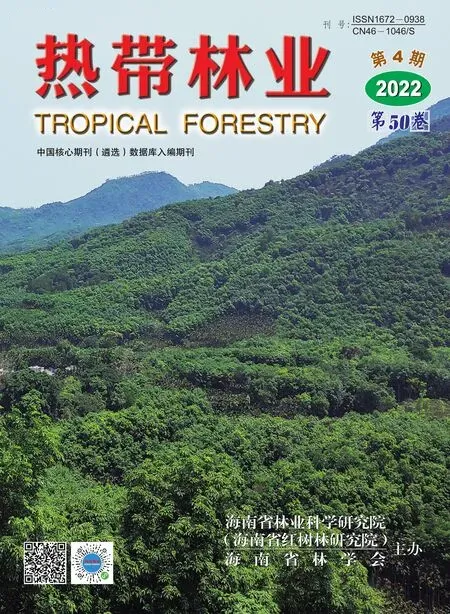熱帶油茶種質資源綜述
劉進平,周揚,胡海燕,吳文嬙,胡新文,賴杭桂
海南大學熱帶作物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油茶是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屬(Camellia L.)一類木本食用油料樹種的總稱,山茶屬是山茶科中最大的屬。油茶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栽培歷史。作為中國特有的木本油料樹種,油茶植物因種子含油率較高,與油橄欖、油棕、椰子并稱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與烏桕、油桐和核桃并稱為中國四大木本油料植物。茶籽油具有合理的脂肪酸構成、豐富的營養成分,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E和山茶甙等特定生理活性物質。因此,除食用和烹調功能外,還具有極高的營養和醫療保健價值,是優質保健食用油和高級天然化妝品原料。尤其是其主要成分為油酸和亞油酸為主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占90%以上,比被譽為“液體黃金”的橄欖油還高出約7%,故有“東方橄欖油”的美稱[1-3]。
1 熱帶地區主要油茶栽培種
油茶主要分布于中國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此外,在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以及日本等國也有少量分布。其中,湖南、江西、廣西3省區加起來面積303.33萬hm2,占全國油茶總面積的75.8%,而其中又以湖南栽培面積最大,占油茶總面積的40%[1]。世界上油茶屬有120余個種,中國約90個種,主要栽培種有普通油茶(Camellia oleifera Abel.)、小果油茶(Camellia meiocarpa Hu.)、越南油茶(Camellia vietnamensis Huang)、攸縣油茶(Camellia yuhsienensis Hu)等10多個種,其中中國現有油茶林中的98%為普通油茶(C.oleifera)[2]。
根據油茶栽培區域的生態環境特點,可以將油茶栽培區劃分為西南高山區、華南丘陵區、華中華東丘陵區、北部邊緣區4個生態類型區。其中,華南丘陵區(該區北界自廣西百色經廣東英德到福州一線。包括臺灣北部、福州以南沿海、廣東南部、雷州半島、海南島北部及廣西南部等低山丘陵)屬熱帶季風濕潤氣候性質的南亞熱帶。華南丘陵區主要栽培的是窄生態幅物種如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廣寧紅花油茶(C.semiserrata Chi.)、博白大果油茶(C.gigantocarpa Hu.)、宛田紅花油茶(C.polyodonea how ex Hu.)[3]。
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是該區最重要的油茶栽培種,樹體高大,生長快,性喜夏熱冬暖和多雨高溫氣候,適合在南亞熱帶低海拔地區[2]。越南油茶在高州市、陸川縣一線以南能正常開花結果,自此往北移,豐產表現越來越差,直到在長江流域不能開花結果。因此,越南油茶適宜于廣東省雷州半島、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和海南省種植。該種因為在油茶中果實最大,因而現在普遍稱其為大果油茶。由于該種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陸川縣和廣東省高州市一線以南的華南油茶產區廣泛種植,因此又稱華南油茶、陸川油茶、高州油茶和大果油茶,是中國繼普通油茶和小果油茶之后的第三種常見油茶造林用種[4-5]。
普通油茶(C.oleifera)屬寬生態幅物種,在中國亞熱帶的南、中、北三個氣候帶都有廣泛的分布和大面積種植,在該區也有分布,但生長不及北部[3]。小果油茶(C.meiocarpa)主要分布于福建、江西、廣西、湖南、貴州、廣東及浙江等省區,栽培面積及產量僅次于普通油茶,適于在中亞熱帶及北亞熱帶南部地區中溫暖氣候條件下生長[3],該區也有少量引種種植。
此外,近年來又報道的一個適合在華南地區栽培的短柱茶組新種——香花油茶(C.osmantha)。該種為灌木,花白色,微有香氣。其苞被不分化為苞片和萼片,多數10~12枚,花瓣6~8枚,均易脫落;雄蕊長短不一,大部分分離;花柱短,基部連生,先端分離,與短柱茶組特征一致。新種花有香氣與窄葉短柱茶C.fluviantlis Hand.-Mzt.接近,但前者葉常為倒卵形,具尾尖,后者葉狹披針形,漸尖[6]。華南地區主要油茶物種中,香花油茶與其它油茶相比,長勢迅速、花芽數量多、果實產量高、抗逆性強。不同物種的生長量依次為:香花油茶>陸川油茶(C.vietnamensis)>廣寧紅花油茶(C.semiserrata)>博白大果油茶(C.gigantocarpa)>普通油茶(C.oleifera)>南榮油茶(C.nanyongensis)>宛田紅花油茶(C.polyodonta)>小果油茶(C.meiocarpa)[7]。
2 海南油茶種質資源
海南島種植的越南油茶可能引自廣東省高州市,故此在海南民間亦稱其為高州油茶。海南油茶種植的歷史至少有500多年歷史,《正德瓊臺志》(明正德十六年,即1521)就有記錄。海南人習慣稱越南油茶為海南山柚[8]。海南油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即解放初期的發展階段。20世紀60~70年代期間,在政府的主導下作為主要經濟作物在海南中、北部種植,如屯昌縣、澄邁縣、文昌縣、瓊山縣、臨高縣、儋縣、定安縣和瓊中縣均有栽培,其中以屯昌縣的烏坡、南呂、新興、大同,澄邁縣的中興、仁興、加樂、石浮,文昌縣蓬萊,瓊山縣甲子栽培較多[7]。(2)第二階段,即砍伐萎縮階段。20世紀80~90年代因經濟效益不高,被大面積砍伐,用于種植橡膠、檳榔等其它經濟效益相對較高的經濟作物。(3)第三階段,即復興階段。2000年后隨著油茶籽油價格上升,油茶林種植面積迅速擴大[9]。對海南油茶資源分布與林分進行實地調查發現,海南的油茶包括野生資源與栽培種,主要分布在9個市縣38個鄉鎮,總面積約1167.3hm2。油茶主要分布在瓊海市的石壁、中原、陽江、會山、龍江和大路鎮(包括東紅農場),定安縣的嶺口(包括中瑞農場)、翰林和龍湖鎮,文昌市的錦山、潭牛和蓬萊鎮,海口市的三江、甲子、石山和永興鎮,臨高縣的皇桐、和舍、南寶和多文鎮,澄邁縣的文儒、加樂、中興和仁興鎮,屯昌縣黃嶺、坡心、新興和烏坡鎮,瓊中縣的灣嶺、長征和黎母山鎮,五指山市的通什、南圣、暢好和水滿鄉[10]。經初步鑒定,海南油茶資源為越南油茶、普通油茶和小果油茶,屬于“寒露籽”型品種。其中栽培最為廣泛的是普通油茶。近年來,在海南五指山等地還引進了紅花大果油茶長林1號、長林4號、長林40號。據《中國植物志》記載,海南島800m以上原始森林中有普通油茶原生種。《海南植物志》《海南島作物(植物)種質資源考察文集》《海南及廣東沿海島嶼植物名錄》均有記載,海南島分布有普通油茶野生資源。分析認為,海南島擁有較為豐富的油茶資源,是普通油茶的原產地。油茶在海南島的栽培歷史悠久,是海南島的傳統植物資源[10]。15年以上林分調查結果表明,海南油茶主要散生于橡膠、檳榔或次生灌木叢林下和林緣,較少為坡地純林。絕大部分的油茶林處于野生或半野生狀態。同一林分不同植株間存在多樣的葉片和果實形態,地徑和產量也參差不一[10]。
海南各縣市都有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油茶樹。定安、澄邁、屯昌和瓊海的部分地區保存有林齡較長的油茶林,其中澄邁縣現有老的油茶林最多,最大植株地徑達150cm[10]。據植物標本記載,萬寧市的興隆、大洲島和銅鐵嶺,保亭縣的牛角嶺以及吊羅山、尖峰嶺和霸王嶺等地區也有零星分布[10]。據原海南省林業廳組織,海南大學、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椰子所、海南省農業科學院共同完成的《海南省油茶產業調查報告》(2016年),海南省油茶種植面積4036.92hm2,主要分布在7個市縣,其中瓊海市1000.27hm2、屯昌縣795.22hm2、澄邁縣662hm2、五指山市425.33hm2、瓊中縣358.13hm2、定安縣323.33hm2、海口市236.6hm2,以上7個市縣占全省油茶林種植面積的95%。全省有666.67hm2以上的海南油茶老樹林處于野生或半野生狀態。在澄邁縣文儒鎮岸嶺村、屯昌縣南坤鎮石銀嶺村、定安縣龍湖鎮石井村等地也發現了一些成片的野生林,在野生林和老林中也發現了一批大樹資源,如瓊海市陽江鎮中酒村的6棵“油茶王”,基徑50cm~89cm;屯昌縣南坤鎮石銀嶺村路邊的山柚林中有數十株基徑50cm~68cm;基徑最大的油茶在澄邁縣中興鎮,基徑150cm,樹齡數百年以上。海南油茶老林分布共有61處,主要分布在7個市縣。
3 海南油茶新種的鑒定
海南本地茶油當地人稱為“山柚油”,一直被認為品質優異,呈金黃色,不飽和脂肪酸含量高,具有獨特的香味,且無苦味;普通油茶所產茶籽油未經精制脫臭處理,呈辣腐乳臭味,且味道微苦。海南山柚油富含維生素、角鯊烯及多酚等物質,香氣主要成分為吡嗪類雜環化合物,醫療保健價值更高;大陸其它茶油風味主要成分為醛類和酸類。因此,普通油茶茶籽油目前市場均價100元·kg-1~160元·kg-1(毛油),而海南山柚油的市場價則高達600元·kg-1~800元·kg-1,甚至1000元·kg-1[5,8]。這種品質上的優勢,除了海南特有的生態環境和土壤條件(如土壤富硒)外,海南本地油茶被認為在長期的適應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與大陸油茶不同的地理小種或新物種。
有研究者對海南本地油茶與高州油茶(即越南油茶)和普通油茶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海南本地油茶樹體、花、果實以及葉片均小于高州油茶;海南油茶鮮出籽率在19.84%~36.21%之間,干出仁率在49.64%~64.22%之間,種仁含油率為44.56%~52.21%;海南油茶子油的不飽和脂肪酸為87.58%~89.68%,亞麻酸含量低,僅為普通油茶的0~88.7%,而飽和脂肪酸顯著高于普通油茶。對海南省油茶資源主要形態和經濟性狀及聚類分析表明,海南油茶同高州油茶和普通油茶具有顯著區別,除海南博鰲資源外,其他海南油茶被劃分為一類[11]。其他的研究者認為,海南本地油茶與內陸油茶相比,主要表現為結果早、果大、果皮粗糙和耐熱性強等特性[11]。對海南本地油茶與高州油茶(即越南油茶)、紅皮糙果茶(C.crapnelliana)在形態學、孢粉學差異進行了比較,發現海南油茶比普通油茶果實更大(直徑約3cm~6cm),果皮褐色,表面粗糙;此外,新種在形態上也可與高州油茶加以區分[13]。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的專家利用海南本地油茶與油茶組近緣種的完整葉綠體基因組序列和DNA條形碼基因matK進行系統發育定位,確認了海南省本地油茶為油茶組的一個新物種,并命名為海南油茶(Camellia hainanica YL Zhao et ZG Xu,sp.Nov.)[13]。隨后,他們對海南油茶的倍性進行了分析,表明海南油茶為八倍體和十倍體,且十倍體占83.3%。考慮到大花窄葉油茶(狹葉油茶)(C.fluviatilis var.megalantha)為二倍體、小果油茶為四倍體、普通油茶主要為六倍體、越南油茶主要為八倍體。因此,他們的研究工作從染色體倍性的角度佐證了海南本地油茶確實是在海南島獨特自然環境下形成的一個地理小種[14]。
海南油茶與普通油茶成熟籽粒代謝組學分析表明,在營養類代謝物方面,海南油茶成熟籽粒含有更加豐富的代謝物質和種類,其黃酮、氨基酸及衍生物、黃酮醇、黃酮類、吲哚及衍生物、多酚、萜類和糖類等顯著差異的營養類代謝物質種類在籽粒中的含量更多。在普通油茶籽粒中,有機酸及衍生物、脂質、核苷酸及衍生物、生物堿、維生素及衍生物、醇類和原花青素等代謝物質種類含量更多。綜合研究結果發現在兩個物種的成熟籽粒中都有物種特有的代謝物,其中海南油茶含有9類15個特有的代謝物,黃酮、黃酮醇、黃酮類和黃烷酮物質占53.33%;而普通油茶含有8類16個特有的代謝物,其中有機酸及衍生物和黃酮醇占43.75%。該研究揭示了物種間顯著差異的代謝物和物種特異性代謝物,闡明了海南油茶品質優良的物質基礎[15]。
海南本地油茶樹(尤其是老樹)是否全部屬于新種——海南油茶(C.hainanica),或者說是否如以前認為的那樣,海南本地油茶樹是從內地省份引種到海南的越南油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鑒定。由于新種鑒定前及之后的一段時間尚不明確海南本地油茶樹中新種的分布范圍,因此,在不少文獻中使用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指海南油茶,或者海南油茶使用(C.vietnamensis)這樣的拉丁名稱。
4 海南油茶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
近年來結合調查和優株選擇,發現不同產區的海南油茶林,甚至同一林分不同植株間在生物學性狀、農藝性狀、脂肪酸含量和組成方面存在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海南油茶資源豐富的遺傳多樣性為海南選育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產品種提供了良好的遺傳物質基礎。
4.1 生物學性狀和農藝性狀的遺傳多樣性
李艷等[16]最早在五指山不同地區選取有代表性的油茶林,對油茶果形、花色以及產量等基本性狀進行調查,發現油茶林的產量存在高、中、低三種狀況,油茶6種營養元素含量含量呈顯著性差異。王興勝等[17]調查海南省五指山市油茶資源(普通油茶和小果油茶),觀察和比較其生物學性狀和經濟性狀,發現果高2.32cm~5.80cm,果徑2.98cm~5.78cm,平均單果重44.76g,果皮厚度2.9mm~10.0mm,每果種子3~15個不等,平均6.9個,均重16.37g,籽殼厚0.3mm~1.3mm。
付登強等[18]經過4年的調查,發現海南油茶大部分果實成熟期為10月上、中旬,屬于“寒露籽”類型,同時也存在少部分屬于“秋分籽”或“霜降籽”類型。從海南當地油茶自然林分中選擇出6株油茶優樹,單株年產鮮果6.5kg~61.3kg,平均每平方米冠幅產鮮果1.04kg~2.67kg,平均鮮果含油率6.51%~9.30%,病果率在3%以下。
王碧芳等[19]對海南50個不同油茶優良單株的果實和大陸油茶‘華金’(對照)的果實經濟性狀指標進行測定和主成分分析。結果表明各優株及其對照的果實經濟性狀的變異程度顯著不同,變異系數在6.73%~46.92%之間:亞油酸(46.92%)、亞麻酸(39.7%)、百粒重(37.46%)和單果重(34.22%)的變異程度較大,具有很大的選擇潛力和豐富的遺傳力。亞油酸的變化幅度很大,最大值28.2%,最小值3.79%,極差24.41%,多態性豐富。變異程度小(CV<10%=的性狀包括油酸(6.73%)和果形指數(8.87%),遺傳變異較小,相對穩定。其他性狀的相對變異程度居中。并找出了海南油茶果實經濟性狀評價的5個主成分(油品質因子、果實大小因子、出籽率因子、果實外觀和種子構成因子、出仁率因子),揭示了海南油茶不同優良單株的茶油品質差異。
陳偉文等[20]對海南省主要油茶分布區35個油茶居群進行調查,實測243株油茶樹的結果表明,海南不同油茶居群茶油的出油率變化不大,平均值為51.98%,變異系數僅為4.21%;酸值、碘值和過氧化值在不同油茶居群間的變化則較大,平均酸值0.45mg/g,變異系數達到38.6%;平均碘值102.99 g/100g,變異系數為20.62%;平均過氧化值為3.39 mmol/kg,變異系數為27.92%。從中初選優樹30株,再經進一步復選和精選,對最終確定的5株優樹進行測定,發現鮮果出籽率45.57%~52.00%,鮮果出油率7.30%~10.93%,單位冠幅產油0.11kg/m-2~0.21kg/m-2,產油量770.55kg/m-2~1470.05kg/hm-2。
賈效成等[12]采用全島普查及3年連續觀測的方法,對海南本地油茶分枝角度、單株鮮果產量、果實數量性狀、種籽經濟性狀等進行研究,發現油茶分枝角度的變異幅度較小(單株間變異系數為4.35%)。大部分單株年度間鮮果產量的變異幅度很大(平均變異系數為35.61%),個別單株年度間鮮果產量穩定(變異系數為2.26%)。果實性狀中單果重變異幅度較大(變異系數為24.20%),變異幅度最小的是果形指數(變異系數為5.94%)。種籽經濟性狀中變異幅度較大的為百粒重(變異系數為39.99%)和每果籽粒數(變異系數為19.91%)。
對海南多個地區的優良單株調查表明,株高最高可達9.4m,而株高最小的僅2.0m。優樹的樹形基本為叢生型、直立型、垂枝型和橫張型四種類型。優樹的葉形則表現為長橢圓形、寬披針形、卵圓形等,其中葉片最大的為長8.3cm~12.8cm、寬3.1cm~6.8cm,最小的為長5.6cm~9.5cm、寬3.4cm~5.8cm[20]。果實性狀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其中果實橫徑最大可達46.48mm,橫徑最小的僅為31.12mm,相差15.36mm;果實縱徑最大可達43.68mm,而最小僅為21.19mm,相差22.49mm;果皮厚度最大的可達4.58mm,最小的僅有1.06mm,相差3.52mm。對40株優樹的果實性狀分析表明,單果重在26.69g~99.78g之間(平均值為54.10g),干出籽率在10.59%~36.21%之間(平均值為20.55%)。出仁率在35.79%~59.11%之間(平均值為44.76%)。種仁出油率在30.17%~57.43%之間(平均值為45.33%)[21]。
另外一項研究對海南省9個縣(市)20個鄉鎮的21個老油茶林的油茶種實的10個數量性狀進行了分析,發現海南油茶的平均單果質量為42.46g,最大單果質量為156.87g,其單果質量較集中分布于28.21g~39.07g這一等級內,其平均鮮出籽率為32.87%,最高可達52.00%,大部分在25.45%~39.61%的范圍內;海南油茶種實數量性狀變異大,大多數性狀表現出顯著或極顯著的差異,10個種實數量性狀的平均變異系數為29.36%。其種實數量性狀類型豐富且均勻度較高,平均多樣性指數為2.7499[22]。
對海南省保梅嶺生態保護區以40年生油茶老林32個豐產單株的主要農藝性狀、經濟性狀和品質性狀分析表明,從32個豐產單株中篩選出果實豐產性良好或果實、種子含油率較高的優株共20株,其中金波16號、23號、25號和32號分別高出平均果實產量效率80.00%、50.00%、197.78%和71.67%,表現出果實極豐產。金波25號果實產量效率高達罕見的5.36kg·m-2,而其果實、種子含油率則分別1.64%和0.65%,果皮厚4.61mm、種子百粒重478.42g。32個單株茶籽油理化性質和脂肪酸含量基本上都達到了《油茶籽油》(GB/T11765-2018)的要求;依據農藝和經濟性狀、茶籽油理化性質和茶籽油脂肪酸組成等差異分別作聚類分析,可以分別歸屬成6類(r2=0.932)、10類(r2=0.864)和7類(r2=0.937),3項聚類分析結果都能區分出豐度較高和較低的基因型種類,20個優株分別歸屬到全部6類、10類中的7類和全部6類中,說明越南油茶實生變異存在豐富的遺傳多樣性、不同種類基因型存在豐度差異和不同優株分屬不同基因型種類,且不乏有特色的稀有種質[23]。
楊超臣等[24]對選育的6個海南油茶(C.vietnamensis)品系果實性狀分析表明,海南6個油茶品系果高范圍在29.05mm~67.57mm。HS1果高均值最大為42.95mm,果橫徑范圍在33.38mm~64.16mm,QD8果橫徑均值最大為55.12mm,單果質量在18.39g~112.99g,QD8單果質量均值最大為70.22g,鮮出籽率在16.34%~51.52%;FH3鮮出籽率均值最高為37.17%,干出仁率在48.72%~59.15%,HS1出仁率最高為59.15%,含油率在45.70%~50.91%;種實性狀中,單果種粒數變異最大,變異系數為42.00%,果形指數變異最小,變異系數為8.99%。
4.2 脂肪酸含量和組成的遺傳多樣性
測定大果(越南、高州、陸川)油茶(C.vietnamensis)油茶茶籽油脂肪酸組成發現,茶籽油所含脂肪酸種類在實生單株間和年際間均存在差異。茶籽油脂肪酸以不飽和脂肪酸為主,平均相對比重占86.625%,其中又以油酸為主,其含量和相對比重分別平均為79.352%和80.253%。不飽和脂肪酸和飽和脂肪酸的相對比重、油酸和亞油酸的含量和相對比重均分別呈極顯著、顯著或極顯著和顯著負相關。主要脂肪酸(油酸、亞油酸、棕櫚酸等)含量和相對比重均無顯著的實生單株間和年際間差異。結果表明,大果油茶茶籽油的主要脂肪酸組成在不同實生單株間和年際間均穩定,且都以油酸為主;不飽和脂肪酸和飽和脂肪酸、油酸和亞油酸可能存在轉化關系[25]。
對海南省澄邁縣福山鎮越南油茶15a生實生成年林豐產單株茶籽油脂肪酸組成分析表明,海南油茶茶籽油不飽和脂肪酸總含量為86.52%,其中油酸含量又高達77.6%;油酸和棕櫚酸含量的變異系數不足10%,說明其遺傳較穩定。對35個豐產單株依據茶籽油的主要脂肪酸含量作聚類分析,可聚成8類(r2=0.885),并且聚類主要是基于油酸和亞油酸含量的類間差異性和類內相似性。因此,按照營養品質分類和針對營養品質進行新品種選育時,可將油酸含量作為分類和選擇的重要參考指標[26]。
陳偉文等[20]對海南35個油茶居群的243株油茶樹實測結果表明,海南不同油茶居群茶油的酸值在0.21mg/g~0.30mg/g之間,不飽和脂肪酸含量85.78%~89.10%,亞油酸含量5.06%~6.32%。
對海南8個不同產區的油茶成年實生豐產樹樣本進行農藝性狀和經濟性狀研究表明,不同產區的單株葉片和果實大小、果皮厚度等農藝性狀差異顯著,但葉片和果實形狀無顯著差異;種子數、百粒重、單位樹冠面積產量等經濟性狀差異顯著。各產區油茶油的過氧化值、皂化值和碘值差異顯著,但酸價無顯著差異。在不同產區油茶油中共檢測到9種脂肪酸,不同產區油茶油的主要脂肪酸組成種類包括棕櫚酸、硬脂酸、油酸、亞油酸、亞麻酸等,在個別產區油茶油中還發現了少量肉豆蔻酸、棕櫚油酸、花生酸和花生一烯酸,所有產區的油茶油主要脂肪酸組分含量均符合《油茶籽油》(GB/T11765-2018)所規定的質量標準。其中油酸含量最高,不同產區均高于75%,且不同產區差異不顯著,說明其在不同產區表現相對穩定。棕櫚酸是油茶油中相對含量最高的飽和脂肪酸,各產區含量差異不明顯,說明其具有較強的遺傳穩定性。肉豆蔻酸、亞油酸含量在不同產區間差異不顯著。花生一烯酸、花生酸、硬脂酸在不同產區均相對含量少,但在不同產區間差異顯著。對全部樣品作聚類分析,聚類結果打破了產區分布特征。可見,環境和基因型通過影響農藝性狀如果實和種子大小等影響產量性狀;海南不同產區的油茶油均為優質油,同時不同產區又有其特色[27]。
對40個優樹及對照的海南油茶油脂品質分析表明,硬脂酸含量在1.19%~3.43%之間(平均值為2.39%)。棕櫚酸含量在7.32%~12.92%之間(平均值為9.19%)。油酸的變化幅度在70.71%~86.21%之間(平均值為79.55%)。亞油酸含量在2.18%~13.22%之間(平均值為5.67%)。亞麻酸含量在0.39%~0.79%之間(平均值為0.54%)。其他脂肪酸含量的變化幅度為0.09%~1.62%(平均值為0.78%)。總體而言,含量占脂肪酸總量98%以上的脂肪酸主要成分為油酸、亞油酸、亞麻酸、硬脂酸和棕櫚酸。其中油酸的含量變異系數為4.55%,說明其含量相對比較穩定,確保了良好的茶油品質。比較分析發現油酸比例由高到低分別為:定安石塘地區>五指山地區>瓊海地區>澄邁地區>屯昌地區。亞油酸的含量變異系數為42.39%,表明不同產區茶油的亞油酸含量變化程度明顯。再一次證明,海南不同產區的茶油中脂肪酸存在一定差異性,其中油酸含量表現相對穩定,而亞油酸含量變異程度較大。油酸含量與亞油酸及棕櫚酸含量均為極顯著負相關,這在以高產優質為育種目標的前提下,在選育海南油茶品種時,可以有效地利用脂肪酸相關性來做輔助指標[21]。油茶籽油酸值在0.96mg·g-1~0.33mg·g-1之間(平均值為0.72mg·g-1),變異系數為22.50%,說明變化幅度較大。碘值在106g·100g-1~75g·100g-1之間(平均值為82.59g·100g-1),變異系數為6.84%,說明碘值相對穩定。過氧化值在1.96mmoL·kg-1~0.56 mmoL·kg-1之間(平均值為1.12mmoL·kg-1),變異系數為39.37%,表明其變異程度較大[28]。
楊超臣等[24]對選育的6個海南油茶(C.vietnamensis)品系茶籽油的脂肪酸組成進行測定表明,FH3棕櫚酸含量最低為8.46%,QD8硬脂酸含量最低為2.32%,HY1棕櫚烯酸含量最高為0.08%,QD9烯酸含量最高為0.52%,FH3油酸含量最高為83.43%,顯著高于其他品系;QD9亞油酸含量最高為8.86%,QD8和QD9亞麻酸含量為0.20%,FH3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為88.53%,飽和脂肪酸含量最低為11.46%,不飽和脂肪酸與飽和脂肪酸比值最大為7.73,且6個品系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均在85%以上。
4.3 海南油茶資源的遺傳多樣性分析和分子鑒定
由于以DNA片段多態性為基礎的分子標記在遺傳多樣性分析和物種(品種)鑒定方面的優勢(相比于傳統的形態和性狀標記,分子標記可直接在DNA水平檢測,不受時空限制,標記數量更豐富,多態性高,因此分辨率也高),不少研究者利用ISSR[29]、AFLP[30]、SRAP[20,31,32]、SRR[33]等分子標記對海南油茶種質資源進行了遺傳多樣性分析。此外,戚華沙等[34]利用trnH-psbA序列和matK序列結合(即油茶種子DNA條形碼),對普通油茶和越南油茶與其他供試油茶物種進行鑒別。
5 展望
盡管目前對海南油茶資源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于起步較晚,只是近10年內才集中對海南油茶資源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未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海南各地的老油茶樹是否屬于新鑒定的海南油茶(C.hainanica),特別是要與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區分清楚。其次,需要結合形態學手段,利用核型分析、葉綠體基因組分析和基因組重測序等遺傳學技術,確定海南油茶資源的遺傳特征、演化和分類關系。第三,利用代謝組學方法,解析海南油茶獨特風味和營養形成的物質基礎,確定海南油茶獨特的代謝物標記。這些工作將對海南油茶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油茶品種改良、海南茶油(海南當地稱“山柚油”)地方特色農產品或地理標志產品申報奠定技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