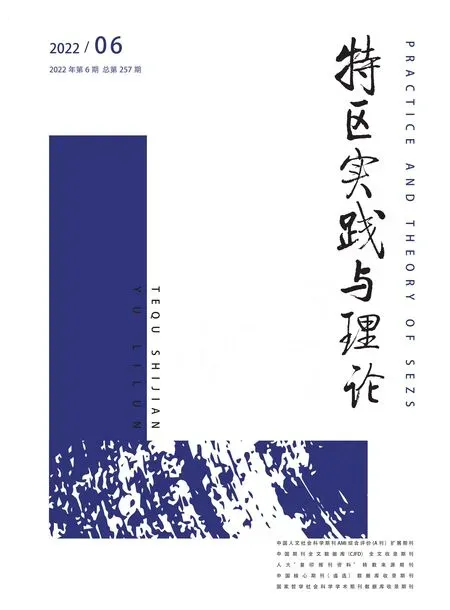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謝春紅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大力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同時指出“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1]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清晰指明了粵港澳大灣區與國家之間緊密相依、同頻共振的關系。
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各民族在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在歷史、心理、社會、制度、政治、文化等層面取得的一致性或共識性的集體身份認同”,[2]其本質體現為一種群體認同意識。鑄牢粵港澳三地民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事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事關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以及能否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力量同心共圓中國夢的戰略全局。
因此,本文嘗試從歷史與文化的視角闡釋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思維進路與當前的重點工作,以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為增強粵港澳青少年對祖國的向心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盡綿薄之力。
一、基于歷史與文化視域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
古今中外,無論國家民族,無論群體個人,都懼于歷史虛無,因為沒有歷史,則不知來處、沒有根源,可謂“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也恐于文化荒蕪,因為沒有文化,則缺乏積淀、失去靈魂,可謂“文化是一種軟實力”“文化興則國興”。沒有歷史與文化,奢談未來與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旨在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新發展、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關系國家發展與百姓福祉,因此,應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
追溯起來,粵港澳大灣區從提出到進入全面實質性建設,經歷了小地方性概念到國家戰略、從自發形成到對標國際的歷程,并在啟動建設后呈加速探索的態勢。“灣區”概念早在20多年前就進入了學者和地方政府的視域,2009年10月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發布《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提出共建世界級城鎮群。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灣區經濟”。“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新概念正式提出是在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等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6年3月國家“十三五”規劃再次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臺建設”,強調“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是在2017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2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中指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有利于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同時還明確要求深圳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經濟概念、政治概念。它是對一定地理地域的區分,也有著明確的經濟和政治的考量,而在經濟與政治的目標追尋中,內蘊著深切的人文關懷。粵港澳大灣區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地處中國南大門,包括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8年末總人口已達7000多萬人,經濟總量超過了12萬億人民幣。然而,從地緣關系看,這一區域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地理空間,它自始至終都在與外界進行著人員、物質、能源、信息等的交流,從粵港澳到整個珠三角地區再到整個中國、整個東南亞乃至整個世界,在全球化的視域下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從地緣經濟看,這一區域是我國經濟活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占據重要戰略位置,它與“一帶一路”倡議是相輔相成的,是“一帶一路”的細化內容之一,是我國參與全球經濟事務的重要一環。從地緣政治看,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的戰略性頂層設計,旨在帶動包括港澳在內的珠三角地區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并形成新格局,探討“一國兩制”背景下粵港澳聯動發展、融合發展的新路徑。從地緣文化看,這一區域承載著國家深切的文化意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五大戰略定位”,如果說,前四個目標側重闡釋的是經濟目標、政治目標,那么,第五個目標“打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則凸顯為人文目標,指向的是人們的美好生活。這一人文目標其實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終極追求。
顯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等目標在內的整體建設。從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系看,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文化不僅賦予經濟發展以深厚的人文動力,對政治制度、政治體制起明顯的導向和引領作用,還能促進社會主體間的相互溝通,凝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進而產生同化作用,以致化作維系一個民族國家生生不息的磅礴偉力。如果說,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議題,那么,文化議題是更為深沉、更為根本的。
從文化議題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文認為,成功的前提是人們對于建設的目標有共識,而關于目標的共識又有個前提,就是人們能夠明白“我是誰”,即有一個清晰的自我意識、一種明晰的自我身份。而自我意識、自我身份的確認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歷史的記憶以及文化的認同。也就是說,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而言,有一個更具根本意義的建設議題在于厘清生活在這片區域上的人們“我(我們)從哪里來”“我(我們)為什么是這個樣子”“我(我們)想成為什么樣子”,而這些問題必須回到更深遠的歷史和文化中去尋找答案。所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切實的行動,需要社會動員和可以描摹的經濟藍圖,也需要更為持久、更為沉靜的文化省思:我們是否有了共識?我們是否擁有共同的清晰的身份意識?
因此,本文認為,歷史與文化視角之于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依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統梳理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的歷史與文化,挖掘整理從古至今、或隱或現地存在于歷史與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的共識,進行闡釋與討論,使之以清晰的歷史敘事和文化血脈來重構集體記憶,并不斷與現實對話,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感覺他們屬于同一共同體,擁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治理、共同分擔命運的愿望,并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以這種“身份共識”以及“人心歸一”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各方面建設。
二、基于歷史與文化視域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維進路
一般而言,共識可以通過政府層面的各種溝通、協商達成,但普遍的共識則來自民間的自覺、自愿、自為。當下共識的核心問題是共同的身份認同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相比世界上其他灣區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國兩制”,即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粵港澳分別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涉及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制度。這既是建設的優勢,也是挑戰所在。粵港澳三地同處一個灣區,文化同源,人緣相親,民俗相近,經濟方面各有優勢,各具特色,彼此緊密合作,必將產生協同效應和放大效應。但是,產生最大效應的關鍵是要處理好“和”與“合”的問題。所謂“和”即“和而不同”,三地求同存異、和諧共處;所謂“合”即相互合作,三地同心協力,合作共贏。而“和”與“合”的背后是“人心”的支撐,是對同一歷史與文化的認同。對于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來說,共同的身份意識還需要在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人當中再次確認。
那么,該如何增強共同的身份認同呢?人具有歷史性,也具有文化性,因此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也需要從歷史——文化的維度看。所謂認同,就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以及我歸屬于哪個群體”,身份認同,需要群體成員之間擁有關于共同體的歷史——文化連續性的認同,而歷史——文化連續感的形成有賴于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歷史”是保留“歷史記憶”的基本方式,通過歷史的認知可使人們了解到自己民族和國家的過去,從而搭建起溝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橋梁;可使人們感受到歷史中的事件、歷史中的人物曾經和自己擁有某種共同的特質,從而建立起心理上的強烈關聯。而文化連續感的形成有賴于共同的符號系統,人具有獨特的使用符號的能力,“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則是這個符號宇宙的各部分,它們是組成符號之網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驗的交織之網”。[3]借助一系列復雜的、等級化的符號意義系統,諸如語言、文本、儀式、節日等等,可建立群體身份的鏈接結構,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為群體成員提供一種“我們感”;可建立起群體成員對文化傳統的眷戀和延續、對現實的焦慮和抉擇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和期許,從而塑造群體成員屬于同一命運共同體的牢固想象。
可見,歷史——文化延續性可調動人們共屬一體的想象,使人們消除“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隔離感而擁有共同體感,認識到擁有共同的血緣紐帶、共同的歷史命運、共享的理想和信念,即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當然,這里的歷史——文化延續性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復制與再現,而是不斷變化、更新中的傳遞與賡續。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綿延幾千年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作為一種“連續性”形態的文明,浩若煙海、綿延不斷的典章文獻是代表其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物質留存,強調和合、重視大一統的思想傳統則是維系其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精神紐帶。應該說,我們擁有足夠多的歷史與文化資源,有通過歷史和文化的力量把億萬人統合在一起的豐富的經驗與智慧。但這些經驗與智慧并不會一代接一代在人腦中“自動轉存”和“自動再造”,因為作為人的歷史——文化是由人在實踐中創造,而實踐是變動不居的,這就必然要由人在實踐中不斷地激活、不斷地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如此,這樣的歷史——文化才不會是一堆存放在倉庫的故紙、文物,而是能與現實視域相融合的一般知識、思想和價值觀。這也是歷史與文化之于人、之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真正意義所在。
本文認為,我們可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底蘊,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與文化為切入,以當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體意識”問題為思維起點,由點及面,由近及遠,追溯與粵港澳大灣區歷史與文化有著直接關聯的嶺南歷史與文化的生成特質,進而追溯與嶺南歷史與文化有著深沉關聯的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生成特質,通過這種由中國而嶺南而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敘事與文化闡釋,在時空交替、古今對話中,聯通過去、現在與未來,以串聯起一條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以至綜合為一種“共識性的整體”或“共同體意識”,最終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一種人文方案。
三、基于歷史與文化視域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點工作
從歷史與文化視角對于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重要的意義,激活歷史資源與文化動力、重新建構起一條基于中華文化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鏈條對于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迫切的,當前我們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目標展開對粵港澳大灣區歷史與文化的考察與探討、整理與研究。
一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歷史與文化本身是個復雜概念,眾說紛紜、歧義叢生,可能需要運用整體性的方法提供一種界說,才能真正揭示其內涵的豐富性與深刻性;中華歷史文化、嶺南歷史文化、灣區歷史文化之間具有一以貫之的邏輯關系與互動品格,可能需要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把灣區的歷史演進與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程相結合。既以大歷史觀的視角宏觀把握灣區作為中國版圖的組成部分的發展脈絡,從而理清灣區的歷史起源和文化淵源;又從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性視角分析粵港澳三地不同的歷史境遇和文化范式,從而展望粵港澳三地跨域協作發展、“和合”共處的未來圖景。
二是搭建新的研究架構。中國歷史文化、嶺南歷史文化、灣區歷史文化所涉及的典籍浩如煙海、內容博大精深,我們可以以“問題”為導向,以粵港澳三地民眾是否擁有“共同體意識”而提問;以鑄牢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旨歸,將粵港澳大灣區歷史文化放置于中國歷史文化整體演進的過程中,沿著灣區歷史文化形成、發展的內在邏輯理路,溯古通今,構建一以貫之、層層遞進的理論體系。不僅敘述中國歷史文化、嶺南歷史文化、灣區歷史文化的源流關系,也闡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鏈接關系。不僅注重歷史闡釋與當代發展的視界融合,也注重文化解讀與當代啟迪的時空對話,以述說粵港澳三地的歷史,從而架構全新的內容體系。
三是進行一些新的分析。新的分析不是就灣區而談灣區,就建設而論建設,而是從現實問題出發,從經濟、政治、科技、生態等建設的熱議話題中抽出灣區人的歷史文化認同和“人心歸一”問題,進而尋找歷史和文化資源,由古至今,由遠及近,使灣區的歷史與文化重新勾連起來、使灣區人作為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脈絡更加清晰起來,從而實現建設目標;新的分析也不是就歷史而說歷史,就文化而言文化,而是將歷史與現實相連、將過去與未來融通,在返本中開新,在開新中返本,從而有了新的視角、新的體例、新的內容。從而使我們的研究有別于同類研究,開闊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視野,深化拓展對粵港澳大灣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以引導灣區發展的人文向度。
“歷史與文化”獨具聯通過去——現在——未來的品格,作為一個過去話語,它深藏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作為一個現在話語,它立足于當下與過去進行對話,并推進我們的歷史延續與文化發展;作為一個未來話語,它將拓展我們的歷史縱深并將給我們帶來直面不確定未來的勇氣和智慧。基于歷史與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而擁有共識、共感、共鳴以及共同行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邁向世界級人文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