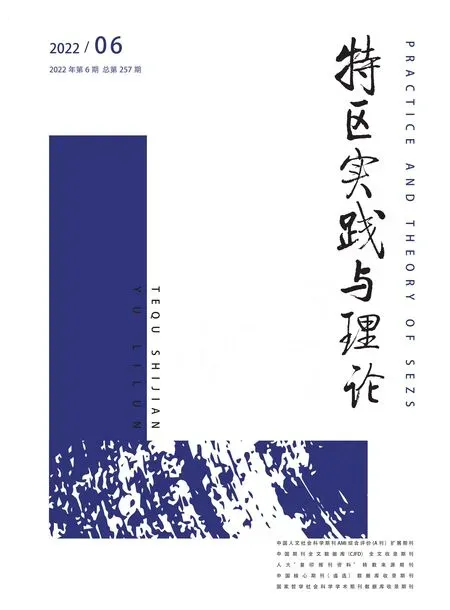古典與現代之間
——重新認識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困境及其價值
陳新華
一、“三千余年未有之變局”語境下的文化誤讀
1872年,李鴻章在《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談及當時情勢,直言“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所謂“三千余年未有之變局”,究其根本,是中西兩種文化傳統、文明體系激烈碰撞,中國一方“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1]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天下”的危機。也正是在“三千年未有”的語境之下,國人逐漸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這一過程,經歷了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的嬗變,眾聲喧嘩,革故鼎新,西潮漸次成為時代主流,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學節節敗退衰落,以傳統為依據的文藝復興成為暗潮。
近代中國的歷史轉型,始終在西潮與中學的緊張關系中艱難前行。百余年間,雖不斷有關于激活傳統以挹注現代危機的思考,然而總體說來,在向現代而行的大變、快變、全變中,在改良與革命中,傳統終不可避免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國人漸漸習慣于一種將中國文化推入歷史深處的敘事思路,以為傳統就是陳舊、落后、阻礙進步的。這種理解,看似清晰明了,實則落入古與今、中與西、新與舊二元對立的窠臼,失去了對中國文化獨特性、多樣性、復雜性的自覺意識,現實中,既無法辯證性地把握文化的內在張力,亦難以恰當處理本土與外來文化體系之間相互建構的關系,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筆者以為,在進行任何關于文化的敘事之前,先要具備一種更具反思意識的語境,避免此類對于傳統文化僵化的理解:即傳統并非永恒不變。任何一種文化體系,都可能同時內涵 “內部與外部” “核心與邊緣”“延續與斷裂”“統一與多樣”等同時并存的內在張力。在歷史的演進中,這些張力既可為動力,推動文化的發展,亦有可能使文化傳統陷入困境。這樣一種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狀態,才是文化發展的常態。
有鑒于此,具體到中國傳統文化,首先,需要澄清一種“古與今”的時間上的斷裂。如同費孝通所言,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的共同經驗,其存在的意義,正是建立在“過去”的投影之上。每個人的“當前”,都包含了個體乃至整個民族“過去”的投影。[2]由此而言,文化是綿延迂回的,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可以清晰切割的“古與今”。[3]只有回歸到時間的河流中探尋中國文化,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國”所內涵的綿延性——實質上,所謂“三千年未有”的斷語,也是在時間的河流當中,它上承西周以來的古典中國,下啟百年激蕩中的現代中國,直至19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不同時段的中國的合力,重塑了“當代中國”。即便今天,當代中國也是一個尚在進行,并未完成的歷史過程。在時間河流的跌宕起伏中,一個純粹的古典意義的中國雖然已不復存在,卻依舊還是構成當代中國的“投影”,依舊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對當前中國發生著影響。
其次,避免“東與西”的空間的斷裂。自晚清變局以至今日,以“中國”為名的文化實踐,在大到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小至衣冠服飾、飲食起居等幾乎所有層面,都和“西方”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聯系。換言之,在文化實踐中, “西方”已經內在于“中國”,成為當代中國的一部分。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文化就此失去價值。恰相反,相對比不是東方的,就是西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東西之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碰撞、互動乃至融合,才更接近文化和歷史的真相——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當代中國是在古典中國的自我更新與現代化浪潮的西學東漸中被塑造出來的。源自本土的、古典社會的傳統文化因素,和源自西方的多元的思想理念,共同構成了我們文化實踐的地平線。[4]客觀上,這是造成當代中國文化問題復雜性以及緊張性的根源所在。同時也說明,對內涵有“東與西”“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當代中國文化而言,任何單一向度的描述,都有可能陷入片面和盲目。
總而言之,關于傳統的困境,筆者試圖想要表達的是,沒有一成不變的傳統,也并不存在一種與當代對立,塵封在時間深處,不被接納,也無法再產生影響的傳統。當代中國實際上是處于古典中國的延長線上、古今中西交匯的歷史時空中。在這個歷史時空中,“傳統”實際上仍然在支撐中國人關于秩序、意義、自我乃至家國認同的整體建構。
二、“道出于二”的緊張:困境的內在成因
當然,雖然我們相信傳統文化永遠是當下和鮮活的。但在現實中也要看到,近代以來曾極大困擾過晚清、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問題,時至今日,仍是當代中國人知識與精神的困境。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人和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實屬同一代人。緣此,回到歷史語境中,回到中國人的精神現場,重新梳理危機與困境之所以形成的復雜脈絡,永遠是必要的。
(一)中西之間的文化沖突造成的文化認同危機
關于中國文化的認同危機,歷史學家雷海宗曾稱,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雖受北方游牧民族、印度佛教的影響,但在整體上仍保持了中國文化的個性。就民族而言,胡人血統融入華夏民族,并沒有改變華夏的主體,而是被華夏民族所同化。就文化意識而言,佛教同樣沒有改變中國文化的主體,而是逐步中國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也仍然能保持。[5]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歷史,受西洋文化的武力與文化雙重入侵,無疑是“傳統文化總崩潰的時代”。[6]
這一涉及文化根本的危機,王國維稱之為“道出于二”,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7]羅振玉在《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亦有類似表達 :“海禁未開以前,學說統一,周、孔以外,無他學也。自西學東漸,學術乃歧為二。”[8]“道出于二”,正是對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進一步解釋,其意在表達:鴉片戰爭以來,以儒釋道為主流的傳統文化不再是中國唯一之道,不僅如此,伴隨武力洶涌而來的西方之“道”還占據了上風——從洋務運動在器物層面的引進西方,經戊戌變法在制度層面的效法西方,到新文化運動在觀念層面的學習西方,國人在不間斷的民族危機中逐漸接受了“以強弱定文野”的標準,[9]即作為強者的西方文化是現代和先進的,被打敗的中國文化是傳統和落后的。這種對自我文化體系的認同危機到辛亥革命,伴隨著儒家文化失去作為載體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再經過新文化運動百罪歸于一身的激烈的反傳統,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賀麟描述“在當時全盤西化、許多人宣言立誓不讀線裝書、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環境下,大家對于中國文化根本失掉信心”,[10]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思慮。其影響既深且久,一直延續至今,這就是何以今日我們重提傳統文化時,思慮和疑問仍然可以成為主流的原因。說到底,今日國人仍然處在現代化的轉型期,仍處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體系遭遇以來的碰撞、融匯期,仍處在以西方文化為他者,對自我文化傳統的審視、自覺期,文化的轉型、重建仍未完成。
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任何偉大的文化傳統都不可能一成不變。如同歷史學家許倬云所言:“‘變’是唯一不變的真相……世界上重要的宗教,沒有一個不是經過一次次經歷改革,才發展而成其面貌:任何論述體系,都需要因時、因地的修正,才能適用于當時當地人心的需求,解答當時當地人所面臨的疑惑。”[11]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歷史學家彼得蓋伊會在《啟蒙運動》里說,“啟蒙運動為了確認自身,必須把宗教當做迷信和謬誤……只有當年的論戰者以偏執的態度對待基督教的千年統治從而使自己掙脫出來,以后的學者才可能公正地對待這段歷史時期。”實際上,不僅是啟蒙運動,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等,無一不帶有反傳統的姿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晚清到“五四”乃至于當下的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對西學的引進,對傳統的質疑乃至于與傳統的決裂、脫隼,其實更是一種基于文化自覺前提下的自我尋找和建設,期待驅逐愚昧以改造傳統,而不是徹底否決、瓦解傳統。可以說,對傳統的省察和改造永遠在路上。
(二)近代歷史記憶的塑造和書寫帶來的陌生與隔閡
中西之間的碰撞沖突帶來深重的文化認同危機,也影響到近代中國關于歷史記憶的書寫與塑造。后者在現實中反過來又推動并且強化了一種對抗傳統的思路。回顧歷史,中國近代的社會轉型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沉重的國難與恥辱。晚清以降的歷史進程中,舉凡大的轉折性事件,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到五四運動等等,無一不是和民族危機有關。故此,李澤厚有“救亡壓倒啟蒙”的總結。以此故,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關于近代史的歷史書寫,也多以侵略和反抗為核心,胸中常有一股不平之氣,基本是“國恥壓倒國粹”,對于傳統急欲去之,“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此日積月累,最終就是 “數千年之文教,因數十年貧弱而淡忘”,[12]自然也就鮮少對于傳統 “文藝復興”式的自我觀照。
(三)以現代性裁量傳統的偏見
從歷史延續進現實,對傳統的焦慮與疑問實質上還源自于 “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內在緊張。1500年以后,由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臘羅馬文明演化而來的西方文明迅速向全球擴張,這場以全球化為其形式的現代化潮流,幾乎將所有國家和民族都裹挾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由于長久以來的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現代性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天然的進步性和正當性。我們普遍接受了現代是普適的、傳統是特殊的、現代是先進的、傳統是落后的觀念。在這樣一種優勝劣汰的歷史進化論的視野里,我們一方面以懷疑的態度對待傳統,為實現現代化和富國強民的理想,希望摒棄我們以為不適用現代化的那一部分傳統,又擔心由此而失去自我的文化認同,進退失據,患得患失,其結果就是以現代性作為裁量傳統的依據和標準。
只是,我們在用現代性取舍傳統文化的時候,往往忽略了現代性自身可能有的種種問題。不必說20世紀的一戰、二戰、冷戰、核危機、經濟危機,21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亦出現了很多新危機:“黑天鵝”與“灰犀牛”,逆全球化與民粹主義,“伊斯蘭國”的陰影與反恐戰爭,能源危機與俄烏戰爭,凡此種種,都在加深全球范圍內以現代性為依歸的價值撕裂。歷史的發展證明,現代性遠遠不是檢驗一切文化體系的萬能公式。在中國從富強走向文明的探索中,我們該做的是開放胸襟,同時終結對西方思想的盲從,探索、建立、發展一種能夠超克現代性危機,對全球發展具有文明示范力量的中國模式,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宏大的時代命題,無疑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傳統,認識傳統在中國的現代化的建設、在當下乃至未來的意義。
三、民族復興語境中的傳統
(一)現代化進程中的內在需求
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曾經感慨,現代化成為一個無可逃避的宿命。如果現代化是無可逃避的宿命,那么,這個宿命到底意味著什么?沿著這個思路,不難發現,現代化自發端以來,至少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富強意義上的現代性,主要以器物層面的科學技術、制度層面的理性化秩序、非人格化的科層管理以及精神層面永不滿足的世俗化追求也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為核心,它無關價值,不信神靈,所到之處,摧枯拉朽,大破大立,營造出了一個個 “普遍同質化的國家”以及程式化的社會——例如大工業的流水線作業、標準化生產以及大數據管理,人們期待通過科學的工具理性的計算,達成資源以及發展的最優化。然而在現實中,工具理性也許能實現富強,卻無法實現人的尊嚴和情感,后者往往需要價值和意義,需要文化來完成。因此,當富強的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全球性的社會結構就發生了重大轉型,由普適性社會轉變為獨異性社會。人們想要的不再是標準化的流水線,而是對“真實自我”的意義和價值的追求。這無疑是一個更高層面的現代化,文明意義的現代化。這一轉型自1970年代開始醞釀至今,逐漸成為時代的潮流。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現代化首先意味著文明的主體自覺,以及對于自身活潑潑的精神傳統的挖掘。任何一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的文明體系,最終其實都和自己的傳統達成了某種程度的自洽,甚至于,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回向自己的傳統和精神資源,譬如西方之回到古希臘,日本之于儒家與神道教。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我們要實現“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文明意義的現代化[13],同樣需要直面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個性,以“古代之良藥”醫治“現代之頑疾”。
(二)全球化時代的自我認同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在經歷一個走向世界的艱難曲折的歷程。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并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恰恰是中國深度融入世界,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之后,關于中國的自我認知這一問題就變得格外突出。換言之,就是需要認知到,全球化里的中國到底是誰,如何認知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因為,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中,全球化的真正意義其實都不是很多人誤以為的世界的同質化、統一化,而恰恰在于價值體系的多元一體。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不同民族國家和而不同的差異性的前提下才有意義和價值。無論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還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場,世界文明發展的角度,關注文化生態的多樣性,警惕一個普遍同質化的世界,才是值得稱道的文化努力。
就此而言,中國融入世界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同質化,而是普遍的文明規則中的差異化,是“認識你自己”基礎上的“講好中國故事”,是“文化自覺”以后的“文化自信”。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文化對全球化中的中國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民族復興愿景里的必要支撐
關于傳統文化之于“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問題,可能需要理解的是,任何時候,所謂中國的發展都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在這個大前提下,民族文化傳統與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顯然是相輔相成,停留在古今中西非此即彼的窠臼當中的任何想法都是缺乏理論自信的表現。
可以看到的是,過去一百七十年間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制度乃至思想觀念層面都從西方汲取了營養,在此背景下,一個古老的儒家帝國經歷了無比的艱難,蛻變成現代型的中國。我們今天處于乾隆朝末期以來最良好的國際地位,并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晚清以來富國強民的理想。但“富強”的現代化并不等于“文明的現代化”,如果我們僅扮演西方主流文明追隨者的角色,即便成功也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復興”。民族的復興歸根結底還在于文化的復興,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4]優秀的傳統文化,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15]因此,如果未來幾十年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有能力、有機會輸出自身價值的歷史時期,那么,這個價值的根基一定是在中國作為民族國家敘述體系中以儒家為主干的文化和思想資源。換言之,如果中國人要具備全球化時代的價值輸出能力,顯然是來自傳統的現代化,來自于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現代社會主義傳統和西方啟蒙主義傳統的有機結合,而不是西方的中國化之后的再西方化或再全球化,那只是二次模仿,不是輸出,更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
(四)身為中國人的生活以及情感需求
從宏大敘事回歸到每一個具體的個體,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個中國人實際上都處在遠超本土性的一個紛繁復雜的世界性文化之中。但無論如何為,不能否認的是,作為支撐中國傳統社會近兩千年的倫理共同體的關鍵的內核價值,以儒釋道為代表的經典的大傳統乃至以血緣、地緣、信緣為聯結的民間社會的小傳統仍然是中國人自我認同、倫理生活的根基,是“人們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情感樣式的集中表達”,[16]這是一種浸潤于日常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情感和精神需求,不是某個階段的政治或者社會發展可以改變的。就此而言,保持一種文化的自覺,從社會的層面、從國家制度的層面弘揚、挖掘傳統文化,無疑有助于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解決,而這本身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和重心所在。
當然,筆者在本文所說的弘揚和發掘傳統文化,并不是要回到傳統,而是在當代的生活和社會挑戰中找到傳統的活力與現代形態,說到底,傳統文化的當代化,也就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才是根本的出路所在。
一百年前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提出“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大責任”,不是將自己國家搞到富強便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讓自己的國家有功于人類全體。因此,中國有一個“絕大責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17]關于傳統文化,任公的回答,他一生欲拉平中西的訴求,放到今日,仍不過時。只有跳出粗陋框架里的中西之爭,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使中華文明成為真正世界性的文明,參與全球文明秩序的建構,進而,為人類文明賦予一種新的可能性,如此,方可稱得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