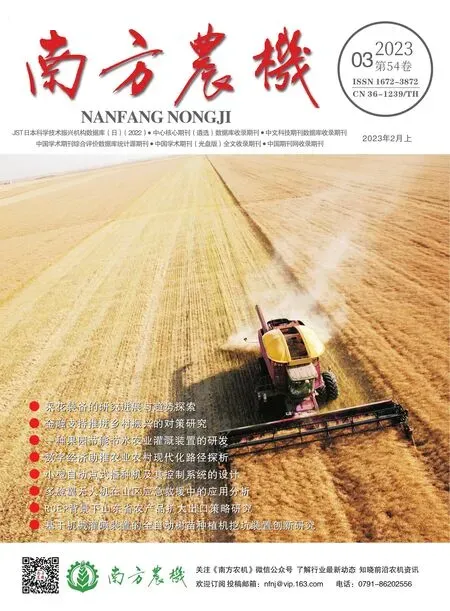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與分析*
張玉玉,倪可洋,邢慶松,孫 寧
(1.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0;2.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 成都 610071;3.濱州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濱州 256603)
近年來,受全球極端氣候、新冠疫情暴發和局部地區沖突等問題影響,全球糧油產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示要穩住中國農業基本盤,做好“三農”工作,全力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當前中國糧油產業發展既有追求質量提升的遠慮,又有在短期內保證糧油產量的近憂,只有在不斷提升各省糧油產業生產穩定性的同時進一步增強糧油產業的競爭力,才能在全面推進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實現保障國家糧油安全的目標[1]。目前,國內外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針對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及分析的成果較少。本文從安全保障、結構保障、基礎設施保障和經濟發展水平4個維度來構建我國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2020年我國糧油產業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剖析當前制約我國糧油產業發展的因素,以期為推進我國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出更多具有可行性的建議。
1 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依據評價指標設計原則,遵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流程。首先,對糧油產業進行分解分析,然后根據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確定反映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一級指標;其次,參考國內外研究文獻綜合分析使用頻率較高的表征指標并進行篩選,將隸屬度、相關性、鑒別力和信度效度較高的指標篩選為最終的表征指標[2];最后,為保證指標體系的科學可行性,向本研究領域專家進行咨詢,根據專家意見進行調整,最終確定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類型、權重及屬性如表1所示。

表1 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 實證分析
2.1 評價方法
本文首先將各表征指標數據根據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按其評價作用分為正、負兩類,使用STATA軟件并采用Minimax算法對各個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各項指標數據間的量綱差異。為了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使用更為客觀的賦權方法——熵值法來確定各層級指標的權重。
2.2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遵循綜合性、準確性、時效性原則,確定選取全國各省糧油產業相關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21》《中國統計年鑒—2020》,部分數據來自農業部及各省區市統計公報。為更清楚地比較分析各地區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按照國家劃分的糧食主產區、主銷區、產銷平衡區進行進一步的分析[3]。
3 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結果分析
3.1 測度結果與指數結構分析
以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為依據,根據上述實證分析方法和數據,通過測度好的各項表征指標權重,最終得出我國31個省(市、區)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標評價結果,如表2所示。
3.1.1 安全保障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除河南地區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發展格外有優勢外,其他地區的發展相對較為均衡。其中,糧食主產區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數中的安全保障發展水平較高。從具體指標來看,主產區糧油作物總產量、油料作物單產極高,農藥、化肥使用量低。主要原因有:具有區域地理優勢,土壤肥沃度高,土壤適合糧油作物生長,在農業方面堅持“四化”方向并秉持生態文明發展理念等。在糧食產銷平衡區中,山西、甘肅、云南等地區的安全保障水平較低,主要是由于中原地區歷經多年耕種土壤肥力下降且受地區氣候條件影響較大,甘肅地區還存在農用化肥施用量、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過高的情況;云南屬于山地丘陵地帶,在水土流失治理上問題較多,水土流失治理面積測度僅為0.172,遠低于全國0.39的平均水平。

表2 我國各地區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標評價結果
3.1.2 結構保障評價
地區糧食數量安全受到區域糧食供需關系的影響,在結構保障指標評價中,黑龍江、內蒙古、吉林的結構保障處于高水平發展狀態。以糧食主產區黑龍江省為例,其結構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地區。一方面,黑龍江省是農業強省,耕地面積廣、糧油產量高,使其較其他地區具有糧油消費供給優勢;另一方面,2022年《黑龍江省“十四五”黑土地保護規劃》出爐,進一步加強了對黑土地的保護,黑龍江嚴守耕地“紅線”,支持土地規模經營政策,這也是其供給結構發展水平遠高于其他地區的重要原因[4]。與安全保障指標不同的是,在結構保障指標中,除糧食產銷平衡區寧夏外,其余排名靠后的區域都屬于糧食主銷區,盡管地區城鎮糧油消費占比高,但主銷區在追求工業化的“GDP沖動”下種植結構指標水平較低,多數糧食主銷區自給率低于90%,使得其供給不足,導致其結構保障水平低。
3.1.3 基礎設施保障評價
基礎設施保障是提高糧油產業生產效率的重要途徑。比較各地區糧油產業基礎設施保障水平發現,寧夏的基礎設施保障水平約高達20,而同屬于產銷平衡區的西藏地區則僅為0.422 2。分區域來看,中部、南部和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保障水平較高而西北地區偏低;從具體指標分析,位于中部地區的寧夏農業機械化總動力占比最高,主要原因在于寧夏以農業機械化引領農業現代化發展,嚴格落實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實現農機服務領域覆蓋農作物耕種全過程。西部地區中,西藏、青海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農林類院校個數、機械化耕作面積、節水灌溉面積4項指標均處于全國較低水平,主要原因有:西部地區在農業財政支出方面的占比較低,適宜耕種的土地較少,實現農業機械化難度大,節水灌溉技術推廣難。
3.1.4 經濟發展水平評價
分析糧油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可以主要從人力、財力、物力上測度各省糧油產業的基本狀況。從具體指標來看,黑龍江省農場耕地占有面積居全國第一且比排名第二的新疆多兩倍,主要因為黑龍江省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農場建設上受中央政策影響較大,且近年來不斷深化農業農村重點領域改革,加快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產業產值高且綜合實力強。此外,比較典型的代表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糧油產業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主要原因是三者均為各自經濟圈重要的工業城市、商貿之都和新興產業城市,其農業功能逐漸淡化。
3.2 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
綜合評價結果上,我國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存在明顯地域差異。其中,31個省(市、區)排名第一的黑龍江省得分為45.497,遠高于第二名四川35.162 9的評價指數,而排名最后的北京得分僅有8.220 7。整體上中國各省糧油產業發展狀況大致可以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是黑龍江、四川、新疆、河南;第二梯隊是寧夏、內蒙古、湖南等;第三梯隊是廣東、湖北、江西等;其余地區為第四梯隊。總體來說,我國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為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銷平衡區>糧食主銷區,并呈現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趨勢。其中,全國平均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僅為21.497 0,有15個省(市、區)超過或等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省(市、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總之,我國各省糧油產業在追求高質量發展并向更高水平發展空間邁進上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4 優化路徑建議
4.1 打造更高水平的糧食主產區
糧食安全是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在打造更高水平糧食主產區時必須更加注重糧油產業高質量發展,確保基本糧油的穩增穩產。在土地資源豐富的糧食主產區應堅持推進“藏糧于技”戰略,以農業技術創新引領農業技術擴散,發揮優質糧食品種的增產價值[5]。同時,以綠色發展為引領,高標準落實質量安全、資源節約的糧油增產目標,打造區域更高水平的糧油產業。在結構保障水平高的糧食主產區要提高糧油產業生產組織化和標準化程度,提升優質糧油產業供給;在供給側方面必須順應食物消費結構升級趨勢,深入推進糧油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保障高的糧食主產區應集成高新技術,全面完成糧食生產過程數字化改造;要切實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深度發掘糧食產業的復合功能價值,推廣應用“農地+特色種植”“農地+康養”“農地+文旅”等模式,為當地現代農業發展注入“活水”。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好的東部糧食主產區,應進一步提高其綜合實力,加大人、財、物的支持力度,完善相關涉農法律法規,創新經營模式,實現多元主體共同發展[6]。另外,打造更高水平的糧食主產區必須強化市場化機制的發展性引領,創新糧油產業發展業態,形成質量效益雙重提升的農業發展方式。
4.2 進一步提高糧食主銷區糧食自給率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主產區、主銷區、產銷平衡區都要保面積、保產量”,特別指出“主銷區要切實穩定和提高糧食自給率,產銷平衡區要確保糧食基本自給”[7]。可見,糧食主銷區也要扛起保障糧食安全的重擔,保持基本自給、保證種糧面積,提高糧食自給率。主銷區必須明確黨政同責,將糧食安全作為政治責任,多管齊下優化種植結構,主銷區要切實穩定和提高糧食自給率,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落實“長牙齒”的耕地保護硬措施。同時有關部門需要調整工作思路,既要加大對糧油生產的財政支持,也要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快出臺綠色技術補貼,發揮政策引導作用,提高農民穩糧擴油的積極性,逐步穩定并提升糧油作物種植面積和生產能力[8]。
4.3 優化產銷平衡區的糧食生產資源
目前,我國產銷平衡區資源約束依舊存在,生產條件不佳的問題亟待解決[9]。一方面,在安全保障上要優化種植結構,提高糧油作物單產水平,保障其數量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強耕地生態環境保護,秉持綠色理念,推廣綠色優質的種植技術,加強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監管,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在結構保障方面應擴大糧食產銷平衡區的糧食耕種面積,優化糧食生產力,推動糧油產業與信息技術融合發展,推進“產運儲加銷”一體化體系建設。在基礎設施保障方面,既要加大科研力度培育高產優質的農作物新品種,又要結合多學科力量聯合攻關“卡脖子”技術難題,提高糧食生產的穩定性[10]。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要支持新型糧油經營主體發展,加強糧油產業人才隊伍建設,提高產銷平衡區的財政支持力度,實施高標準農田建設再提升工程。尤其要注意西部地區的糧食主產縣、鎮應與其他糧食主產區的產糧大縣享有同等財政待遇,以保證其在地區糧油生產工作中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