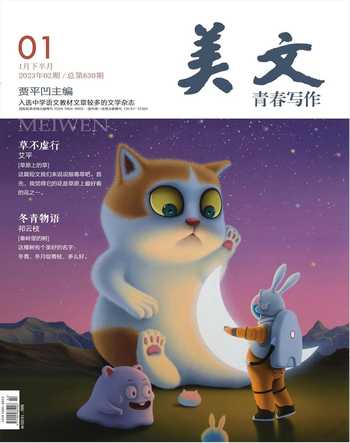文學入夢
張琳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歲月一點點地將天真浪漫從童年這匹華美的錦緞中抽離,又一點點地用沉靜與克制填補著那些幾不可查的空隙。它安靜地編織著色彩斑斕的生活圖景,推著人們移步向前,不自覺地跟著卷軸展開的節奏憧憬著未來。在對未來的期許中,我偶爾會回望過去走過的路,循著俯拾即是的感動,眷戀地嗅著青春的氣息。文學,是眾多感動中最璀璨的明珠,它聽著輕悄悄的、摸著軟綿綿的、嘗著甜絲絲的。
我與文學的緣分,要從睡前故事說起。大概是在三四歲的時候,每天睡前都要纏著父母講一個故事才肯上床。從中國傳統寓言三個和尚的故事、盲人摸象,到西方童話故事,小紅帽、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等。這些故事像滿天的繁星,裝點了我每個入睡前的夜晚。沒過多久,母親的故事儲備就告罄了,我枕著母親的手臂埋怨她千篇一律的故事風格和敷衍的敘述態度。在母親無奈的目光中,父親買了一摞故事繪本回來,每天照著書給我念,從那時起,哄我睡覺的工作就順利交到了父親手上。他用方言給我念書,總是聲情并茂,我聽得津津有味。有一晚他念了阿拉丁神燈的故事,我睡得很安穩,第二晚便要求他從頭念,父親略微氣惱地說:“昨晚你沒多久就睡著了,我還一直念,故事都念過了大半,全白念了。”我回道:“誰讓你只顧埋頭念,不關心聽眾的?是你自己被故事吸引了吧?”他拿我沒辦法,只好從頭開始念。阿拉丁神燈的故事比較長,連著念了三個晚上才念完,隨著父親的聲音,我腦海里閃現著故事里的畫面,可以許愿的神燈、無所不能的精靈、會飛的魔毯,不斷撩撥著我的想象力,甚至天真地期盼著有一天自己也能撿到一盞神燈,把那些不著邊際的愿望都給實現了。每天晚上一個故事,成了我與父親的默契。有時候,故事沒念完我就睡著了。有時候,故事念完了我還沒睡著,父親也不再念下去,他走出房間和母親在客廳里輕聲地聊天、看電視。我就躺在床上,聽著客廳里輕微的噪音,回顧剛才的故事內容,然后放任思緒被想象力描繪的駿馬拉著,在腦海中狂放地飛馳。
我不是個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小孩兒,只要有睡前故事,父母就可以避免“十萬個為什么”持續轟炸,但繪本總有讀完的一天。這天,父親因為沒有及時采買新的故事繪本,只好拿從前講過的故事來應付,我并沒有妥協。他看著天花板上的燈罩呆了一會兒,忽然起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翻到中間靠后的部分開始念了起來。本以為他要拿學生時代的課本來應付我,沒想到聽了幾句還真是個動人的故事。后來,我從書架上把那本書重新抽出來,前前后后翻了幾遍也沒看出來那是一本什么書,只記得紙張上印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沒有插圖,沒有漢語拼音,以我當時的知識水平還沒辦法把那個凄美的愛情故事從字里行間找出來,他那晚念的是牛郎織女的故事。如果父親沒有看到上面這段文字,他一定想不起來那個柔情似水、佳期如夢的夜晚。
上小學后,睡前故事就被小學生優秀作文給替代了。我清晰地記得父親給我買的第一本作文書是紅色的封面,正中間印了一只肥肥的手握著一支鉛筆,封皮上寫著“小學生作文起步”,作者是楊冰晶。自那之后,童話故事功成身退,優秀作文成了父親親子時光的主旋律,有時候他也會從雜志上選一些勵志小故事來啟發我。六年級那年,父親因為工作要長期出差。至此,他持續了多年的睡前朗讀工作,光榮地結束了。為了填補睡前時段的文學空白,我每天堅持背兩首古詩,父母并沒有過多地擔心我的課業,也許要感謝那些古詩了。只是沒想到,在那之后,我的睡前故事就徹底終結了。中學時期,我每天被課后作業壓得喘不過氣來,睡得比父母還晚,更沒有機會聽父親講睡前故事了。初二那年,他從單位帶回來一本有點厚度的雜志,橙色的封面上印著一條被晚霞染紅的高速公路,兩側是云南特有的紅土地,襯得畫面更加熱烈,右上角簡潔地寫著三個字:“八月風”。那天晚上,我完成家庭作業大概已經是凌晨十二點多了,看了一眼放在梳妝臺上的《八月風》,隨手翻了下目錄,里面都是與筑路人有關的故事。在這本雜志里,我第一次看了愛情主題的小說。即便窗外夜色深沉,但我饒有興味地連著看了幾個短篇。過了幾天,父親問我要閱讀反饋,我坦率地回答:“好看!”他沒說什么,只是笑笑。
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是個很有個性的中年女性,第一天上課她就交代我們,語文作業是每天一篇小作文,她稱之為“練筆”,題目自擬,主題自選,500字左右。如果語文老師課后沒有布置家庭作業,那么作業只有“練筆”,如果布置了其他作業,“練筆”也不能停,寒暑假作業也是每天一篇“練筆”。得益于她的培養方案,初中三年,我積累了近一千篇小作文。天上地下,花鳥魚蟲,大到人生哲學,小到桌上的一顆飯粒,都能觸發我的創作思路。由于寫作時間大多數是在晚飯后,初入夜幕,云層微涼,月亮像一張薄薄的白色剪紙,被輕輕地貼在天際,等著更濃重的夜色把它熏成透亮淡黃。后來我把這些小作文整理成冊,取名《晴月集》。語文老師不僅督促我們每天練筆,還要求我們做課外閱讀,每周要交一篇讀書報告。那時候《讀者》《青年文摘》就成了我課外閱讀的最佳選擇。看了三年的課外讀物,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題為《姐姐,你是我第一個在雨里等候的女生》的小說。不只怎地,這篇描寫姐弟親情的成長小說對身為獨生子女的我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帶入感。我不止一次地回顧這篇小說,每次看,都幾乎被感動的淚水淹沒。彼時的我也許無法領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式心理描寫,但文學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物敏感而矛盾的內心,或許我也渴望有一個精神上的弟弟來寬容我平時因故作堅強而呈現的不成熟的小錯誤吧。
大學時代,我依興趣報了文學專業,作為專業人士要超然于故事內的文學世界,似乎多了些責任感,少了些主觀代入感。文本里的風花雪月和溫情脈脈,被永遠看不完的作品和理論吞噬了,直到我在法國西北部的魯昂小鎮看到了那座聞名遐邇的教堂。包法利夫人艾瑪和萊昂在魯昂大教堂里幽會的畫面仿佛陽光透過玫瑰窗那般自然地投射在了管風琴下方的空地上。駐足于那方空地,我可以感受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在輕喃。我的同伴是個學口腔醫學的日本留學生,我用簡單的法語給她上了一堂法國經典文學作品賞析課。諾曼底四天的行程被莫泊桑、福樓拜、左拉這些文藝巨擘的名字和作品塞得滿滿當當,相較于我的激動,她非常耐心地聽著我的敘述,似乎是在履行身為同行者的義務。法國的西北部不像南部城市那般受游客青睞,我倒是覺得在最好的季節邂逅了諾曼底。高聳的哥特式教堂、可愛的木頭房子、古老的鐘樓、甜得發膩的蘋果撻、涼爽的夏風,再加上一個寬容而隨和的同伴,讓那個夏天被一條金燦燦的絲帶纏繞著,每當記憶的開關被打開,它就會從腦海里眾多的時光膠片中脫穎而出,重新閃耀出奪目的光彩。
在法國,我雖然沒有以文學為業,但從來沒有擱置對文學的喜愛。留學的那幾年,我重拾了寫日記的習慣。有時用中文寫,有時用法文寫,有時中法夾雜,或記敘、或抒情。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個初春的早上,踩著厚厚的青草,站在電車的終點站,望著滿眼新綠,聞到了生命特有的氣息;我記得那個仲夏的午后,在英吉利海峽南側的海岸線上,海鷗的叫聲和著岸邊石子被拍打得嘎吱作響的節奏,我陶醉在海天一色的壯闊中,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贊嘆被聳立在懸崖上的小教堂里傳來的鐘聲敲打著,震碎在湛藍的海面上,伴著波濤的韻律,化成粼粼波光跳躍著游向海的深處。我還記得當三色堇在吸收了一天的光照而更加舒展時,兩個女學生各自拿著一個甜筒,興致盎然地站在十四世紀的老房子前拍照留念。她倆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日本人,操著還算流利的法語談天說地,聊文化、聊歷史、聊地理、聊美食,慢悠悠地走在被太陽曬得發亮的石板路上……這些美好的記憶都被仔細地收錄在柔軟的文字里。不論過去多久,重新翻閱由一個個文字符碼串聯起來的記憶,溫故它們背后建構的強大的所指,總是美得令人心醉。透過字里行間,我可以看見一望無際的薰衣草花田,散發著夏日閑適的香氣撲面而來;可以聽見海浪卷著來自地心深沉的力量,拍在海岸邊的鵝卵石上;可以聞到櫥窗里五顏六色的小點心,被教堂管風琴厚重的音弦包裹著送到餐桌前。
我的導師幾年前開過一個講座,題目是“文學是弱者的偉業”。他談到童年的文學記憶對他后來學術道路的影響,讓有著多年睡前故事陶養的我十分動容。老師還說早年曾經凌晨四點起床,翻山越嶺去趕車,看著車子從眼前開走,只能站在原地嘆息。雖然沒有相同的經歷,但我能體會那種差之毫厘的無可奈何。文學總是能通過一些不經意的感動,在有著不同生活經歷的人之間,輕松地建立起一種妙不可言的共情。
文學可以是關乎江山社稷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可以是美人“淚眼問花花不語”的哀怨。對我而言,文學是童年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是成長過程中匆忙收割的美好回憶,是未來職業生涯的榮譽。文學的種子早在幼年時期就通過日復一日的睡前故事,播種在我稚嫩的夢里,多年來不斷給予我精神滋養,讓我收獲感動與幸福。我很慶幸今生有文學入夢,愿看了我的故事的你也能從文字中汲取更多的不易察覺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