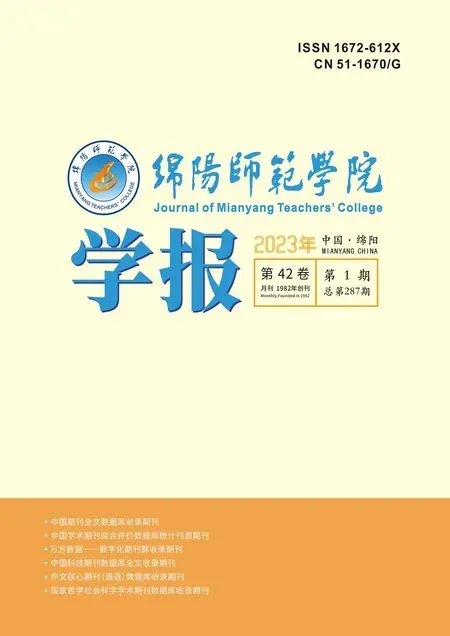先秦“盾”字考
蘇 櫟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盾”是漢語常用字之一。同“戈”“矛”等字一樣,“盾”本為軍語用字。盾作為古代最重要的防御武器,在軍事活動中有著極大的作用,幾乎作為戰爭必備武器而存在。語言作為對社會現實的反映,盾的使用促使用來指稱相關概念的字也隨之產生。“盾”產生時間非常早,殷商甲骨文已見,經過演化發展,在西周中晚期逐漸定型。同時,由于盾作為武器從古到今歷代不廢,“盾”字也處于被不斷使用并發展的過程,在歷代文獻中都保持了較高的使用頻率。凡涉及“盾牌”概念的,大多回避不開“盾”字。產生時間早、使用頻率高、持續時間長,使得“盾”廣為人們熟知,最終進入了漢語常用字匯,這種發展在先秦就已經完成了。

二、毌

“毌”的卜辭義沒有用來指稱“盾牌”的,《甲骨文字典》釋之為“方國名”和“疑為祭名”[2]755,此言確然。“毌”亦可作爵名,卜辭中有“侯毌(盾)”(《合集》03354、03355)②數例,或可作人名,但均不表“盾牌”義。相關詞義金文中始見,“毌”有“秉毌戈”(《集成》10870)、“毌斧”(《集成》11767)③等例,“盾”有“俘戎兵盾矛戈弓”例[5]242,但總的來說相關文例較少。




綜合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干”正反同詞現象的產生,是二者用字不同的結果。郭錫良先生指出:“反義為訓、美惡同辭的說法實際上是傳統訓詁學在沒有弄清某些辭的詞義演變的情況下而作出的一種以今義釋古義的現象。”[12]258“干”的“犯”義與“捍”義最初并非由同一個字來承擔的,而是分別由“干”和“”來表達。卜辭“干”表“捕獵武器”當是無誤,后來引申出了“犯”義;而作“盾牌”義的字本為“”,后來引申出了“捍”義。《說文解字注》云:“干戈字本作。干,犯也。,盾也。俗多用干代,干行而廢矣。”[8]630所言甚是。“干”有“捍”義實為后世假借所致,本義實非“盾牌”。上文說過卜辭合體象形字源于作“”,或作“”,后人因不識二字而以為“盾”古字作“瞂”,“瞂”實為后起形聲字。但與并不相同,隸定后的“毌”與“”或“”有別。“毌”“干”“”上古屬見母,“”字依王力先生觀點則屬于匣母元部[13]578,“毌”“”為見匣旁紐、疊韻,二者不為同一字,于省吾先生也持此說[6]9.946。故郭沫若先生以為“毌”也為“干”,應是未明此處字作“”,“干”則是“”后來的借字。《金文編》卷三“干”下作(豦簋)[5]130,釋為“干戈”,“干”為“盾牌”義無疑。這說明很可能西周時期“干”已經用來借指“”。之后經過發展,文獻中“干”徹底代替了“”。《廣韻》“上平聲寒部”下“”作“古寒切”,可證“干”已經完全與“”相同了。
五、盾;楯

六、結語

注釋:
① 本文黑底甲金文圖片,均引自北京師范大學“漢字全息資源應用系統”。另文內古籍語料如《詩經》《韓非子》《史記》《爾雅》《釋名》及字書《說文解字》《玉篇》《說文解字系傳》《說文系傳考異》、韻書《集韻》等未標出處者皆見于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制作V7.0)。
② 全文所言《合集》均為《甲骨文合集》略語。
③ 全文所言《集成》均為《殷周金文集成》略語。
④ 《古文字詁林》凡12冊,故標注引文時頁數前數字為冊數。

⑥ 讀如“干”或讀如“毌”,均見母元部無疑。
⑦ 詳見向熹《簡明漢語史(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第59頁。
⑧ 詳見羅振玉《遼居乙稿》石印本1931,第25-26頁。
⑨ 筆者所調查的先秦文獻為《楚辭》《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春秋左氏傳》《管子》《國語》《韓非子》《老子》《禮記》《六韜》《呂氏春秋》《論語》《孟子》《墨子》《商君書》《尚書》《申子》《慎子》《詩經》《司馬法》《孫臏兵法》《孫子》《尉繚子》《吳子》《孝經》《逸周書》《晏子春秋》《儀禮》《戰國策》《周禮》《莊子》,共3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