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危局中挽救中國(guó)革命: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的歷程及作用
魏德平
(陜西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毛澤東對(du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杰出貢獻(xiàn)。《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lǐng)導(dǎo)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lǐng)導(dǎo)執(zhí)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zhuǎn)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zhàn)略和各項(xiàng)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jī)中挽救中國(guó)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guó)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duì)指明堅(jiān)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zhǎng)時(shí)間。”[1]299長(zhǎng)征結(jié)束之際,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就是反映《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強(qiáng)調(diào)的“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jī)中挽救中國(guó)革命”的重要史實(shí)。然而,權(quán)威版本的《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等對(duì)這段歷史的記載卻較為簡(jiǎn)要和概括。①參見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4 年版;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3 年版。由于各種復(fù)雜原因,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這段基本史料完整、敘事邏輯清晰的黨史上的重大史實(shí)也受到一些質(zhì)疑。一些歷史親歷者和學(xué)者對(duì)這段歷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曾提出過異議,如毛澤東是否下令“刀下留人”制止“陜北肅反”惡性蔓延。②參見何方:《送劉英大姐遠(yuǎn)行》,《何方談史憶人:紀(jì)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7 頁(yè);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5—136 頁(yè)。筆者曾專門對(duì)毛澤東下令“刀下留人”制止“陜北肅反”基本史實(shí)進(jìn)行考辨,回應(yīng)了關(guān)于該問題的一些主要觀點(diǎn)。[2]筆者在繼續(xù)從事相關(guān)問題研究的過程中逐漸認(rèn)識(shí)到,要對(duì)此問題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認(rèn)識(shí),就必須提高研究站位,擴(kuò)展研究視角,要將該問題研究與中國(guó)革命發(fā)展特別是中共克服中國(guó)革命危局聯(lián)系起來(lái)。這樣既可以克服考證具體事件時(shí)可能存在的以“碎片化”凸顯研究?jī)r(jià)值的傾向,也可以從宏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構(gòu)建更為清晰、完整和有說(shuō)服力的歷史敘事。有鑒于此,筆者以毛澤東成功應(yīng)對(duì)中國(guó)革命“最大的困難”,隨即果斷下令制止“陜北肅反”惡性蔓延和領(lǐng)導(dǎo)粉碎國(guó)民黨“圍剿”,最后成功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為基本歷史線索,深入分析毛澤東如何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以期進(jìn)一步豐富和深化對(duì)這段歷史的既有研究。
一、毛澤東遭遇中國(guó)革命“最大的困難”
長(zhǎng)征期間,中共中央與張國(guó)燾及其領(lǐng)導(dǎo)的紅四方面軍會(huì)師后,雙方即圍繞政治路線和軍事戰(zhàn)略等發(fā)生“北上”還是“南下”的分歧和爭(zhēng)論。中共中央為團(tuán)結(jié)張國(guó)燾,促使其執(zhí)行“北上”戰(zhàn)略,對(duì)其做了耐心的爭(zhēng)取工作。但是,張國(guó)燾并未接受中共中央的政治和軍事決策,公開挑戰(zhàn)中共中央權(quán)威,最終導(dǎo)致紅軍公開分裂,迫使中共中央和部分中央紅軍單獨(dú)執(zhí)行“北上”戰(zhàn)略。張國(guó)燾對(duì)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遭遇中國(guó)革命“最大的困難”。
中共中央與張國(guó)燾在長(zhǎng)征途中會(huì)合后,雙方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主要負(fù)責(zé)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lái)等和張國(guó)燾在中共政治路線、紅軍發(fā)展戰(zhàn)略方向等方面逐漸發(fā)生尖銳分歧和激烈爭(zhēng)論。雙方的矛盾最后逐漸聚焦到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是“北上”還是“南下”這一戰(zhàn)略抉擇上。1935 年9 月9 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guó)燾,在批評(píng)其“南下”戰(zhàn)略的同時(shí),也簡(jiǎn)要陳述了“北上”戰(zhàn)略設(shè)想:“陳③指陳昌浩,時(sh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談?dòng)衣奋娔舷码娏睿醒胝J(rèn)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xiàn)懇切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yǎng)都對(duì)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huán)境。中央認(rèn)為北上方針絕對(duì)不應(yīng)改變,左路軍應(yīng)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shí),可以西渡黃河,占領(lǐng)甘、青交通新地區(qū),再行向東發(fā)展。”[3]932-933但是,中共中央的“北上”戰(zhàn)略方針并沒有得到張國(guó)燾的贊同和支持。相反,張國(guó)燾在當(dāng)日致中共中央的回電中對(duì)“北上”戰(zhàn)略設(shè)想還明確提出了批評(píng)。張國(guó)燾在回電中指出:“時(shí)至今日,請(qǐng)你們平心估計(jì)敵力和位置,我軍減員、彈藥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zhàn)而擊破之。敵是否有續(xù)增可能。”“左路二十五、九三兩師,每團(tuán)不到千人,每師至多千五百戰(zhàn)斗員,內(nèi)中病腳者占三分之二。再北進(jìn),右路經(jīng)過繼續(xù)十天行軍,左路二十天,減員只在半數(shù)以上。”張國(guó)燾接著分析“北上”可能出現(xiàn)的三種后果:“向東突出岷、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wú)止境的運(yùn)動(dòng)戰(zhàn),冬天不停留的行軍,前途如何?”“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wěn)腳跟?”“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wú)南返之機(jī)。背告[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3]933可見,對(duì)于中共中央的“北上”戰(zhàn)略計(jì)劃,張國(guó)燾不但不認(rèn)同、不準(zhǔn)備執(zhí)行,而且作了針鋒相對(duì)的質(zhì)疑和批評(píng)。
隨即,張國(guó)燾激化矛盾,造成中共黨和軍隊(duì)公開分裂。1935 年9 月9 日,張國(guó)燾電令陳昌浩,如果中共中央不同意他的“南下”戰(zhàn)略,則要陳昌浩扣留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強(qiáng)行率領(lǐng)右路軍南下。雖然這場(chǎng)迫在眉睫的危機(jī)在葉劍英及時(shí)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通報(bào)消息后,被毛澤東等機(jī)智化解,毛澤東等人也迅速脫離險(xiǎn)境,[4]107-109但這場(chǎng)危機(jī)后張國(guó)燾采取了更為公開的挑戰(zhàn)中共中央權(quán)威的政策。9 月10 日,張國(guó)燾向部隊(duì)發(fā)出“南下”宣傳號(hào)召:“同志們!北進(jìn)已經(jīng)失去了時(shí)機(jī),我們的紅軍決定大舉南下,南下的戰(zhàn)略方針是首先消滅四川軍閥赤化全四川。”[3]934這無(wú)異于將中共高層的分歧公開化。中共中央和張國(guó)燾在之后幾天一直圍繞“南下”和“北上”頻繁發(fā)電報(bào),都想說(shuō)服對(duì)方,但結(jié)果依然是各持己見,難以達(dá)成共識(shí)。[3]941隨后,張國(guó)燾公開對(duì)中共中央“北上”戰(zhàn)略和中共中央主要領(lǐng)導(dǎo)人進(jìn)行批判。時(shí)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1935 年10 月5 日,張國(guó)燾在卓木碉(腳木足)召開高級(jí)干部會(huì)議。出席會(huì)議的有朱德、張國(guó)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王樹聲、周純?nèi)⒗钭咳弧⒘_炳輝、余天云等軍以上干部,大約四五十人。會(huì)址在一座喇嘛寺廟里。在這個(gè)會(huì)上,張國(guó)燾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指責(zé)中共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實(shí)行戰(zhàn)略退卻,是‘政治路線的錯(cuò)誤’,而不單是軍事路線問題”。“北上”的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被敵人的飛機(jī)、大炮‘嚇破了膽’,對(duì)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繼續(xù)其北上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直至發(fā)展到‘私自率一、三軍團(tuán)秘密出走’,這是‘分裂紅軍的最大罪惡行為’”。張國(guó)燾還從組織上公開否認(rèn)“南下”黨政軍機(jī)關(guān)與中共中央的隸屬關(guān)系。“他宣布中央已經(jīng)‘威信掃地’,‘失去領(lǐng)導(dǎo)全黨的資格’,提倡仿效列寧和第二國(guó)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shí)中央’,要大家表態(tài)。”“接著,就宣布了‘臨時(shí)中央’的名單,以多數(shù)通過的名義,形成了‘決議’。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lái)、張聞天、博古的黨籍。”[5]299-300在此過程中,隨同張國(guó)燾“南下”的某些原中央紅軍領(lǐng)導(dǎo)人和高級(jí)將領(lǐng)也公開支持“南下”戰(zhàn)略,并批評(píng)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這對(duì)張國(guó)燾“另立中央”活動(dòng)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張國(guó)燾對(duì)中共中央的發(fā)難和指責(zé)無(wú)疑對(duì)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當(dāng)時(shí),中共中央只有在實(shí)踐上突破嚴(yán)峻形勢(shì)考驗(yàn),才能有力化解黨內(nèi)高層的意見分歧,震懾張國(guó)燾的分裂活動(dòng),進(jìn)一步鞏固“北上”戰(zhàn)略,維護(hù)自身權(quán)威。
中共中央率領(lǐng)中央紅軍單獨(dú)“北上”后,面臨許多嚴(yán)峻考驗(yàn)。中共中央雖然機(jī)智地?cái)[脫了張國(guó)燾的威脅并迅速脫離險(xiǎn)境,但是紅軍隊(duì)伍的公開分裂也影響了當(dāng)時(shí)堅(jiān)持“北上”部隊(duì)的士氣。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中央紅軍所屬紅三軍團(tuán)政治委員的楊尚昆回憶:自從1935 年9 月9 日,中共中央擺脫張國(guó)燾威脅后,“本來(lái),中央不讓向下面隨便講張國(guó)燾鬧分裂的事,但是,許多中下級(jí)干部還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緒不太好”。[6]151并且,當(dāng)時(shí)中共中央還曾針對(duì)革命發(fā)展可能遭遇的嚴(yán)重困難作過安排部署。為預(yù)防萬(wàn)一,毛澤東曾動(dòng)員參加長(zhǎng)征的林伯渠、謝覺哉等幾位年紀(jì)比較大的老干部想辦法離開部隊(duì),保存實(shí)力,再謀發(fā)展。在翻越大雪山后,毛澤東曾對(duì)謝覺哉說(shuō):“看來(lái)咱們的部隊(duì)是要長(zhǎng)期無(wú)后方地打游擊,你們年紀(jì)大了,在部隊(duì)上長(zhǎng)期拖下去,會(huì)把你們拖死的。到了甘肅以后,你們可以自找掩護(hù)關(guān)系,到白區(qū)去做黨的地下工作,請(qǐng)預(yù)作考慮。”[7]2126快到哈達(dá)鋪前,毛澤東的態(tài)度依然很謹(jǐn)慎。林伯渠回憶:“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快走到哈達(dá)鋪時(shí),毛澤東同志把徐老、董老、謝老和我找去,對(duì)我們說(shuō):‘紅軍到甘肅以后,你們幾位老人是不是化裝輾轉(zhuǎn)到南方去,找我們留在蘇區(qū)的地下黨,不然你們會(huì)被長(zhǎng)途行軍拖垮的。’”[8]119由此可見,在中共中央堅(jiān)持和踐行的“北上”戰(zhàn)略與張國(guó)燾“南下”戰(zhàn)略對(duì)立相持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尤其是當(dāng)“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遇到一定困難時(shí),毛澤東等人已經(jīng)作了經(jīng)受嚴(yán)峻考驗(yàn)的打算。
在長(zhǎng)征途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要應(yīng)對(duì)國(guó)民黨軍隊(duì)的圍追堵截,還要解決黨內(nèi)張國(guó)燾的公開挑戰(zhàn),其間張國(guó)燾對(duì)中共中央的威脅在某種程度上更甚于國(guó)民黨。張國(guó)燾問題對(duì)中共中央和中國(guó)革命造成了極為嚴(yán)重的后果,情勢(shì)一度發(fā)展到千鈞一發(fā)的程度。毛澤東后來(lái)對(duì)張國(guó)燾問題進(jìn)行定性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張國(guó)燾“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9]668中共中央與張國(guó)燾的斗爭(zhēng)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60 年10 月,曾在延安采訪過毛澤東的國(guó)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再次訪問中國(guó),并采訪了毛澤東。在他們談話時(shí),斯諾問道:“在你一生中,當(dāng)你觀察中國(guó)革命的命運(yùn)時(shí),哪個(gè)時(shí)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時(shí)期?”毛澤東回答:“我們是有過那樣的時(shí)候的,……張國(guó)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10]213由此可見,長(zhǎng)征中張國(guó)燾問題對(duì)毛澤東影響之深遠(yuǎn)。現(xiàn)在回顧歷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定和踐行的“北上”戰(zhàn)略,是高瞻遠(yuǎn)矚和改變中國(guó)革命命運(yùn)的正確抉擇。而在當(dāng)時(shí),張國(guó)燾公開批判“北上”戰(zhàn)略,進(jìn)而否定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使中國(guó)革命陷于嚴(yán)重危局。
二、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之際,根據(jù)地外部正遭遇國(guó)民黨規(guī)模空前的第三次“圍剿”,內(nèi)部“陜北肅反”也在惡性膨脹和蔓延。這導(dǎo)致陜甘根據(jù)地處于嚴(yán)重危險(xiǎn)境地。中共中央率領(lǐng)中央紅軍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立即開始鞏固根據(jù)地的斗爭(zhēng)。在此過程中,毛澤東領(lǐng)導(dǎo)粉碎了國(guó)民黨的第三次“圍剿”,解除了根據(jù)地外部軍事威脅,還指導(dǎo)解決了根據(jù)地內(nèi)部“陜北肅反”問題,鞏固了根據(jù)地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
中共中央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毛澤東立即著手領(lǐng)導(dǎo)粉碎國(guó)民黨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解決根據(jù)地外部威脅。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中央紅軍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前夕,國(guó)民黨正準(zhǔn)備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發(fā)動(dòng)規(guī)模空前的第三次“圍剿”。1935 年9 月26 日,國(guó)民黨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蔣介石兼任總司令,張學(xué)良為副總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quán),統(tǒng)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山西等省的國(guó)民黨軍隊(duì)。國(guó)民黨軍在西(安)蘭(州)公路和平?jīng)鲋翆幭牡墓飞喜贾梅怄i線。[9]475國(guó)民黨方面部署在陜甘根據(jù)地周圍的軍隊(duì)有張學(xué)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陜北井岳秀、高桂滋等部,還有國(guó)民黨中央軍系統(tǒng)胡宗南、毛炳文等部。國(guó)民黨直接用于第三次“圍剿”的兵力有十余萬(wàn)人。9 月中旬,國(guó)民黨軍開始發(fā)動(dòng)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中共中央率領(lǐng)中央紅軍抵達(dá)根據(jù)地之時(shí),“圍剿”陜甘根據(jù)地的國(guó)民黨軍隊(duì)雖然在勞山戰(zhàn)役和榆林橋戰(zhàn)役中受到兩次沉重打擊,但“圍剿”依然沒有被粉碎,軍事形勢(shì)仍然嚴(yán)峻。時(shí)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彭德懷回憶:“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到達(dá)陜北吳起鎮(zhèn),正是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張學(xué)良十余師向陜北蘇區(qū)紅軍進(jìn)行第三次‘圍剿’之時(shí)。敵第一線有董英斌軍四個(gè)師集結(jié)慶陽(yáng),準(zhǔn)備由慶陽(yáng)、合水夾葫蘆河?xùn)|進(jìn);王以哲三個(gè)師集結(jié)洛川,準(zhǔn)備北進(jìn);甘泉、延安各一個(gè)師駐守。第二線有西北軍楊虎城部?jī)蓚€(gè)軍,還有東北軍數(shù)師,當(dāng)時(shí)位置不明。”[11]176當(dāng)時(shí)陜甘根據(jù)地主力紅軍主要是由中央紅軍改編的紅一軍團(tuán)和原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改編的紅十五軍團(tuán)。紅一軍團(tuán)有七千余人,紅十五軍團(tuán)約計(jì)六千人。紅一軍團(tuán)剛經(jīng)歷長(zhǎng)征,亟需休整。紅十五軍團(tuán)當(dāng)時(shí)也屢經(jīng)戰(zhàn)斗,加之受根據(jù)地“陜北肅反”問題影響,軍心不穩(wěn),處境艱難。由此可見,中共中央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之際,陜甘地區(qū)國(guó)共軍事力量對(duì)比懸殊,陜甘根據(jù)地正面臨著極為沉重的軍事壓力。
針對(duì)上述形勢(shì),毛澤東積極謀劃和領(lǐng)導(dǎo)陜甘根據(jù)地反“圍剿”軍事工作。毛澤東抵達(dá)吳起鎮(zhèn)后就開始部署反“圍剿”軍事計(jì)劃。10 月22 日,毛澤東出席吳起鎮(zhèn)會(huì)議。他在會(huì)上強(qiáng)調(diào):“我們的任務(wù)是保衛(wèi)和擴(kuò)大陜北蘇區(qū),以陜北蘇區(qū)領(lǐng)導(dǎo)全國(guó)革命。”[9]481隨后,毛澤東等即派遣賈拓夫、李維漢等作為先遣隊(duì)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毛澤東進(jìn)駐下寺灣后對(duì)反“圍剿”作了更為周詳?shù)陌才挪渴稹T谙滤聻常珴蓶|、張聞天、周恩來(lái)等進(jìn)一步了解了陜甘根據(jù)地面臨的嚴(yán)峻軍事形勢(shì)。根據(jù)了解到的情況,中共中央于11 月3 日在下寺灣召開了政治局會(huì)議,集中研究反“圍剿”等工作。關(guān)于反“圍剿”軍事問題,毛澤東在會(huì)上作了重要發(fā)言。毛澤東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較適當(dāng),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作戰(zhàn)方針,應(yīng)在這個(gè)月解決第三次‘圍剿’問題,經(jīng)過一個(gè)深冬讓敵人慢慢做堡壘是不好的。同紅十五軍團(tuán)會(huì)合后,紅十五軍團(tuán)編制應(yīng)保存,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因歷史關(guān)系也不要合并。陜甘支隊(duì)可編成紅一軍團(tuán),并成立紅一方面軍。”[9]483關(guān)于中央軍事領(lǐng)導(dǎo)人員組織問題,時(shí)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huì)(名義上稱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并提議由毛澤東擔(dān)任軍委主席。張聞天提出:“大的戰(zhàn)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于戰(zhàn)斗指揮問題,由他們?nèi)珯?quán)決定。”[12]193會(huì)議討論同意張聞天提出的方案。就在當(dāng)日,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發(fā)布通令:“奉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茲委任毛澤東、周恩來(lái)、彭德懷、王稼薔、聶洪鈞、林彪、徐海東、程子華、郭洪濤九同志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lái)、彭德懷為副主席。”[13]387中共中央在下寺灣召開的這次政治局會(huì)議為粉碎國(guó)民黨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奠定了政治基礎(chǔ)和組織基礎(chǔ)。自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軍事工作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肩負(fù)整合陜甘根據(jù)地各種軍事力量投入反“圍剿”,全面領(lǐng)導(dǎo)保衛(wèi)根據(jù)地的軍事重任。隨后,毛澤東率領(lǐng)中央紅軍和陜甘紅軍聯(lián)合粉碎了國(guó)民黨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下寺灣會(huì)議后,毛澤東、周恩來(lái)、彭德懷等迅速南下與徐海東、程子華會(huì)合,隨即安排部署反“圍剿”作戰(zhàn)。11 月21 日,在毛澤東、周恩來(lái)等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和陜甘紅軍聯(lián)合發(fā)起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至24 日戰(zhàn)役結(jié)束。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共殲滅國(guó)民黨軍東北軍一個(gè)師又一個(gè)團(tuán),俘敵五千三百余人,繳槍三千五百余支。11 月30 日,毛澤東在出席紅一方面軍營(yíng)以上干部大會(huì)時(shí)作《直羅戰(zhàn)役同目前的形勢(shì)與任務(wù)》報(bào)告。毛澤東在報(bào)告中對(duì)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作了高度評(píng)價(jià):“中央領(lǐng)導(dǎo)我們,要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jù)地——領(lǐng)導(dǎo)全國(guó)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guó)賊的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根據(jù)地,這次勝利算是舉行了奠基禮。”[14]365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勝利粉碎了國(guó)民黨軍隊(duì)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圍剿”,為根據(jù)地的鞏固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軍事環(huán)境,具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還指導(dǎo)解決了“陜北肅反”問題,鞏固了根據(jù)地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歷經(jīng)長(zhǎng)征轉(zhuǎn)戰(zhàn)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之際,也正是陜甘根據(jù)地內(nèi)部“陜北肅反”惡性擴(kuò)張和急速蔓延之時(shí)。“陜北肅反”嚴(yán)重影響和削弱了陜甘根據(jù)地紅軍內(nèi)部的團(tuán)結(jié)。原陜甘紅軍八十一師師長(zhǎng)賀晉年告訴楊尚昆:“如果中央不來(lái),我們就要同二十五軍他們打起來(lái)了。”[6]153原陜甘紅軍八十一師主要由原陜北紅軍改編而來(lái),尚不是“陜北肅反”的重點(diǎn),肅反的重點(diǎn)是以原紅二十六軍為主改編的紅七十八師。陜甘紅軍與紅二十五軍的矛盾已經(jīng)激化到白熱化的程度。曾任中共陜甘邊特委書記的張秀山回憶:“在陜北的老百姓中,傳說(shuō)紅25 軍是白軍,他們化裝成紅軍來(lái)消滅紅26 軍;紅26 軍的機(jī)關(guān)槍全部被25軍收繳了,紅26 軍的戰(zhàn)士拿著標(biāo)槍、大刀被人用槍逼著去沖鋒送死;劉志丹、張秀山等人已經(jīng)被他們殺害了……”[15]88由于“陜北肅反”惡性蔓延,“26軍、27 軍中發(fā)生了問題,在前方軍心完全動(dòng)搖的時(shí)候,前方軍隊(duì)一連、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點(diǎn)精神都沒有,恐怖、懷疑、準(zhǔn)備暴動(dòng)”。[15]393“陜北肅反”還誘發(fā)了陜甘根據(jù)地的嚴(yán)重危機(jī)。時(shí)任中共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xí)仲勛對(duì)“陜北肅反”的危害有過評(píng)述:“當(dāng)時(shí),蔣介石正在對(duì)陜甘邊區(qū)進(jìn)行第三次‘圍剿’。于是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種怪現(xiàn)象:紅軍在前方打仗,抵抗蔣介石的進(jìn)攻,不斷地取得勝利,‘左’傾機(jī)會(huì)主義路線的執(zhí)行者卻在后方先奪權(quán),后抓人,把劉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來(lái),紅二十六軍營(yíng)以上的主要干部,陜甘邊縣以上的主要干部,幾乎無(wú)一幸免。白匪軍乘機(jī)大舉進(jìn)攻,邊區(qū)日益縮小,引起了群眾的極大疑慮;地主、富農(nóng)乘機(jī)挑撥煽動(dòng),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gè)縣都‘反水’了。根據(jù)地陷入嚴(yán)重的危機(jī)。”[16]427張秀山回憶:“‘左’傾路線執(zhí)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眾的疑慮和恐慌,根據(jù)地人人自危,軍心渙散;地主、富農(nóng)乘機(jī)挑撥煽動(dòng),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gè)縣都‘反水’了(我黨建立的游擊區(qū)和根據(jù)地,在肅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軍閥和國(guó)民黨,‘紅區(qū)’變成了‘白區(qū)’);白匪乘機(jī)大舉進(jìn)攻,根據(jù)地日益縮小,陷入嚴(yán)重危機(jī)。”[15]89由于“陜北肅反”惡性擴(kuò)張蔓延,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zhǎng)征轉(zhuǎn)戰(zhàn)至陜甘根據(jù)地之際,陜甘根據(jù)地的存亡已到了千鈞一發(fā)的危機(jī)時(shí)刻。
毛澤東獲悉“陜北肅反”的情況后果斷下令制止肅反繼續(xù)惡性蔓延。中共中央經(jīng)歷長(zhǎng)征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隨即獲悉“陜北肅反”正在惡性蔓延。在吳起鎮(zhèn)期間,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通過和陜甘根據(jù)地部分干部群眾接觸,才逐漸獲悉“陜北肅反”詳情。10 月20 日,毛澤東接見活動(dòng)在吳起鎮(zhèn)的一支游擊隊(duì)負(fù)責(zé)人張明科后,才得知?jiǎng)⒅镜さ缺淮恫⑶谊P(guān)押在瓦窯堡的情況。[17]413在張明科的介紹下,毛澤東又于22 日晨接見了了解“陜北肅反”詳情的陜甘邊區(qū)游擊隊(duì)第二路政委龔逢春。毛澤東從龔逢春處得知陜甘根據(jù)地正在進(jìn)行肅反,劉志丹等陜甘根據(jù)地領(lǐng)導(dǎo)人被逮捕,有些被捕人員已經(jīng)被殺害的消息。[18]160毛澤東當(dāng)即向龔逢春表示要正確解決“陜北肅反”問題。龔逢春回憶:“我還向毛主席匯報(bào)了當(dāng)時(shí)陜北肅反的情況和劉志丹被捕的問題,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見,我認(rèn)為劉志丹等同志不應(yīng)逮捕,我說(shuō)我的看法,劉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關(guān)心陜北的肅反問題,毛主席曾親切的向我說(shuō),中央紅軍和中央到了陜北以后,陜北的肅反問題,劉志丹的問題,都可以得到正確的解決,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19]305毛澤東在獲知“陜北肅反”危急情況后果斷下令制止肅反繼續(xù)惡性蔓延。時(shí)任中央紅軍保衛(wèi)局局長(zhǎng)王首道回憶:“正當(dāng)毛主席緊張部署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時(shí)候,陜甘邊區(qū)的干部和群眾向毛主席反映了一個(gè)嚴(yán)重的情況,一個(gè)多月前,劉志丹、習(xí)仲勛、馬文瑞等大批負(fù)責(zé)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殺害了。對(duì)此,廣大干部群眾無(wú)比義憤,希望毛主席、黨中央公道處理。毛主席仔細(xì)地傾聽了當(dāng)?shù)馗刹咳罕姷姆从澈螅⒓粗赋觯旱断铝羧耍V共度恕C飨f(shuō):我們剛剛到陜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zhàn)斗力很強(qiáng),蘇維埃政權(quán)能鞏固地堅(jiān)持下來(lái),我相信創(chuàng)造這塊根據(jù)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干部,請(qǐng)大家放心,中央會(huì)處理好這個(gè)問題。”[20]166-167隨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派遣李維漢等作為先遣隊(duì)繼續(xù)了解“陜北肅反”等詳情。李維漢對(duì)此有詳細(xì)回顧:“黨中央到了吳起鎮(zhèn)以后,即派賈拓夫①賈拓夫于1934 年代表陜西省委到中央蘇區(qū)參加黨的六屆五中全會(huì)。會(huì)后,他留在中央白區(qū)工作部工作,隨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北上,并任總政破壞部部長(zhǎng)。攜帶電臺(tái),作為先遣隊(duì)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我與他同行。我們?cè)诟嗜滤聻秤龅搅斯闈弥儽碧K區(qū)正在對(duì)紅26 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jìn)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吳起鎮(zhèn)時(shí),曾有同志向黨中央反映陜北肅反和劉志丹被捕的事,現(xiàn)在得到了證實(shí)。我們當(dāng)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黨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lái)解決!”[7]2235在抵達(dá)下寺灣聽取“陜北肅反”詳情匯報(bào)后,“毛主席當(dāng)時(shí)決定,趕快審查釋放,要迅速做”。[21]182毛澤東積極果斷決定制止“陜北肅反”繼續(xù)蔓延為肅反問題的解決創(chuàng)造了條件。
隨后,在毛澤東的積極干預(yù)下,“陜北肅反”問題得到較為妥善的解決。王首道回憶:“由于毛主席和周恩來(lái)副主席等中央負(fù)責(zé)同志正忙于戰(zhàn)役準(zhǔn)備,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派我和劉向三等同志到瓦窯堡去,接管陜甘邊區(qū)保衛(wèi)局的工作,先把事態(tài)控制下來(lái),避免進(jìn)一步惡化。毛主席在下寺灣的一次干部會(huì)上,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我們說(shuō):殺頭不能象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zhǎng)起來(lái),人頭落地就長(zhǎng)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cuò)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diǎn),要慎重處理。”[20]167與王首道同行前去處理“陜北肅反”的劉向三也就此事作過詳細(xì)回憶:“正當(dāng)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lái)副主席指揮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緊張時(shí)刻,當(dāng)?shù)馗刹亢腿罕娤蛎珴蓶|主席反映一個(gè)重要問題:劉志丹同志等領(lǐng)導(dǎo)干部被捕入獄,要求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道處理。毛主席認(rèn)真、仔細(xì)地聽取來(lái)自陜北干部和群眾的呼聲,經(jīng)過認(rèn)真思考研究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當(dāng)即派王首道、賈拓夫和我前往瓦窯堡接管陜甘邊區(qū)肅反工作。當(dāng)王首道同志帶領(lǐng)我們離開下寺灣趕赴瓦窯堡時(shí),毛澤東主席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我們說(shuō):‘殺頭不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zhǎng)起來(lái),人頭落地就長(zhǎng)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cuò)了人,殺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diǎn),要慎重、要做好調(diào)查研究工作。’我們深感任務(wù)緊迫、責(zé)任重大,沒有時(shí)間更多思考和商量就跨馬直奔瓦窯堡。”[22]961935 年11 月10 日,張聞天率領(lǐng)中共中央機(jī)關(guān)入駐瓦窯堡,隨即開始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此時(shí),毛澤東雖然在前方部署和指揮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但仍然關(guān)注“陜北肅反”問題。11 月18 日,毛澤東在前方致電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張聞天、秦邦憲等,請(qǐng)他們?cè)敿?xì)考察“陜北肅反”問題,指出“錯(cuò)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shí)”,[9]487提出要糾正肅反中的錯(cuò)誤。隨后,中共中央經(jīng)過審查,釋放了劉志丹等“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挽救了陜甘根據(jù)地當(dāng)時(shí)的嚴(yán)重危機(jī)。毛澤東對(duì)“陜北肅反”問題的重視以及果斷制止肅反繼續(xù)蔓延的得力舉措是肅反問題能迅速得到解決的重要保證。
毛澤東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投入根據(jù)地反“圍剿”工作,化解了根據(jù)地面臨的嚴(yán)重軍事威脅,給根據(jù)地的鞏固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外部條件。與此同時(shí),毛澤東及時(shí)和迅速介入對(duì)“陜北肅反”問題的處理,制止了肅反進(jìn)一步膨脹和惡化,保全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陜甘根據(jù)地的黨政軍干部。這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鞏固和中共中央在陜甘地區(qū)迅速立足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三、毛澤東推動(dòng)中國(guó)革命轉(zhuǎn)危為安的范例
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對(duì)中國(guó)革命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積極影響。陜甘根據(jù)地的鞏固徹底扭轉(zhuǎn)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zhǎng)征期間被迫不停轉(zhuǎn)戰(zhàn)的窘境,并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紅軍保留了碩果僅存的“落腳點(diǎn)”,為中國(guó)革命復(fù)興提供了重要根據(jù)地。
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革命不斷受挫的窘境。土地革命時(shí)期,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cuò)誤路線統(tǒng)治中共中央后給中國(guó)革命造成嚴(yán)重危害。《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qiáng)調(diào):“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jù)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qū)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qū)。‘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zhǎng)征的軍事行動(dòng)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cuò)誤,使紅軍繼續(xù)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shù)革命根據(jù)地(閩浙贛區(qū)、鄂豫皖區(qū)、湘鄂贛區(qū)、湘贛區(qū)、湘鄂西區(qū)、川陜區(qū))和廣大白區(qū)的工作,也同樣由于‘左’傾路線的統(tǒng)治而陷于失敗。”[23]86《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明確指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領(lǐng)導(dǎo)中國(guó)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zhēng)的過程中,經(jīng)歷了國(guó)共合作的北伐戰(zhàn)爭(zhēng),土地革命戰(zhàn)爭(zhēng),抗日戰(zhàn)爭(zhēng)和全國(guó)解放戰(zhàn)爭(zhēng)這四個(gè)階段,其間經(jīng)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嚴(yán)重失敗的痛苦考驗(yàn)。”[1]295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功應(yīng)對(duì)“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嚴(yán)重失敗的痛苦考驗(yàn)”,尤其是應(yīng)對(duì)1934 年第三次“左”傾錯(cuò)誤路線造成的“嚴(yán)重失敗的痛苦考驗(yàn)”時(shí),毛澤東發(fā)揮了關(guān)鍵性作用。長(zhǎng)征期間,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處境艱難,甚至在獲悉陜北有蘇區(qū)根據(jù)地并向陜甘根據(jù)地進(jìn)軍后情況仍然比較緊張。彭德懷回憶:“在哈達(dá)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bào)紙上看到陜北有劉志丹蘇區(qū)根據(jù)地,很高興。從哈達(dá)鋪到保安縣,還有千余里,要經(jīng)過六盤山脈。那時(shí)干部和戰(zhàn)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還必須戰(zhàn)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因此,部隊(duì)不斷減員,“在哈達(dá)鋪整編時(shí)一萬(wàn)四千余人,到吳起鎮(zhèn)只剩七千二百人”。[11]174-175但是,當(dāng)中央紅軍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境遇有了明顯改觀。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進(jìn)駐陜甘根據(jù)地后才獲得了難得的休整和補(bǔ)給機(jī)會(huì)。時(shí)任中央紅軍陜甘支隊(duì)司令部作戰(zhàn)科科長(zhǎng)伍修權(quán)回憶:“吳起鎮(zhèn)戰(zhàn)斗結(jié)束,我們前進(jìn)到保安,一方面軍的長(zhǎng)征就宣告勝利結(jié)束。”“陜北的10月已經(jīng)下雪了,我們穿的還是單衣短褲。保安房子很少,只有些窯洞。部隊(duì)到后,第一個(gè)來(lái)歡迎我們的是白如冰,他是陜北紅軍的后勤部長(zhǎng)。他們已經(jīng)為我們準(zhǔn)備了糧食和衣服,每人發(fā)了一套棉衣。這真是雪里送炭!長(zhǎng)征以來(lái),一路行軍,好久沒有正式吃過一頓飽飯。因?yàn)椤蟆瘍A路線錯(cuò)誤,我們丟掉了根據(jù)地,屁股沒有坐處,吃盡了苦頭。這時(shí)吃到根據(jù)地群眾送的小米稀飯,真像過年一樣,高興得很。許多同志捧著飯碗,就流下了淚水。”[24]100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能進(jìn)駐陜甘根據(jù)地結(jié)束長(zhǎng)征與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密不可分。原陜甘根據(jù)地創(chuàng)建人張策回憶:“一九三五年十月,黨中央經(jīng)過艱苦的長(zhǎng)征,勝利到達(dá)陜甘根據(jù)地。當(dāng)時(shí)中央首先著手解決的有兩大問題:其一,迅速組織紅軍力量粉碎國(guó)民黨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圍剿’;其二,立即派人制止當(dāng)時(shí)陜甘晉省委所推行的錯(cuò)誤肅反。前者經(jīng)過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的全勝,粉碎了國(guó)民黨對(duì)陜甘根據(jù)地的‘圍剿’,后者由于糾正了錯(cuò)誤肅反,釋放了數(shù)十名被關(guān)押的革命骨干,消除了根據(jù)地我黨、我軍內(nèi)部存在的危機(jī),取得了革命陣營(yíng)內(nèi)部的團(tuán)結(jié)。這就使黨中央在陜甘根據(jù)地這塊土地上站穩(wěn)了腳跟。”[25]64-65如前所述,這些工作都與毛澤東密不可分,甚至在某些具體工作中毛澤東還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主導(dǎo)作用。正是由于毛澤東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果斷制止“陜北肅反”惡性蔓延和領(lǐng)導(dǎo)粉碎國(guó)民黨“圍剿”,才使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贏得了一個(gè)寶貴的補(bǔ)給休整的關(guān)鍵時(shí)機(jī)。
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為中國(guó)革命保存了碩果僅存的“落腳點(diǎn)”。陜甘根據(jù)地主要領(lǐng)導(dǎo)人大都對(duì)毛澤東在鞏固陜甘根據(jù)地過程中的貢獻(xiàn)作過高度評(píng)價(jià)。習(xí)仲勛強(qiáng)調(diào):“西北根據(jù)地的歷史地位是很關(guān)鍵,但當(dāng)時(shí)如果黨中央、毛主席不來(lái),這個(gè)根據(jù)地也不復(fù)存在了。當(dāng)時(shí),陜甘根據(jù)地外受國(guó)民黨重兵‘圍剿’,內(nèi)遭‘左’傾路線的危害,開展了錯(cuò)誤肅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監(jiān)禁,許多優(yōu)秀的黨員、干部、知識(shí)分子和下級(jí)軍事指揮員都被槍殺、活埋。他們也已經(jīng)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準(zhǔn)備活埋我們。是黨中央、毛主席到達(dá)陜北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 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26]“毛主席挽救了陜北的黨,挽救了陜北革命。”[16]428張秀山曾說(shuō):“當(dāng)我們從牢獄中走出來(lái)時(shí),個(gè)個(gè)淚流滿面,對(duì)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紅軍充滿了無(wú)限的感激之情,是黨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毛澤東說(shuō):是中央救了陜北,也是陜北救了中央。但對(duì)我們西北的同志來(lái)說(shuō),心中永遠(yuǎn)不可忘懷的是黨中央救了陜北。如果不是黨中央及時(shí)趕到,采取正確果斷措施,西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根據(jù)地和紅軍還能存在嗎?”[15]90陜甘根據(jù)地的保存和鞏固在中國(guó)革命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央紅軍重要將領(lǐng)黃克誠(chéng)對(duì)此評(píng)價(jià)道:“我們從江西出發(fā)長(zhǎng)征,艱苦跋涉兩萬(wàn)多里,一路上連共產(chǎn)黨的支部都很少遇到過,真沒有想到會(huì)在陜北找到一塊革命根據(jù)地。這無(wú)異于絕處逢生,使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歷史是按照其必然規(guī)律在發(fā)展,但往往表現(xiàn)出許多偶然性。陜北根據(jù)地當(dāng)時(shí)并不大,陜北紅軍也比較弱小,且處于國(guó)民黨軍隊(duì)的‘圍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到此,陜北革命根據(jù)地要想堅(jiān)持下來(lái)是很困難的。然而,正是這塊不太大的革命根據(jù)地,此時(shí)卻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使中央紅軍得以站住腳跟,休養(yǎng)生息,重整旗鼓,為爾后創(chuàng)建紅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27]160-1611945 年4 月21 日,毛澤東在作《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的工作方針》報(bào)告時(shí)指出:“歷史的教訓(xùn)就是要我們謙虛謹(jǐn)慎。過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勝利。但是可惜沒有勝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萬(wàn)黨員、幾十萬(wàn)軍隊(duì),頭大了,急躁起來(lái)了,結(jié)果只剩了一個(gè)陜北。有人說(shuō),陜北這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shuō),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shuō)陜北是兩點(diǎn),一個(gè)落腳點(diǎn),一個(gè)出發(fā)點(diǎn)。”[28]297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使中國(guó)革命大本營(yíng)從南方轉(zhuǎn)移到西北地區(qū),并成為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抗日戰(zhàn)爭(zhēng)、解放戰(zhàn)爭(zhēng)的指揮中樞,對(duì)推進(jìn)新民主主義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時(shí)期,陜甘根據(jù)地的存亡事關(guān)中國(guó)革命成敗。毛澤東在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關(guān)鍵性作用。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的歷程是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從危機(jī)中挽救中國(guó)革命”的重要范例。
四、結(jié) 語(yǔ)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毛澤東在推動(dòng)中國(guó)革命發(fā)展進(jìn)程中作出了卓越貢獻(xiàn)。毛澤東多次在關(guān)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中國(guó)革命危急存亡的關(guān)鍵時(shí)刻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使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中國(guó)革命轉(zhuǎn)危為安。毛澤東在抵達(dá)陜甘根據(jù)地后憑借中共中央權(quán)威和自身威望迅速制止了“陜北肅反”惡性蔓延,化解了它給根據(jù)地造成的內(nèi)部危機(jī);領(lǐng)導(dǎo)粉碎國(guó)民黨軍對(duì)根據(jù)地規(guī)模空前的第三次“圍剿”,解除了根據(jù)地外部的嚴(yán)重軍事威脅。這不但鞏固了陜甘根據(jù)地,也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以及其他各路主力紅軍能夠順利落腳陜甘根據(jù)地,進(jìn)而將中國(guó)革命大本營(yíng)建立在陜北創(chuàng)造了條件。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實(shí)現(xiàn)了土地革命時(shí)期中國(guó)革命由屢遭挫折到實(shí)現(xiàn)復(fù)興的關(guān)鍵性轉(zhuǎn)折,在中共黨史、中國(guó)革命史上是意義重大而又影響深遠(yuǎn)的事件。
應(yīng)該說(shuō),在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其他領(lǐng)導(dǎo)人也曾發(fā)揮過程度不同的重要作用。在這些中共中央領(lǐng)導(dǎo)人中,張聞天、周恩來(lái)的貢獻(xiàn)比較有代表性。張聞天不但和毛澤東一起決定制止“陜北肅反”惡性蔓延,而且在瓦窯堡親自領(lǐng)導(dǎo)對(duì)肅反案情的審理、定性以及善后工作。[29]周恩來(lái)在鞏固陜甘根據(jù)地過程中也曾發(fā)揮過重要作用,不但協(xié)助毛澤東指揮前線軍事工作,其后還對(duì)“陜北肅反”受難幸存者做了許多安撫善后工作。[30]90因此,陜甘根據(jù)地能得到鞏固是當(dāng)時(shí)中共中央核心領(lǐng)導(dǎo)層集體協(xié)力決策的結(jié)果。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推動(dòng)陜甘根據(jù)地轉(zhuǎn)危為安的歷程,體現(xiàn)了中共中央核心領(lǐng)導(dǎo)層駕馭復(fù)雜局面的魄力和能力,也展示出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lái)等中共領(lǐng)導(dǎo)人杰出的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領(lǐng)導(dǎo)才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核心領(lǐng)導(dǎo)層逐漸成熟的重要體現(xiàn)。不過,毛澤東在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過程中發(fā)揮的關(guān)鍵性作用更需要肯定。在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以超凡的政治敏銳性當(dāng)機(jī)立斷果斷制止“陜北肅反”,在粉碎國(guó)民黨軍“圍剿”過程中也體現(xiàn)出了杰出的軍事才能。毛澤東在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過程中發(fā)揮了極為關(guān)鍵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對(duì)中國(guó)革命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wú)數(shù)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guó)各族人民長(zhǎng)期犧牲奮斗的結(jié)果。我們不應(yīng)該把一切功勞歸于革命的領(lǐng)袖們,但也不應(yīng)該低估領(lǐng)袖們的重要作用。在黨的許多杰出領(lǐng)袖中,毛澤東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lǐng)導(dǎo)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lǐng)導(dǎo)執(zhí)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zhuǎn)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zhàn)略和各項(xiàng)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jī)中挽救中國(guó)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guó)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duì)指明堅(jiān)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zhǎng)時(shí)間。”[1]299因此,由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的卓越貢獻(xiàn),以及在鞏固陜甘根據(jù)地過程中發(fā)揮的關(guān)鍵性作用,中共黨史敘事以及眾多歷史親歷者、當(dāng)事人、知情人將中共中央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的主要貢獻(xiàn)主要集中在毛澤東身上也就有其歷史合理性。
中國(guó)革命復(fù)雜而坎坷,在前進(jìn)過程中既有凱歌行進(jìn)、舉世矚目的輝煌時(shí)期,也有艱辛探索、遭遇挫折的黯淡歷程。但是,自從遵義會(huì)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后,中國(guó)革命開始一步步走向成功。《關(guān)于建國(guó)以來(lái)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zhǎng)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huì)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lǐng)導(dǎo)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lái),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zhàn)勝?gòu)垏?guó)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zhǎng)征,打開中國(guó)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gè)生死攸關(guān)的轉(zhuǎn)折點(diǎn)。”[1]296毛澤東領(lǐng)導(dǎo)鞏固陜甘根據(jù)地扭轉(zhuǎn)中國(guó)革命危局正是毛澤東領(lǐng)導(dǎo)“打開中國(guó)革命的新局面”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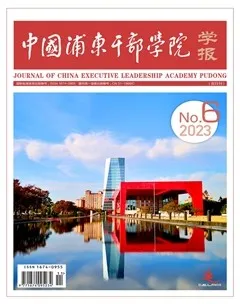 中國(guó)浦東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中國(guó)浦東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 中國(guó)浦東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陳希在中央黨校(國(guó)家行政學(xué)院)2023 年秋季學(xué)期第二批進(jìn)修班開學(xué)典禮上強(qiáng)調(diào) 深入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近平文化思想
- 開展新一輪干部教育培訓(xùn)的行動(dòng)指南
—— 學(xué)習(xí)貫徹《全國(guó)干部教育培訓(xùn)規(guī)劃(2023—2027 年)》 - 科學(xué)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歷史規(guī)定性
- 第六屆基層黨建創(chuàng)新論壇暨中浦長(zhǎng)三角論壇(昆山)·2023成功舉辦
- 以高質(zhì)量黨建促進(jìn)高質(zhì)量發(fā)展
—— 第六屆基層黨建創(chuàng)新論壇暨中浦長(zhǎng)三角論壇(昆山)·2023會(huì)議綜述 - 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背景下文化產(chǎn)業(yè)融入新發(fā)展格局的機(jī)遇與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