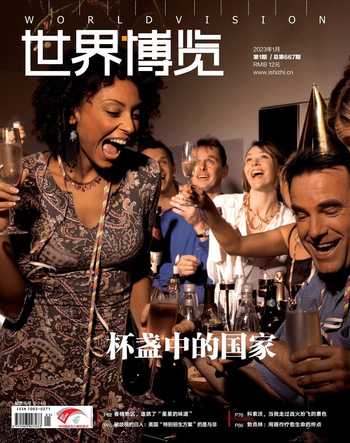基耶斯洛夫斯基:看到真實的眼淚
源遠

享譽全球的電影哲學大師——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是20世紀最負盛名的藝術電影大師之一。1941年出生于波蘭的他,大部分生命光陰是在華沙度過的。波蘭這個歷經災難的國家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終其一生都不愿意放棄的故國,即便在他以作品享譽整個歐洲的時候,他始終不承認“世界公民”的身份。
電影詩人
大器晚成和英年早逝這兩樣是所有藝術家最不愿意面對的事實,然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樣沒落下。40歲方才在法國嶄露頭角,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如日中天的他,55歲(1996年)便倉促離世,留下為數不多的電影劇情片和電視短片。然而,有關其影片討論的熱情絲毫沒有隨著他的離開而衰減,反而更盛。特別是到了21世紀,他的電影幾乎成為“藝術電影”的代名詞。有關其人、其事、其電影被后世言說成為一種電影文化,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影迷不斷加入。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初被歐洲影壇乃至世界影壇發現并接受,始于電視短片集《十誡》(1988年)。這是一部靈感來自于《圣經》,卻又以現代精神質疑歐洲文明的系列電視短片,仿佛“靈感一現”,引起了影壇久違的持續集體熱議。基耶斯洛夫斯基獲得了幾乎眾口一詞的贊譽,一位世界級電影大師橫空出世。
他的出現,一掃藝術電影在20世紀后半葉相對沉默的局面。接下來的幾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相繼推出了《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藍》《白》《紅》等重量級的作品,令這位世界級的電影大師毫無懸念地摘下了藝術電影大師的桂冠。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序列風格鮮明、難以模仿,擅長運用精巧的電影語言探討個體存在狀況,深刻表達具有濃厚人文主義情調的現代文明的主題,被譽為“深紫色的敘事思想家”。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擅長在私人化敘事中呈現現代文明的痼疾,充滿對傳統歐洲精神的質疑,卻無時不向影片里精神困境中苦苦掙扎的個體投以深切的關懷。

《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被解讀得最多的一部。

《白》是一部有關“平等”的電影。

《紅》不是一部“王子和灰姑娘”式的愛情故事,而是一部不斷發現“絕對的愛”是不可能的故事。
文明的“反命題”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負盛名的“顏色三部曲”——《藍》《白》《紅》分別代表歐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三種精神——自由、平等和愛。然而,基耶斯洛夫斯基欲要呈現的顯然是文明的“反命題”,即在實際意義上,自由、平等和愛的不可能。
《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被解讀得最多的一部,某種意義上,《藍》被認為是最能夠體現其風格的一部電影。電影《藍》講述了一名作曲家的妻子(茉莉),在失去了丈夫和女兒時,獨自面對生活的故事。這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失去“愛”的女人,這是一個在瞬間被移除“妻子”和“母親”雙重身份的女人。電影一開始的車禍奪取了茱莉身邊兩個最重要人的生命,身心俱損的朱莉賣掉了鄉間別墅、處理了家產,搬到市區一個沒有小孩的公寓居住。仿佛一切都沒有了。然而,反向理解,生活優渥的茱莉卻獲得了空前的“自由”——身體自由、情感自由、選擇自由。可是,光有自由有什么用呢?起初茱莉萬念俱灰,她對住在養老院老年癡呆的老母親哭訴: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于是,電影呈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命題:人是自由且孤獨的存在。因此,自由變成了一種囚禁。如同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說:“《藍》中的牢獄是由情感和記憶這兩件事造成的。茱莉在電影的某一時刻曾明確表示這一切都是陷阱:愛、憐憫、友誼。”茱莉努力想抓住的情感是她的桎梏,她努力擺脫的孤獨卻伴隨著巨大的自由。然而茱莉對自由與否是沒有選擇的。自由和禁錮這一對正反命題共同加力,成為茱莉生命的“牢籠”。更加無奈的是,茱莉陷入空前的“自由”是無法抗爭、不可改變的陷落,之于她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不自由的自由”。
《藍》的劇情反轉與電影基調是相同的——機智里透著荒誕。漸已習慣“自由”生活的茱莉,偶然發現摯愛的丈夫生前有一個情人,還有一個遺腹子。爛俗的橋段卻有著極大的“殺傷力”。對一切都失去興趣的茱莉開始跟蹤丈夫的情人、詰問奧利維耶(丈夫生前的助手)實情,甚至重拾舊曲續寫為歐洲聯盟誕生而作的交響樂……接下來的情節也許可以輕微地撫慰一下糾結許久的觀眾的心靈:茱莉選擇與丈夫的情人和解,把房子和丈夫的姓都給了那個遺腹子;茱莉接受了奧利維耶的愛;茱莉完成了歐盟的交響樂。茱莉與世界的不堪和解,然而“獲解”的茱莉進入了另外一個牢籠:感情和牽掛,茱莉又一次選擇放棄“自由”。
這部電影甚至可以理解成“茱莉一個人的電影”,導演借著茱莉這個抽象個體,對現代自由倫理作注解。電影沒有封閉式的結尾,茱莉今后又將如何?電影在講述“有關茱莉的故事”的同時,設定了一個迷障:生活是人類永遠逃不出的“牢”。電影最后用了9分多鐘的時間,給所有的人作了交代:母親在奔跑而來的護士穿越玻璃的目光中安詳睡著(離世);腹中胎兒有規律地運動著;睡夢中的安托萬醒來;一直堅強的茱莉終于落下眼淚……像是一本小說的結尾對每個人的交代,又像是一幅人類生存長卷畫:經歷苦難卻癡心不改,終難逃遁苦樂參半的人生。
《白》是一部有關“平等”的電影,或者說這是一部有關絕對“平等”并不可能的電影。卡洛是波蘭的一名受歡迎的理發師,在漂亮的妻子多明尼的鼓動下一同去了法國。卻在那里語言不通、生活無以為繼,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性能力,被妻子告上法庭被判離婚。走投無路的卡洛被一個“神秘人”用行李箱托運回了波蘭,發了筆橫財卻十分想念前妻多明尼。卡洛與合伙人謀劃,制造死亡的假象騙多明尼返回波蘭領取巨額遺產,最終卡洛與妻子和好如初。卡洛與多明尼的感情關系是電影中的情感蹺蹺板。不得不說這部劇情上不無荒誕的電影呈現了再真實不過的現實:即便在人類最親密的兩性關系中“平等”也是有條件的,愛情是所有社會要求滿足后,最后的“生活甜點”。失去語言和生活能力的卡洛必須重新獲得這些能力方能重返“愛的家鄉”。有關愛情的“真相”,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的電影中從不避諱,只是在《白》中,愛情的社會意義和殘酷性被放大。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普世價值——“平等”被放置于一對小夫妻的情感旋渦里考量,荒誕且真實。
《紅》是一部有關“愛”的電影。然而,這不是一部“王子和灰姑娘”式的愛情故事,而是一部不斷發現“絕對的愛”是不可能的故事。大學生兼模特瓦倫蒂娜因撿到一條流浪狗而結識了一位竊聽他人電話的老法官,純潔而美好的瓦倫蒂娜非常反感老法官的不良行為。然而當她通過竊聽電話發現衣冠楚楚的人們的骯臟的實質后,她愕然了。當發現男朋友一直以來的謊言,瓦倫蒂娜開始覺得原來世界遠沒有她想象的那么簡單美好。電影總是帶領人們“偷窺”別人的私事,最后發現,只是暴露了自己的一樁私事而已。瓦倫蒂娜與老法官成了“忘年之交”,老法官講述了他年輕時的愛和被背叛的故事。瓦倫蒂娜乘坐的去英國的船發生了海難。
影片中瓦倫蒂娜的愛情夾雜在“電話竊聽丑聞”里,從道德角度出發,自然是為人所不齒的。然而,電話里那些被竊聽的丑聞更可恥,接受并與真相共存顯然很殘酷。電影依然持“反命題”,絕對的、毫無保留的愛是不存在的,要在此生中愛,就要義無反顧地接受愛的不完美。《紅》里的老法官是頗能引起觀眾諸多心境的一個人物形象。他的“竊聽”行為必然在情感上引起人們的反感和鄙夷,然而隨著他竊聽的那些人的丑聞紛紛暴露,人們開始建立了新的道德判斷,反感和鄙夷多少會轉嫁到“那些人”身上。隨著“竊聽”行為的暴露,“道德的人們”憤怒地向老法官的房子丟石頭,瓦倫蒂娜看到老法官家里鋼琴上擺放得整整齊齊的6塊石頭,觀眾與她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那6塊仿佛載著“人類之惡”的“道德之石”齊刷刷地丟向了一個發現真相的人。連瓦倫蒂娜都沒有想到,告發者是老人自己。老人去法院“自首”,在那里遇見了一對年輕男女:實習法官和他的女朋友。這一段落的敘事與老人講述他的“過去的故事”幾乎是一樣的,甚至很難分辨那一對年輕人是老人看到的,還是他自己的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經常出現如此沒有交代清楚的情節,也許他認為如同這個復雜的世界,有些事情無須解釋,也解釋不清楚。然而恰好是這個具有模糊意味的情節為《紅》的敘事增加了想象空間,年輕法官如同當年的老人(也許就是當年的老人)被愛背叛,試圖遺棄了自己的寵物狗開始新的生活,恰好在海難中與經歷情感變遷的瓦倫蒂娜相遇。這是《紅》這部電影在情節上的障眼法,卻是感情上的彌補。他們的相遇彌補了老法官過去的“傷痕”,也撫慰了瓦倫蒂娜現在的“傷痕”。電影終于還是在殘酷現實中保留了溫暖的結局。

《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最浪漫也最憂傷的一部。
《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最浪漫也最憂傷的一部。波蘭和法國各有一個名叫“維羅妮卡”的女孩,她們素未謀面卻如同孿生姐妹,在生命的每一次重大轉折時彼此都能夠體認到這個世界上有另外一個生命跟自己相感知。華沙的女孩追求靈性生命、藝術人生;巴黎的女孩追求享樂生命、世俗人生。她們同樣的孤獨著,卻又同樣的幸福著。波蘭的維羅妮卡在演唱的舞臺上去世了,法國的維羅妮卡開始尋找這個世上的另外一個“共同體”,終于在外出旅游的照片里發現了曾經偶然拍下的另外一個女孩的身影,感慨萬分。電影以詩意的敘事和鏡頭呈現了人類獨有的一種心理體驗——“在世的孤獨”。人的在世感往往是通過他人而獲得的,從更深的層面上,電影將兩個完全一樣的美好女孩隱喻為分離已久的古老歐洲,將其斷裂許久的裂痕和憂傷傾注在兩個女孩身上,讓她們彼此體認,苦苦追尋。這部電影同《藍》一樣,拍攝于歐洲聯盟成立之前,雖然導演本人無緣親眼目睹期盼已久的“歐盟”誕生,但電影《維羅妮卡的雙重生命》可以看作對“歐盟”最深情的告白。
自由與不自由、平等與不平等、愛與背叛,這些命題與反命題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為數不多卻部部經典的電影中幻化成生動的生活實景,茱莉獲得空前的自由同時必須忍受巨大的孤獨;卡洛失去了語言和生活能力同時失去了兩性關系中的平等;瓦倫蒂娜見證了愛情的不堪卻更勇敢地投入了新的生活。生活永遠不完滿、生存的困境和悖論永遠存在。然而,人類最大的勇氣在于,在不堪的世俗生活里葆有熱情。在死亡迫近的征途中討論自由、在愛里討論平等、在背叛里討論愛、這既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最殘酷的一面,同時也是最直面人生真實的一面。他不鐘情于講述脈脈溫情“王子與灰姑娘”的故事,對刻意的“大團圓結尾”也沒有興趣,只是通過影像剝離生活中的矯飾和浮夸,把終難回避的人類整體性悲劇命運呈現給觀眾。
(責編: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