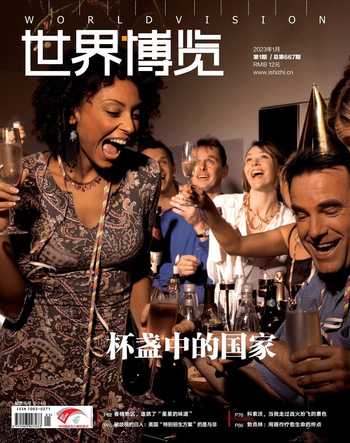弗里茨·哈伯,德國猶太人的悲劇
寒武

弗里茨·哈伯(右)在實驗室里。
19世紀人口爆發式增長,對糧食的需求也日趨增大,1845年至1850年間在愛爾蘭爆發了大饑荒,導致100萬愛爾蘭人餓死。各國科學家們一直致力于提高農業的產量,不久便發現在所有的化學元素中,氮元素對農作物的生長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就導致有一種東西和石油一樣珍貴,以至于各國競相開采,美國甚至還為此立法,這東西就是鳥糞。海鳥糞由于富含氮和磷,是十分理想的有機肥料。
為了提升糧食產量,美國進口了大量的鳥糞,美國國會甚至通過了一項聯邦法案——《鳥糞島法》。大致意思是美國公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占有無人認領的有鳥糞的島嶼,并且可以要求美國總統授權,利用軍隊來保護相應的利益。最終,美國憑借這項法案在全球占領了100多座島嶼,雖然大部分已獨立或歸屬原所有國,但至今仍有十多座島嶼劃入了美國領土。
但是消耗鳥糞的速度遠遠大于鳥類生產鳥糞的速度,珍貴的鳥糞終究是越來越少,到時候挖完了可怎么辦呢?一些有遠見的化學家指出:植物的生長需要氮元素,如果能將空氣中的氮氣變成植物可以吸收的氮元素,就可以徹底解決糧食危機問題。向空氣要“面包”吧!如何將空氣中豐富的氮元素固定下來并轉化為可被利用的形式,成為一項受到眾多科學家關注的重大課題。而一位毀譽參半的科學家將完成這一重大的歷史使命,他就是德國化學家弗里茨·哈伯。
天使哈伯
1868年,哈伯出生于德國的布雷斯勞,這是座名副其實的教育之城,64萬人口的城市中遍布著11所大學,從這里走出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哈伯的父親是知識豐富、善于經營的猶太染料商,家境優渥,家庭環境的熏陶使哈伯從小和化學結緣。他是個天才少年、超級學霸,19歲就被破格授予了博士學位,28歲就在大學任教。

哈伯在實驗室進行固氮實驗的小型裝置。

1908年哈伯所獲得的合成氨技術的專利證書。

弗里茨·哈伯
1904年,哈伯在兩位企業家的支持下,決定向人工固氮這個世界難題進軍。眾所周知,空氣中的氮元素占據了78%的體積。它們隨著呼吸進入我們體內。氮氣分子由兩個氮原子組成,它們被三個化學鍵死死地綁定在一起,導致氮氣的化學性質非常不活潑,木炭也好,蠟燭也好,都無法在其中燃燒。
而要轉變為能被植物利用的氮元素,只有像閃電這種級別的超級能量,才能擊碎氮氣中間的那三個化學鍵,讓游離的氮元素與空氣中的氧元素和氫元素反應,變成氨基和硝基物質,落到地面,被植物吸收利用;第二個力量是細菌。某些細菌可以分解氮氣,讓它變成可以被植物利用的有機氮,它們一般共生在植物的根部,為植物提供氮肥。所以在當時的化學家們看來,一定是存在一種人工固氮的方法的,而難點就在于如何用盡可能小的成本拆解氮氣。
當時美國已經開始嘗試用人造閃電來轟擊氮氣,英法化學家也正在打算用高溫高壓來暴力破解,這些方法耗能非常高,而精明的哈伯選擇了用催化劑來以柔克剛。歷經數次失敗后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采用600℃、200個大氣壓和鋨元素作催化劑的條件下,固氮成功,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人工固氮技術的重大成就。合成氨的原料來自空氣、煤和水,因此這也是最經濟的人工固氮法。這種辦法結束了人類完全依靠天然氮肥的歷史,給世界農業的發展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工業生產、軍工需要的大量硝酸、炸藥解決了原料問題。合成氨的成功也為德國節省出了巨額經費支出,哈伯從此一舉成名。
1913年哈伯氨合成產業化的夢想在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公司的幫助下實現了,一個日產30噸合成氨的工廠建成并投產,人造“鳥糞”源源不斷地從生產線上涌出,在農民的手中變成累累果實。自此,全球農作物的畝產量平均增長了4倍,也讓數億在饑餓線上掙扎的窮苦百姓得以生存下來。1918年哈伯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并被譽為“用空氣制造面包的圣人”,作為合成氨工業的奠基人,哈伯也深受當時德國統治者的青睞,他數次被德皇威廉二世召見,委以重任。43歲時他就擔任了威廉皇家物理化學和電化學研究所所長,并兼柏林大學教授。但在諾獎揭曉的時候,英法等國的一些科學家卻公開反對,他們認為,哈伯沒有資格獲得這項榮譽。原因是哈伯卷入了由德國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惡魔哈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外國首腦和軍事專家曾預測:由于含氨化合物的短缺,大戰將在一年之內結束。不料德國合成氨技術的成功,使德皇威廉二世認為只要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氨和硝酸,德國的糧食和炸藥供應就有了保證。這也促成了他開戰的決心,從而延長了一戰的時間。
彼時的哈伯沒有考慮戰爭是否正義,他在戰爭爆發后立刻自愿入伍。他寫了一封信給軍方,信中說道:“德軍彈藥即將消耗殆盡,我生產的硝酸銨,除了是最高效的化肥,也可以是最強悍的炸藥。”從化學原理上來看,用巨大的能量拆解氮氣原子之間的化學鍵,成為含氮的化合物,那么反過來說,這些化合物中的氮元素重新合并成為氮氣的時候,也就必然釋放巨大的能量。當時的德軍一路高歌猛進,但沒多久,就陷入了泥潭,因為在漫長的陸軍防線上,戰壕縱橫交錯,德軍和英法聯軍在比利時對峙不下。同時法國前線還出現了一種新式武器——催淚彈。德軍為了改變不利勢態,統帥部在哈伯的建議下,揭開了世界第一次化學戰的帷幕。
夜間,德軍在長達6000米的戰線上秘密安放了數以千計的氯氣罐。第二天下午德軍借助有利的風速以突襲的方式將180噸氯氣吹放至法軍陣地。剎那間在6000米寬的正面形成2米高的黃色氣體幕墻,滾滾向前推進,縱深達10公里至15公里。對手毫無防范,致使5000多人死亡,15000多人中毒致傷。吸入的氯氣在士兵體內和水結合,形成了鹽酸,強烈地腐蝕著呼吸道,法國士兵感覺到了窒息和灼燒的疼痛,只能丟盔棄甲,抱頭逃竄。德軍借助氯氣的幫助,最終突破法軍陣地近10公里。哈伯因此受到了德皇嘉獎,但也遭到各國科學家的強烈譴責。他卻被所謂的“愛國主義”所惑,當年又研制出新型毒氣——光氣(COCl),其毒性是氯氣的10倍,并在戰場上使用。
哈伯的妻子,卻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為什么要這樣做,成了一樁懸案。但很多人認為,“化學殺手”丈夫的惡名讓她的心理不堪重負。而哈伯卻執迷不悟,更不可思議的是哈伯居然認為:“死亡就是死亡,死于飛濺的彈片還是死于毒氣,這并沒有任何區別,不要因為看不到冒著槍林彈雨沖鋒的騎士精神,就說毒氣比彈片更加邪惡。相反,毒氣比那些彈片給人體造成的殘缺更小。”
化學戰的“潘多拉盒子”在哈伯等科技人士的“努力”下終于被打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雙方共生產各類毒氣15萬噸,中毒傷亡的士兵、無辜的百姓多達130萬人,占大戰傷亡總人數的4.6%。從1917年開始,幾乎每一次戰役都有化學武器的魔影,化學戰已經事實上成為一戰各個戰場上的主角。英、法、俄、美等國也以牙還牙,大量使用刺激性、窒息性、糜爛性毒劑等化學武器。而作為始作俑者,哈伯的戰爭暴行,在歷史上留下了極不光彩的一頁,受到了世界愛好和平的科學家和各國人民的強烈譴責。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曾氣憤地指責哈伯是“科學界的無賴、喪心病狂的走狗! ” 對此哈伯也曾辯解,他說了一句頗有爭議的話:“在和平年代,一個科學家是屬于全世界的,但在戰爭時期,他卻屬于他的祖國。”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失敗而告終。戰后的一段時間里,哈伯曾試圖設計一種從海水中提取黃金的方案,希望借此來支付協約國要求的戰爭賠款。但遺憾的是,在研究了3年以后,哈伯發現,海水中真實的黃金含量比自己預估的要低了100倍,這個方法根本就行不通,他的努力只能付諸東流。很快,時間來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臺,納粹黨開始在全國大肆屠殺猶太人。盡管哈伯不信猶太教,但他的猶太血統是無法更改的,他被稱為“猶太人哈伯”,成為被納粹針對的對象。當時哈伯的好朋友普朗克正在幫德國研制原子彈,在他的極力擔保下,哈伯逃過了初期的一些反猶迫害。但是政策慢慢變得越來越嚴格,哈伯的研究所里還有大量的猶太員工,政府命令哈伯必須立刻解雇這些員工。

德軍在化學戰中要求一定要處于上風的一側。

防毒面具是因化學戰的需求應運而生的。
雖然自己一直狂熱地愛著德國,但現在自己也變成了愛國者口中猶太奸商的子孫,狼狽不堪的哈伯只能選擇背井離鄉。1933年6月,哈伯流亡到英國,在劍橋大學講學。1934年初,他應邀出任設在巴勒斯坦的西夫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赴任途中,因心臟病突發,于1934年1月29日在瑞士巴塞爾與世長辭,終年66歲。哈伯在去世前留下了一條遺囑,希望能把他和妻子的骨灰安葬在一起,并且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上一句話:他為祖國服務,無論戰爭和平,只要祖國需要他。但是最后,這句話并沒有出現在他的墓碑上。
留給世人的反思
具有多重人格又頗具爭議的哈伯走了。他既是一個聰明的、才華橫溢的化學家,又是一個以科學知識支持沙文主義的狂人。人們憤怒譴責他犯下的戰爭罪行,但也對他凄慘的晚年寄予深切的同情。很多年后,當有人問愛因斯坦,如何評價哈伯時,愛因斯坦說:“這是德國猶太人的悲劇,一場單相思的悲劇。”哈伯的一生也給人們留下了探討與反思的沉重話題:科學家應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
如今世界人口進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來最迅猛地增長時期,全球的科學家們又一次面臨解決人類吃飯的挑戰。中國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投入于稻田,在泥濘當中尋找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鑰匙,通過“雜交水稻”解決了世界糧食短缺的問題,被譽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展望未來,科學技術正以空前的規模加速發展,其雙刃劍作用與日俱增。科學家每做出一項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突破的同時,不得不認真考慮社會責任的問題。有一位社會歷史學家曾經說過,從善需要思想深度,而思想空洞低俗就會導致從惡。同樣是解決了糧食危機的兩位科學家,哈伯與袁隆平卻給世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這值得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借鑒、深思。
(責編: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