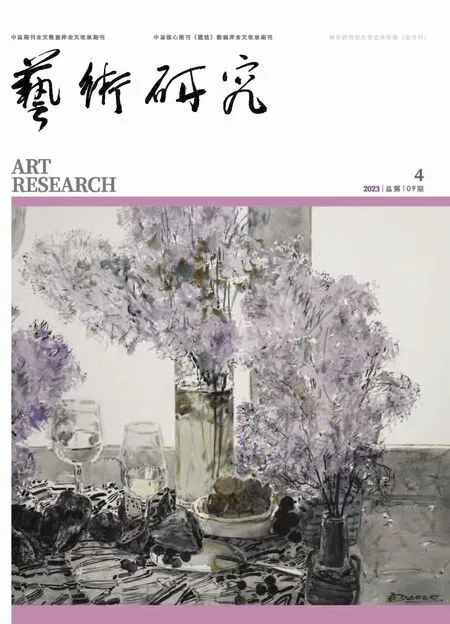室內樂本土化融合的特點
黑龍江省藝術職業學院國家二級演奏員博士/李洪達 哈爾濱師范大學副教授博士/陳 萌
從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弘揚中國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到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推進文化自信,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可見我國文化自信的“核心”是“文化”。“民族”與“文明”密切相關,“中華文明”所體現的“古國情懷”,就是對我們國家文化的肯定;“和平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也是對我們國家傳統文化的繼承。同時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中華民族自有它悠久燦爛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有著強大的凝聚力。無論是傳統宗教、民間舞蹈還是少數民族音樂以及民族樂器等,都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瑰寶,在歷史長河中積淀下了豐富而深厚的發展底蘊。
作為一種精神與物質并存、歷史與現實并存、形式與內容同構,室內樂的發展與本土化融合且與時俱進的發展也成為當代音樂創作熱點和難點之一。民族民間音樂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今的室內樂發展成為不同民族特有藝術形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有特色的演奏形式。本研究基于中國古典民樂傳統創作和實踐與理論研究為切入點,從內容和形式等層面對我國室內樂發展歷程進行探討。目的在于了解中國音樂元素在不同歷史時期融合本土文化特性的過程,并從中探討中國的室內樂發展中存在問題與困難。
一、在思想層面:對優秀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以《詩經》為例,我國各民族通過不同語言向外界傳達文化、民族精神以及價值觀念,同時這一類的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從《詩經》里的《國風》《小雅》看出,“雅”“贊”皆可視為文言文形式,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有深遠影響。此外,《詩經》還以樂章命名,如《大雅》里記樂章數有七十二之多。《國風》以樂章命名可以從《詩經》看出其思想在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下形成了“雅樂”“大雅”現象。無論是儒家傳統文化或是其他民族文化在《詩經》里留下了深深印記,然而在這些詩歌作品中也反映出不同地域音樂與生活方式所包含的共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對今后美學理論的影響和借鑒。
到當今20 世紀70 年代末,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已經成為世界一大亮點。國際作曲家們對我國音樂的認可程度開始大幅度提高。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國音樂創作者也在尋求突破與發展,室內樂創作者需要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來提高自身藝術水平和創作能力。為了更好地吸引國外作曲家來我國演出、合作交流、從而上演原創作品以及在我國各大劇院推廣普及室內樂等,室內樂創作者們在充分借鑒外來演奏模式,并在民族音樂精華的基礎上融入了我國歷史文化底蘊從而形成特有的創作風格。
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樂器和不同的音樂風格。比如,在山西、內蒙古、甘肅、四川等地,當地居民喜歡使用二胡、簫、笛子、中阮、琵琶等演奏樂器。其中尤以二胡的演奏最為突出且深受歡迎。在新疆地區的木卡姆等樂器,也是新疆民間藝人喜愛使用演出和演奏的樂器。此外還有部分樂器與少數民族傳統樂器如二胡、大提琴、葫蘆絲、笛子等進行了融合。在天津和北京地區,樂隊演奏樂器則以管樂、打擊樂等為基礎,曾采用琵琶、二胡和中阮等樂器進行融合。在河南、湖北、安徽、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則出現了帶有當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管弦樂《中原情》。在新疆地區還有以蒙古族民歌《呼倫貝爾大草原》、維吾爾族民歌《阿依努爾》等改編的民族室內樂作品;在福建地區還有傳統器樂合奏《采茶燈》等;這些類型豐富多樣、風格多樣的器樂作品正是當代室內樂典型的發展與融合過程的代表作。
二、在內容層面:吸收民族文化元素
從時間上看,中國室內樂的興起與發展是我國各個民族之間在相互交流中逐漸產生的。也是民族樂器之間吸收西方音樂元素從而進行相互演奏、融合與發展的過程,以豐富傳統音樂和民族劇目為表現內容,這一過程也體現了中國音樂家在不斷對現實生活中進行自我表達的過程。同時我國的室內樂也具有豐富本土文化特征的特點,從內容上來看,室內樂除了保留西方傳統音樂的韻味以外,還體現出民族性與豐富性。例如,“中國少數民族風格”這一概念在室內樂創作中就有體現。蒙古族音樂多用弓弦樂器演奏,其風格具有很強的立體感,節奏自由豪放,富有很強的沖擊力,在傳統戲曲中更多運用打擊樂器伴奏。因此有學者指出:“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代表著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演奏技藝。”這反映了民族演奏現代化是一個很大層面的創新發展問題。雖然現在多數人對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了解不多,但室內樂在融合過程中確實吸收了諸多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等因素。
近代以來,中西音樂融合開始將中國的音樂文化帶入世界,并逐漸影響了中國音樂界,進而為中國原創音樂提供了一種新的創作理念。其中以《春江花月夜》《梁祝》《梅花三弄》等一系列具有傳統文化氣息的作品為代表。這些作品既繼承了古曲音色變化大,音色清脆明亮等特點又富有一定藝術性和抒情性。這些樂曲在表現手法上既有古典音樂嚴謹、莊重的特征又有現代氣息表達等特點。在形式上也比較靈活多樣。《春江花月夜》中加入了很多具有濃郁中國風味或中國特色的音符作為點綴,使曲目在表達形式上更加豐富多姿。《梁祝》中運用了西方中常用的樂器——小提琴與交響樂協奏的演奏形式,使整部作品充滿了濃郁的中國民族氣息的同時又體現出了西方交響樂輝煌的表現形式。也體現了中西文化交流所帶來的影響;《梅花三弄》中融入了傳統戲曲音樂特點,運用了多首古曲中常用唱詞和唱段,表現了古曲中蘊含著的美好寓意。
三、在形式方面:對民族樂器的接受與運用
雖然對一些民族樂器的接受已經成為了室內樂發展的主流。但“中西融合”也確實會影響到本土特色的室內樂發展。例如蒙古族打擊樂曲中融入了新疆族元素,如打擊樂《哈拉哈》(中國民歌)馬頭琴演奏的《達坂城的姑娘》等;以及大提琴改編的《鴻雁》、琵琶《春回大地》等;還有一些其他傳統民族樂器如嗩吶、笙等等也在室內樂中得以運用和發展。所以說我國的室內樂發展到現在已經相當成熟并走向了一定輝煌。而在民族樂器中與西洋音樂相遇與融合過程中也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比如西洋樂器單簧管在當今室內樂作品發展中,與古箏、古琴、大提琴等中國樂器合作,當代作曲家陳欣若創作了《水墨》《頤和園華爾茲》《赤子花園》等作品,深受人民喜愛和傳唱。
從國際交流的角度來看,室內樂作品在傳播音樂藝術的同時,也促進了外國樂團與中國觀眾之間的接觸與交流。據中國音協相關負責人介紹,通過長期的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培養和選拔、引進高水平樂團、演出中使用交響樂、室內樂等演出形式。同時,我國音樂家也通過廣泛收集整理西洋音樂作品和我國民族樂器合作而產生的音樂表現形成。通過這些音樂編曲和作曲家作品的創作實踐,促進了中國當代器樂人才隊伍的建設。目前國內職業作曲家以西方音樂家優秀作品為基礎進行本土化創作。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副教授陳欣若為例,他近期創作的作品在繼承自身音樂風格及內涵的同時,創作作品形式以西洋樂器和中國民樂相結合的方式,創作了大量室內樂作品。這些作品弘揚中國傳統音樂促進中西音樂交流,是民族音樂走向國際舞臺,被世界音樂愛好者認知和喜愛。陳欣若說:“在創作的時候,古琴就是一種獨特的聲音,我尊重它的傳統表達方式以及聲音美學,并且不會讓這個傳統觀念約束我對聲音組合搭配的想象力。當代著名青年作曲家方崠清,創作的現代作品中,善于把中國少數民族樂器融入作品中,比如在《醉八仙》中,將琵琶、鋼琴大提琴結合在一起。將琵琶的“點描碎影”與鋼琴的“冰刀撞碰”和大提琴的“柔情俠義”詮釋得淋漓盡致,使聽者有很強的畫面帶入感。樂曲中三件樂器的相互融合表現出了酒與武術這兩種中國自古以來博大精神的傳統文化精髓與獨特魅力。同時方崠清在創作中也用西方樂器演奏中國題材的音樂故事,比如創作了大提琴作品《林沖》,全曲的三個段落——踏雪、殺戮、夜奔。用西方樂器將中國名著中家喻戶曉的情節用音樂的手法表現出來。運用滑音,強烈撥弦等現代技法和中國的五聲調式結合其中,也是具有民族化的現代室內樂經典作品之一。
20 世紀50 年代,我國作曲家們廣泛地吸取西方音樂的表現方式,使創作手法更加多樣。例如,管弦樂團和民族樂團經常進行不同形式、不同題材的作品演出;作曲家往往在不同國家、民族傳統文化背景下創作作品。這些不同形式的音樂風格結合成了作曲家們不同表現形式組合而成的室內樂表現形式。例如,“20世紀60年代國際室內樂作曲家大會”以及一年一度的“北京現代國際音樂節”,創作了大量具有不同風格的交響樂,室內樂作品。創作手法和創作形式多樣。如將管弦樂隊與民樂樂隊相結合演繹小提琴協奏曲;將民族管弦樂隊與合唱團相結合演繹大提琴協奏曲等等。西方音樂對中國室內音樂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它們在形式技法上有著豐富多變、多種表現手法;而在內容和表現上則能從歷史與現實等多個角度去把握、表現一部作品當中所蘊含的深刻含義甚至哲理。中國當代室內樂風格開始呈現多樣化之態,并最終形成了“多維”風格。以作曲家葉小綱為例,他在音樂創作中,大量結合中國音樂元素,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葉氏風格”,他用音樂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作出思考和闡釋。創作《嶺南四首》《大地之歌》都是將中西音樂融為一體,是中國時代變遷的寫照和代表。
四、中國室內樂發展中存在問題與創新
在發展室內樂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其一是受外國風格影響的程度不同。近年來,隨著外國文化和西方室內樂理念逐漸融入國內音樂創作隊伍,國內的室內樂創作水平期待逐漸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創作出更多風格多樣、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優秀室內樂演奏精品。其二是中國當代室內樂還存在著各種創作模式或手段之間協調不足、相互借鑒問題。其三是國內室內樂觀眾群體在總體規模和結構上仍不夠龐大,使其普及程度仍然有限。所以培養音樂的受眾者,推廣聽眾喜愛的音樂作品,也是當今音樂產業發展的重要部分。
從近幾年室內樂的比賽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作曲家的作品豐富多樣,如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承辦的室內樂作品比賽等;有相當一部分高校教師,學者,作曲家參與到了中國現代室內樂創作中,這說明國內外室內樂藝術家在融入國內室內樂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有相當一部分原創音樂也表現出了與國外室內樂藝術家共同創作而形成的風格特點。如陳其鋼創作《道情》是以雙簧管和民族室內樂組合的形式,雙簧管本是西方樂器,以往的演出編制都是交響樂協奏,但是在這部作品中是民樂室內樂團協奏。這種中西方音樂的碰撞,展示了中西融合,繼承與發展并重的原創形式。
西方音樂在表達情感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技巧和手段。比如歌劇《波西米亞狂想曲》中,女主角經常使用各種和聲手段,以此來表達其內心的情感變化和感情宣泄。這說明在西方音樂史上,西樂表現為和聲樂器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西方音樂在表現方式上也是多維度、多層面地,在中西方融合的創作過程創作過程中,作品創作方面就使用了交響曲中最為復雜的變奏法、以及大量和聲創作手法等來表達內容。當今,我國已有不少在國際舞臺有一席之都的作曲家,紛紛創作出優秀作品。比如中國作曲家陳其鋼,他曾留學法國創作出作多部中西音樂結合的作品,代表作《京劇瞬間》雖以京劇命名,卻沒有拘泥與京劇的藝術元素,作曲家使用打擊樂和交響樂共同演奏,感受音樂織體的錯落有致,配器的變幻多織。這些手法和思路都是當今作曲家需要學習的方向。
這些創新和融合問題需要音樂工作者積極思考認真總結,以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為目標進一步不斷創演出更多優秀的作品。在中國的交響樂團和室內樂團一直以來多以演奏西方古典音樂為主,從西方古典作品和當今新作品的創作手法上來看,有些人認為這些樂團演奏的都是西方作曲家作品風格和演奏手法的簡單復制和移植。這種片面理解與錯誤認識不僅會阻礙我國室內樂創作水平提升,而且還不利于中國的傳統音樂不能得到更好地傳承和發展。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必須繼續加強對相關知識及實踐方法的研究、不斷提升藝術修養和演奏水平,為我國室內樂發展做出更多、更大貢獻!
五、結語
對于中國傳統音樂而言,在一定意義上說,室內樂文化發展正是以傳承為目的,通過傳承過程的探索并在融合與創新上做出嘗試,最終實現本土化。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階層間文化交融不斷加深,促使不同樂器相互借鑒滲透、互相融合,從而形成自己獨特風格與特色,這其中自然包括“本土化”融合發展。但不可否認,中國室內樂自產生至今,其“融合”發展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歷史過程。它既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繼承與發展運動,也不是一個自發演進而形成的過程,而是在一定意義上處于不停融入變化中。隨著時代前進和歷史發展變化,本土化融合出現了“變幻莫測”等問題。“變幻莫測”使室內樂在今天已經成為當今各種新興演奏形式之間融會貫通、相互學習及借鑒吸收的橋梁與紐帶——它承載著傳統樂器之間相互吸收借鑒乃至融會貫通的新功能與新要求。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樂隊形式上還是整體表現形式上都經歷著不斷進步、不斷更新。我們堅信在新時期及未來社會中,中國室內樂一定會以自身獨特風格和特點為大眾所接受并傳承并發展下去——它將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貢獻!
作為音樂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室內樂在內容上具有與民族音樂相同的獨特性、豐富性和復雜性,同時它又具有自身發展完善的階段性特征。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器樂元素加入了很多民間小調的元素,二是樂器形態和演奏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與傳統意義上的民樂相比,它們更強調“雅俗共賞”和“實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生活場景中對精神生活的審美追求。傳統樂隊在樂器融入中也變得更加廣泛和豐富,其樂器結構、演奏風格、演奏者、演奏方式等都進行了變革和創新。這其中不僅表現在樂器種類上,更表現在曲目內容上。當今世界各國人民都越來越關注本國文化遺產;各國間相互交流學習也在逐漸增加;這也意味著中國樂器在走向世界上具有更大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挖掘、傳承、發展少數民族音樂和古典樂隊特色時要考慮自身具體情況并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來推進建設與維護、弘揚和傳播我國優秀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