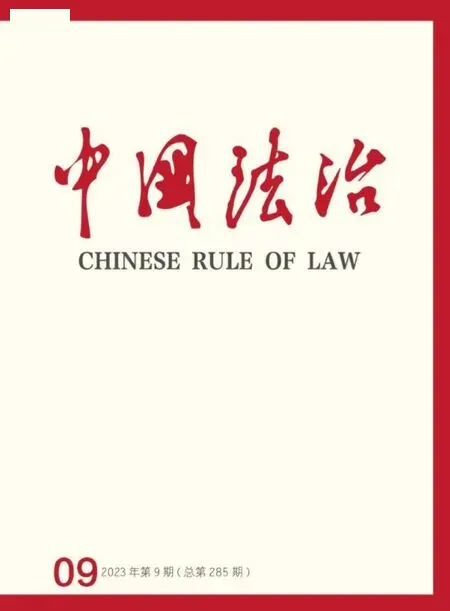論中國式輕罪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程序法供給
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個國家的刑事政策總是隨著犯罪態勢的變化不斷地進行調整。相關權威數據表明,近年來,刑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雖然案件總量在高位徘徊,但嚴重暴力犯罪比例大幅下降,輕罪案件不斷增多,我國逐漸進入“輕罪時代”。面對這一變化,應站在中國式刑事司法現代化的背景下,將輕罪治理融入國家治理大局,及時轉變理念,注重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同時,更強調輕罪案件刑事司法的寬和,尊重和保障人權。對此,有必要以輕罪治理體系現代化為基本目標,不斷加強刑事程序法的供給,提升我國輕罪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一、以實體法為主明確劃分輕罪與重罪
何為輕罪?這一問題顯然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答案。輕罪可能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不同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法律對于輕罪的界定往往會有所調整。雖然,從我國刑事程序法上能夠大致推導出“輕罪”劃分標準,如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16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對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可以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也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第222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可以適用速裁程序。但是,區分輕罪與重罪,毫無疑問是一個刑事實體法應當解決的問題,許多國家的刑法明文將犯罪區分出了輕罪與重罪,而我國刑法學界對于輕罪與重罪的劃分,尚未達成共識,且大體上存在“微罪說”(即1年以下自由刑為微罪,1年以上3年以下為輕罪)、“3年說”(即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為輕罪)、“5年說”又“罪名說”(即以罪名為單位進行劃分)等不同的劃分標準,這種分歧使得“何為輕罪”這一輕罪治理的根本性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當務之急在于,盡快在實體法層面厘清我國輕罪的范圍,可以考慮適度擴大輕罪的范圍,再推進其他領域的改革。否則,缺乏刑事實體法的支撐,輕罪治理背景下的程序法供給恐難以為繼。
二、減少羈押性強制措施與強制性偵查措施的適用
如果從刑事程序法的視角來評價輕罪,那么輕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能較低,或者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不少輕罪案件涉案人員實際上沒有羈押的必要。正因如此,可以看到,過往一段時期伴隨著一系列刑事司法政策調整以及2022年9月“兩高三部”《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頒布,我國訴前羈押率顯著降低,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此外,在一些涉企輕罪案件中,還應當減少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性偵查措施的適用,原因在于,從學理上講,無論是刑事強制措施還是強制性偵查措施,都屬于“強制處分”的范疇,而強制處分通常需要依合法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為之,對于一些涉企輕罪案件,若動輒就對涉案企業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性偵查措施,則很可能導致“辦理一個案子,垮掉一個企業”,這種做法有違比例原則(特別是狹義的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所以,在一些涉企輕罪案件中,應盡量減少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性偵查措施的適用,降低對涉案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未來,在輕罪治理中還應在法定基礎上強調“強制處分”的輕緩化,合理降低訴前羈押人數,減少非必要的“查凍扣”措施,避免將更多輕罪案件涉案人員推向社會對立面。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正式寫入。發展至今,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已超過90%,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創新。事實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時代背景之一,就是由于犯罪的輕刑化與案件數量的不斷增長,面對劇增的輕微刑事案件,有必要創新刑事司法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兼顧公正與效率。不難看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輕罪治理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可以考慮以輕罪治理為目標,進一步提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在輕罪案件中激發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活力。當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本身還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當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職權性邏輯”過重、“協商性邏輯”不足,從“治理”的角度出發,還需要在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中加入更多的“協商”因素。一方面,要轉變公訴方“從嚴從快、打擊犯罪”等傳統追訴理念,從源頭上盡可能杜絕“強迫認罪”“引誘認罪”“逮捕籌碼化”等類似問題的發生;另一方面,應強化辯護方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防御權”,例如,可以進一步發揮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作用,充分保障輕罪案件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確保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輕罪治理中發揮“良法善治”的獨特作用。
四、探索拓寬輕罪案件的不起訴范圍
談及輕罪治理的問題,程序法學者關注較多的就是不起訴制度。例如,有學者著眼于犯罪數量激增的“醉駕案件”提出了“醉駕案件附條件不起訴”;有學者則更為關注當前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并提出了“合規不起訴”的概念。從理論上講,這種賦予檢察官起訴裁量權的制度稱為“起訴便宜主義”,是與“起訴法定主義”相對應的一個概念。“起訴便宜主義”強調的是具體正義的重要性,其背后的刑法思想更偏向于特殊預防,即更為注重對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矯正與防止再犯。這里就可以看出,不起訴制度特別是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本就蘊含“犯罪治理”的理念,對于輕罪治理而言,不起訴制度有望成為一種有力的“治理工具”。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在立法層面拓寬不起訴的輕罪案件范圍是極有必要的,但現階段關于擴張不起訴制度的探索仍應在現行《刑事訴訟法》設定的框架下進行。此外,不少學者也關注到了與不起訴制度緊密相關的犯罪記錄封存(消除)制度,主要觀點在于,我國犯罪記錄對于違法者的影響過大,且記錄終身無法消除,這不利于輕罪案件的涉案人員回歸社會,應當建立切實可行的犯罪記錄消除制度,有條件地消除輕罪犯罪記錄,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
五、輕罪治理的刑事證據法應對
在輕罪治理的大背景下,刑事證據法應當作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回應。第一,堅持證據裁判原則,依法全面收集證據。證據裁判,作為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證據裁判原則的要旨為事實認定應當根據證據,其中根據的“證據”指的是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在證據裁判原則下并無輕罪與重罪的區分,輕罪案件可能案情相對簡單,事實和證據也并不復雜,但絕不意味著辦案機關在輕罪案件中可以違法收集證據或不全面徹底地收集證據。第二,堅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依據2019年10月“兩高三部”印發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3條的規定,辦理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也要堅持法定證明標準。如果站在現代刑事裁判中“自由心證”原則的角度來解讀,證明標準可以被理解為辦案人員內心的確證程度,即證據能否將事實確證到法律要求的程度,所以,輕罪案件中的證明標準既沒有降低的必要,也沒有降低的可能。第三,可以在刑事訴訟法框架下,適當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例如,在一些輕罪案件中,可能案情相對簡單,控辯雙方對證據均沒有異議,法庭可以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適度簡化庭審中的證據調查程序,適當簡化舉證、質證等環節(速裁程序已經簡化),依靠后端的法定證明標準來確保案件質量,提升輕罪案件的辦理效率。綜合上述幾點,可以說,刑事證據法是輕罪治理不偏離法治軌道的根本保障。
總而言之,輕罪如何有效治理本就是世界范圍內的法治難題,很多國家都曾面對這一問題,并探索出了不同的應對方案。因此,我國的刑事實體法、程序法以及證據法研究者應當共同努力,立足于我國司法實踐,以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為己任,給出輕罪治理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