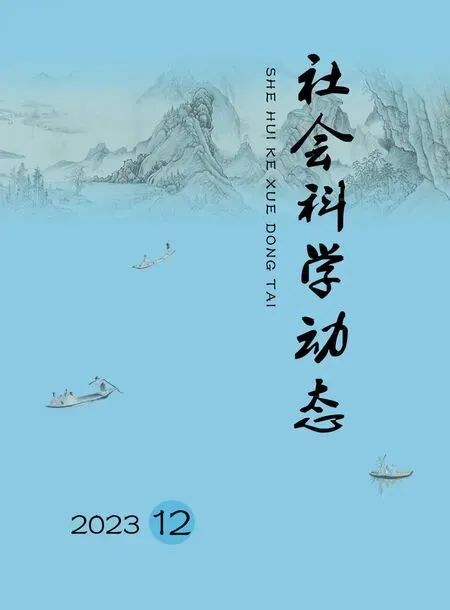“中國新詩與中外詩歌傳統國際學術論壇”綜述
溫琳舒 王 瀟
2023年9月16日至17日,“中國新詩與中外詩歌傳統國際學術論壇”在華中師范大學召開。本次論壇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首都師范大學詩歌研究中心、湖北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聯合舉辦。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澳門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京都女子大學、日本城西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等國內外70多所院校以及《新華文摘》《文藝研究》《學術月刊》《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等國內20多家學術期刊共190多名專家學者齊聚武漢桂子山,回顧新詩百年歷史,探究中國新詩發展的重要課題。
學術論壇歷時一天半。9月16日上午,華中師范大學校黨委書記夏立新、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名譽院長謝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劉勇、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劉云出席會議開幕式并致辭,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澤龍擔任主持。學術報告上半場由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譚桂林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點評;下半場由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何錫章主持、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貴良點評。16日下午,共設6個分會場依次圍繞“中國新詩與古代詩歌傳統”“中國新詩與外國詩歌傳統”“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新詩史問題研究”“新詩創作與中外詩歌傳統”“傳播視野中的新詩及其研究”主題分組討論。9月17日上午,學術報告上半場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編審秦曰龍主持、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呂周聚點評;下半場由《新華文摘》編審陳漢萍主持、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遇春點評。會議閉幕式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王雪松主持,王澤龍教授總結發言。
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總結百年新詩的經驗教訓,探究中國新詩與古代詩歌、外國詩歌豐富復雜的關系,是新詩發展亟須直面的問題。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名譽院長謝冕評價中國新詩誕生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它一方面堅持中國詩歌的千年傳統,一方面向世界詩歌尋求新的啟蒙和啟發,化古為新、古為今用、繼往開來是百年新詩自由精神的取向。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劉勇認為,中國現代新詩興起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它延續了中國傳統和參照西方外來文化因子,更要探究它新在哪里,為何而新。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澤龍在大會總結發言中表示,此次論壇匯聚四代新詩研究學者,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指導性、啟發性的命題,為新詩研究帶來沖擊與啟示,可謂近年來中國新詩研究的一次盛會。
一、吐故納新:中國新詩與古代詩歌傳統
系統檢視中國新詩與古代詩歌傳統的源流關系,既是新詩研究中無法繞過的舊命題,又是本次論壇深入推進的新貢獻。王澤龍教授形象譬喻中國古代文化是“遠傳統”,現代文化是“近傳統”,傳統是一條河流,只有不斷吐故納新,才能永葆生機。百年新詩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現代性傳統,成為一種別具一格的現代性文體和文類,這是與會學者的共識。而如何與古為新,讓古代詩歌“遠傳統”在現代詩歌“近傳統”的河流中實現現代性轉化,哺育當下新詩創作與研究,則是學者們致力于思考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是探究新詩與古代文學傳統之間的承變關系,為新詩繼承傳統提供啟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李俊國教授《30年代現代派詩歌與六朝文章晚唐詩》一文對六朝文與新詩間文學聯系展開解讀,使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作品呈現出更為生動、豐富的面向,即除了來自晚唐詩的溫暖頹廢之感,還有中國傳統散文的彈性與活力。但現代派詩歌對傳統文學資源的過度迷戀,導致其陷于依附的“他者”文化或藝術理念,失去冶煉、提升“自我”的機遇。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朱壽桐教授以《為漢語小詩正名》為題,闡釋了漢語小詩的正統性,他認為古老漢語詩歌的原初形態無不是今天所謂的“小詩”。小詩的獨特不在于形式長短,而在于對現代詩抒情本質的反映、對人的內在感覺的迫切表達,這構成了象征詩學、現代詩學興起的條件和現象。暨南大學語言詩學研究所趙黎明教授在其發言《“境界”傳統與中國新詩學的建構》中談到,境界詩學在中國具有深遠傳統,它在新詩壇看似“斷裂”,實際上是以碎片的形式在詩人心中回響。境界詩學既是一種精神向度,也是一種藝術向度,它對糾正當今詩壇的精神之失和藝術之弊,對于中國新詩學的建構具有多重價值。湖北大學文學院劉繼林教授充分開拓古代詩歌傳統的內涵邊界,將長期被正史忽略的俗文學傳統中的“民間話語”統籌進來。他在《百年新詩的民間話語研究視角》一文中肯定五四以來的中國新詩,正是借助源于“傳統”的民間話語彌合了與古典詩歌之間的裂隙,但同時民間話語也給新詩帶來了缺憾和問題,這需要學術界客觀正視和辨析其有效性與復雜性。
二是對新詩總體發展路徑的宏觀爬梳,為新詩的未來發展檢視具體方法。西南大學文學院王本朝教授的《中國新詩的兩個傳統,兩條路徑》和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高玉教授的《新詩的語言問題》,都從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出發,討論自由與格律、文與詩、文與質的關系,揭示了早期新詩發生的多種矛盾與多重張力。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楊四平教授在其發言《當下新詩深陷歷史周期率,“性命”堪憂!》中認為,新詩發展至今的隱患,就是每當一種詩歌文體發展到成熟、極致時,它就必然衰敗,被新的詩歌文體取代。對此他提出了破解方法——“新詩性命論”,致力于維護新詩的“三性”與“三命”,即新詩的抒情性、戲劇性、敘事性和新詩的天命、生命、使命。在對新詩發展路徑的宏觀探討中,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王澤龍教授的《新詩聲音的變革與重構》一文指出,詩歌是一種聲音,但不是傳統的聲音。新詩仍然需要音樂性,需要韻律,但不是傳統的音樂性和韻律。現代詩歌聲音發生了轉變,總結起來便是從歌的聲音到說的聲音,從形式的聲音到意義的聲音,從聽覺的聲音到綜觀的聲音,從音律化的聲音到節奏化的聲音。這些研究著眼于新詩與古代詩歌傳統的核心話題,從比較視野出發,對語言、聲音等本體詩學話語予以深度闡釋,并真切反思新詩發生與發展的外部議題,為當下研究者處理新詩發展過程中舊與新、遠與近、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等復雜詩學問題提供了鏡鑒。
二、別求新聲:中國新詩與外國詩歌傳統
“中國新詩與外國詩歌傳統”是個相對古老但常說常新的話題,具有歷久彌新的生命力。中華文化作為世界多維文化之一維,必然會受到外來思潮及文化影響,中國新詩也同樣是在外國詩歌傳統的深刻影響下展開變革的。謝冕教授在開幕式上擲地有聲地談到,我們要學習魯迅別求新聲,化古為新,古為今用,繼往開來。此次會議的論題直面紛繁復雜的外來詩學資源,深入聚焦新詩的主體問題,也就是新詩如何在關系中建構自身的詩史母題,整體上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多角度的立體研究空間。
國外文化資源、詩學經驗對中國新詩創作的影響研究,成為學者們在不同研究視角與方法下共同涉及的普遍問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的《徐霞村評戴望舒、姚蓬子的新詩》一文,考究20世紀30年代刊物中徐霞村借用保爾·瓦雷里的保爾之名發表的新詩評論文章,發掘出戴望舒、姚蓬子的新詩中對西方象征主義的本土化探索。他對徐霞村史料的新發現,使得同時代詩評與經典化論述構成潛在對話,回到了新詩寫作、閱讀、交流、評價的最初場景。復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的《〈野草〉“外典”二題》,充分考證魯迅《死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創作如何從周氏兄弟合譯小說《紅星佚史》、魯迅譯作《出了象牙之塔》和《工人綏惠略夫》中引用外典,從而生成對兩部作品生成語境和思想內涵的新解讀。他指出,此案例啟發我們研究新詩、新文學語言感覺的生成,研究其現代性問題,不能簡單的只從語言工具、經驗方式的變化來看,而要根植于晚清以降一系列跨語境、跨文體、跨文化的復雜語境和流動視域,嵌入新詩內部構成和生成脈絡,特別是新詩的語言形式與構思方法中。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貴良教授的發言《郭沫若〈女神〉:“真藝術與真科學本是攜手進行的”》,同樣考慮到新詩生成的復雜背景,闡釋了郭沫若詩的世界品格。他認為,現代漢語詩學與古代漢語詩學的不同之一就在于將科學元素融入了現代漢語詩學中,郭沫若的《女神》將藝術性和科學思維納入藝術思維,加固了美的內核,顯示了力的美學的硬度。
除了域外詩學資源對中國新詩的影響研究路徑,還有學者通過還原動態的文化語境,更新了影響研究的范式。南開大學文學院盧楨教授關注到早期新詩人從海外觀景體驗中覓得新詩質素的創作實踐,其《域外風景對早期新詩節奏的激發:從郭沫若的創作談起》一文,從郭沫若的海外游學經歷出發,結合穆木天、王獨清、孫大雨等留學詩人的行旅寫作,探討了域外風景對新詩的激發效應。香港嶺南大學文學院龔浩敏老師題為《“漢語語音詩”的啟示——以石江山詩學實驗為例》的發言,從“漢字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潛能”“漢字聲音藝術”“漢字字音的魔術”三個層面,對美國漢學家石江山的“漢語語音英文詩”詩學實驗展開細讀,認為漢字的“潛能”在中國當代文學與藝術中被重新想象和建構了出來,漢字的功能也得到了重新定位,而這意味著新詩語言學視野中的變革,對我們思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還有學者將外國詩學理論的經驗反思,回饋當下中國新詩理論建設。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李章斌教授在《論帕斯〈弓與琴〉中的韻律學問題——兼及中國新詩節奏理論的建設》中,系統闡述了帕斯在《弓與琴》中涉及的韻律學問題,分析其觀點對于中國新詩節奏理論建設的啟發。他提出,我們不能將節奏問題的思考局限于詩歌領域,而要擴展到其他文體乃至整個語言,還要比較別國語言與詩體,用外國詩歌理論經驗指導中國新詩的理論發展。總之,上述多重研究路徑啟示著我們要從新問題、新思路、新方法的視角,對中國新詩與外國詩歌傳統母題展開多元探討。
三、理論探賾: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
中國現當代詩學既是對新詩創作實踐的理論總結與指導,又是在中外詩學傳統的雙重影響下充分發展與演進的。可以說,百年中國新詩的源流發展離不開詩學理論建構的有力支撐。但在新詩史理論縱深之處,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傳統間的駁雜影響仍需深入挖掘。為從詩學理論之維檢視新詩百年來的經驗教訓,推進中國現當代詩學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研究,論壇圍繞“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話題展開了深度探討。
一方面,部分研究站在宏觀視角關注百年新詩發生發展,致力于不同角度的新詩理論體系構筑。詩人、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張執浩在《音區:漸于詩律細》一文中,從聲音的角度而非音樂的角度探討詩歌,將詩學導入更為廣闊的存在空間。他借用音樂發聲學的音區概念,分析古代高低音區詩人之別,強調找到自我特有音區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小濱老師同樣從傳統中汲取詩學養分,在《作為殘存的抒情主體:當代詩如何見證歷史》一文中指出,抒情主體對于當代詩來說是非常本質的東西,詩無論用何種表述,總會展現出抒情主體的獨特聲音。但面對當代現實,主體必然是殘余的,即所謂“剩余主體”。我們只有通過“創傷性的快感”,才能讓文字發揮力量參與其中。對殘存的抒情主體而言,溢出便是欠缺的表現。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從微觀視角打撈中國現當代詩學經典個案,從中推進詩學理論反思與經驗升華。河南大學文學院劉濤教授在《朱光潛對于新詩格律的學理求證》一文中,通過細密嚴謹的史料分析還原朱光潛對新詩格律的學理探索,認為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心理學中尋找詩歌格律的學理依據,科學論析了詩歌格律自然律與規范律,以及詩歌的音樂性問題,其對舊詩聲、頓、韻等傳統“形式詩學”的探討,為中國新詩創作和詩學理論系統化、科學化發展提供了參考。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張中宇教授的《漢語詩的“整齊”基因及其現代形態——兼及聞一多格律詩論的相關問題》一文,同樣探討新詩格律問題,特別針對漢語詩的“整齊”基因及其起源、漢語新詩形態和走向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解答。他認為新詩需要在自由活潑的基礎上,一邊追求貼近社會的思想感情抒寫,一邊把部分詩句錘煉成厚重精辟的“文化因子”,讓時代風采以更優雅的形式進入文化深層積累。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童龍超老師的《趙元任與中國新詩的聲音建設》一文,從個體詩學實踐的角度切入聲音詩學研究,認為趙元任融合音韻學家和音樂家的思維,從聽覺上打通語言、詩歌和音樂,拓展了新詩的文體邊界、表現領域和生存空間,奠定了新詩聽覺化道路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跨學科交叉視角下頗為新穎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在了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傳統的議題當中。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向天淵教授的《漢語和新詩彼此形塑的機制與啟示》一文,以詩學與語言學交互的視野回顧漢語和新詩現代化之間相互牽纏、彼此形塑的發展歷程,倡導學者挖掘現代漢語的詩性潛質,盡可能地拓展新詩語言智慧,創造出滿足現代人精神需求并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詩歌作品。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王書婷教授在《博物詩學視野下的新詩文體研究芻議》中指出,博物學涉及到對自然與萬物、科學與人文、經驗與藝術、文明與生態、自然與空間等不同范疇的認識,這又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文學,尤其是文體特征比較明顯的詩歌文體的發生、發展與演變,而從博物詩學的視野下考察中國新詩研究,可以為中國現當代詩學與中外詩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尋史診脈:新詩史問題研究
百年中國新詩史在與社會文藝思潮、詩學理論論爭等的激蕩中,產生了大量經典的新詩史問題。對這些新詩史問題的研究,是我們重新檢視、診斷新詩百年具體面貌與詩學經驗的關鍵一步。與會學者一方面以實證材料與理論闡述,回歸新詩發展的歷史現場,梳理還原新詩發展的歷史流脈,揭示詩歌與社會、政治和文化事件間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通過挖掘和重估被忽視或隱沒的詩人與詩歌群體,豐富了文學史書寫版圖,為窺覽中國新詩發展整體面貌,促進新詩發展邁出步伐。
一是對新詩研究新領域、新空間的發掘、開創和建構。武漢大學文學院金宏宇教授在《關于新詩話的話》一文中,運用史料研究的方法重新建構“新詩話”,認為新詩話具有說話、簡化、閑話漫話、對話的性質。南開大學文學院羅振亞教授的《“反”取向探索與百年新詩的形象建構》一文指出新詩形象建構中存在的悖論:一方面,眾多詩人和闡釋者努力打造新詩文體概念;另一方面,“反”取向探索卻在大量文本中以異端方式表現出來。他認為反詩取向是一把雙刃劍,反詩探索要適當控制節奏。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易彬教授的《木槿花開:“捧血詩人”辛勞在當代被發現的歷程》,發掘詩人辛勞,認為辛勞最初只在“孤島”文學視域中略被提及,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世紀的回響”中方浮出地表,其文學史地位有待重新考察。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張立群教授的《打開一片新世界——晉冀魯豫邊區詩歌(1937-1948)創作綜論》一文,對以往關注較少的晉冀魯豫詩人進行挖掘與梳理,拓展了晉冀魯豫文藝研究空間。
二是從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層面探討新詩史的個案、群體、時段問題,豐富中國新詩學術史研究版圖。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伍明春教授在《論早期新詩話語場域的張力結構》中,將早期新詩中的話語場域分為三派:早期新詩追隨者的自我論述;被壓抑的反對派的聲音;調和論者的微弱聲音。他認為,新舊之間的二元對抗構成了早期新詩話語場域的內在張力。云南大學文學院段從學教授在《梅光迪和胡適:“文章”與“文學”錯位沖撞》一文中指出,新舊文學的關系應放在古代性的“文章”和現代性的“文學”兩種不同思想類型層面上討論,“新文學”取代了“舊文學”的中心地位成為了“中國文學正宗”,“舊文學”則變成了現代性“文學”知識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武漢大學文學院陳建軍教授《聞一多詩集〈紅燭〉出版始末》對聞一多的《紅燭》進行了詳細的版本考據,致力于還原其出版始末。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熊輝教授在《徐志摩留美時期思想管窺》中考察徐志摩留美時期史料,從徐志摩的愛國情懷、人格修養、社會交往三方面呈現出更加真實立體的徐志摩形象。京都女子大學島由子老師的《顧城的初期寫作和環境》一文,通過訪談、實地調查與文獻材料互證等形式,透視了文學活動與讀書環境對顧城早期創作的影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張松建教授在《冷戰年代的抒情現代主義:論楊際光》一文中,從離散的角度分析楊際光冷戰時期的詩歌創作,解讀出現代主義和亞洲冷戰之間的幽微關聯,反映了新詩主體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程國君教授的《陜甘寧邊區的“紅歌”實踐及抒情傳統的價值意義》一文指出,在20世紀中國“紅色革命文藝”歷史構成的序列里,紅色經典、現代音樂史、現代歌樂傳統的革命抒情歌曲等極具“中國特色”,而陜甘寧邊區的“紅歌”詩學實踐有力推進了這一抒情傳統的發展。他認為,重釋這一詩學實踐對理解“紅色革命文藝”歷史構成,打撈革命詩歌與“五四”新文學的內在關聯具有深刻啟發。
五、回歸文本:新詩創作與中外詩歌傳統
宏大命題的選擇和研究路徑的把脈,對于新詩研究而言固然有引領方向的前瞻意義,但對具體詩作的文本細讀亦是新詩研究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王毅教授在發言中提出:“中國新詩的成就究竟如何?對于這個問題,宏觀的答辯固然必要,具體的文本可能更具說服力,與其爭辯,莫若寫作。”與會學者們立足具體詩歌文本,圍繞“新詩創作與中外詩歌傳統”這一話題,或著眼當下詩歌創作的典型現象,或以回溯姿態探討新詩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現代性、審美性、經典性等問題,探討了對新詩研究中已存問題的新認識。
其一,論壇對百年新詩發展史中的重要詩歌史現象與問題展開反思,在新語境、新視角、新觀點的研討中推進創新。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譚桂林教授的《現代佛教期刊上的白話新詩創作論》一文,認為由于意識形態和傳媒形態等原因走向淪滅的佛教白話新詩,從其創作實際看,它對社會發展、民族現實與文化的積極貢獻非常明顯,此優秀傳統是否應該保存發展,值得新詩研究者的思考。南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李志元教授在《抗拒閱讀:〈野草〉的審美現代化及其經典化過程中的意圖錯置》中,著眼于分析《野草》文本“抗拒閱讀”的反闡釋傾向。他認為,該傾向違背了讀者的審美慣常和趣味,而這也正是現代文學先鋒性與審美現代性的體現。同時,這種傾向導致《野草》在經典化過程中出現了意圖錯置的問題。上海大學文學院錢文亮教授以《AI訓練、語言“高級感”與人類的詩歌傳統》為題,在總結AI詩人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醒當下人類詩歌寫作者:僅僅依靠對前人既有詩歌的高強度學習與模仿遠遠不夠,未來的人類詩歌需要拓展生命維度,需要現實感、歷史感、自然感和神圣感、神秘感的交通互振,需要生命的遭遇與反應。
其二,論壇對當下某些新詩創作現象進行了系統展示,從詩歌史現象深入到了學理性的思考當中。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張巖泉教授題為《接續新詩傳統的努力:〈新九葉集〉初論》的發言指出,《新九葉集》的出版標志著“北外詩群”的亮相。這群詩人以接續“九葉詩人”和“作者兼譯者”的新詩傳統為目標,與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朦朧詩”“第三代詩歌”的潮流同聲相應。嶺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張德明教授在《學人之詩:百年新詩的小傳統》中,以桂子山學人詩群為考察對象,研究“學人之詩”這種突出詩學現象,認為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學人之詩儼然成為中國現代新詩的重要組成。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王毅教授的發言《新詩如何是好:以胡弦〈下游〉為例》,以胡弦的短詩《下游》展開新詩典型文本細讀,深入分析了短詩《下游》對漢字的理解,對分行、節奏的把握和對古今中外詩歌資源的借用,由此確證了新詩“詩之為詩”的身份問題。
其三,論壇對時下新興的新詩理論視野與文本解讀展開典型探討,如風景與新詩文本的相關討論成為焦點話題。“風景”視野研究是當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熱門話題,與會學者們的風景討論涵蓋中國古代與現代詩歌,有力推進了風景概念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擴充與完善。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亞思明教授在《虛空的現實與對位的風景——以陳東東、張棗的詩學對話為考察中心》文中指出,風景是以文化為媒介的自然景色,而想象力可以拓展夢想的邊界,豐富自我感知的世界,使之外化為詩學意義上的風景。云南大學文學院李海英教授的發言《在自然與風景之間:中國新式現代審美的生成與主要表現》,從中國新詩審美意識的轉換、審美主題的選擇、現代審美經驗的變化與演進三個方面,闡明了新詩創作中從“自然”到“風景”主題的新變。
六、傳播接受:傳播視野中的新詩及其研究
中國新詩的發生、發展與經典建構,是在現代傳播接受的場域中進行的。新詩已走過百年歷程,系統考察中國現代詩歌的傳播接受,是為了從新詩傳播的歷史語境與讀者接受視角,為當下詩歌理論建設與創作實踐提供歷史參照。現代傳播接受從多元渠道開啟了中國詩歌的現代轉型,成為建構中國現代詩學品格、形成現代詩歌豐富形態的重要動因與思想資源。因此,此次論壇“傳播視野中的新詩及其研究”主題,圍繞新詩傳播空間以及新詩經典化等問題顯示出廣闊的探討空間。
一是從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外部視角,觀照傳播空間中的新詩及其研究,進而在詩學理論方法層面反思中國新詩的現代轉型與新詩史重構等問題。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梁笑梅教授在《抗戰時期遷渝國立中央大學新詩空間的創構》一文中,從文學期刊的傳播這一重要文學生產環節入手,以新詩空間的創構為視角,凸顯了現代學人、媒介與國家權力三者間的互動關系。她指出從“中央—地方”“政黨—大學”的視野,探討抗戰時期高校文學、文化空間,對當下大學的文學、文化區域間互動,以及民族國家視域下的文化建設等具有重要意義。武漢大學文學院方長安教授在《傳播接受與新詩史重構》中,從詩學理論層面反思內外部研究聯動的新詩現代轉型與新詩史重構問題。他指出,以新詩近百年的歷史為軸,囊括重要的新詩創作流變、詩歌圖文、詩學轉向等內容在內的新詩傳播接受考察路徑,并著重強調了傳播接受對象參與新詩自身的發展衍變、影響新詩走向的具體進程應為新詩史重構的著力點。他認為這有助于打通新詩內外部研究,揭示出新詩詩意與詩性的生成原因,看到更加真實的新詩史內在衍變過程。
二是從副文本、跨語際交流等新詩的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著眼,探究傳播視野中的新詩及其研究。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陳愛中教授聚焦“編者按”這一輔助性副文本,以《編者按與朦朧詩的生成》為題發言。面對朦朧詩生成的詩歌史研究舊命題,他從“編者按”視角出發對其展開新論,認為詩歌刊發期刊的存在樣態和編輯思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某時代詩歌美學標準的養成。日本城西大學田原教授的《中國現代詩的域外接受與中西詩歌互譯》一文,從“中國現代詩跟日本現代詩最大的區別”的思考入手,介紹了近20年日本現代詩的存在形態,還有中國現代詩被譯成日語后的詩歌呈現形態和接受程度。特別是他以日語詩、旅居日本的中文新詩創作和翻譯實踐為比較主體,進而得出我們一流詩人的一流詩作不被日語體系接納的接受現狀,并提出了重視跨語際交流的重要性和相應的解決、提升方案。
三是從編輯出版的專業視角切入當前中國新詩研究的傳播生態,為新詩研究在期刊媒介平臺的選題需求提出意見。此次論壇有許多從事編輯工作的專家與會,他們在新詩傳播接受議題的探討中發揮了獨具特色的專業優勢。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楊程老師以《學術論文的關鍵詞的提取與功能》為題,關注到中國新詩研究在當前學術期刊的選題發表中處于薄弱環節。《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編審秦曰龍的《人文科學類論文選題的現實維度》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審宋媛的《學術論文的選題與創新》,都從編輯角度討論新詩研究的選題問題,達成了共識性理解,一致認為關注現實是中國新詩研究的關鍵,但更要有對新詩史、新詩學術史的關切。同時,能反映現代傳播接受多元渠道中的新詩研究文章,更能促進各方交流,推動學術研究多方發展。
綜上,本次“中國新詩與中外詩歌傳統國際學術論壇”云集四代專家學者,在深挖新詩內部發展演變的同時,注重新詩與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對話融合,積極引導新詩創作與研究走向更加多元、開拓與前瞻的方向。大家秉持對中國新詩發展的深厚責任意識,以宏闊的現代視野,回顧新詩的中外詩學源頭及傳播接受語境,深入檢視了中國新詩的百年教訓。本論壇對“中國新詩與中外詩歌傳統”的六大核心議題進行的深入討論與梳理,基本確立了從傳統中尋求資源并加以現代性轉化,從而實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與古為新”的學術共識。可以說,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的發生與發展,既離不開古代詩歌傳統的現代轉化,又少不了面向世界詩歌傳統的開放性形態。總之,今天的新詩既要繼承優秀傳統,又要面向未來吐故納新,唯有如此,中國詩歌的長河才會生生不息,氣象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