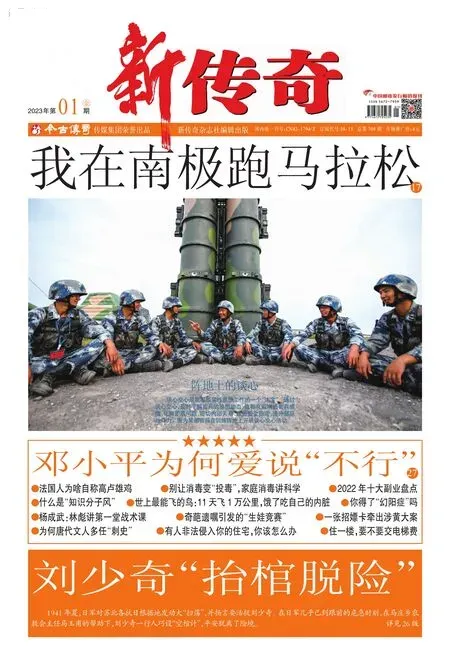古代皇帝想聽真話,都有哪些操作
歷史上,清醒的皇帝深知,專喜聽阿諛話的皇帝會犯糊涂,而皇帝犯糊涂,就意味著有可能步歷史上昏君的后塵。但是,皇帝要想聽真話、實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唐宋時期的皇帝為了聽到真話,可是煞費苦心。
歷史上,清醒的皇帝深知,專喜聽阿諛話的皇帝會犯糊涂,而皇帝犯糊涂,就意味著有可能步歷史上昏君的后塵。但是,皇帝要想聽真話、實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監察、確保信息暢通方面,唐宋時期的制度較為完善,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對輿情的及時把握。
唐朝設立“投匭”制度,保證下情上達
投匭制度形成于武則天垂拱二年(686 年),原先是在朝堂內放置了四個銅匭,銅匭四面開門,中有隔檔:東面叫“延恩”,涂成青色,凡向皇帝進獻頌賦、上養民、勸農之表,請求獲得官爵的則投之;南面叫“招諫”,涂成紅色,凡向皇帝上書論朝政得失的則投之;西面稱“伸冤”,涂成白色,凡有冤屈向皇帝申訴的可投之;北面稱“通玄”,涂成黑色,凡有關天象災變、軍謀秘劃之策以及告密者投之。
知匭官員的職能主要是收納投狀,分檔歸類,進行初步處理。唐朝規定,凡投匭文狀必須要有副本,知匭官員可以拆閱副本,進行初步處理,決定是否呈報皇帝。可見其權力還是很大的,其態度直接決定了投狀的成功與否,這種情況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視。

唐宋時期的監察、問責、多渠道疏通等制度堪稱完密,這種煞費苦心的頂層設計是很值得后人借鑒的
至德元載(756 年),右補闕閻式提出應先檢查投狀內容,然后再確定是否可以投匭。唐肅宗認為這樣會造成“壅塞”,下情不能及時上達,于是便將閻式撤職貶官。
為防止知匭官員隨意扣押投狀,保證上訪渠道暢通,唐代宗在寶應元年(762 年)索性下詔規定,不許知匭官員拆閱所投文狀,并不許盤問投狀人。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宋朝為官的常態
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后,吸取了前代各層官員欺蒙朝廷的慘痛教訓,陸續在州郡設立了“通判”一職,從而對知州知府起到監察的作用。
通判是由朝廷直接委派,而不是知州知府征辟的屬僚。此外,這個官無所不管,當然也包括州府屬下的縣級官員。
通判的設置,為知州知府加上了一道緊箍咒,有效規避了州府一把手獨斷專行的可能,他們不受知州知府甚至上級官員的轄制,直接對朝廷負責。
宋朝政區劃置采取三級制,即中央之下設路,路里設安撫使司(帥司)、轉運使司(漕司)、提點刑獄司(憲司)、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司(倉司),統稱“四大監司”,各管一攤,互補統轄。
宋朝統治者設置這四司除了“各管一攤”的分權理念之外,另賦予各司主管官員以監察之權,不論是安撫使還是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都負有為朝廷監察平級諸司官員、下級州縣官員的職責。這就好比朝廷在每個官員的身邊同時安裝上諸多的“監控探頭”,令所有官員都心懷畏懼,不敢輕易欺瞞朝廷。
對宋朝官員來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為官常態,為官者皆如此,最高統治者獲取各方面信息的渠道就大為暢通了,官員也不敢不說實話了。
宋朝官員很難堵塞信息傳遞之門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仁宗天圣七年再次設置理檢使,由御史中丞親自兼任,原因是“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并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這說明宋朝官民有各種傳遞信息的渠道,甚至可以直達御史臺,即使中間某些環節發生打壓欺瞞、不作為或亂作為,也封不住任何一個人的嘴。
宋馬永卿《元城語錄》記載,蘇軾被誣陷入獄后,友人張方平憤然不平,打算將訴狀交給所在應天府轉遞給朝廷,應天知府不敢接,于是張方命其子直接到京城由登聞鼓院投進。
除通判、監司、鼓院、檢院等制度外,宋朝還有一些臨時性或輔助性措施。如“風聞”,指的是不必證據確鑿,只要聽到風聲,即馬上進行深入調查核實并予以處理。
“體量”和“勘會”等詞語在宋朝史籍中也經常出現。所謂體量,即下層出現問題后,朝廷便派官員到事發地進行“一對一”的精準處置。“勘會”是指朝廷派專員到事發地詳細核查,代表朝廷進行案件的審理處置。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1016 年,河北轉運使隱瞞了大名府(今河北)、澶州(今河南濮陽)、相州(今河南安陽)的霜旱災情,當地民眾不得不到京城擊登聞鼓訴冤。宋真宗對大臣說道:“因為轉運使隱瞞了災情,使當地民眾沒得到朝廷應減免的稅賦。為弄清實情,朝廷必須再派大員到當地核查,按實際情況進行稅賦減免。”
唐宋時期的監察、問責、多渠道疏通等制度堪稱完密,這種煞費苦心的頂層設計是很值得后人借鑒的。但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實施這些制度的人特別是高層官員蛻變成了貪瀆之徒,造成制度和規矩成了一紙空文的結果,因此采取各種有效手段杜絕腐敗,也是執政者的頭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