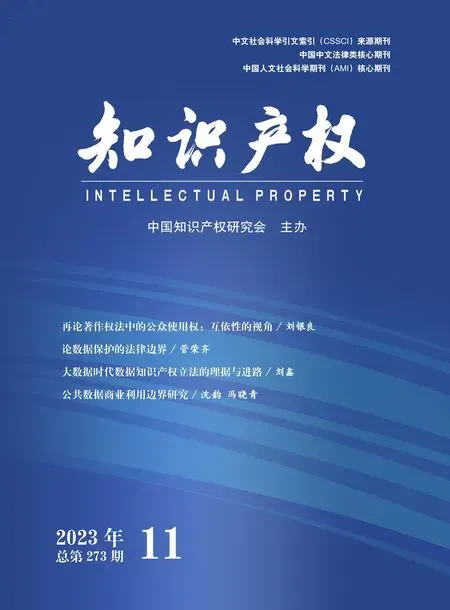人工智能合成音樂的著作權風險及其化解
焦和平 梁龍坤
內容提要:AI合成音樂以現(xiàn)有音樂作為原材料,其中包含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音樂作品和音樂錄制品。“AI表演”對現(xiàn)有音樂素材的復制性使用、表達性使用和傳播性使用使其面臨著作權侵權風險。由于“AI表演”與著作權法上的“表演”之間存在解釋論障礙,AI使用音樂素材面臨合理使用豁免困境和規(guī)范授權困境,傳播AI合成的音樂面臨侵權抗辯困境。建議從著作權法表演者權條款的擴大解釋、合理使用的有限豁免、法定許可的使用保障、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的機制迭代四個維度化解AI合成音樂的著作權風險。
一、問題緣起與研究現(xiàn)狀
(一)問題緣起
2023年上半年以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音樂①從字面上理解,與音樂相關的包括音樂作品(詞曲)、音樂表演、音樂錄制等,本文所探討的音樂僅指音樂表演,即演唱音樂作品的行為,為表述和理解方便,將其稱為AI合成音樂。合成技術的廣泛應用引起音樂從業(yè)者的強烈擔憂,也對版權制度提出新挑戰(zhàn)。2023年4月14日,網(wǎng)絡用戶“幽靈作者”(Ghostwriter)利用歌手德雷克(Drake)和威肯(The Weeknd)的聲音訓練AI模型并生成了歌曲Heart on My Sleeve,該歌曲在Spotify的播放量超過62.5萬次,在TikTok的累計播放量超過1500萬次。作為版權方的環(huán)球音樂集團對此表示,使用集團旗下歌手的音樂訓練AI,同時違反了合作協(xié)議和版權法,而且平臺在服務中提供AI生成的侵權歌曲,將嚴重破壞音樂生態(tài)。經(jīng)環(huán)球音樂方投訴后,該歌曲被各類平臺下架。②See ReportWire, Universal Music Group Responds to 'Fake Drake' AI Track: Streaming Platforms Have 'A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the Use of their Services in Ways that Harm Artists'-Music Business Worldwide, REPORTWIRE (17 April 2023), https://reportwire.org/universal-music-group-responds-to-fake-drake-ai-track-streaming-platforms-have-a-fundamentalresponsibility-to-prevent-the-use-of-their-services-in-ways-that-harm-artists/.4月18日,環(huán)球音樂方再度通過媒體表示其“有義務阻止未經(jīng)授權使用集團旗下的音樂,包括從歌曲中提取侵害歌手和其他創(chuàng)作者權利的內容”,并且已向Spotify等流媒體平臺發(fā)函,要求對方阻止將環(huán)球音樂方授權的歌曲用于AI訓練。③See Vanessa Yurkevich, Universal Music Group Calls AI Music A 'Fraud', Wants It Banned from Streaming Platforms. Experts Say It's Not That Easy, CNN BUSINESS (18 April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8/tech/universal-music-group-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ex.html#:~:text=The%20music%20group%20likens%20AI%20music%20to%20%E2%80%9Cdeep,ways%20that%20 harm%20artists%2C%E2%80%9D%20the%20UMG%20statement%20said.在版權制度的挑戰(zhàn)與回應方面,5月17日,美國國會召開AI與知識產權問題聽證會,其中第一單元的議題就是“AI與版權法的交互性”。美國詞曲作家協(xié)會(Society of Composers & Lyricists)主席、艾美獎得主阿什莉·歐文(Ashley Irwin)在聽證會上表示:“生成式AI對創(chuàng)意行業(yè)的生存和延續(xù)已經(jīng)構成威脅,除非在法律和經(jīng)濟方面能夠采取措施解決這些新問題。”④參見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官網(wǎng),https://judiciary.house.gov/committee-activity/hearing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llectual-property-part-i,2023年8月14日訪問。
AI合成音樂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的代表性事件是“AI孫燕姿”的爆火。據(jù)媒體報道,“AI孫燕姿”完成演唱的歌曲總數(shù)已經(jīng)超過1000首,遠超歌手本人出道以來的作品總和,⑤參見劉長欣、戴雪晴:《“二創(chuàng)”時代,幸運還是困境?》,載《南方日報》2023年5月28日,第A08版。此類AI歌曲在視頻網(wǎng)站的累計播放量超過千萬次。⑥在嗶哩嗶哩網(wǎng)頁端搜索“AI孫燕姿”,篩選分區(qū)為“音樂”,共有相關視頻1020條,其中最高播放量275.8萬次,播放量10萬次以上的視頻104條,參見嗶哩嗶哩網(wǎng):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ai%E5%AD%99%E7%87%95%E5%A7%BF&from_source=webtop_search&spm_id_from=333.1007&search_source=3,2023年8月14日訪問。2023年5月22日,歌手孫燕姿發(fā)表博文《我的AI》回應“AI孫燕姿”事件,其中寫道:“你怎么可能打得過一個在幾分鐘之內就能出一張新專輯的家伙?”而在此前,也有AI歌手的實踐案例。2023年3月22日,華語歌手陳珊妮宣布,新歌《教我如何做你的愛人》實際是由自身音色訓練的“AI陳珊妮”演唱,并希望借此推動藝術創(chuàng)作群體的思考——如果AI時代必將到來,在意的或許不該是“是否會被取代”而是“可以做些什么”。⑦參見沈昭:《還在談AI歌手?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歌手AI了》,載《揚子晚報》2023年3月27日,第A11版。可見,在AI合成音樂的實踐中,已出現(xiàn)了“正版”的AI歌手(如AI陳珊妮)和“盜版”的AI歌手(如AI孫燕姿)。
國內外關于AI合成音樂的各類事件反映出音樂權利人與AI服務行業(yè)之間已產生了利益沖突和著作權法律困境。從微觀視角,涉及AI利用歌曲合成音樂是否存在著作權侵權風險、能否獲得著作權侵權豁免,以及著作權法如何定性AI歌手;從宏觀視角,涉及AI合成音樂的發(fā)展與音樂權利人利益之間應當如何平衡。這加劇了音樂著作權保護的復雜局面,而如何化解AI產業(yè)發(fā)展與音樂權利人利益之間的復雜沖突和激烈矛盾,是著作權制度亟待回應的新挑戰(zhàn)。
(二)研究現(xiàn)狀
隨著AI音樂合成技術的應用,“AI孫燕姿”“AI周杰倫”等AI歌手現(xiàn)象所存在的著作權侵權風險問題也開始引發(fā)學界關注。目前既有研究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第一,從討論的內容來看,現(xiàn)有研究各有側重。有研究從被合成的音樂作品的角度討論了AI合成音樂是否侵害相關音樂作品的復制權、表演權、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及錄音制作者權等權利;⑧參見張偉君:《“AI孫燕姿”翻唱歌曲,侵權了嗎?》,載微信公眾號“知產前沿”2023年5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2uzCGFwLqETSCtiqKgT9rw.還有研究從目標歌手和被覆蓋歌手的角度討論了AI合成音樂是否侵害表演者權,以及AI歌手是否享有表演者權,并且提出不同的保護路徑。⑨參見陳杰:《AI表演的知識產權問題研究》,載《知識產權》2023年第7期,第56-75頁。第二,從所持觀點來看,已有研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如在狹義著作權視野下,關于在模型訓練中輸入音樂版權數(shù)據(jù)是否侵權:有學者認為這一問題的結論并不清晰;⑩同注釋⑧。相反觀點則認為構成復制權侵權是明確的。?參見焦和平:《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中數(shù)據(jù)獲取與利用的著作權風險及化解路徑》,載《當代法學》2022年第4期,第128-140頁。對于使用音樂作品的其他著作權問題:有研究認為合成歌曲的傳播構成對音樂作品著作權的侵權,?參見行海洋、陳琳:《人工智能浪潮下,法律風險不只存在于“AI孫燕姿”》,載新京報網(wǎng)2023年5月19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8447406414655.html.還可能涉及著作權人的表演權、廣播權及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參見王遷、孫維飛:《“AI孫燕姿”引發(fā)的著作權法與民法問題》,載嗶哩嗶哩網(wǎng)2023年5月24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s4y1T71u/?vd_source=cfb019a9a2f0740b0281ab5325d9181c.但另有研究從AI表演?“AI表演”是“AI合成音樂”的主要環(huán)節(jié),為便于理解和行文,本文使用的“AI表演”指代利用AI完成音樂演唱或演奏的行為。的視角提出,詞曲作者的著作權人應當是“不在場”的,在制度安排考量中也無需關注詞曲作者的利益。?同注釋⑨,第62頁。第三,在鄰接權視野下:有學者認為,“AI歌手”的表演既不會侵害目標歌手的表演者權,也不會產生表演者權;?同注釋?。但另有學者認為應當賦予目標表演者“表演者權”,并且提出“反淡化”的實現(xiàn)路徑。?同注釋⑨,第72頁。對于被覆蓋歌手及歌曲錄音的鄰接權:有觀點認為“AI孫燕姿”使用錄音制品,涉嫌侵害錄音制作者權及表演者的表演者權;?參見壽鵬寰、滿羿:《AI風口中音樂版權應該如何被保護》,載《北京青年報》2023年5月20日,第A07版。但另有觀點認為,表演者權和錄音制作者權項下都沒有“改編權”,因此,模仿表演、錄制風格等情形并不會構成對二者權利的侵害,但未經(jīng)許可使用目標歌曲原伴奏音頻,存在侵害錄音制作者權的風險?參見朱開鑫:《“AI孫燕姿”背后的版權迷宮》,載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2023年5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fDk_w-CqnTNsZYbgG9Q2yA.。
從現(xiàn)有研究的簡要梳理來看,當前關于AI合成音樂的研究成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需要進一步辨明;還有一些觀點值得商榷,需要進一步討論。實際上AI合成音樂涉及的問題不止這些,還有合成音樂的風險來源、風險類型、防范困境以及化解方案等。由于AI合成音樂真正引發(fā)關注始于2023年上半年,其中的諸多法律問題特別是著作權問題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剛剛開始,無論是從內容廣度還是分析深度上都待進一步加強,故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立足于此,本文在現(xiàn)有研究基礎上,揭示AI合成音樂的風險表現(xiàn),明晰產業(yè)應用的邊界,檢視現(xiàn)行制度之下著作權風險的防范困境,對比借鑒國內外立法,尋求AI合成音樂著作權風險的化解對策,希冀有利于深化AI的知識產權問題研究,助力AI賦能產業(yè)應用和依法合規(guī)發(fā)展。
二、AI合成音樂的著作權風險表現(xiàn)
(一)AI 合成音樂的產生機理
“AI合成音樂”涉及的著作權風險伴隨合成音樂的整個生成過程,故在評估其著作權風險之前有必要對其生成過程進行解析。從合成聲音來看,AI合成音樂使用的核心技術源自一種聲音轉換模型,它可以將不同的聲音進行自由轉換,并且高度還原目標歌手的音色、慣用唱腔和發(fā)音特點,進而合成與目標歌手演唱風格相一致的音樂歌曲,基本能夠達到難以辨別的真實度。其具體生成過程可分解為四個環(huán)節(jié):首先,收集聲音元素,向模型中輸入目標歌手的聲音素材,例如歌曲錄音、活動訪談等過程中出現(xiàn)的真人聲音;其次,提取演唱特征,歌聲轉換模型通過內容編碼器提取目標歌手的音調、音高等特征(如要合成孫燕姿的聲音,就需要從她曾演唱的歌曲中提取),然后將具備前述特征的聲音素材做成時長很短的切片;再次,匹配目標歌曲,將第一個環(huán)節(jié)收集到的目標歌手(如孫燕姿)的聲音數(shù)據(jù)作為訓練數(shù)據(jù)源交給算法提取特征,再將這些特征數(shù)據(jù)與歌曲的切片對應;最后,對生成的歌曲進行后期優(yōu)化,比如加入混響或簡單修音。如此下來,一首AI合成的歌曲就制作完成了。從技術原理上分析,AI合成音樂是通過采集目標歌手的聲音素材并進行反復“訓練”,最終輸出接近歌手本人音色的聲音模型。這個模型需要大量的訓練數(shù)據(jù)和不斷反復迭代的訓練過程,以使生成的輸出效果盡可能接近目標歌手,目前代表性的相關技術有So-vits-svc、VITS、soft-vc、VISinger2等。按照上述原理,AI合成音樂的便利化程度及其仿真程度已經(jīng)非常高,用戶使用AI合成音樂服務十分便利,歌曲創(chuàng)作變得觸手可及,用戶無需具備專業(yè)的音樂制作知識,就可以創(chuàng)作出歌曲。
(二)圍繞AI 合成音樂作品產生的著作權風險
1.侵害復制權的風險
侵害復制權的風險源于AI系統(tǒng)進行的數(shù)據(jù)采集與使用行為。AI的“智能”源于其強大的學習能力,大量數(shù)據(jù)的“喂養(yǎng)”使其深化對模仿對象風格和特征的規(guī)律認識,這個過程包括閱讀和學習兩個主要階段,也稱為機器學習。機器學習是培養(yǎng)機器智能的必要手段,機器學習的對象主要是現(xiàn)有素材,其中包含了受版權保護的作品。AI合成音樂侵害復制權的風險同樣體現(xiàn)在機器學習過程中,機器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數(shù)字化的音樂作品,還包括數(shù)字化的音樂錄音制品。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儲存訓練數(shù)據(jù)的復制權侵權風險。機器輸入中對數(shù)字形式音樂作品的備份可能構成復制行為。AI服務提供者需要構建一個數(shù)據(jù)庫,并用一個合成音樂的算法模型不斷訓練,從概率上無限接近于特定歌手的音色和演唱風格,最終達到足以“以假亂真”的水平。數(shù)據(jù)庫的構建需要將大量數(shù)字化音樂作品作為訓練素材導入素材庫,需要儲存數(shù)字復制件,可能構成對原音樂作品復制權的侵害。按照我國著作權法,數(shù)據(jù)留存行為可能落入復制權的控制范圍。實踐中也出現(xiàn)了對將音樂作品用于機器模型訓練的反對聲音,2022年10月,美國唱片業(yè)協(xié)會(RIAA)警告稱,AI供應商使用現(xiàn)有音樂來訓練他們的機器,“是一種集體侵犯版權的行為”。?參見音樂財經(jīng):《AI創(chuàng)作歌曲版權如何界定?美國版權局發(fā)布最新政策報告》,載新浪財經(jīng)網(wǎng)2023年3月18日,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3-03-18/doc-imymheuh1006173.shtml.在2023年5月舉辦的“第八屆音樂產業(yè)高端論壇”上,擁有孫燕姿歌曲版權的環(huán)球音樂集團相關負責人對“AI孫燕姿”問題表明立場:“AI公司如果要使用到我們的作品,必須要先得到許可,必須要合法地使用。”?? 同注釋?。? 參見史正丞:《環(huán)球音樂施壓流媒體禁用侵權AIGC作品“AI不犯法”仍是難題》,載財聯(lián)社網(wǎng)2023年4月12日,https://www.cls.cn/detail/1320510#headerWrap.該負責人同時表示,環(huán)球音樂集團已要求流媒體平臺“刪除由AI生成的歌曲”。不過一些詞曲作家或歌手并不反對使用AI,認為可以通過收取版稅的方式取得合法授權。
第二,音樂采樣與輸出的復制權侵權風險。音樂采樣是指從現(xiàn)有歌曲錄制品中采集曲調、旋律或節(jié)奏,用于即將創(chuàng)作的作品當中,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可以對樣本的音色、音調進行不同程度的調整,也可以將樣本直接加入到新作品中。由于采樣對象中含有音樂作品的曲調、表演者演唱并經(jīng)錄制者固定的聲音,在采樣時不僅可能侵犯音樂作品的著作權,還可能侵犯圍繞錄音制品產生的鄰接權。AI合成音樂也可以從現(xiàn)有歌曲中采樣,如果對被采樣歌曲進行機械復制(未進行一定的藝術加工便融入新作品),使得AI合成音樂的詞曲等核心組成部分與現(xiàn)有音樂作品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若二者構成實質性相似,則可能構成侵權。據(jù)AI生成音樂領域的谷歌Music LM模型的開發(fā)團隊披露,該模型使用了28萬個小時的音樂來訓練,然而在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該模型存在“生成不當內容風險”(Music LM生成的音樂中,有1%會直接照搬版權作品)后,該公司一直沒有發(fā)布成品。?? 同注釋?。? 參見史正丞:《環(huán)球音樂施壓流媒體禁用侵權AIGC作品“AI不犯法”仍是難題》,載財聯(lián)社網(wǎng)2023年4月12日,https://www.cls.cn/detail/1320510#headerWrap.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關于AI表演中是否涉及音樂作品詞曲作者的權利問題,有學者提出“詞曲作者不在場”的觀點,理由是“在名義上,詞曲作者是名正言順的權利人,有權直接否認AI表演的合法性,但這種否認并不符合法理;在實益上,AI表演是與詞曲作者無關的事情,他們不操心也不應當操心AI表演的影響”,進而得出“在制度安排的價值判斷中,知識產權法無需考量詞曲作者的得失”的結論。?? 同注釋⑨,第62頁。? See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p.113.這一觀點似乎值得商榷:其一,為什么詞曲作者“有權直接否認AI表演的合法性,但這種否認并不符合法理”?這與該學者在同一篇論文中提出的“AI表演最可能侵犯的權利恰恰是音樂作品的著作權”觀點似有矛盾。其二,正是因為實踐中詞曲作者的權益經(jīng)常被忽略,所以才需要包括學者在內的全社會更加重視,以推動該項權利從被忽視的“紙上的權利”轉化成“現(xiàn)實的權利”。因此,在提出“AI表演最可能侵犯的權利恰恰是音樂作品的著作權”的同時,卻作出“在AI表演問題的研究中,詞曲作者應當是‘不在場’的”“在制度安排的價值判斷中,知識產權法無需考量詞曲作者的得失”的結論,無疑是對本來就被忽略的詞曲作者利益的“再次忽略”。其三,前文引述的國內外音樂作品作者反對AI表演擅自使用其作品的實例表明,音樂作品權利人并非“不在場”,而是對自己在AI表演產業(yè)鏈條中的主體地位有清醒的認識,并且一直在積極主張權利。因此,認為在產業(yè)利益中不考慮詞曲作者的觀點,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實踐,對處于AI表演產業(yè)鏈源頭的音樂作品權利人而言更難謂公平。
概言之,將他人的音樂作品用于訓練算法模型,提取詞曲、旋律等內容作為音樂樣本、音樂元素以輔助生成音樂,如未獲得相應授權,可能構成侵權。同時,由于將他人的音樂作品用于自己的商業(yè)活動,比如AI開發(fā)者將他人的音樂作品提供給用戶自由使用,屬于利用他人的音樂作品進行營利活動,因此難以主張侵權豁免(后文詳述),存在侵害復制權的風險。世界范圍內觀察,正是為了應對AI創(chuàng)作在使用訓練數(shù)據(jù)時可能會侵害復制權的法律風險,歐盟《單一數(shù)字市場版權指令》第二章規(guī)定了機器學習有關的例外情形,第3條規(guī)定了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文本與數(shù)據(jù)挖掘的例外,第4條規(guī)定了出于其他目的的文本與數(shù)據(jù)挖掘的例外。?? 同注釋⑨,第62頁。? See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p.113.前述規(guī)則為AI訓練行為的數(shù)據(jù)復制問題提供了安全框架,為AI時代的機器訓練鋪平了道路。由此,不難窺見AI合成音樂面臨的侵害復制權風險是客觀存在且無法回避的,亟待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推動解決。
2.侵害表演權的風險
第一,現(xiàn)場表演權侵權風險的排除。音樂作品主要借助表演傳達藝術價值,因此表演權是音樂作品權利人的重要財產權。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第9項規(guī)定:“表演權,即公開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種手段公開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權利。”該規(guī)定表明,表演權包含現(xiàn)場表演權和機械表演權兩項子權利,AI表演音樂是否落入表演權的控制范圍,需要考察AI表演的行為特點和制度依據(jù)。之所以認為AI表演音樂不是現(xiàn)場表演,是因為從現(xiàn)有規(guī)定的文義解釋來看,現(xiàn)場表演是指演員通過語言、動作、表情、道具、樂器等現(xiàn)場再現(xiàn)作品的過程,因此現(xiàn)場表演又被稱為“活表演”。從《著作權法》對表演權的規(guī)定來看,《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表演行為應符合表演行為的實施者是自然人這一要求。從《視聽表演北京條約》關于“‘表演者’系指演員、歌唱家、音樂家、舞蹈家以及對文學或藝術作品或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進行表演、歌唱、演說、朗誦、演奏、表現(xiàn)或以其他方式進行表演的其他人員”之規(guī)定來看,表演者也是指自然人。??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第2條。? 參見焦和平:《“機械表演權”的法源澄清與立法完善——兼論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載《知識產權》2014 年第4期,第27頁。因此,按照國際法源和國內法依據(jù),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表演”要求主體的自然人屬性,故AI表演不存在侵害現(xiàn)場表演權的風險。
第二,侵害機械表演權的風險的證成。機械表演,是指通過機器設備等手段向公眾傳播作品的表演的行為,即用各種手段公開播送作品的表演。??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第2條。? 參見焦和平:《“機械表演權”的法源澄清與立法完善——兼論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載《知識產權》2014 年第4期,第27頁。現(xiàn)行《著作權法》并沒有明確機械表演中“各種手段”和“公開播送”的范圍,一般認為,商場、超市、酒店、餐廳等營業(yè)場所播放背景音樂的行為,屬于典型的機械表演。雖然AI合成音樂中的“表演”實際由AI完成,與傳統(tǒng)意義上對表演主體的理解有出入,但從解釋論視角來看,《著作權法》規(guī)定的表演權是對表演(動詞)作品行為的控制和對傳播作品表演(名詞)的控制,AI表演實際上達到了音樂作品被呈現(xiàn)(被表演)的客觀效果,在AI合成音樂普及的環(huán)境下,AI能夠通過表演將作品傳播給公眾,符合著作權法上表演權控制的“向公眾傳播表演的行為”。從立法目的而言,表演權條款旨在規(guī)制對作品的演繹性再現(xiàn),以保護著作權人因創(chuàng)作作品而產生的財產性權益,起到激勵再創(chuàng)作的作用。而利用AI技術“翻唱”[27]翻唱一般主要針對音樂作品,AI表演針對的是表演者(例如模仿孫燕姿的聲音)。由于“AI孫燕姿”等具有擬人化的特征,“翻唱”也能夠直觀反映本文討論的行為,即AI對現(xiàn)有歌曲的使用中包含的類似“翻唱”行為,因此本文會在需要的語境下使用“翻唱”。他人歌曲在本質上實施了將他人的音樂作品以聲音再現(xiàn)的效果,符合機械表演的特征。退一步講,即便認為AI表演本身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的表演,但AI表演客觀上將音樂作品演唱后生成了數(shù)字化形式的錄音文件,也即將一個音樂作品固化為錄音,產生了鄰接權意義上的錄音制品,將該錄音制品通過網(wǎng)絡再現(xiàn)的行為,仍然可能落入機械表演權控制的范疇。
3.侵害傳播權的風險
傳播權是著作權人重要的財產權,包括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和廣播權。
第一,通過信息網(wǎng)絡傳播AI合成的音樂存在侵犯音樂作品權利人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風險。根據(jù)《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對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定義可知,[28]參見2013年《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26條。通過信息網(wǎng)絡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并使公眾能夠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而自由獲取,即為實施了信息網(wǎng)絡傳播行為。關于提供行為的認定,根據(jù)相關司法解釋[2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2020年根據(jù)法釋〔2020〕19號決定修正)。,在行為方式上,包括通過上傳到網(wǎng)絡服務器等方式;在行為效果上,使公眾可不限時間地點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應當認定其實施了“提供”行為。實踐中,AI合成音樂目前有兩種主要的傳播渠道:一種是通過音樂類的網(wǎng)絡內容服務提供者傳播,比如QQ音樂、網(wǎng)易云音樂等音樂平臺;另一種是通過短視頻類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傳播,比如抖音、嗶哩嗶哩等短視頻平臺。不論采用哪一種渠道,其在網(wǎng)絡中提供作品、表演或錄音制品的行為均符合“提供”的構成要件,難以脫離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控制范圍。
第二,通過有線或無線方式廣播或轉播AI合成的音樂存在侵犯廣播權的風險。廣播權與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傳播源與傳播受眾之間是否具有交互性。根據(jù)2020年《著作權法》對廣播權的修改,如果“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公開傳播或者轉播作品”,同時這種傳播又不具有交互性,即可以受到廣播權的控制,不論其傳播源是有線還是無線。AI合成音樂中關于廣播權的復雜判斷,集中在直播AI表演音樂作品是否落入廣播權的控制范圍。例如在直播中,“AI孫燕姿”作為主播演唱了陳奕迅作為原唱者的《十年》,應該如何判斷?司法實踐中,法院曾將直播間翻唱的行為納入“其他權利”的控制范圍,[30]參見北京麒麟童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訴武漢斗魚網(wǎng)絡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表演權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民事判決書(2020)京73民終2905號。原因是該案判決生效前,適用的是2010年修正的著作權法。但是在2020年《著作權法》修正后,“網(wǎng)絡直播”歸類為“廣播權”,而非“其他權利”,于是在直播間中表演并通過網(wǎng)絡進行公開播送的行為應納入廣播權的控制范圍,音樂的網(wǎng)絡直播行為(包括演唱、演奏)、網(wǎng)絡實時轉播行為均落入廣播權范疇。因此,AI主播在直播間翻唱的行為同樣會落入廣播權的控制范圍,存在侵權風險。但應當注意的是,在外在體現(xiàn)上,直播行為將AI合成音樂的過程覆蓋了,使AI合成音樂行為容易被忽略。除了直播行為,AI合成音樂以其他方式傳播的廣播權問題,與常規(guī)的音樂作品廣播權問題在判斷上并無本質區(qū)別,只要以非交互方式傳播AI合成的音樂,其中又包含了版權音樂作品,即會落入音樂作品權利人廣播權的控制范圍。
(三)圍繞錄音制品產生的著作權風險
1.侵害表演者權的風險
第一,AI翻唱存在侵害表演者的表明身份與保護表演形象的精神權利的風險。《著作權法》第39條第1款第1項和第2項規(guī)定了表演者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和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權利。在AI合成音樂問題中,這同時涉及被覆蓋的表演者和目標表演者。從被覆蓋的表演者視角而言,在表明身份層面,AI翻唱對原歌曲的表演進行音色替換,雖然在完成換音后的歌曲中找不到被覆蓋歌手的音色痕跡,但是其作為原唱者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與翻唱者在翻唱歌曲中應當表明歌曲原唱者身份的邏輯是相同的。正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guī)定表演者表明身份的權利不可剝奪且不因時效而喪失,甚至可被轉給繼承人。[31]參見《十二國著作權法》翻譯組譯:《十二國著作權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頁。因此,AI翻唱如果沒有正確標明原表演者,可能侵害原表演者(即原唱歌手)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權利。在保護表演形象層面,AI翻唱未經(jīng)表演者授權模仿他人聲音覆蓋原歌曲表演者的聲音,這種未經(jīng)許可改變表演內容的行為涉嫌侵犯原唱歌手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權利。
從目標表演者視角而言,歌曲被AI翻唱并非與其無關。歌手的聲音、技巧等元素的組合或已構成特定風格的表演形式,AI歌手的任意翻唱行為,涉嫌侵犯表演者的著作人身權,比如署名、表明表演者身份、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等權利。以目標表演者(例如孫燕姿)對于翻唱歌曲的選擇權與決定權為例,在傳統(tǒng)音樂市場中,翻唱何種歌曲,本應由表演者本人與其經(jīng)紀公司或唱片公司,基于歌手風格、音樂市場、作品質量等因素綜合考量共同決定。在AI時代,用戶代行了表演者的選擇權與決定權,用戶可以根據(jù)自身喜好選擇“AI孫燕姿”的翻唱歌曲,比如“AI孫燕姿”翻唱騰格爾演唱的《天堂》、屠洪剛演唱的《霸王別姬》等風格迥異的歌曲。這種風格上顛覆性的差異,難以謂之是基于感受藝術創(chuàng)作的目的,更多的是滿足觀眾的娛樂心理,將風格反差的翻唱音樂作為消遣的娛樂內容,極大地滿足聽眾的好奇心,產生強烈的喜劇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表演者原表演形象的歪曲,從而涉嫌侵犯表演者著作人身權。
第二,侵害表演者財產權益的風險。如前所述,AI表演生成者代行了目標歌手對表演對象的選擇權與決定權。一方面,從經(jīng)濟角度考量,AI翻唱歌曲對歌手本身的市場資源會產生一定影響。傳統(tǒng)音樂市場下,音樂公司基于商業(yè)考量,會與歌手就翻唱目標歌曲進行協(xié)商,歌手可以就擬翻唱的歌曲風格、詞曲內容等提出意見,并基于知名度取得表演獲酬的議價權,而AI表演歌曲則完全跳過這一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雖然AI只是模仿了目標歌手的音色,但是基于上述分析,以及考慮《著作權法》同等保護表演者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立法意涵,AI表演涉嫌侵犯孫燕姿作為表演者獲取報酬等財產權利。
第三,許可他人復制對作品的表演的權利。對AI訓練的復制權問題,理論上存在不同認識。有觀點認為,AI訓練素材的復制權侵權問題“目前似乎沒有清晰的答案”[32]同注釋⑧。,并且對各種規(guī)則能否真正落地實施表示擔憂。本文認為,這一答案是清晰的,前文述及的《著作權法》第39條第1款第5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2023年8月15日起實施)第7條對此已經(jīng)作出明確規(guī)定。此外,本文認為,法律規(guī)則如何實施是法律實際運行層面的問題,本文討論的是行為的定性問題,即未經(jīng)允許復制對作品的表演是否侵權,不能因為法律規(guī)則無法落實而回避侵權定性,并且侵權規(guī)制是否無法操作也值得商榷。[33]筆者另一篇文章對此問題有探討,同注釋?,第128-140頁。
本文認為,AI合成音樂提取錄音制品中的表演存在侵權風險。根據(jù)《著作權法》第39條第1款第5項規(guī)定,表演者對其表演享有“許可他人復制錄有其表演的錄音制品,并獲得報酬”的權利。該條規(guī)定了表演者對載有表演的錄音制品享有的權利范圍,指向的權利客體是表演者的表演,而不是載體錄音制品。AI表演主要涉及對表演的復制,利用AI軟件在音頻素材中“提取”特定歌手的聲音,屬于對錄音制品中表演的復制,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復制表演者的表演(聲音)須征得許可,因此提取聲音并利用聲音訓練涉嫌侵犯表演者權中的復制權。同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7條規(guī)定的提供AI服務不得侵害他人知識產權,自然包含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要求。在AI合成音樂過程中提供對錄音制品中的表演的提取服務,也違反開展預訓練、優(yōu)化訓練等訓練數(shù)據(jù)處理活動不得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規(guī)定。
2.侵害錄音制作者權的風險
對于AI表演涉及哪些錄音制品制作者的問題,有研究將其歸納為被覆蓋的原錄音的錄制者和利用AI表演制作新錄音的錄制者兩類。[34]同注釋⑨,第65頁。本文認為這一概括并不完整:第一,AI表演涉及的錄制者還有錄制目標歌手聲音的原錄音制作者(如出版孫燕姿專輯的唱片公司),因為提存、訓練和合成環(huán)節(jié)中需要使用目標歌手的演唱聲音。第二,如果按照該觀點,認為由于AI表演不涉及對原錄音制品的使用,所以才不涉及原錄音制品制作者的權利,這與該研究對AI表演的定義(認為AI表演并不只涉及著作權法上的表演問題,而是一個集作品表演和錄音制作于一體的行為集合)相左。該文在技術原理分析中也認為目標表演者和被覆蓋表演者之間發(fā)生了音色替換,如果AI表演不涉及原錄音制作者制作的錄音制品,那么AI表演所使用(提取和替換)的聲音來源與替換對象從何而來?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進一步判定AI表演是否涉及原錄音制作者。第三,如果不涉及原錄音制作者制作的錄音制品,那么其工作原理應該是輸入詞、曲后,AI自行合成并演奏,不借助任何已有的同作品的演唱的錄音載體(當然,這種方式并非絕對不存在,但并非本文的研究重點)。
換言之,錄音制品的使用不僅涉及新錄音制作者權利,而且同樣涉及被提取聲音的錄音的制作者權利。具體而言,AI合成音樂主要涉及被提取聲音的錄音的制作者的兩種侵權風險:一是錄音制品的復制權。《著作權法》第44條第1款規(guī)定:“錄音錄像制作者對其制作的錄音錄像制品,享有許可他人復制、發(fā)行、出租、通過信息網(wǎng)絡向公眾傳播并獲得報酬的權利……”錄音制品,是指任何憑聽覺可感知的對表演的聲音和其他聲音的固定,[35]參見黃薇、王雷鳴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導讀與釋義》,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頁。AI合成音樂對演唱聲音的提取實則就是對錄音的復制。二是錄音制品的傳播權,包括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和廣播權。如果在AI服務中內置用戶可以自由選取的錄音制品,供用戶生成任意風格的翻唱歌曲,則存在侵害錄音制作者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風險。
三、解釋論下AI合成音樂的著作權風險化解困境
(一)合成音樂中“AI 表演”規(guī)制的困境
1.AI 表演對表演者主體范圍的沖擊
我國加入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均將表演者限定為自然人。[36]參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1996年)第2條(a)項、《視聽表演北京條約》(2012年)第2條(a)項。《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國際公約》也作出相似規(guī)定。[37]參見《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國際公約》(1961年)第3條(甲)項。為了與國際條約接軌,我國2020年修正的《著作權法》刪除了“表演者(演員、演出單位)”表述中的“(演員、演出單位)”,意味著“表演者”只能是自然人。因此,從規(guī)范解釋的視角來看,AI表演并不符合傳統(tǒng)著作權法上“表演者”的“自然人”主體要求。但如果就此否定AI表演在著作權法上的評價意義,似乎又難以解決AI表演對音樂作品著作權人和表演者的權利造成沖擊的困境。
2.AI 表演對錄音制作者權利正當性的挑戰(zhàn)
AI表演的音樂會以數(shù)字音頻的形式傳播,使公眾能夠通過在線音樂平臺或短視頻平臺獲取,因此,AI表演過程中存在一個新的錄音制作行為,對該行為需要單獨評價。但是通過考察錄音制作者權的立法目的發(fā)現(xiàn):一方面,錄制者對表演的錄制按照一定的規(guī)律選取了音源,進行編排組合,最終形成一個具有一定藝術效果的錄音制品;另一方面,《著作權法》對錄音制作者的保護其實針對的是錄音制作者(通常是企業(yè)或組織)在組織人員、提供環(huán)境和設備、唱片技術處理等環(huán)節(jié)對作品固定做出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最終的錄制品一定程度反映了制作者的思想。英國《版權法》甚至曾主張:創(chuàng)作一部作品,表演者表演這部作品或者錄制者將該作品或對該作品的表演錄制下來,這些都屬于創(chuàng)作過程,在版權保護上應當一視同仁。[38]參見劉家瑞編:《〈鄭成思知識產權文集〉版權及鄰接權卷(一)》,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頁。也即錄制者權是基于錄制者對作品或者表演的錄制投入了創(chuàng)造性勞動和必要成本。但回到當下AI表演的錄音制品,這一賦權的正當性基礎似乎不再具有說服力。理由是:從效果而言,AI表演的錄音制品與傳統(tǒng)的錄音制作者制作的錄音制品并無明顯差異,但從錄音制作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和必要成本而言,無法捕捉到AI表演的錄音制作者有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應排除AI設計者,畢竟其并非慣常的實際使用主體)。于是,上述兩方面的沖突導致了基于AI表演賦予錄音制作者權可能存在權利賦予的不正當,進而打擊傳統(tǒng)錄音制作者繼續(xù)投入錄音制作的積極性,也可能導致鄰接權客體確認的標準出現(xiàn)混亂。概言之,AI表演的錄音制品,對賦予錄音制作者權利的正當性提出了挑戰(zhàn),雖然我國《著作權法》并未明確規(guī)定錄制者權的條件,從行為效果上似乎可基于AI表演的錄制品賦權,但從立法目的進行考量,缺乏賦權的正當性基礎。
3.規(guī)制AI 表演的必要性爭議
AI表演在規(guī)范評價上的困境,引出對AI表演規(guī)制必要性的討論。有學者就是否有必要對AI表演進行規(guī)制提出觀點,認為“如同盜版會增加正版的銷量,AI表演與目標表演者也可以是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關系”,以及AI表演雖然涉及表演者權益,但是“目標表演者并沒有動力去控制和阻礙AI表演”,AI表演讓目標表演者更具知名度,表演者因此具有了更多元的收入渠道,因此沒有規(guī)制的必要。[39]同注釋⑨,第64頁。上述觀點似有待商榷:第一,即使目標表演者因AI表演提高了知名度,也不能因此得出“用了白用”的結論。這正如雖然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可以提升每一位表演者的社會影響力,但不能因此認為可以無視表演者的著作權。正因如此,中央電視臺曾表明堅持與每一位參加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作者(表演者)簽訂版權協(xié)議以獲得授權并支付相應報酬。[40]參見《春晚年年辦 稿酬一直有》,載鳳凰網(wǎng)2011年10月13日,https://news.ifeng.com/c/7faYERGPrAU.
第二,“目標表演者并沒有動力去控制和阻礙AI表演”的觀點也與實踐不符,目前國內外均有詞曲作者和表演者反對AI表演擅自使用其音樂作品及聲音素材的實例。前文提及的國外“幽靈作者”事件就是例證,網(wǎng)絡用戶利用歌手的聲音訓練AI模型并生成歌曲,該歌曲在流媒體平臺獲得千萬次點擊,而作為歌手音樂版權方的環(huán)球音樂集團則發(fā)起了維權行動,一方面發(fā)出警告,指出類似行為既違反協(xié)議也違反版權法,另一方面也通過投訴要求平臺將該歌曲下架,并且要求平臺避免類似行為再次發(fā)生。美國唱片協(xié)會等組織也發(fā)起“人類藝術運動”(Human Artistry Campaign),組建了藝術家聯(lián)盟以抵制AI表演,該聯(lián)盟的成員不斷增多,并且覆蓋了創(chuàng)作者、表演者以及錄音制作者。[41]同注釋④。環(huán)球音樂集團的發(fā)言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個影響音樂歷史進程的選擇,指出問題在于音樂行業(yè)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希望站在歷史的哪一邊:是站在藝術家、粉絲和人類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一邊,還是站在深度偽造、欺詐和拒絕給予藝術家補償?shù)囊贿叄縖42]參見WUSF新聞網(wǎng),https://wusfnews.wusf.usf.edu/2023-04-21/when-you-realize-your-favorite-new-song-was-written-andperformed-by-ai, 2023年8月15日訪問。因此,不論是從法理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通過法律明確回應AI表演中目標歌手的利益,都是必要且緊迫的。
(二)權利例外與限制侵權抗辯的困境
1.AI 合成音樂與“個人使用”
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著作權法》第24條第1款第1項的規(guī)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jīng)發(fā)表的作品”,可以不經(jīng)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此即我國立法上的“個人使用”合理使用類型。在AI表演中,使用者對AI系統(tǒng)發(fā)出指令后,AI系統(tǒng)對歌曲的表演能否構成個人使用的學習、研究或者欣賞,需要考慮以下因素。一是被使用的音樂作品,是否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合法獲取,并且不屬于禁止使用的范圍。如果作品尚未公開或者不屬于被允許使用的范圍,則相關行為可能屬于侵權行為。二是使用的數(shù)量和質量,是否符合合理限度,即不超過合理使用所需的數(shù)量和質量。三是使用產生的影響,合理使用不會影響音樂作品的市場價值,即對音樂著作權人的利益不應產生負面影響。
AI音樂合成軟件通過分析已有的音樂素材,生成新的、與原始素材相似度較高的歌曲,甚至生成與輸入素材的詞曲元素完全相同的歌曲,而僅僅改變了演唱者的音色。在部分音樂平臺檢索發(fā)現(xiàn),AI合成的音樂已經(jīng)上傳,并且能夠正常播放。在視頻平臺也可檢索到大量以AI合成音樂為主要內容并配以相關畫面的視頻,但實質上此類視頻的價值在于用戶能夠收聽歌曲,因為大量在音樂平臺收費的曲目在視頻平臺并不需要付費。盡管AI歌曲的最終呈現(xiàn)方式有所不同,但客觀上不可否認的是,AI 合成音樂對原音樂作品的市場價值產生了沖擊,這種沖擊超出了合理使用的制度預設。因此,AI合成音樂不論從使用主體、數(shù)量還是目的方面考察,均不符合法律規(guī)范的意旨,難以適用合理使用抗辯。我國《著作權法》第24條第2款規(guī)定:“前款規(guī)定適用于對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限制。”據(jù)此,AI合成音樂對表演、錄音制品等鄰接權客體的使用,也應當根據(jù)前述規(guī)定進行判定,并且能夠得出同樣的結論。
2.AI 合成音樂與“免費表演”
AI合成音樂對音樂作品的使用,若要構成免費表演,應符合三個要件:一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二是僅針對已發(fā)表的作品;三是雙向免費,即公眾獲取該表演無須支付對價,表演者不因表演而獲得報酬。其中,“營利目的”的排除是2020年《著作權法》修改時的新增要件,修改原因是為防止變相實現(xiàn)營利目的,以免費表演為名吸引觀眾,進而通過收取廣告費等方式獲取利益。[43]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載中國人大網(wǎng)2020年11月11日,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1/t20201111_308676.html.這一修改契合平臺經(jīng)濟時代的特點,優(yōu)質內容服務的獲利來源并不完全依賴用戶提供直接對價,而是通過累積“粉絲量”“播放量”“用戶量”等新型指標,以廣告等方式實現(xiàn)流量變現(xiàn)。AI系統(tǒng)具備按照作詞、編曲進行表演的能力,其對作品的使用行為并不符合“免費表演”的條件。理由如下:首先,營利目的無法排除,AI合成音樂本質上是一種商業(yè)行為,意圖通過提供服務或者優(yōu)化功能實現(xiàn)獲利,即便沒有直接支付對價的買賣行為,此類行為的商業(yè)性質也不難窺探。其次,不符合雙向免費的要件,通過AI表演歌曲的行為,聽眾與表演者之間即便不存在直接的對價交換,表演方仍可以通過提高聽眾數(shù)量、播放量等平臺經(jīng)濟模式獲利,故雙向免費難以成立。如短視頻平臺嗶哩嗶哩上關于“AI孫燕姿”翻唱的視頻,點擊總量高達數(shù)千萬次;在短視頻平臺抖音上,“AI孫燕姿”的話題視頻點擊量也達到數(shù)千萬次。與這些高點擊量相對應的,是平臺和用戶可觀的流量收益。最后,免費表演只針對已發(fā)表作品,AI表演的如果是尚未發(fā)表的作品,即使是免費的,也應當獲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否則難以主張合理使用作為抗辯理由。雖然AI合成音樂中使用的多為已發(fā)表的音樂作品,但結合前述要件的分析,仍然不符合免費使用的條件。
(三)AI 合成音樂規(guī)范授權的困境
1.音樂作品和錄音制品的權利結構復雜
在AI合成音樂的場景下,音樂作品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制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十分復雜。表演者表演的內容主要是著作權人的作品,錄音制作者錄制的對象是表演者的表演,因此在授權使用時涉及復雜的權利結構。圍繞音樂作品涉及到復制權、表演權、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以及廣播權,圍繞表演還涉及表演者權。但是表演者權又分為多項子權利,包括許可錄制表演、復制已經(jīng)錄制的表演、傳播或者廣播表演的權利,圍繞錄音制品則產生了錄音制作者權及其子權利,包括許可他人復制、發(fā)行、傳播錄音制品。行為的交錯及技術的融合使得權利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筆者曾對技術變革中“廣播權”與“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交叉重疊問題進行梳理,并提出避免再走技術立法主義的道路,以免落入“技術—修法”的怪圈,并總結出“一個傳播終端、六類傳播行為、三種法律定性”的復雜局面。[44]參見焦和平:《三網(wǎng)融合下廣播權與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的重構——兼析〈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前兩稿的相關規(guī)定》,載《法律科學》2013年第1期,第152頁。在著作權法視野中,在AI技術對表演、錄音等行為產生主體淡化、方式簡化、流程扁平化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這種復雜的權利構造和保護體系的交叉重疊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因此,權利結構的復雜化,是音樂類生成式AI服務中授權問題難以規(guī)范化的一個原因。
2.法定許可與集體管理機制銜接不暢
按照前文分析,AI合成音樂中對受版權保護的歌曲的使用應當獲得授權,但在規(guī)范授權問題上面臨如下困境。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guī)定,音樂作品授權有兩種途徑,一是集體管理組織授權,二是權利人自行授權。在集體管理授權方式中,存在的障礙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經(jīng)濟成本高昂。完成授權是一個由使用者到授權者的單向鏈條,使用者提出授權請求,授權者按照規(guī)定進行授權,使用者支付報酬,授權者將報酬轉付著作權人。在這個鏈條中,使用者面臨的困難是請求授權的范圍無法確定,AI使用作品作為訓練數(shù)據(jù)的量級是非常規(guī)的,為了保證訓練數(shù)據(jù)的全面性和多樣性,AI服務提供者只能在數(shù)量上選擇大規(guī)模批量授權,在權利范圍上選擇完全授權,這勢必造成AI服務提供者須支付高昂的經(jīng)濟成本。同樣,對于集體管理組織而言,如此海量的授權規(guī)模使其無法確定授權范圍、使用方式以及付酬標準。[45]關于錄音制品計酬的標準已經(jīng)難以滿足新技術應用下錄音制品傳播的現(xiàn)狀,參見閆書芳:《廣電使用音樂作品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報酬分析》,載《電視研究》2020年第8期,第55-57頁。其二,集體管理組織方案的作用不斷降低。在AI、區(qū)塊鏈等技術的應用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被替代逐步成為事實。[46]業(yè)內已有多個代表性應用,如螞蟻區(qū)塊鏈版權保護解決方案、紙貴版權、網(wǎng)易區(qū)塊鏈—數(shù)字版權等。對于這一點,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與螞蟻集團共建“數(shù)字版權鏈(DCI體系3.0)”,以期實現(xiàn)“數(shù)字內容的版權資產錨定,讓版權權利流轉全鏈路可記錄、可驗證、可追溯、可審計,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版權權屬確認、授權結算、維權保護”等環(huán)節(jié)。[47]參見《中國版權保護中心攜手螞蟻集團共建數(shù)字版權鏈(DCI體系3.0)》,載新華網(wǎng)2022年8月1日,http://www.news.cn/info/ 20220801/c890e867bc174d1494c0443718e5f45b/c.html.這一實踐也從側面印證了變革著作權管理體系的迫切需求。
就尋求著作權人自行授權而言,在集體管理制度發(fā)展的過程中,尋求權利人的授權在理論上可行,現(xiàn)實中卻難以實現(xiàn),一個主要原因是著作權人授權的方式存在版權流通的信息差。在海量的作品中,找到心儀的授權對象,與著作權人建立聯(lián)系,并且通過協(xié)商達成許可協(xié)議,這是一個漫長復雜且?guī)в胁淮_定性的過程,其中的信息搜尋成本異常高昂。也正是因為未納入集體管理的作品在流通過程遭遇了授權阻礙,才有學者頻頻呼吁建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以滿足數(shù)字化利用對作品授權高效性的需求。[48]參見孫新強、姜榮:《著作權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的中國化構建——以比較法為視角》,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2期,第39-40頁;劉平:《我國建立著作權延伸集體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分析》,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1期,第110頁。
(四)AI 合成音樂參與者侵權抗辯的困境
1.AI 合成音樂制作者的版權注意義務擴大化
前已述及,AI合成音樂生成環(huán)節(jié)的多個行為無法主張著作權的例外與限制條款得到豁免。從AI服務提供者到AI使用者,在合成音樂的行為鏈條中,各方均難以主張其不負有防止侵犯著作權的注意義務。在平臺端,立法明確了提供AI服務不應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故AI服務提供者負有更高的著作權注意義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提供AI服務和開展模型訓練作出不得侵害他人知識產權的規(guī)定。[49]參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4條、第7條。在用戶端,如果上傳受著作權保護的歌曲,對其進行智能編輯,制作翻唱歌曲,但是并未將歌曲發(fā)布至網(wǎng)絡,僅僅是用于個人欣賞,則不會存在侵權風險。但是,這是理論上個人用戶的使用情況,然而更貼近實際的情況是AI音樂制作者恰好可能是以普通用戶的外觀活動在網(wǎng)絡空間的侵權人,利用合成軟件制作大量AI翻唱音樂,投放到各類音樂平臺或者短視頻平臺,以獲取流量收益。對于這類個人使用者,在主觀上,應當認為其對行為的預期、性質以及后果均有全面的認識。在這種情形下,個人使用的數(shù)量、方式和目的都超出了一般公眾正常使用的范圍,難以主張其不負有著作權注意義務,主觀上應當認定為存在過錯。
2.AI 合成音樂傳播者適用“避風港”規(guī)則的阻礙
AI 合成音樂最終將通過網(wǎng)絡傳播并且存在侵權風險,因此引出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平臺)在傳播AI合成音樂時被控侵害信息網(wǎng)絡傳播侵權的責任豁免問題,即傳播AI合成音樂的平臺能否通過“避風港”規(guī)則豁免責任。我國的“避風港”規(guī)則是借鑒國外制度的產物。《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就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滿足相應條件時可以不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規(guī)定,被稱為“避風港”規(guī)則或者“通知—刪除”規(guī)則。該規(guī)則中的“通知”是指權利人發(fā)出合格侵權通知;“刪除”是指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收到前述通知后及時采取包括“刪除”在內的必要措施,避免損害進一步擴大,在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沒有過錯的情形下,可以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實踐中,“通知—刪除”規(guī)則的適用引發(fā)較多爭議。
首先,“有效通知”的認定,作為對權利人的要求,事實上的判定主體是平臺,具體何為有效,缺乏可操作的標準。雖然《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14條對通知的有效要件作了規(guī)定,司法實踐認為只要提供的信息足以使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準確定位涉嫌侵權內容,即可以構成有效通知。[50]參見2018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9.21條。
其次,“必要措施”的內涵不明確。這是對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收到通知后應當采取措施的要求,即“屏蔽”“斷開鏈接”“刪除”等必要措施。AI合成音樂傳播者的“必要措施”義務并不是一個清晰的范圍。按照AI技術的應用,傳播AI合成音樂的平臺會被要求重點監(jiān)管,當其收到權利人的通知后,應該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否則可能承擔侵權責任。平臺主張無法采取事前過濾等必要措施的觀點將難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AI合成音樂帶有顯著的標識。《網(wǎng)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內容標識方法》(以下簡稱《AIGC標識方法》)對AI生成內容的標注規(guī)范作出了規(guī)定。[51]參見《網(wǎng)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內容標識方法》(信安秘字〔2023〕124號)第3.3條、第3.4條。按照該規(guī)定,AI合成音樂應帶有明確的標識信息,以提示其由AI生成,制作音頻不僅應當在生成的內容中添加隱式水印,而且在文件元數(shù)據(jù)中也應當添加擴展字段作為標識信息,10秒以上的音頻必須保持有完整標識信息。按照該標識方法,至少在傳播鏈條中,AI生成的歌曲從內容上將顯著區(qū)別于其他傳播內容,AI合成音樂將具有較強的識別性。第二,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可能被要求采取事前必要措施。按照上述錄音文件的標識方式,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有能力對帶有標識的內容進行事前過濾,這在客觀上已經(jīng)是可行的。傳播者無法再主張其對AI合成音樂傳播事實不知情,不得消極采取行動,否則不能豁免其侵權責任。
四、AI合成音樂的著作權風險化解
(一)AI 合成音樂中“表演”行為的規(guī)范回應
1.AI 表演行為的著作權法定性
AI表演中的“表演”和“表演者”究竟應該如何定性?我國著作權制度僅有關于表演者和表演權的規(guī)定,并沒有專門對“表演”進行界定。立法參與者認為,“表演是指演奏樂曲等直接或借助技術設備以聲音、表情、動作公開再現(xiàn)作品的行為”[52]同注釋[35],第204頁。。對此需要進一步理解。一是“借助技術設備”的內涵和外延如何確定。從內涵上,借助技術設備是輔助性的借助還是允許是替代性的借助:輔助性的借助中技術設備不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其中行為人的主體作用明顯強于技術設備;替代性的借助則完全依托技術設備,其中行為人的主體作用弱于技術設備,主體對技術設備只起到提示作用。從傳統(tǒng)的視角來看,前者似乎是當前實務界更容易接受的一種理解,因為這正是AI創(chuàng)作對自然人中心主義提出的嚴峻挑戰(zhàn)——人的主體性如何得到保障的問題,因而這種保守的理解或許在過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法律的理解不應超出一般人對社會生活的客觀經(jīng)驗,但是從當前以及面向未來的視角,在對表演行為的規(guī)范評價中,不得不面對自然人主體性的弱化以及技術設備的替代性趨勢。從外延上,AI應當屬于技術設備的一種,但是這種技術設備又不完全等同于“音響”“麥克風”“樂器”等不能自主完成表演的工具意義上的技術設備,因為其自身具有脫離主體完成表演的功能。二是據(jù)此可以認為,表演是對文學藝術作品公開再現(xiàn)的一種方式,AI表演只要能夠客觀上實現(xiàn)這一效果,將其理解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表演也應當成立。因此,對于AI合成音樂中的“AI表演”,可以在法律評價上將其定性為利用AI程序通過演唱或者演奏方式再現(xiàn)音樂作品的行為,進而將其納入著作權法的調整范圍之內。需要強調的是,對AI表演中的表演還需要作一個廣義理解,文義解釋上雖然將其表述為表演,但是AI表演實則包含了著作權法意義上“表演、錄制”行為(錄制問題下文詳述),廣義上的AI表演中的表演行為、錄制行為分別指向不同的權利對象或者客體,應當單獨分析。
2.AI 表演規(guī)制路徑的反思
首先,當AI表演被定性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表演后,隨即應解決的問題是完成表演的主體是誰?換言之,誰會享有“表演者權”?有觀點認為,“在目標表演者和錄制者中,只有目標表演者才能成為AI表演上‘表演者權’的權利人”[53]同注釋⑨,第66、69頁。。無論是從立法論視角為目標表演者另設“表演者權”,還是從解釋論視角將目標表演者的表演者權的控制范圍延伸至AI表演,該觀點的意圖都是將“AI表演”納入表演者權的客體或者對象,權利人就是目標表演者(例如孫燕姿)。值得疑問的是,無論是從歷史上還是法理上,表演者權產生的基礎都是表演者自己實施了“表演”行為,但在AI表演中,目標歌手沒有任何參與,甚至都不知道他人制作了AI表演。也就是說,目標歌手在AI表演中沒有任何投入和付出,那么其針對AI表演享有表演者權的事實基礎、理論基礎和邏輯基礎在哪里?
其次,對于AI表演所產生的錄音制品如何確定權利歸屬,上述研究認為,“為了回應AI表演產業(yè)化的制度需求,應當在AI表演的新錄音上設立錄制者權”“新錄音與傳統(tǒng)錄音之間的差別在于錄制過程中是否使用了AI軟件,而非錄音成果的表現(xiàn)形式,將傳統(tǒng)的錄制者權擴大至AI表演的錄音之上,并無理論上的障礙”。本文認為,現(xiàn)有制度完全可以適用于此種情形,因此無需“新設錄制者權”,理由如下:法律對于錄音制品的制作并未限制技術手段,因此使用AI軟件制作的錄音制品如果符合條件也可以直接被認定為錄音制品,也就是前述觀點所認為的“將傳統(tǒng)的錄制者權擴大至AI表演的錄音之上,并無理論上的障礙”。這樣的話,將使用AI軟件制作的錄音制品認定為現(xiàn)行著作權法意義上的錄音制品就是順理成章地適用現(xiàn)有制度,而并非“在AI表演的新錄音上設立錄制者權”。
3.AI 表演規(guī)制路徑的修正
本文認為,AI表演不應納入目標表演者的表演者權的客體范圍。第一,不符合表演者主體的自然人主義。前文述及,從表演者的國際條約、國際立法和國內立法來看,對于表演者均堅持自然人主義,如果在表演者權上突破了對鄰接權的自然人主體要求,將導致著作權自然人中心主義與鄰接權主體的體系內部出現(xiàn)割裂。第二,目標表演者缺乏在AI表演上享有表演者權的事實基礎和法理依據(jù),應將AI表演與對AI表演的錄制一體評價,使錄制行為吸納表演行為。從歷史上看,表演者權產生于錄制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正是由于表演者的表演能夠被記錄于載體之上,才有了表演者權保護的問題,易言之,表演者權是通過表演的載體得以實現(xiàn)的。第三,被覆蓋的表演者對AI表演的歌曲也不能享有表演者權,因為在事實上被覆蓋的表演者同樣沒有在AI表演上投入任何勞動,他所發(fā)揮的作用僅僅是作為被替換音色的目標,供目標表演者能夠實現(xiàn)音色的準確匹配和替換。
以上是從AI表演中產生的新表演的角度做出的考量。從被使用的舊表演的角度而言,應當對原始表演者的權利作擴大解釋,以應對AI對原始表演進行超出社會公共利益范圍的無序使用。為了應對AI音樂合成技術對表演者權利的沖擊,避免原始表演者同其表演之間的聯(lián)系被割裂,《著作權法》第39條第1款第1項、第2項應該被解釋為具有以下法律意涵。
第一,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權利不僅包括正向署名,也應當包括反向署名。反向署名是指未經(jīng)許可,不得在可能引起公眾誤認的利用技術實施的表演及其錄制品上署名,比如“AI孫燕姿”“AI周杰倫”等署名方式不應隨意使用,因為“AI孫燕姿”“AI周杰倫”應當是其本人或者授權使用者等特定主體可以使用的署名方式。又如歌手陳珊妮正式發(fā)行了AI歌曲,由自己的聲音訓練的AI演唱,她署名“陳珊妮”或者“AI陳珊妮”是合法的,也在作品與目標歌手之間建立起可信任的人身聯(lián)系。因此,對于合法使用與非法使用應當進行區(qū)分。這是對音樂市場秩序的基本保障和對公眾知情權的保障,因為聽眾有權知道哪些AI音樂是得到歌手授權的,哪些是沒有得到授權的。對目標歌手本人而言,這也是其精神權利的重要保障。
第二,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范圍,不僅包括對表演者原表演風格的保持,還應當包括通過計算機程序使表演者改變或失去原有風格的行為。對于表演者錄制的錄音制品,未經(jīng)許可,他人也不得篡改聲音形象。
通過對《著作權法》第39條第1款第1項、第2項的擴大解釋,在解釋論的范圍內降低AI對表演者權制度的影響,以現(xiàn)有制度作為表演者應對AI表演的法律保障,以增強法律的適應性。
(二)AI 合成音樂的合理使用豁免
1.合理使用擴張應當采用的路徑
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源于《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關于“三步檢驗法”的內容。[54]參見焦和平:《網(wǎng)絡游戲直播的著作權合理使用研究》,載《法律科學》2019年第5期,第80頁。2013年《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1條中規(guī)定的合理使用制度,被視為對“三步檢驗法”的延續(xù),但限定適用依據(jù)為“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guī)定”。這一封閉性規(guī)定在實踐中引發(fā)諸多適用爭議,并在理論上引起了較多討論。于是2020年《著作權法》修法將封閉式規(guī)定修改為“列舉+兜底”的半開放式規(guī)定,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情形”作為兜底條款,并且吸納了“三步檢驗法”的部分規(guī)定。于是圍繞兜底條款應當進行解釋性適用還是立法性適用又產生了爭論:有觀點認為應當堅持立法的明確性和可預期性,減少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間;[55]參見張偉君:《也談新修改〈著作權法〉“合理使用”條款的適用》,載微信公眾號“同濟知識產權與競爭法中心”2021年1月14日,https://mp.weixin.qq.com/s/cDg_ecTfEhaR7vQVKJVVeQ.也有觀點認為按照促進技術創(chuàng)新和商業(yè)發(fā)展的司法政策,法院仍然可以根據(jù)個案突破對權利限制的限制性規(guī)定。[56]參見王遷:《著作權法權利限制模式闡釋》,載《中國版權》2020年第6期,第 21頁。本文贊同前一種觀點,按照該兜底條款的立法用語,尤其當AI等新技術對合理使用不斷形成挑戰(zhàn)的當下,突破現(xiàn)有立法的弊端在于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預期造成很大的不確定性,個案的結果可能影響一個行業(yè)的走向,對AI產業(yè)的發(fā)展將難以起到促進作用。在立法論視角下,除了筆者曾提出對《著作權法》第24條的修法路徑,[57]同注釋?,第139-140頁。還有一條路徑可供選擇,即通過AI專門立法,對合理使用問題進行規(guī)定。
2.通過AI 專門立法對作品使用問題作出規(guī)定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19年AI技術趨勢報告》指出,世界上僅有少數(shù)國家對AI生成內容的法律屬性進行了立法規(guī)定,比如英國。大多數(shù)國家還沒有對AI進行立法規(guī)制,國際組織也沒有出臺關于AI法律問題的公約或條約,這使得AI的相關法律制度基本屬于空白狀態(tài)。[58]參見《WIPO〈2019年人工智能技術趨勢報告〉述評》,載國家知識產權局網(wǎng)2019年3月29日,https://www.cnipa.gov.cn/art/2019/3/29/art_1415_156947.html.歷時近5年,多數(shù)國家在醞釀或加速推動AI立法。對于版權問題,歐盟議會推出首部《人工智能法案》(The AI Act),規(guī)定用于生成藝術、音樂和其他內容的生成基礎AI模型(如ChatGPT)將受到嚴格的披露義務的約束。此類模型和生成內容的提供者必須披露內容是由AI而不是人類生成的,訓練和設計其模型以防止生成非法內容,并發(fā)布有關使用受版權法保護的訓練數(shù)據(jù)的信息。[59]參見歐洲議會新聞網(wǎng),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230601STO93804/eu-ai-act-firstregula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2023年9月5日訪問。
2023年8月,美國版權局發(fā)布了一份關于版權和AI的調查通知,該通知的內容是圍繞使用生成式AI平臺而產生的大量版權問題開展調查,這些問題包括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訓練AI模型的侵權責任以及人類作者資格要求,其中也涉及合理使用問題。美國版權局承認在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內容訓練AI時,關于潛在侵權責任問題存在分歧。除了就訓練數(shù)據(jù)集來源的侵權責任提出意見外,美國版權局還希望獲得關于可行的報酬制度信息,以補償其作品被用于此類訓練數(shù)據(jù)集的藝術家。美國版權局還就AI系統(tǒng)生成模仿特定藝術家的聲音、肖像或風格的作品所涉及的公開權和不公平競爭法以及國際條約征求公眾意見。[60]參見美國版權局網(wǎng),https://www.copyright.gov/newsnet/2023/1017.html?utm_campaign=subscriptioncenter&utm_content=&utm_medium=email&utm_name=&utm_source=govdelivery&utm_term=,2023年9月5日訪問。可見各國在推進立法的過程中均在正面回應AI與版權的沖突問題。
我國在AI立法領域已邁出了步伐,針對生成式AI行業(y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落地實施,其中第4條、第7條雖然涉及生成內容和模型訓練的知識產權問題,但也只是作出了較為原則性的規(guī)定,整體上屬于保守型立法,尤其對于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的訓練使用,以及生成的內容可能涉及侵權、應當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做出衡量等爭論較大的問題,只是作出反對侵權的模糊表態(tài),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未來在AI專門立法完善過程中,建議增設著作權問題專門條款,明確生成式AI服務使用著作權材料的內容范圍和行為方式。在內容上,建議包括:作品、表演和錄音錄像制品等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在行為上,建議包括:滿足模型訓練的復制、提供服務不可避免的表演和傳播。
(三)AI 合成音樂的法定許可保障
1.AI 制作錄音制品納入法定許可范圍
AI制作錄音制品應當納入法定許可范圍的理由是:第一,錄音制品是音樂作品及表演的載體,是音樂著作權人和表演者控制權利的最后手段。著作權人及鄰接權人因AI創(chuàng)作的合理使用所讓渡的權利,在法定許可環(huán)節(jié)應當予以同等程度的平衡,以使權利的讓渡與合理保護之間的取舍符合公平原則。第二,控制了錄音制品的制作行為實則控制了音樂作品和表演的傳播載體。AI合成音樂過程中,最終呈現(xiàn)在網(wǎng)絡空間的主要是以錄音制品形式存在的歌曲,而在音樂作品和表演難以控制的情況下,從輸出端控制傳播載體,才能使音樂作品、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的權利不至于失去最后的依托。第三,通過法定許可制度的調整,賦予音樂作品權利人、表演者、錄音制作者維權的能力,以構建起清晰的權責關系,為權利人尋找侵權人的困境設置突破口。第四,制度框架下放開智能服務對音樂作品及錄制品的利用,有利于促進音樂作品的傳播,在智能技術頻繁更新?lián)Q代的背景下,音樂作品以錄音制品為載體的傳播潮流勢不可擋,只可疏解,不可封堵,否則將導致權利溺水于封堵的圍墻之下。
2.制定AI 使用錄音制品的付酬標準
付酬標準是許可制度之“車”落地執(zhí)行的“兩輪”,縱有完善的法律規(guī)定,如果實施標準缺位,終究無法真正惠及相關權利主體。中國音樂作品著作權人的廣播獲酬權從呼吁廣播付費到進入立法再到付諸實踐,耗時近20年的歷程就是一個例證。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未對音樂權利人的廣播權提供保護,其中規(guī)定廣播電臺、電視臺以“播放已經(jīng)出版的錄音制品”方式使用音樂作品,既無須獲得音樂創(chuàng)作者許可,也無須付酬。2001年《著作權法》第一次全面修改后,其第43條規(guī)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經(jīng)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jīng)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guī)定。”2005年底,原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正式啟動廣播權付酬標準的起草工作。2009年11月10日國務院頒布的《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第4條規(guī)定,中國音樂著作權協(xié)會(以下簡稱音著協(xié))與廣播電臺、電視臺才有了協(xié)商支付報酬的具體標準。截至2022年底,音著協(xié)共與130多家電臺、電視臺簽署了音樂作品付酬協(xié)議。[61]參見朱嚴政:《完善音樂著作權仍任重道遠》,載《音樂周報》2023年7月5日,第A14版。
音樂作品廣播獲酬權發(fā)展的艱辛歷程的啟示是,在將AI制作錄音制品納入法定許可范圍的同時,應同步制定AI使用錄音制品的專門付酬標準。我國及國外均有就專門行業(yè)制定錄音制品許可標準的實踐,AI作為一種完全改變了錄音制品使用方式的行業(yè),具備單獨制定許可付酬標準的條件。國內方面,《錄音法定許可付酬標準暫行規(guī)定》對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付酬問題作出一般性規(guī)定。在具體行業(yè)方面,有《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專門針對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廣播行為使用錄音制品的付酬標準。此外,直播行業(yè)也開啟了制定專門許可費率的嘗試。為促進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產業(yè)健康發(fā)展,2021年12月21日,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xié)會和中國音像與數(shù)字出版協(xié)會共同啟動了直播中使用錄音制品獲酬權的費率協(xié)商工作,并已形成初步標準。[62]參見《專家熱議網(wǎng)絡直播中音樂版權保護,音集協(xié)公開協(xié)商中的版權費標準》,載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xié)會網(wǎng)2022年7月11日,https://www.cavca.org/newsDetail/1867.錄音制品使用費的收取標準應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音樂作品著作權人代表、表演者代表、錄音制作者代表以及生成式AI服務提供者代表協(xié)商確定,并由國家版權職能部門牽頭建立一個協(xié)商溝通的穩(wěn)定機制。這是在現(xiàn)有的法律規(guī)定下的一個務實且有效的解決途徑。英國在AI版權治理的路線中,仍然考慮將行業(yè)力量放在優(yōu)先位置,以促成雙方的妥協(xié)和讓步,避免立法平衡的失敗對行業(yè)造成負面影響。[63]參見英國議會網(wǎng),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5803/cmselect/cmsctech/1769/summary.html, 2023年8月15日訪問。
(四)完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
根據(jù)《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9條的規(guī)定,中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設立采用的是行政許可模式,即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決定是否批準設立申請。同時,根據(jù)該條例第7條第2項關于新設管理組織的規(guī)定,新的集體管理組織設立“不與已經(jīng)依法登記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業(yè)務范圍交叉、重合”,即同一業(yè)務范圍內,只允許存在一家集體管理組織,由此確立了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壟斷合法性。橫向對比世界各發(fā)達音樂市場的集體管理制度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發(fā)展水平與世界音樂版權大國還有較大差距。從數(shù)量看,美國音樂著作權管理市場是鼓勵競爭的。美國傳統(tǒng)音樂市場上有三家音樂集體管理組織,包括美國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協(xié)會(以下簡稱ASCAP)、美國廣播音樂協(xié)會(以下簡稱BMI)和歐洲戲劇作家和作曲家協(xié)會(SESAC)[64]最初代表的是歐洲音樂人在美國的詞曲權益,后逐漸本土化為美國詞曲表演權的集體管理組織。,2013年又成立了一家名為“全球音樂版權”(GMR)的集體管理組織。從許可費用規(guī)模看,美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市場活躍度較高。以2022年為例,音著協(xié)2022年音樂作品授權費用收入4.17億元,相較國際同類組織存在巨大差距。BMI在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財年中,創(chuàng)造了破紀錄的收入15.73億美元,詞曲作者、作曲家和出版商獲得的收入高達14.71億美元,連續(xù)第7年成為世界上所有音樂版權組織中公開演出收入和版稅分配最高的組織。[65]《BMI年報(2021-2022)》,參見BMI音樂廣播公司網(wǎng),https://www.bmi.com/pdfs/publications/2022/BMI_Annual_Review_2022.pdf,2023年8月15日訪問。另一管理組織ASCAP的許可費用也達15.22億美元。[66]《ASCAP年報(2022)》,參見美國作曲家、作詞家和出版商協(xié)會(ASCAP)網(wǎng),https://www.ascap.com/annualreport,2023年8月15日訪問。單BMI的收益總和已是我國的24倍多,可見,競爭性集體管理組織與壟斷性集體管理組織相比,往往更具有創(chuàng)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動力。
因此,有必要在保持非營利性集體管理組織設立要求不變的基礎上,為營利性集體管理組織的設立提供法律依據(jù)和條件。以下方案可資考慮:第一,修改《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7條關于“(二)不與已經(jīng)依法登記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業(yè)務范圍交叉、重合”的規(guī)定。該條事實上確立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唯一性,從法律上否定了著作權集體管理主體多元化的可能性。第二,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AI)聯(lián)盟,吸納地方著作權登記平臺、民營音樂著作權交易平臺加入。第三,下放集體管理權利,允許平臺行使法定許可授權,以及追蹤和收轉使用報酬。第四,制定營利性集體管理成員活動規(guī)范,加強對平臺的集體管理活動的監(jiān)督。第五,推動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的新技術應用。采用區(qū)塊鏈技術獲得音樂作品權屬證據(jù)已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承認,[67]參見王婧:《區(qū)塊鏈技術賦能音樂作品版權保護——法院采信存證證書作為有效權屬證據(jù)》,載《法治日報》2021年10月12日,第10版。中國數(shù)字版權鏈——中國數(shù)字版權唯一標識(DCI)標準聯(lián)盟鏈體系應當在音樂行業(yè)中加快普及和應用,為音樂錄音制品打上可供確權、交易和追蹤的數(shù)字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