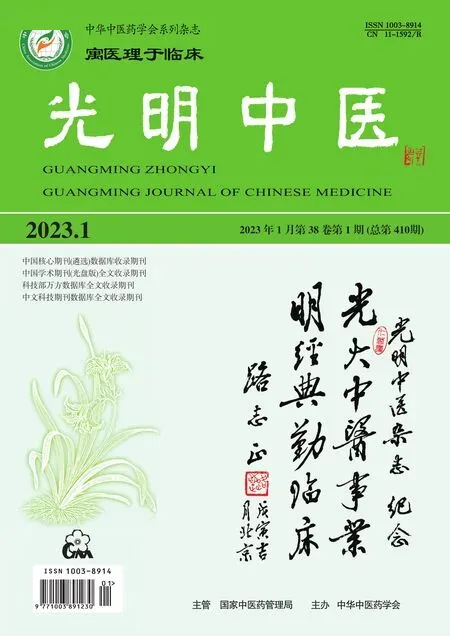賀玥名老中醫辨治痛經經驗*
周一民 賀 玥
賀玥,女,1950年生,副主任中醫師,鎮江市名中醫,為孟河醫派馬派之支流——丹陽賀氏醫派開創者賀季衡的嫡系傳人。2015年入選成立全國基層名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賀玥承襲家學,長于運用賀派辨證及用藥治療婦科疾病及內科雜病,臨床經驗豐富,療效肯定,成為當地具有顯著特色的中醫流派代表人物之一。筆者有幸跟師于門下學習,受益頗多,現將賀老師治療痛經的經驗總結介紹如下。
痛經是婦科常見疾病,屬于中醫“經行腹痛”范疇,臨床表現多為經期或行經前后出現周期性小腹疼痛或痛引腰骶,甚則劇痛難忍,并伴有惡心嘔吐,頭昏厥逆等。西醫則將痛經分為原發性痛經和繼發性痛經。原發性痛經又稱功能性痛經,多見于青少年女性,生殖器官無器質性病變。繼發性痛經則常見于育齡期婦女,多由盆腔器質性疾病如子宮內膜異位癥、子宮腺肌癥、盆腔炎或宮頸狹窄等引起[1]。
1 病因病機
《諸病源候論》為痛經的病因病機奠定了理論基礎,認為“婦人月水來腹痛者,由勞傷血氣,以致體虛,受風冷之氣,客于胞絡,損傷沖、任之脈”[2]。元代朱丹溪《丹溪心法·婦人》云:“經水將來作疼者,血實也,一云氣滯。四物加桃仁、黃連、香附”[3],認為此病的病因病機為氣滯血實。孟河醫派各醫家對痛經病因病機的論述散在見于各自的醫案中。《丁甘仁醫案調經類》1則醫案中治吳女,“經事衍期,臨行腹痛,血室有寒,肝脾氣滯。血為氣之依附,氣為血之先導,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欲調其經,先推其氣,經旨固如此也”[4],治療上予嚴氏抑氣散,加入溫通之品,病機及治療著眼于氣血,氣行則血行,血暢則痛止。賀季衡在其醫案中對痛經的病因病機論述有“氣瘀凝滯,榮衛失和,沖任不調”“熱結血分,肝胃失和”“血虛生熱,榮衛不和,加以肝失條達,氣火易于升騰”“沖帶二脈已傷,榮衛失和,肝氣橫梗”“血瘀氣滯、肝胃失和”[5]等,表明氣滯血瘀、瘀熱、血海空虛、沖任不調等為痛經常見病因病機。在賀氏醫派的傳承中,基本沿襲了對病因病機的認識。
賀老師認為痛經發生的病因為外感寒濕,飲食失調,情志不暢及素體稟賦不足,血海空虛,肝腎、沖任虧虛。基本病機為肝氣郁結,血行不暢,經脈不通。血瘀者,因體質而異分為寒瘀或濕熱瘀結。氣帥血行,氣行滯緩則血流必定艱澀,濕熱膠著難化,瘀血阻滯胞宮,不通則痛。肝為藏血之臟,肝血不足,血海空虛,子宮失于濡養,不榮則痛。女子月經依時而下取決于腎氣的盛衰。腎的功能異常,也會影響月經。女子痛經病的形成也與沖任有關。沖為血海,任脈為陰脈之海。《萬氏婦人科》中認為婦人經候不調有三:一曰脾虛,二曰沖、任損傷,三曰脂痰凝塞。沖任內傷,沖任失守,經事失其常而致月經諸病。綜上,可見此病涉及的臟腑經絡主要有肝、脾、腎、胞宮、沖任等。
2 辨證論治特色
2.1 常見證型賀老師認為此病臨床常見證型有氣滯血瘀、寒凝血瘀、濕熱瘀結、氣血虧虛及肝腎不足等。氣滯血瘀型常見有肝氣不舒表現,如受情志影響而發病,經前乳房或小腹脹痛,經行不暢,胸悶不舒,脈弦等。寒凝血瘀型可有小腹冷痛,受涼加劇,形寒肢冷,脈沉緊等表現。濕熱瘀結可見面紅、腹痛灼熱拒按,帶下色黃臭穢,小溲色黃,苔黃膩,脈滑數等。氣血虧虛型可見月經量少、色淡、顏面不榮,或經行將凈甚則經后腹痛。肝腎不足型可見經期或經后腹痛綿綿,腰膝酸軟,頭暈耳鳴,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等。
2.2 常見兼證部分痛經患者經期伴有腹瀉,賀老師認為多為肝旺克脾土所致,在辨證用藥基礎上,會酌情加用炒白術、肉豆蔻、砂仁等以健脾和胃止瀉。患者經前或經期亦會出現痤瘡加重,多為濕熱蘊結皮膚所致,處方中酌情予大青葉、忍冬藤、赤芍、五加皮、薏苡仁等清熱利濕涼血之品。
2.3 治療原則治療此病需分虛實論治。實證以疏肝理氣、活血化瘀為基本大法。寒凝經脈者,治以溫化;濕熱者,輔以清熱涼血化濕;虛證表現為氣血虧虛者,益氣養血。肝腎不足者,以補益肝腎、調沖任為主。臨床上,此病常虛實夾雜為患,臨證多以瀉實補虛調和之法統籌兼顧。
3 遣方用藥特色
3.1 用藥平和輕靈治病標本兼顧用藥法度上,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之法講究緩補氣血陰陽,輔以祛邪,待正氣足而病退身安。霸道之法立足祛邪為先,應用猛藥重折病勢,邪去之時不免傷正。兩者各有優劣,也各自有應用的時機。隨著時代發展,中醫臨床遇到的疾病已然發生改變。痛經在婦科疾病中則屬于慢病范疇。賀老師用藥平和輕靈,藥味也相對固定,多立足氣血陰陽,扶正以祛邪,達到標本兼顧的目的。
3.2 理氣活血治其標培補肝腎固其本氣能行血,亦能攝血,故氣為血帥,氣行則血行。氣的生成依賴血的濡養,故血為氣之母。賀季衡醫案中記載治療費氏經行腹痛時,認為此為“榮衛失和,肝氣橫梗”[5]而來,治以理氣和營,養血調經。王雅娟等[6]研究孟河醫派先賢馬培之先生對月經病的治療重在調和肝脾,一方面補益肝脾;另一方面,通過疏肝、寬中、宣肺、活血等令氣機舒展。氣血充盈,氣血暢達,月事按時而下。
賀老師治療痛經,傳承家學,以理氣活血、調氣和營貫徹始終,輔以平補氣血、培補肝腎。平補氣血多選當歸補血湯。孟河醫家費伯雄《醫方論》理血之劑中述“至精求之,以為凡治血癥,當宗長沙法,兼用補氣之藥,無陽則陰無以生,此論最確”。黃芪、當歸平補氣血,又能活血,考慮既能防止祛邪傷正,又能不助長邪氣,以防戀邪。培補肝腎常用藥有制黃精、益智仁、山萸肉、鹿角霜、生地黃、熟地黃、女貞子、墨旱蓮等。疏肝理氣藥常選醋柴胡、木香、金鈴子、青皮、月季花等。平抑肝陽多選用白蒺藜、干地龍、杭菊花等。活血多選血中氣藥,即入血分能行血中之氣的藥物,如川芎、郁金、香附等。王妍等[7]總結魏紹斌教授治療月經病的對藥就有當歸配川芎,取寓疏于補之義。還有既能活血又能利濕的益母草、澤蘭等均是賀老師常用藥物。
3.3 溫化辛通苦泄降氣以暢達氣機辛味藥“能散能行”,行者,行氣血也。散者,散寒濕邪氣也。辛開苦降法是治療脾胃升降失常所致寒熱錯雜病證的治療法則,廣泛用于多種脾胃系統疾病的治療[8]。賀老師善于將此法應用于痛經病治療。這也是賀氏醫派治療內科、外感等疾病常用的治法之一,即“苦辛通降”。賀老師常以炮姜、吳茱萸、小茴香等辛溫藥溫化寒瘀,益母草、澤蘭苦泄降氣,配合起來辛開苦降恢復氣機升降,旨在達到暢達氣機,氣行痛緩的目的。
3.4 靈活運用對藥效專力宏。賀老師臨床開方喜用小方對藥,應用此類藥物時,多能做到心中有底,效專力宏。如吳茱萸配白芍,溫經湯中有此二藥相配。賀季衡治療月經病、脘腹痛、便結等,方藥中常用大白芍(吳茱萸拌炒)柔肝緩急止痛。吳茱萸味辛性熱,溫陽散寒。周巖在《本草思辨錄》中謂:“肝病者脾必病,吳茱萸能入肝驅邪,化陰凝為陽和,脾何能不溫,腹痛腹脹何能不治”。白芍味苦性微寒,柔肝養陰,緩急止痛。馬曉娟[9]采用腹腔注射己烯雌酚與縮宮素制備原發性痛經模型,通過試驗證明白芍、炙甘草藥對具有鎮痛作用,其通過抗氧化應激及鎮痛作用達到治療效果。吳茱萸和白芍兩藥相合,散寒不致傷陰血,平肝不使抑肝氣,相輔相成又相互制約。香附配郁金,血中氣藥,行血中之氣。益母草配澤蘭,活血利水,可相須為用。蒲黃、五靈脂,即失笑散,歷代醫家治瘀血內結多用之。
3.5 沖任虛損補之以血肉之品賀老師治療女子經病常用藥物有阿膠、龜甲、醋鱉甲、鹿角、鹿角霜等。如患者先天稟賦或后天流產等導致肝腎虧虛,沖任不足,賀老師在常規運用生地區、熟地黃、制黃精、山萸肉、續斷等草木之藥外,都會酌情加入阿膠、龜板、鹿角等血肉有情之品。溫病大家葉天士曾言:“五液全涸,草木藥餌總屬無情,不能治精血之憊,故無效,當以血肉充養,取其通補奇經”。在賀老師早期醫案中,這些藥物比較常見,該用則用。但目前因這些藥品價貴,賀老師考慮患者經濟負擔重,逐漸少用,或以鹿角霜、阿膠珠等代之,或干脆棄之不用。醫者仁心,心系患者,值得后輩學習。
4 醫案舉例
4.1 氣血瘀滯證王某某,女,32歲。2017年10月17日初診。痛經綿延有年,周期尚正,經前感乳房脹痛,行時腹痛,其色尚正,血塊不多,脈弦細,苔薄。辨為痛經——氣血瘀滯證。治當疏肝調沖,理氣活血。處方:當歸15 g,醋柴胡9 g,炙黃芪15 g,白芍9 g,吳茱萸4 g,炮姜6 g,郁金9 g,五靈脂(包)15 g,炒蒲黃(包)10 g,肉桂6 g,丹參15 g,紅花10 g,木香9 g,澤蘭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2017年11月3日二診:經事已行(10月30日—11月7日),此次經行腹痛已輕,乳房脹痛亦減,稍有小血塊,色尚鮮,量尚可,脈細,苔薄,治當原法出入。處方:當歸15 g,醋柴胡9 g,炙黃芪15 g,白芍9 g,吳茱萸4 g,炮姜6 g,五靈脂(包)15 g,炒蒲黃(包)10 g,木香9 g,益母草15 g,紅花9 g,郁金9 g,澤蘭15 g,炙甘草6 g。繼服7劑。
按:患者以經行腹痛就診,其痛經綿延數年,伴隨癥狀僅有經前乳房脹痛,無明顯寒熱傾向,脈弦細,苔薄,辨為氣血瘀滯型。治以理氣活血。當歸、炙黃芪補益氣血;吳茱萸祛寒行氣止痛,與養血柔肝、緩急止痛的白芍配伍;失笑散通利血脈、消瘀止痛;木香、郁金、丹參、紅花行氣活血,少佐炮姜溫經散寒。二診諸癥減輕,原方調整加益母草、澤蘭苦辛通降,活血利水,平調寒熱。方中以行氣活血祛瘀為主,兼顧平補氣血,使邪去不傷正;苦降辛通,恢復氣機升降,收效滿意。
4.2 寒凝血滯證唐某某,女,33歲。2016年10月19日初診。患者近2年來每逢經前或行經時小腹冷痛,得溫則舒,經量少,色紫黯有塊,小便清長,經行時伴腹瀉,帶下不多,無嘔吐,刻下經事方凈,胃納如常,二便通調,夜寐尚可,苔白,脈沉細。辨為痛經——寒凝血滯證。治當溫化。處方如下:當歸15 g,炙黃芪15 g,肉桂6 g,炮姜6 g,白芍9 g,吳茱萸4 g,益母草15 g,香附9 g,郁金9 g,丹參10 g,五靈脂(包)15 g,生蒲黃(包)10 g,木香9 g,澤蘭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2016年10月26日二診:刻下無特殊不適,帶下色稍黃,感腰膂畏寒,脈細,苔薄。治當原法出入。處方:當歸15 g,炙黃芪15 g,白芍9 g,吳茱萸4 g,肉桂6 g,炮姜6 g,香附9 g,丹參15 g,紅花9 g,杜仲15 g,山萸肉9 g,鹿角片15 g,五靈脂(包)15 g,生蒲黃(包)10 g,澤蘭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11月2日三診:腰膂畏寒已輕,帶下色黃,余如常。脈弦細,苔薄黃。治當原法出入。處方:熟地黃15 g,當歸15 g,炙黃芪15 g,肉桂6 g,炮姜6 g,赤芍、白芍各12 g,吳茱萸4 g,香附9 g,郁金9 g,丹參15 g,五靈脂(包)15 g,生蒲黃(包)10 g,椿根皮15 g,木香9 g,澤蘭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11月9日四診:經事先期1周而行(11月7日—11月12日),腹痛已輕,其色漸鮮,血塊亦少。脈細,苔薄。原法出入。處方:當歸15 g,炙黃芪15 g,赤芍、白芍各12 g,吳茱萸4 g,郁金9 g,丹參15 g,紅花9 g,桃仁15 g,五靈脂(包)15 g,生蒲黃(包)10 g,香附9 g,炮姜6 g,木香9 g,澤蘭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11月18日五診:經行已凈,此次經行腹痛明顯好轉,其量較前多,色尚正,血塊不多。刻下惟腰痛頗甚,帶下尚可。脈細,苔薄。以原法出入。處方:熟地黃15 g,當歸15 g,炙黃芪15 g,山萸肉9 g,紅花9 g,杜仲15 g,雞血藤15 g,桂枝9 g,續斷15 g,炮姜6 g,益智仁15 g,五靈脂(包)15 g,桑寄生15 g,絲瓜絡6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
按:本案患者痛經的特點為冷痛,得溫緩解,月經色紫黯有塊,經行腹瀉,小便清長,故應辨為寒凝血脈證。葉天士在《葉選醫衡》論:“蓋氣,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則血活,氣寒則血凝,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故本案治療原則側重溫經散寒,祛瘀止痛。單從方藥來看,貌似每診所書之方大同小異,所以完全可以在后面的處方過程中以原方加減代替,省去繁瑣的再次處方。賀老師醫案均為自己書寫,理法方藥精簡清晰。患者的每1次就診即是賀老師完成整個辨證論治的過程展現。在這則醫案中,可以略微窺探出賀氏醫派診治及用藥特色。在臨床上,賀老師針對疾病更注重病因病機及治療法則的把握。賀老師雖師承家學,但并不以祖傳秘方惑世,理法精當,足以讓后學者推衍而行之。心中有法,處方有序,自然能收效頗良。溫經散寒者,多用炮姜、吳茱萸、肉桂、小茴香等,這些藥多作用于下焦為主。理氣調經者,多選用木香、香附、郁金等。補氣血多選用炙黃芪、當歸。活血多用失笑散、丹參、紅花、益母草、澤蘭、桃仁等。補肝腎選用熟地黃、制黃精、山萸肉、鹿角片等。同時,根據患者有腰痛,加用杜仲、桑寄生、絲瓜絡、雞血藤等補腎通絡之品;帶下色黃,加用椿根皮等清熱利濕。賀氏醫派用藥講究輕靈醇正。“輕靈”即用藥的“量”,藥量相對較小,以防孟浪傷正。“醇正”即用藥的“質”,精良考究,當用則用,絕不畏首畏尾。
5 總結
賀老師認為“痰飲、濕熱、瘀血等病邪阻滯沖任,沖任閉阻,通利失司可致痛經”[9],另外氣血虧虛、肝腎不足等亦可導致此病。痛經辨證首先要注意辨清虛實。臨床上可見虛實夾雜,以虛少實多為多見。實者不外乎氣滯、寒凝、濕熱、血瘀所致。虛證則往往是氣血兩虛、肝腎不足。虛實夾雜之證在治療上則需要施以虛實并治。明確了痛經發病的機制,治療就可以針鋒相對,直達病所。治療過程中,行氣活血祛瘀止痛貫徹始終,恢復氣機升降,兼顧補益氣血及培補肝腎。生活調攝方面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合理膳食,清淡并注重營養均衡;平素注意保暖,切忌貪涼;情緒保持舒暢;適當進行體育鍛煉,增強體質。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注意得當,從而促進疾病向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