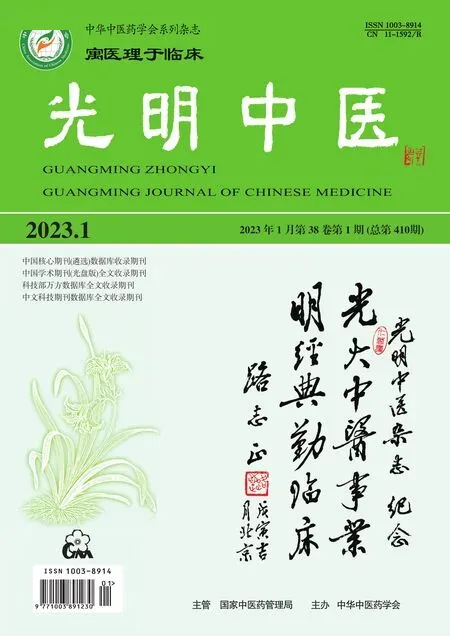從濕論治支氣管哮喘探析*
王旭輝 孫 英 胡海波 劉 利 陸學超△
支氣管哮喘是呼吸系統(tǒng)常見的慢性疾病,是由多種細胞和細胞組分參與的氣道慢性炎癥,臨床表現(xiàn)為反復發(fā)作的喘息、氣急、胸悶或咳嗽等癥狀。王辰院士于2019年6月在《柳葉刀》發(fā)表的研究顯示[1],中國支氣管哮喘患病率高、社會經(jīng)濟負擔重,20歲以上患者總人數(shù)高達4570萬,患病率為4.2%。現(xiàn)代醫(yī)學認為支氣管哮喘的發(fā)生機制主要是長期存在的氣道慢性炎癥,在遇到變應原刺激后,氣道發(fā)生痙攣,黏液分泌增多,氣道狹窄,呼吸不暢。臨床治療多應用糖皮質激素抑制炎癥反應,β2受體激動劑擴張支氣管,但部分患者對激素的認識存在偏差,依從性不好,不能做到規(guī)范用藥,以致支氣管哮喘急性發(fā)作的次數(shù)增加,對氣道和肺的損傷增加。
支氣管哮喘在中醫(yī)學稱“哮病”,病機是肺、脾、腎三臟功能失常,水液不能運化,聚濕成痰,宿痰伏肺,遇外感引觸,痰氣搏結,氣因痰阻,壅塞氣道,以致痰鳴如吼,氣息喘促。濕邪是病因學中的六淫之一,有重著、黏滯、趨下等致病特點,病程長,病證變化多樣,難以速去。中醫(yī)治療哮病的原則是發(fā)時治標,平時治本,意為發(fā)作時重在治肺,平時重在治理肺、脾、腎三臟。支氣管哮喘發(fā)作時主要是痰阻氣道,痰的產(chǎn)生根本源于水液代謝失常,濕為水液的根本,既可為有形實邪,也可為無形濕氣;既是引起一系列臨床癥狀的病理因素,也可以是病理變化的產(chǎn)物。無論在支氣管哮喘的緩解期還是急性發(fā)作期,“濕”作為重要的病理因素,長期存在。重視祛濕法的應用有利于提高支氣管哮喘患者的治療效果。
1 濕的產(chǎn)生
1.1 環(huán)境因素支氣管哮喘發(fā)病率的逐年增加與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有一定的關系。夏季順應四時養(yǎng)生應該做到“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而室內空調的應用引起汗孔的堵塞,減少了肌表的發(fā)汗,導致夏季的濕邪難以從肌表而發(fā),郁于體內,成為支氣管哮喘發(fā)作的潛在致病因素。冬季寒冷、污染等刺激呼吸道容易誘發(fā)支氣管哮喘的急性發(fā)作,即“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歐洲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家中潮濕與呼吸系統(tǒng)癥狀、支氣管哮喘的發(fā)作有關,在家和工作中,潮濕會增加呼吸道癥狀的發(fā)病風險,并且降低緩解率[2]。不僅在挪威、瑞典等海洋性氣候的國家,支氣管哮喘患者普遍存在濕邪為患的現(xiàn)象,在國內一項針對烏魯木齊市住宅內潮濕表征與兒童支氣管哮喘相關性研究中,所有的潮濕表征與兒童近12個月的喘息、鼻炎及濕疹癥狀均成正相關[3]。這表明即使在內陸地區(qū),濕邪也是引起支氣管哮喘的重要因素。
1.2 內傷所致過食肥甘油膩之品,極易引起濕邪內生。葉天士曾說:“內生之濕,必其人膏粱酒醴過度,或嗜飲茶湯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膩之物”。便捷的交通和工作壓力使得人們鍛煉的時間減少,導致氣機運行不暢,水濕不化。支氣管哮喘的病機與肺、脾、腎三臟關系密切,肺不能布散津液、脾不能轉輸津液、腎不能蒸化水液,導致津液不化,聚而成痰,伏藏于肺,成為宿根。《素問·經(jīng)脈別論》曰:“飲入于胃, 游溢精氣, 上輸于脾, 脾氣散精, 上歸于肺, 通調水道, 下輸膀胱, 水精四布, 五經(jīng)并行”。津液若能得到正常的輸布,或是通過汗液的蒸發(fā)、尿液的排泄,便不會留積于體內。哮病是津液不歸正化,聚而為痰,阻塞氣道而致。中醫(yī)的濕是病理性概念,指水液輸布排泄障礙而致濕濁停滯的病理變化,有內外濕之分。濕與痰、飲是水液停聚形成的病理產(chǎn)物,在中醫(yī)學上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但是卻有著程度的差異,水聚成濕,濕凝成痰、飲,濕當利,痰當化,飲當逐,從治法上可以看出濕邪進一步深入可轉化為痰飲。內傷是體內濕、痰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
2 濕的致病機制濕有重著、黏滯、隱匿、彌漫之性,清代張璐在《張氏醫(yī)通》中說:“風寒皆能中人,惟濕氣積久,留滯關節(jié),故能中……人只知風寒之威嚴,不知暑濕之炎暄,感于冥冥中也”,這與支氣管哮喘的夙根伏痰學說有相似之處,支氣管哮喘的氣道炎癥也是長期存在,支氣管哮喘患者不發(fā)作時可如常人,因此容易忽視本身一直存在的氣道炎癥,不重視治療,容易導致急性發(fā)作。濕邪可與他邪合而為患,與多種病理產(chǎn)物相互依存,形成新的病理因素。古人講“十人九濕”, 而又“濕生百病”, 以至于濕證成為臨床常見的中醫(yī)證候。周欣蕓[4]發(fā)現(xiàn)高濕環(huán)境有加重小鼠支氣管哮喘疾病發(fā)展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通過影響小鼠肺部氧氣利用、肺部形態(tài)及腸道菌群穩(wěn)定性和多樣性而加重了小鼠支氣管哮喘的疾病發(fā)展。張六通等[5]發(fā)現(xiàn)濕邪致病組大鼠不僅出現(xiàn)腸道菌群失調的情況, 而且出現(xiàn)T淋巴細胞總數(shù)不足、亞群異常以及白細胞介素2活性下降, 提示濕邪致病可引起T 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功能低下, 同時還發(fā)現(xiàn)濕邪致病大鼠巨噬細胞吞噬功能降低。這與支氣管哮喘患者T細胞亞群失衡有著相似之處。
3 濕的病理特點
3.1 重著蒙蔽《景岳全書·雜證謨·濕證》云:“濕之為病……為重,為筋骨疼痛,為腰痛不能轉側,為四肢痿弱酸痛”。濁是濕邪致病的客觀體征,即濕邪為患易出現(xiàn)分泌物和排泄物穢濁不清的特點。 如濕濁蒙上的面色晦垢、眵多,濕濁蒙蔽于頭面部可導致頭暈、頭重,支氣管哮喘發(fā)作時,氣體交換不暢,機體處于輕微的缺氧狀態(tài),導致頭部出現(xiàn)昏蒙不暢的感覺,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
3.2 流注趨下濕性類水,有流動之性,根據(jù)重力向下的特點,濕邪容易積聚于身體的下部。《素問·太陰陽明論》云:“傷于濕者,下先受之”, 故而濕邪為病多見泄利、帶下、淋濁、下肢水腫等。
3.3 易傷陽氣濕為陰邪,易傷陽氣。《素問·生氣通天論》載:“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陽氣者,精則養(yǎng)神”。陽氣可以通過氣化作用,內化為精微,充養(yǎng)神氣,使其精明,功能正常。一切生理功能的正常運行、一切物質的正常代謝都要以充足的陽氣為基礎。支氣管哮喘的發(fā)生是由于肺的功能失常所致,緩解期與脾腎的關系密切,脾主運化、主升清降濁,脾陽不足,運化功能低下易致腹脹、泄瀉、水腫等證。《證治準繩·雜病·喘》云:“真元耗損,喘生于腎氣之上奔”。腎陽是全身陽氣的根本,為一身之元陽,真陽衰微,致使氣不歸元,腎不納氣導致氣無以下行而引起喘息、氣促。陽氣不足,不能溫煦,體內濕邪不能得以蒸化、運化,積于體內,久而蘊濕成痰,成為支氣管哮喘發(fā)作的宿根。
4 從濕論治支氣管哮喘的現(xiàn)代醫(yī)學證據(jù)
青島市中醫(yī)醫(yī)院肺病科周兆山教授提出“病熱痰者當須滲利”的觀點,從絕痰源的角度,重視滲濕法的應用,創(chuàng)制清肺滲濕湯,在青島市多家醫(yī)院應用10余年,收到了良好的臨床療效。清肺滲濕湯是以清肺熱、利濕濁為法,在麻杏石甘湯的基礎上,加以浙貝母、射干、冬瓜仁清化熱痰;薏苡仁、茯苓健脾利濕,助痰濕之運化;車前草、魚腥草、石韋導濕熱之邪從小便而去。諸藥各司其職,使?jié)駸崛ァ⑻禎崆濉T谇宸螡B濕湯和麻杏石甘湯在治療支氣管哮喘大鼠的療效評價中,發(fā)現(xiàn)二者均能改善失衡的IFN-γ/IL-4比值,但清肺滲濕湯的作用更為顯著[6]。深入的研究表明,清肺滲濕湯減輕氣道炎癥的機制可能是促進炎癥局部細胞的凋亡[7]。
支氣管哮喘是以氣道慢性炎癥為病理特點,現(xiàn)代藥理研究表明,常用的祛濕藥中,廣藿香醇通過抑制炎性細胞因子如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1β(IL-1β)和白介素-6(IL-6)的產(chǎn)生,減輕炎癥反應[8]。厚樸酚可通過降低TNF-α、IL-1β含量,改善肺組織病理狀態(tài)[9]。茯苓有很好的抗炎作用,并能提高免疫力[10]。澤瀉提取物能抑制炎癥因子活化和炎癥介質增生,減少急性肺損傷和抑制肺部感染,升高肝組織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及活力,降低丙二醛(MDA)含量[11]。澤瀉醇B(19)、23-乙酰澤瀉醇B(20)在1~10 mmol·L-1能顯著抑制白三烯產(chǎn)生和β-己糖胺酶的釋放,還可顯著抑制遲發(fā)性過敏反應[12]。薏苡仁降低大鼠血清中TNF-α、IL-1、IL-6的含量[13]。冬瓜子具有抗炎,解熱鎮(zhèn)痛的作用[14]。魚腥草水提物可以調節(jié)TNF-α、IL-6等促炎因子的表達水平,從而有效改善機體的免疫功能[15]。車前草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其中,車前草多糖能增強過度運動大鼠血漿中CD+4/CD+8比值,改善免疫功能[16]。瞿麥在動物體內能有效抑制IgE的分泌,提示瞿麥是一種潛在的抗過敏藥物[17]。豬苓多糖對于大鼠淋巴細胞具有不同的免疫調節(jié)作用, 可使淋巴細胞分泌TNF-α減少、γ-干擾素(IFN-γ)的分泌增加, 腸道上皮內淋巴細胞 (IEL)和固有層淋巴細胞 (LPL)分泌TNF-α和IFN-γ的水平呈不同程度降低[18]。白術內酯III能抑制脂多糖(LPS)誘導的RAW264.7小鼠巨噬細胞的炎癥反應,其機制可能與抑制NF-κB和MAPK信號通路相關的NO、PGE2、TNF-α和IL-6的釋放有關[19]。以上研究提示,常用的祛濕藥物具有減輕炎癥反應的作用,可能是其發(fā)揮平喘作用的機制。
5 從濕論治支氣管哮喘
根據(jù)支氣管哮喘本虛標實的特性、濕的病理特點等的影響, 在應用祛濕藥物的同時, 應重視與清肺、溫肺、和解相結合, 做到辨證用藥。
5.1 清肺與祛濕相結合對于陽盛體質的患者而言,采用祛濕兼以清解肺熱之法。陽盛之人,體內多有熱邪,臨床表現(xiàn)有口干舌燥、喜冷飲、怕熱、易出汗、小便熱赤、便秘、大便熏臭、呼吸氣粗、易腹脹。此類患者存在濕熱并存的情況,在應用平喘祛濕之法的同時,結合個體的不同表現(xiàn),加用清熱的藥物,清除體內的熱邪,有利于清肅肺內邪氣,恢復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主要是祛濕藥物配合麻杏石甘湯。肺中有熱,蒸煉津液成痰,痰阻于肺,導致痰液黏稠,難以咳出,阻塞氣道,引起喘息、氣促的表現(xiàn)。段磊等[20]在舒利迭霧化吸入基礎上聯(lián)合支氣管哮喘2號方(麻黃、杏仁、石膏、金銀花、杏仁、連翹、桑白皮、射干、地龍、蟬蛻、紫蘇子、枇杷葉、前胡、浙貝母、薏苡仁),治療4周后,臨床總有效率提高,聯(lián)合用藥組較單純中藥組、單純西藥組FeNO、EOS、FEV1指標上改善更為顯著,且能減少激素用量。
5.2 溫肺與祛濕相結合對于陽虛體質的患者而言,采用祛濕兼以溫肺化飲之法。此法用藥是在小青龍湯的基礎上,加入祛濕之品。患者臨床表現(xiàn)主要有咳嗽、咳吐白色泡沫樣痰。陽氣是生理功能正常發(fā)揮的重要推動力,肺中陽氣不足,不能起到溫煦的作用,津液不能蒸化,停留于肺,故可見咳痰質清稀、量多。徐小小等[21]在舒利迭吸入基礎上,加服溫肺定喘湯(麻黃、桂枝、五味子、法半夏、萊菔子、白芥子、杏仁、陳皮、干姜、細辛、甘草),治療2周后,其臨床療效、肺功能指標(FVC、FEV1、PEF)及細胞因子(IL-4、IL-6、INF-γ)較對照組有明顯的改善。
5.3 補腎與祛濕相結合對于久病體虛的患者而言,腎虛是常見的證候。這類患者平素短氣息促,動則尤甚,吸氣不利,或喉中有輕度哮鳴,腰膝酸軟,腦轉耳鳴,勞累后易誘發(fā)哮病,或畏寒肢冷,面色蒼白。治療上應以補腎攝納為主,可以金匱腎氣丸合祛濕之法。補腎清肺法治療哮喘急性發(fā)作期(熱哮證)較傳統(tǒng)清宣肺氣治療可明顯提高療效。在姜洪玉等[22]研究中,治療組(六味地黃丸合清肺滲濕湯)與對照組(清肺滲濕湯)相比,治療組在癥狀、體征及相關實驗室檢查方面的改善效果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以六味地黃丸補腎以固其本,清肺滲濕以治其標,如此做到標本兼治。
6 小結
支氣管哮喘作為一種慢性疾病,往往需要長期的治療。在中醫(yī)的診療中,抓住濕是主要的致病因素,從濕論治,①通過藥物治療,使水液得以運化,截斷痰的生成;②通過健康宣教,引導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習慣,減少外濕的產(chǎn)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減少支氣管哮喘急性發(fā)作的次數(shù),延緩疾病的進展,為治療支氣管哮喘拓展了新的診療思路。
近些年發(fā)現(xiàn),NLRP3炎癥小體在哮喘氣道炎癥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23]。水通道蛋白1(Aquaporin1,AQP1)是介導肺部水跨膜轉運的一種蛋白質,主要參與調控細胞內水分的轉運,其表達異常可引起細胞水液代謝障礙。AQP1表達明顯下調,Th2相關細胞因子IL-4、IL-5表達上調,肺濕/干比升高,提示肺部水液代謝障礙與氣道炎癥反應有關[24]。 拉曼光譜技術已經(jīng)成為一種多功能的生物醫(yī)學分析工具。單細胞拉曼光譜通常包含上千個拉曼光譜帶, 可以提供豐富的細胞分子信息, 例如核酸、 蛋白質、 脂質等, 并可反映細胞的基因型、表型和生理狀態(tài)[25]。因此,從濕論治支氣管哮喘的現(xiàn)代生物學機制可利用拉曼技術,通過對細胞內核酸、蛋白質等的檢測,動態(tài)觀察藥物對細胞的影響,從而探究祛濕藥物對NLRP3炎癥小體和AQP1的調節(jié)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