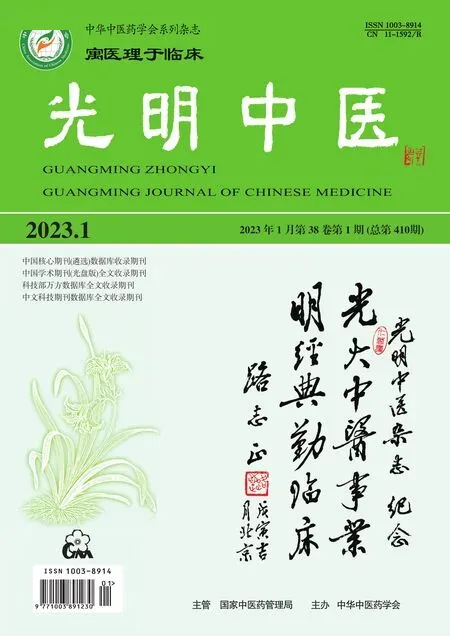黃帝內針在頸源性失眠中的應用
張文硯
失眠是最常見的睡眠問題,可以作為獨立的疾病存在,也可以與其他疾病共存,即共病性失眠癥。近年來,受長期低頭伏案工作或應用手機等電子產品的影響,頸椎病的發病率逐年上升。隨著對失眠的深入研究,頸源性失眠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中國成人失眠癥的患病率為10%~15%[1],而頸椎病患者中失眠癥的發生率可達48%,明顯高于普通人群[2]。此病以入睡困難、睡后易醒等睡眠障礙伴頸背部疼痛為主要臨床表現[3]。臨床醫師在治療失眠時很容易忽視頸源性因素,從而使療效大打折扣,病情遷延不愈。
頸源性失眠在中醫學中屬 “不寐”“項痹”范疇,頸項經筋不利,痹阻不通,氣血失和,陰陽失衡,則導致不寐。針灸是中醫學一大瑰寶,可有效松弛頸項痙攣肌群,調和氣血陰陽,在治療不寐和項痹方面均具有滿意的療效。目前針刺治療頸源性失眠,多采用傳統體針療法,以頭頸部局部取穴為主,如頸夾脊、天柱、風池、百會等,再配合三陰交、足三里、神門等穴位[4-8],常采用臥位,對診療設施和針刺技術水平要求較高。黃帝內針作為一種特殊針法,操作簡單,實用安全,治療頸源性失眠收效明顯,本文特此介紹如下。
1 西醫發病機制與治療現狀
現代醫學針對頸源性失眠的致病機制尚未完全明晰,有關其發病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1 疼痛研究顯示, 慢性頸背痛患者中,有47%存在失眠現象[9],在另一項研究中,有為[10]。孫振曉等[11]、粟勝勇等[12]也通過研究發現,頸椎病頸痛與失眠具有顯著相關性,頸痛VAS評分與失眠的PSQI總分呈高度正相關。患者睡眠不足或質量不佳,頸背肌筋膜不能得到有效放松,可進一步加重肩頸背部疼痛[13],使二者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1.2 腦供血不足睡眠與下丘腦的覺醒、睡眠中樞和腦干上行網狀結構的功能密切相關,后兩者皆由椎動脈系統供血以維持正常功能。當頸椎病引起椎動脈血管痙攣、管腔變窄,致其血流下降時,可導致上述結構功能下降而出現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14-16]。俞中平[17]就曾提出顱外高張性失眠,認為頸顱部肌筋膜張力增高時,可導致入顱血管的血流前阻力增加,血流量下降,腦干供血不足而出現失眠癥狀。朱建琳等[18]通過對隨機抽取的120例體檢人員研究發現,睡眠障礙組的左、右側頸內動脈和椎動脈阻力指數以及PSQI各項分值、總分值均顯著高于睡眠正常組。
1.3 植物神經功能失調交感神經與頸椎周圍組織關系密切。頸交感干由3個交感干神經節組成,其中以頸上神經節為最大。頸椎病靜態性壓迫或者動態性失穩,可導致交感神經受壓或刺激,使下丘腦興奮反射增加,從而出現睡眠障礙。此外,松果體分泌的褪黑素與睡眠也有緊密的聯系。而頸上交感神經節的節后纖維與松果體細胞形成突觸聯系,因此睡眠與頸交感神經相關,頸部周圍軟組織失衡將導致失眠[19]。
目前該病的西醫治療以口服鎮靜催眠類藥物為主,包括苯二氮卓類與非苯二氮卓類,雖可獲得短期療效,但由于常常存在白天嗜睡、藥物依賴、易成癮等不良反應,且無法緩解頸項疼痛等頸源性失眠的主要癥狀,難以糾正其致病原因,故遠期療效不佳,病情容易反復[20]。
2 黃帝內針的理論基礎及治療原則
2.1 執兩用中黃帝內針源于《黃帝內經》,其傳承綿密久遠,至楊真海老師,始公之于眾。該針法以調整“陰陽”為核心,所謂“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其“中和”為黃帝內針追求的最佳狀態,其意為中正平和,本是中庸思想的精髓。中醫學認為,人體之所以發病,乃是機體之氣血、陰陽出現了盛衰變化,即“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失其“和”而發病。黃帝內針便是調“中”之針法。
《中庸》第六章中記載:“執其兩端,用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黃帝內針以此為指導,對如何調中做出了規定。由于上下、左右皆為一對陰陽,把握陰陽的兩端,才能用中、有中,才會達到陰陽平和的狀態。故黃帝內針禁刺患處, 嚴格遵循“上病下治,下病上治”“左病右治,右病左治”的原則,正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曰:“故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
2.2 同氣相求《周易》乾卦文言的九五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到了《系辭》,孔子將這一概念表述成“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求同氣,是黃帝內針應用時的重要目標,同氣相求,則有求必應。其包括2個方面的內容,即經絡同氣與三焦同氣,二者互參互求。
經絡同氣是指同名經同氣相求。人體的十二條正經據其名稱被分為6組,即手足太陽經、手足陽明經、手足少陽經、手足太陰經、手足厥陰經、手足少陰經,每組中的2條經絡互為同名經。例如病變部位在手太陽經所循行的經絡上,則可以在足太陽經上進行取穴,此即為經絡同氣,也稱為六經同氣。
所謂三焦,即上焦應天,中焦應人,下焦應地,在人體有相應的各屬區域劃分。上焦是指前為鳩尾穴、后為至陽穴以上的軀干部分,以及肢體的腕、踝部分;中焦是指前為鳩尾穴至神闕穴、后為至陽穴至命門穴之間的軀干部分,以及肢體的肘、膝部分;下焦是指前為神闕穴、后為命門穴以下的軀干部分,以及肢體的肩、胯部分。舉例而言,頭面部的疾病隸屬于上焦,則可在同屬于上焦的腕部或踝部附近取穴,此即為三焦同氣。
2.3 陰陽倒換求考慮到安全因素,黃帝內針的取穴嚴格限制在肘膝關節以下,因此當病變在下焦的肩、胯部位時,就要依據“陰陽倒換求”的原則,“下病上取”,即從上焦的腕踝部位來解決。
2.4 重視導引的作用“導引”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刻意》:“吹昀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黃帝內針所強調的導引是指通過醫者的語言指導,把患者的神識調動到患處,反復感受、覺察癥狀的變化,以實現針刺的效用最大化,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孔子《系辭》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讓患者感的過程就是一個陰陽相引的過程,通過感而實現機體陰陽的自和。
3 黃帝內針治療方案
3.1 選穴黃帝內針講求走出疾病,走出臟腑,治療的耳目在于尋“癥”。具體到頸源性失眠來講,穴位的選擇就要依據此病的主要臨床表現,即入睡困難、睡后易醒、頸項背部疼痛甚至伴頭暈頭痛等去考慮。可根據審穴要訣“六三二一”進行。
六:即經絡辨證,確定三陰三陽經。失眠之病機,總屬陰陽失和,陽不入陰。任脈與督脈為人身最大的一對陰陽,且有腧穴與十二經脈相通,故治療失眠可首選任、督二脈。頸項背部的疼痛,根據具體部位的不同又有差別。項背正中疼痛者,屬于督脈,偏于兩側者屬于太陽經;頸前正中疼痛者,屬于任脈,偏于兩側者,則屬于少陽經。 若伴有頭暈頭痛者,亦根據其循行部位行經絡辨證,如病變位于前額者,屬陽明經;位于兩側者,屬少陽經;位于后枕部者,屬太陽經;位于巔頂者,屬厥陰經。
三:即三焦辨證。頸項部隸屬于上焦,與腕、踝為三焦同氣,臨證應從腕、踝部取穴。而對于頸項部以上的頭部病變,則應從手、足取穴。
二:即陰陽。根據“左病右治,右病左治”的原則,癥在頸項左側者,取右腕或右踝同氣;癥在頸項右側者,取左腕或左踝同氣;癥在頸項兩側者,以嚴重一側作為主癥取同氣,若程度相似則按男左女右原則[21]。
一:即阿是穴。癥屬督脈者,取八脈交會穴后溪穴;屬任脈者,取八脈交會穴列缺穴。頸項疼痛屬太陽經者,取陽谷穴;屬少陽經者,取陽池穴;屬陽明經者,取陽溪穴。對于頭暈頭痛者,則根據陽明經、少陽經、太陽經、厥陰經之不同而選用合谷、中渚、后溪和勞宮。以拇指指腹適度按壓穴位及周邊區域,患者所訴酸麻脹痛之處,即下針之處。如無明顯痛點,則直接取上述經脈之原穴即可。
3.2 操作選穴后,囑患者采取適當的體位,腕、踝部穴位采用1寸針,在阿是穴附近斜刺40°進針,留針45 min。《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阿是穴”的選擇實際上就起到了定位的作用,位的不同便有了陰陽的不同,從而具備了變化的條件。因此與普通針刺講求補瀉的手法不同,黃帝內針無需提拉捻轉,不追求針感,不講究深度,所謂“透皮即有效”。對于畏懼疼痛的患者,還可以采用指壓的方法代替針刺,同樣可起到良好的療效。
3.3 導引接受傳統體針治療的患者,在留針過程中常常靜臥于床,凝神休息。與之顯著不同的是,黃帝內針特別強調針刺后的導引環節,在取穴準確的前提下,治療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導引是否做得好。對于頸源性失眠的患者來說,應囑其輕微活動身體,轉動頸部,時常去感受局部的變化,詢問其頸項僵緊或疼痛的癥狀是否減輕,注意調勻呼吸,感受氣息是否可下沉丹田。整個過程中,應盡量不看手機、電視等,減少因與人聊天而分散神識。
4 醫案舉例
王某,女,42 歲。主因“入睡困難1年加重1周”于2021年3月5日就診。現病史:1年前因工作壓力大出現入睡困難,就診于某精神專科醫院,給予口服佐匹克隆后睡眠好轉,每日服藥維持。近1周再次因家中瑣事出現入睡困難,口服3片佐匹克隆仍徹夜不眠,伴胸悶心煩、脅肋脹滿、口干口苦、便干,舌紅苔黃,脈弦。給予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處方:柴胡15 g,黃芩10 g,黨參10 g,清半夏15 g,生石膏30 g,茯苓30 g,桂枝10 g,大黃10 g,龍骨30 g,牡礪30 g,炙甘草6 g,生姜10 g,大棗10 g。顆粒劑7劑,水沖服,日1劑。并針刺列缺、后溪,針后不行針,于待診區座椅處留針45 min左右。3月13日二診:患者訴近1周睡眠較前好轉,口服1片佐匹克隆后晚上12點前可入睡。中藥繼服上方7劑,針刺列缺、后溪,由于仍有心煩、胸悶癥狀,故遵“六三二一”原則,六:心胸為厥陰經所主;三:心胸屬上焦,于腕踝附近取穴:二:男左女右,故在右側取穴;一:阿是穴:右手厥陰經內關附近找到阿是穴。于待診區座椅處留針45 min左右,其間囑患者做幾組深呼吸,起針時訴胸悶、心煩已較前減輕。3月21日三診:訴入睡較前進一步好轉,但夜間幾乎每小時覺醒1次,胸悶、心煩已不明顯。不愿意繼續口服中藥,要求僅針刺治療。問診過程中提及右側項背拘急疼痛多年,低頭則頸項僵緊明顯,有時伴頭暈,故于列缺、后溪基礎上加用左手太陽經陽谷穴。留針45 min,囑其輕微活動頸部,訴項背拘急較前明顯減輕。此后予隔日針刺1次,共6次,項背疼痛基本緩解,無頭暈,每晚11點前可入睡,覺醒次數明顯減少。
綜上所述,黃帝內針具有疏通氣血、調整陰陽之功效,陰陽合、疼痛解則神自安,在治療頸源性失眠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該針法操作安全,便捷實用,無需脫衣暴露胸腹等重要部位,不會傷及人體重要的臟器、血管、神經,對診療場所和設施要求相對較低,不受特殊針刺體位的限制,因此值得臨床推廣。